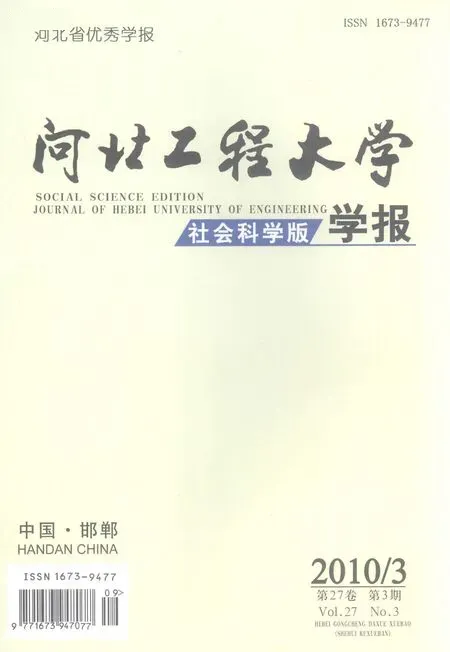魏州 (大名)兴衰初探
2010-04-07赵九洲
赵九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魏州 (大名)兴衰初探
赵九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魏州 (大名)的兴起有较大的偶然性,特殊的政治形势将其推上了历史前台。而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大运河的开通又为其迅速繁荣提供了保障。经过长期发展之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大名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魏州;大名府;兴衰 ;政治经济格局;大运河
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隋唐为魏州,五代宋元明清为大名府,在历史上曾长期扮演河北地区中心城市的角色,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历来关注大名的人却并不是特别多,本文拟对其兴衰做一初步探讨。
一、魏州兴起的历史背景
翻开历史地图来,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魏州、邺县和邯郸三者恰能构成一等腰三角形,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同反响的三角形区域,自先秦以迄宋辽,该地区一直是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所在,也一直对河北乃至全国有重大之影响。战国至两汉,邯郸始终是河北最重要之都会。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邯郸衰落而邺城崛起。到北周末年,邺城被焚毁为魏州的崛起扫平了道路,此后独领风骚达六七百年之久。
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三者所依托的经济腹地本就是重合的,且属于同一地貌单元,本就是一块完整的区域,故而在如此狭小三角区域里显然不可能同时出现数个大都市。历史上三者也确实没有同时雄居河北,而是依次坐庄,构成了历史上独特的区域城市竞争现象。邯郸的没落使得邺城得以崛起,而邺城的残破又为魏州的崛起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
很多城市的崛起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就魏州的兴起来看,偶然性的色彩也极浓重。在邺城衰落之前,魏州虽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若无特殊的机遇,魏州断难反超邺城而成为河北地区的领军城市。
某种程度上说,是隋文帝的猜忌心理使得魏州得以长足发展。隋文帝历来对地方多有防范,江东王气之说由来已久,故而灭陈后彻底荡平了建康城邑,犁地三尺以镇王气,史称“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1](P876)观览天下州县时,还会别出心裁地改动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地名。“十八年,文帝因览奏狀,见东燕县名,因曰:‘今天下一统,何东燕之有?’遂改为胙城,属滑州。”[2](P49)而尉迟迥起兵时所显示出来的邺城及其周边区域在河北地区的巨大号召力,更是让他担心不已,故而一俟战乱平息,立即着手整顿,先是彻底焚毁邺城,南迁相州于安阳,以防河北再次出现分裂割据势力。接着,他又进一步弱化相州,析置毛、魏二州。史载:“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邑居皆毁废之。分相州阳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3](P133)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隋文帝认为可以消除隐患了。至于日后魏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紧邻运河的便利交通条件而羽翼渐丰并雄居河北,完全取相州之位而代之,则是他始料之所未及的。
就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广袤的河北地区必然会形成一个政治与经济上的中心,而冀南的三角形区域显然还将在较长时间内是领跑者。但沉寂已久的邯郸暂时还无回天之力,而本来如日中天的邺城又被强行拉下马来。初生的魏州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抓住了难得的机会,稳稳坐上了头把交椅。
二、魏州的演变及其通向强盛之路
魏州始建于北周大象二年 (580年),治所在贵乡县 (今河北大名东北),隋大业初改为武阳郡,入唐复为魏州。史料记载:
贵乡,后魏分馆陶西界,置贵乡县于赵城。周建德七年,自赵城东南移三十里,以孔思集寺为县廨。大象二年,于县置魏州。武德八年,移县入罗城内。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移于罗城西百步。大历四年,又移于河南岸置……元城,隋县,治古殷城。贞观十七年,并入贵乡,圣历二年,又分贵乡、莘县置,治王莽城。开元十三年,移治州郭下。[4](P1494)
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京畿采访使理京师城内、都畿理东都城内、关内以京官遥领、河南理汴州、河东理蒲州、河北理魏州……[4](P1385)
则其治所先为贵乡而后为元城,且魏州同时为河北道的治所。
关于魏州的沿革分见于正史的地理志中,较为零散,此处不一一列举,清人顾祖禹已有有详细考证,摘录如下:
禹贡兖州之域,夏为观扈之国,春秋晋地,战国属魏。秦属东郡,汉属魏郡。三国魏分置阳平郡,晋因之。前燕分置贵乡郡,寻省。宋文帝置阳平郡,后魏因之。后周末置魏州,隋初因之,大业初改为武阳郡。唐武德四年复为魏州,龙朔初改为冀州,咸亨中复故。天宝初曰魏郡,乾元初复曰魏州。五代唐同光初升为东京兴唐府,三年改东京曰邺都。晋曰广晋府,汉曰大名府。周显德初复罢邺都为天雄军,而府如故。宋因之,庆历二年建为北京。金仍为大名府路,元曰大名路,明改大名府。[5](P695)
可见魏州的发展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状,宋以前为上升趋势,至宋达到最高点,宋后颓势已成,开始走向没落。正如前面所说,邺城的衰落使得魏州开始踏上强盛之路。但其强盛亦非一蹴而就,经历几十年的时间。限于篇幅,势难一一展开,主要看看对其崛起影响至为重大的几点因素。
首先,交通是城市的生命线,没有发达的交通,巨大的能量需求无从保障,是不可能有繁荣的大都市的。白沟的开掘使邺城迅速繁荣起来,而大运河的南北贯通也使魏州迅速走红。大业年间,大运河北段永济渠得以修筑,“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P70)史书中的记载虽只寥寥数语,亦未提及魏州,但永济渠对于魏州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我们来看几条关于户口的史料:
武阳郡后周置魏州。统县十四,户二十一万三千三十五。[1](P844)
清河郡后周置贝州。统县十四,户三十万六千五百四十四。[1](P846)
魏郡后魏置相州,东魏改曰司州牧。后周又改曰相州,置六府。宣政初府移洛,以置总管府,未几,府废。统县十一,户十二万二百二十七。[1](P847)
京兆郡开皇三年,置雍州。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东面通化、春明、延兴三门,南面启夏、明德、安化三门,西面延平、金光、开远三门,北面光化一门。里一百六,市二。大业三年,改州为郡,故名焉。置尹。统县二十二,户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1](P808)
则立州仅二十余年后的大业年间,魏州 (时为武阳郡)户数即达到二十余万,远超相州之上,仅次于京兆郡和清河郡,可见此时魏州之繁荣已足以傲视河北了,故而李密降元宝藏而势力大振,刘黑闼取魏州而唐之山东即乱。但真正使魏州达到巅峰状态的却是另外一次对运河的小小改造。工程的指挥者是卢晖,时间在开元年间,意图是使魏州得以沟通江淮。史载:
开元二十八年,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6](P1011)
史书上的记载虽只有寥寥数语,但这一改造对魏州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说要超过永济渠的开凿也在情理之中了。魏州出现“原野垦,府库实,氓庶安”,“川原材麓之富,舟车士马之殷”[7](卷四百四十,封演《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P4492)的繁荣景象,卢晖可谓功不可没。再摘录一段当今学者的描述来看开元年间魏州之变化:
贞观十二年 (639),唐太宗曾下诏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设置常平仓储粮,而魏州不在其内,显然此时魏州尚不具备设仓储粮的条件。(《旧唐书·太宗纪下》)至开元年间,情况大变,大批粮食供应关中,三年共运粮 700万石,主要来自晋、绛、魏、濮、邢、贝、济、博各州,开元时魏州与同在永济渠旁的贝、博二州都成了重要的粮食基地了。[8](P447)
可见,开元年间是魏州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新渠的开凿则是魏州腾飞的关键举措。魏州之所以能“河朔三州,魏为大”[6](P4492),之所以会“河北之患二百余年,而腹心之忧常在魏博”[5](P696),都与大运河息息相关。魏州,是运河催生的大都市。
顾祖禹称:“(大名)府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势强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5](P696)又称:“自秦以降,黎阳、白马之险恒甲于天下。”[5](P696)
正德《大名府志·疆域志·形势》中的相关记载如下:
大名府近则地回沙麓,河抱卫漳;远则东连齐鲁,西接太行。故前辈诧其气势联络,隐若重关。真河朔之重镇,北门之锁钥也。
元城县卫河襟其南,漳水遶其北,合流于东。阻三面而守之,盖亦有天堑之险焉。
大名县逯堤东抱白潭,南驰况,枕惬山而带卫水,形势之盛,几可与大国争雄矣。[9](P12A)
同治《元城县志》记载如下:
元城界在中原,独殿河朔,太行之所融结,黄河之所迂回,天地雄浑混朴茂之气独盛于此。故每登大丕之巅,纵目万里,知元城之地灵不在于佳丽山水也。[10](P147)
一要以公平之心对待每个学生。既要创造条件让成绩优异的学生脱颖而出,更要让全体学生均衡发展,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以公正之心安排班级座位。
特别值得点出的是,后晋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一马平川的河北地区失去屏障而无险可守,国防重心大幅度南移,魏州之地位遂愈发重要。
再次,特殊的地缘优势。繁盛的魏州进可镇遏整个河北地区,退可屏蔽政治腹里的中原地区。自隋迄宋,中原的政治经济意义对全国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而河北则为中原之外院,魏州安则中原安,魏州乱则中原危。唐高宗龙朔年间曾改魏州为冀州大都督府,掌控河北地区,何以改魏州为冀州虽原因不明 (疑高宗以魏为冀当与《禹贡》冀州之说颇有关系),且至咸亨年间又罢废大都督府,魏州、冀州恢复旧名。但魏州军政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实为日后设立魏博镇之先声。
相关记载如下:
(龙朔二年公元 663年)十二月辛丑,改魏州为大都督府,改冀州为魏州。[4](P84)
(咸亨三年公元 672年)九月乙卯。冀州大都督府复为魏州,魏州复为冀州。[4](P97)
此后,魏州军事地位日渐上升,入五代而为邺都,入宋而为北京。这里也不再对此做过多展开,还是引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窦建德及刘黑闼皆有问鼎中原之志,辄争魏州以临河南。唐得魏州,亦为重镇。迨安史倡乱,河北之患二百余年,而腹心之忧常在魏博。朱温据有汴州,依魏州为肩背,魏州入晋而梁祚遂倾矣。自庄宗以魏州称帝,其后邺都军乱,李嗣源因之而承大统。郭威复自邺都南向,竟移汉祚。邺都于河南,遂成偏重之势。宋亦建陪京于此以锁钥北门,契丹不敢遽窥也。[5](P696)
关于魏州的崛起,影响最大的大致就是这三点。
三、魏州 (大名)的进一步发展和没落
五代至北宋,魏州在很长时间内是陪都。不过,自后唐起,魏州名号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亦并非完全消失,如后唐天成四年“六月……戊申……诏邺都仍旧为魏府”,[11](P551)即恢复了魏州的名号。魏州在后唐又称兴唐府,后晋称广晋府,入汉而最后确定大名府之称。《史记·魏世家》中有如下记载: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12](P1853)
唐、晋、汉三代均建邺都于此。实际上魏州与古邺城并非一地,但邺为战国魏地,至曹魏复建邺城为都。在世人观念中,魏与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魏州以魏名州,故而五代君臣便以邺名都。至后周显德元年 (954年),郭威借王殷入朝之际罢邺都,实为消除地方叛乱势力之举,而大名 (即原魏州)之重要地位并未削弱,如周世宗灭佛时所下敕文称:“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处置戒坛,侯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大名府等三处,只委本判官录事参军引试。”[11](P1530)大名府紧随二京之后,且一句之内两次提及大名,则其地位可见。
宋初,宋辽两国对峙,大名府地位更显重要,至庆历年间为防范北方强敌而被建为北京。史称:“是月,契丹集兵幽州,声言来侵,河北、京东皆为边备。”[13](P214)该月指庆历二年 (1042年)五月,即建大名为北京之月。契丹军事压力显然是升大名为北京的一大推动力。
《宋史·地理志一》又载:“北京。庆历二年,建大名府为北京。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驻跸行宫。城南三门:中曰顺豫,东曰省风,西曰展义。东一门,曰东安。西一门,曰西安。顺豫门内东西各一门,曰左、右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祥,西曰丽泽。殿东南时巡殿门,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时巡殿前东西门二:东曰景清,西曰景和。京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门一十七。”[13](P2105)这是大名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陪都,且城市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展,这是大名发展的巅峰状态。
可惜好景不长,成为北京后仅八十余年,女真人的铁蹄即踏入了中原,一代名都未能屏蔽中原,金军直逼东京城下。宋钦宗定城下之盟而将黄河以东以北全部割让给金,[13](P435)则不待绍兴和议成而北京已沦陷于金人。此后宋、金在大河南北拉锯,经历战火的河北一片残破,大名也盛况难再,后刘豫在大名称帝,史称“(建炎四年九月)戊申,命秦凤将关师古领兵赴行在。刘豫僭位于北京。”[13](P482)《宋史》本纪行文至此为最后一次提及北京,此后当是不废而废。
金代大名府虽走上了抛物线的后半段而开始衰落,但似乎亦还足称河北一大都会,虽无北京之尊荣,却得有大名府路之建制。史称:
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府一,领剌郡三,县二十,镇二十二。贞祐二年十月置行尚书省。[14](P627)
到金末移都汴梁而大名亦堪称北门,惜乎数年而金亡。
经过蒙古人的洗劫后,入元虽仍有大名府路,但户口大减,颓势已成。史书关于金、元两代大名户口的记载如下:
《金史 》卷 25《地理志下 》:“大名府 ,上 ,天雄军 ,旧为散府,先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罢,以其所辖民户分隶旁近总管府。正隆二年升为总管府,附近十二猛安皆隶焉,兼漕河事。产皱、縠、绢、梨肉、樱桃煎、木耳、硝。户三十万八千五百一十一。县十、镇十三:旧有柳林、侯固二镇。”[14](P627)
《元史·地理志一》:“大名路。中唐魏州。五代南汉改大名府。金改安武军。元因旧名,为大名府路总管府。户六万八千六百三十九,口一十六万三百六十九。领司一、县五、州三。州领六县。”[15](P1361)
则元代户口较之于金代,几乎损耗了五分之四!故而方志中有“金元以来不可复问”之语。[10](P210)
入明,大名亦仅为普通一府,未见其重要,户口视元亦仅略有增加而已,史载:
大名府元大名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为府。十月属河南分省。二年三月来属。领州一,县十。东北距京师千一百六十里。弘治四年编户六万六千二百七,口五十七万四千九百七十二。万历六年,户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口六十九万二千五十八。[16](P898)
城市规模之缩减更为明显,据上文所引《宋史·地理志》中的史料看,宋代北京城周达四十八里二百六步,而据方志记载有:“县城原在城东十里,唐魏博节度乐彦祯所筑,周八十里,号河北雄镇。”[10](P210)或有夸大之词,但城池极为壮丽自无疑问。但明代之府城却极小,“明洪武三十四年,水汜为患,都指挥吴成始徙筑今城,视原基什九之一,高三丈有奇。”[10](P210)清代较明代无大变化。
步入民国,大名复丢掉了府的地位而变成普通一县。期间亦有戏剧性的一幕,即民国三年大名兼并魏、元城二县而成为河北省首屈一指的大县,但也仅为县级建制而已。[17](P92-P113)再后来,随着京广铁路的开通,古城邯郸得以复兴,衰弱已极的大名遂复成为其属下一县。
四、对大名 (魏州)没落原因的思考
大名 (魏州)的没落虽不像邯郸的没落那样在汉末一蹴而就(邯郸在汉魏之际的衰落很奇特,往日的天下五都之一似乎是在无声无息中就突然衰落了,个中原由颇为耐人寻味,留待他日详考),也不像邺城那样悲壮惨烈到被直接从地图上抹去,但其从大都市到小县城的发展历程还是让人感慨良多。下面重点谈谈我对魏州衰落原因的几点看法。
首先,大名 (魏州,为行文方便,以下只称大名)的没落与全国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有着莫大的牵连。金元以后的大格局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剥离,政治中心大幅北移到幽燕,而经济中心则远徙江南,中原地区的战略意义大幅度降低,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原北大门的大名地区重要性大为降低,不再具有屏蔽政治腹里的作用,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因天子守边使得国防前线也大幅北移,所谓的“北门锁钥”也失去了作用。而历经金元战乱后,整个北方经济残破,大名的繁荣也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等级系统的形成有较深厚的历史根源,由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单一小农经济基础之中,政治军事因素对城市等级的制约力非常强”[18](P659),经过一番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之后的大名,失去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撑,又失去了军事上的坚强后盾,更失去了经济上的深厚基础,怎能不残破,怎能不衰落!
其次,大运河的改道。元世祖灭南宋后即着手改造大运河,裁迂取直,运河全线东移,经济州而过临清,不复经过大名。大名虽得以通过卫河与大运河连接,但毕竟失去了直通江淮的通道,这在南方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的情况下对大名的经济发展是至为不利的。入明清,运河漕运在全国的重要性更是非同小可,运河沿岸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如临清、济宁等。相形之下,大名的境况却让人感伤不已。某种程度上说,运河改道对大名的衰落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可谓一剑封喉。对于大名的兴衰来说,或许这样说更形象一些:成也大运河,败也大运河。
其三,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北方气候在金元以后更显干燥,水环境急剧恶化。原有的湖泊沼泽相继消失,河流的径流量普遍减少。宋太祖围攻晋阳时还曾决河灌城,史载:
(开宝二年三月)乙巳,临城南,谓汾水可以灌其城,命筑长堤壅之,决晋祠水注之。遂砦城四面,继勋军于南,赞军于西,彬军于北,进军于东,乃北引汾水灌城。辛亥,遣海州刺史孙方进率兵围汾州。”[13](P28-29)
宋以后类似情况未曾听闻。入元以后,原先直通江淮的御河即已与黄河无法沟通了,河运路线到达中滦 (今封丘)旱站后即需走旱路 180里方能入御河。
明清时代,漳河、卫河水量的季节性更加显著,雨季洪灾频繁。就《同治元城县志·舆地志·年纪》中的记载做一统计可发现,从明初建文三年 (1401年)到清末同治十一年 (1872年)的 471年间,元城县 (即大名府治所所在)遭受较大水灾多达 54次,平均不到 9年就会发生一次。
而直接威胁城池的特大洪水也频繁发生。如建文三年,大名旧城被水淹没而吴成筑新城。但此后大名仍未摆脱洪水的威胁,“嘉靖以来,漳流并卫,颇有啮城之势。”[10](P211)此外万历二十二年、康熙十二年又曾发生洪水浸城事件,城池勉强得以保存。至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魏县、大名一带发生洪灾,“漳河决溢,大水灌入 (魏县)城内,墙垣倒坍,庐舍倾圮,而城遂墟。城既被水冲淹,方议迁治,乃未及一月而大名县城复为御河所圮。二县相继淹没,势难同复旧观。”[17](P103)于是有废魏县而入大名、元城及民国三县合并之举。乾隆四十年又发生一次大洪水,“水薄府城”,[10](详见卷一)形势颇为危急。频繁的洪涝灾害发生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利于大都市存在的。
而植被的破坏也日趋为严重,宋代河北地区的水土流失状况已经极为普遍,沈括《梦溪笔谈》卷 24《杂志》载:“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类,悉皆浊流。”[19](P173-P174)又载:“今齐、鲁间松林尽矣 ,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19](P171)则可见魏州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之一斑。
宋以后,情况更显恶化,由于关于魏州一地的资料相对缺乏,此处也就不作过多展开了。
总之,魏州在自隋至宋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的兴衰变化与全国政治、经济的演变密不可分,亦与生态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天地生三因素的互动,把魏州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又最终使魏州复归于默默无闻。研究魏州的兴衰,对于我们把握中古以后我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将不无裨益。
[1]魏征.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令狐德棻.周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1.
[4]刘昫.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董浩.全唐文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9]唐锦,陈滞.正德大名府志 [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10]吴大镛等.同治元城县志 [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0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11]薛居正.旧五代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2]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脱脱.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脱脱.金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宋濂.元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张廷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程廷恒、洪家禄.民国大名县志 [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16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8]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 [A].王天有.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 [C].北京:北京大学,1998:659-671.
[19]沈括.梦溪笔谈 [M].长沙:岳麓书社,2002.
[20]李亚.大名府故城之陪都历史探析——大名府故城考略之一 [J].文物春秋,2005(3)
[责任编辑:王云江]
A prel im inary study in the rise and fall ofWeizhou(Dam ing)
ZHAO Jiu-zhou
(Center of China Evironment History Studies,Nankai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re was a great chance in the rise ofWeizhou who was help by the special political situation.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advantage,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Grand Canal,all the above three had provided a guarantee for its prosperity rapidly.After long-term development,with the change of national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situation,Daming inevitably fell into decline.
Weizhou;Daming;rise and fall;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the grand canal
K207
A
1673-9477(2010)03-0081-04
2010-03-16
赵九洲 (1980-),男,河北武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生态环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