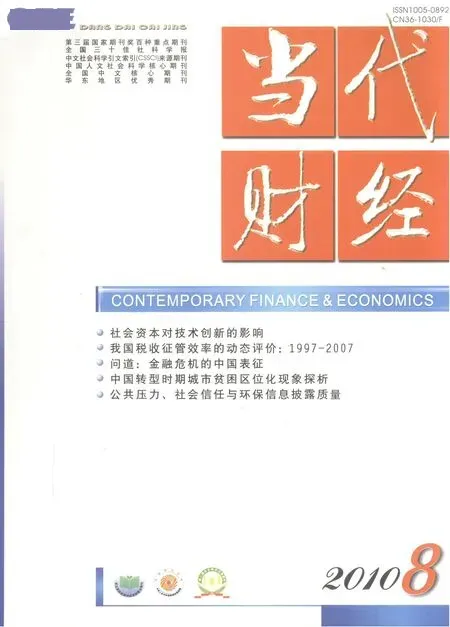问道:金融危机的中国表征
2010-04-06李华民
李华民
(广东金融学院 区域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521)
发源于美国“次贷”问题的全球金融风暴基本上偃旗息鼓了,其衅发萧墙,祸延四海,当自有别论(蔡卫平,2009)。[1]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传染与防疫之对决中,依照有关经济危机理论的指标体系,中国在保稳定方面绩效显著。然而,本轮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表征,却有悖于教科书的经典逻辑,值得深思。
一、金融危机应该有一个中国指标体系
无论是1997年爆发于泰国然后遍染亚洲各国乃至俄罗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7年因美国“次贷”问题而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国内政、学、业各界对于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境况的判断,几乎众口一词,即中国因为应对措施及时得以独善其身。①当然,犹有学者所言,美国金融危机所暴露的问题,值得借鉴(李扬,2009)。[2]同样,美国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中国问题,更不容忽视!依据经典教科书之对于金融(经济)危机的经典描述,金融危机的表征如下:(1)银行机构资不抵债、倒闭、兼并或者被拯救;(2) 股市崩溃;(3) 本币贬值;(4)GDP滑落以及失业率倍升。由此,按照教科书逻辑来推演,中国不曾陷入金融(经济)危机。但问题是,教科书用以描述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的危机逻辑及其“精致工具”,是否适合用来丈量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经济现象?进而言之,金融危机是否存在着中国特色的指标体系?
(一)经济衰退以及失业率
从经济增长切入分析。2007年中国GDP的修正数据为13%,2008年的修正数据为9.6%,滑落3.4个百分点。这3.4个百分点意味着出口导向型的民营企业大量歇业,意味着广东省“双转移”战略被要求缓期执行,意味着全国5000万农民工返乡及由此估算的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计农民工失业)超过10%。美国“次贷”危机高峰时期,甚至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也不过如此。
在被称为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2009年,尽管全国经济宏观层面“被”整体企稳,季度曲线也表现为“V”型反转,但中国年度GDP(未调整数据) 仅为8.7%;②相比2008年(调整数据)的9.6%,继续滑落0.9个百分点。需要高度关注的是,这个“继续滑落”是中央政府为“保八”而在2008-2009年3.5万亿③财政投资之后的继续滑落,该财政投资规模对于2009年中国GDP的贡献,粗略匡算约占2.0个百分点。④这还没有计入中央财政投资计划所引致的2009年9.7万亿天量信贷规模以及18万亿地方财政投资所拉动的GDP的贡献额度。这个“继续滑落”,意味着2008年返乡的5000万农民工,依然在等待就业机会,直至2010年第一季度。⑤
如此分析,从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拯救力度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中国是否曾经陷入金融(经济)危机,需要在教科书经典理论中嵌入中国调控能力指标才能作出准确判断。
(二)银行业资产不良率
经典理论所强调的作为金融危机表征的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兼并或者被政府拯救等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大面积出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各大银行机构都对外宣称,因为在美国“次贷”中涉水不深,因此损失不重。尽管各银行机构损失拨备有所增加,但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银行机构都是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金融机构。
尽管如此,高资产不良率和高利润率并存一直是中国的银行机构的诟病(唐旭,2009)。[4]对于中国的银行机构而言,其“国家(政府)的银行”性质以及隐性的储蓄保险制度,决定了银行机构不存在破产和倒闭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金融危机的中国银行机构状况表征,不在于其破产或者倒闭,也不在于其即期利润率的高低,而应该在于整个银行业的资产不良率以及由此“倒逼”的国家拯救问题。与中央财政4万亿投资计划相配套的银行机构信贷资产,大都是长期贷款,其资产质量状况直到还贷期才将显现。根据2009年9.6万亿的信贷资产投向来看,银行机构的资产质量预期不容乐观。1997年亚洲危机之后,尽管中国的银行机构利润不负,但其资产不良率居高不下,面临技术指标上的破产境地,最终“倒逼”中央政府分别在1998年以2700亿财政资金注入充实资本金,以及2003年以来为国有银行机构改制(如吸收外国战略投资者)而进行了两次450亿美元的资本金注入。国家信誉基础上的中国居民刚性储蓄,无疑成为国有银行机构在居高不下的资产不良率基础上能够岿然屹立的资金支撑。2008-2009年的3.5万亿财政投资经过乘数倍加后,成为银行机构资产负债表广开负债的来源。更有甚者,2008年和2009年,在微观层面并没有明显向好的境况下,银行机构能够成为全球最具盈利能力的金融机构,只能说明中国的银行机构深度攫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而2009年的经济滑落,则可解释为宽松的央行货币政策的背后,存在着银行机构对于民营经济的信贷紧缩。
(三)本币升值与外汇储备损失
无论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还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问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中国货币都没有贬值。前者是中国政府为帮助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各国走出危机困境,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发展中国家的弱经济实力,承担起大(强)国责任的“政治”效果;而后者本身就是美元危机。美元贬值,衬托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何况,在本轮金融风暴中,美国以邻为壑,通过美元贬值把危机后果转嫁给中国。一方面,把人民币汇率问题置于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企图通过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来减轻其国内就业压力。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以来,包括本轮金融风暴在内的四次美元危机(刘源,2009),[5]每一次都是美元的贬值,对应着的是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的对价升值。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本币升值凸现出巨大的破坏力。日本“失落的十年”可以追溯至导致日元升值的“广岛协议”,典型地凸显了金融危机的本币升值表征。中国目前是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外汇储备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为2.27万亿美元,超过了中国5.2万亿美元GDP的45%,其中美元资产(储备)占比接近80%。美元每跌1毛,中国人均资产减少1200元人民币。按照美元兑人民币比价自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贬值了18%匡算,⑥中国因为本币升值的直接损失超过4000亿,这还不统计因为本币升值导致的出口减少所计量的经济损失。⑦
如此逻辑如果成立,当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发行国爆发并辐射国际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本币升值幅度,毫无疑问应该列入国际货币储备国家金融陷入危机的衡量指标。另外,美国美元这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所无法根治的“特里芬”难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和大国崛起,共同决定了中国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大幅度升值是迟早的必然。既然如此,当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出现金融危机时,外汇储备损失也应该列入中国金融陷入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
(四)资本市场波动问题
在能够体现金融运行状态的中国各种经济现象中,股票价格以及体现股票市场价格总体态势的股指,是中国最具市场力量决定价格的体制所在。因此,用股指波动幅度来衡量金融运行状态是否处于危机状态,最具有市场说服力。一方面,在2007年非理性冲高之后需要回落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受美国“次贷”危机的传染,中国股指从2007年10月最高峰时的6100点到2008年10月谷底时的1600点的轮回中,被蒸发掉了3/4。中国媒体对于外国股市波动幅度的描述用语是,当其股指日跌幅超过3%,就界定为“黑色”交易日;而连续跌幅超过10%,就惊呼“崩盘”了。那么,按照这一衡量标准,中国股市早已超出了短线“崩盘”的界点,但国内学界以及媒体从未使用过如此词汇来描述中国股指的波动状态,即便是2008年初到11月的股指连续滑落,也是如此。如此比较,作为最具有市场力量决定价格体制特征的中国股指,其波动幅度超过多大范围,才表征中国金融陷入危机?
二、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表征疑惑
(一)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忧虑
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经济宏观层面因为3.5万亿元财政资金支撑而趋稳,季度曲线“V”型反转,但经济微观层面并没有向好的明显表征;全年GDP数据为8.7%,相比2008年的9.6%,继续滑落。然而,中国经济中有两个超速增长指标显得特别刺眼:(1)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超收2247亿元,财政/GDP的比例超幅度提高;(2)“央企”利润猛长,达14.6%,高出同期GDP达5.9个百分点。这在金融危机后经济亟待复苏之际,当属异常现象。财政收入和“央企”利润从哪里来?⑧
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听到民营企业主的抱怨是,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初,民营企业处于萧条阶段,生意惨淡,然而开业遇到的第一件事却是税务部门“光荣纳税大动员”,被“自觉”补交2006-2009年漏欠税款。2009年11月份,收税任务提前完成,却不成想“漏税补收动员”措施恶化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滞缓了市场经济的真正复苏,政府信用遭受破坏,国民收入分配的经济刺激功能被严重扭曲。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市场内需只能依赖财政投资拉动。2008-2009年的财政资金3.5万亿元投放出去,再通过68477亿元的财政收入收回来,然后再用下一拨的财政资金投下去,形成一种循环依赖,也成为一种扭曲的财政政策。但这种扭曲的财政政策势必有退出之日;而一旦财政政策退出,则意味着如此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链条断裂,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为继。
(二)民营企业流动资金富余与内需缺口
本轮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各国经济的微观运行层面。截至2008年10月,仅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7万家港资企业,有统计显示,超过二成五拟注销歇业(佚名,2008),[7]其中不乏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是最具市场经济特征的。然而,在广东省中山市的调研结果却给笔者带来了不尽的疑惑:众多企业歇业,但不差钱。作为课题组调研对象的广东省中山市民营企业中,超过80%有富余资金躺在银行账上,而不是去追求利润;诸多民营企业不贷款了,以至于整个中山市2008年底的贷存率仅为46.03%,而银行机构为了完成信贷规模任务,不得不去说服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贷款(有些民营企业主在2008年几次“被”贷款);民间融资利率甚至接近银行机构官方利率水平。这引发了笔者思考:微观经济主体出现了什么变异,以至于金融危机在广东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面前变得如此温和?面对传染性金融危机对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如此破坏方式,学界必须慎重考虑,该如何拯救广东式的危机?⑨内需拉动为什么不能覆盖具有富余资金的民营企业呢?
(三)持续的“中国之谜”
2008年底到2009年底,中央财政投入3.5万亿元,带动银行机构信贷规模在2009年天量投放9.6万亿元,M2为26%,贷款/GDP为1.19,即便是第三季度紧急刹车,M2也比2008年增加了4.7万亿元;2010年3月,银行机构单月信贷规模达1.89万亿元,M2为25.51%。自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30年间,达到该值的年份仅有3个。2009年中国GDP为8.7%,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和物价指数(CPI)双双负值。⑩按照权威文献(张思成,2008;吴敬琏,2009) 来推算,[8-9]2009年货币投放应该在2010年体现在拔高的CPI上。但事实是,中国经济成为一个四棱镜:一个面是“金融危机”;一个面是流动性过剩;一个面是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面是处于零度以下的CPI。M2极度超过了GDP和CPI之和,货币投放去向不明,“中国之谜”持续成为不解之“谜”,而金融危机使得“谜底”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需要理论界提出非教科书式的理论解释。
三、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的豁口判断
(一)宏观调控下的中国“次贷”问题
中国房价下跌幅度有多深,下跌能够持续多久?2009年初以来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终于在2010年4月15日国务院调控重拳出击和国土资源部土地供给宽松政策的共同打击下给刺破了;尽管有某房地产开发商表示“不打算降价销售”,但也有城市楼盘销售价格在调控政策出台的第二天就优惠10%,而购房者态度却由积极转向观望。按照2009年购房者首付20%的政策,如果商品房价格跌幅达20%,就意味着有购房者开始成为资产“负翁”。如果房价继续下跌,“断供”并把按揭房丢给银行机构就成为“负翁”们的理性选择。这意味着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式的“次贷”开始成为问题,意味着房贷银行机构资产不良率的提升,意味着住房金融危机的发酵,意味着中国银行机构即便没有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被击跨,也要被自己的“次贷”问题所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危机的引爆点之一。按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进展以及房地产价格趋势,大概在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银行机构有望与“次贷”问题触手。换个角度思考,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推演中国政府的住房市场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审慎,以避免银行机构遭受危机损失,从而导致国家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安全的中国式金融危机的过早爆发。
房地产价格的滑落,除了银行机构资产不良率提高效应之外,还存在其它无法准确预测的后果。第一,股指跌宕效应。直接引致股票市场的房地产板块指数的跌落,以及其波动幅度的加大。实际上,2010年初特别是4月份以来的交易日里,中国股指房地产板块已经跌去了40%,沪市综指从3400点向2500点下方的滑落以及波动幅度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第二,人民币币值变动效应。引致原本追索人民币升值预期收益而潜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国资本寻机从房地产市场撤离,有可能会回旋于中国资本市场,更可能是撤离中国资本市场。撤离中国资本市场的效应分为两种:(1)如果是较为缓慢地撤离中国,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2)如果是迅速撤离中国,其结果则可能引发人民币的恐慌性贬值。第三,经济增长衰退效应。后金融危机的2009年,中国经济宏观面能够趋稳,其中房地产业的贡献不菲,粗略估算为23%,即约1.9个百分点(中国建设银行课题组,2009)。[10]房地产价格崩溃的经济增长效应,关键在于市场预期:(1)在下跌幅度直至预期之前,购房者会持币观望,商品房销量持续下滑,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下降;(2)一旦商品房价格下跌幅度接近预期,商品房销量反弹,其经济增长效应会“改”负为正。就此逻辑,房地产价格下跌幅度一步到位,忽略其它效应而言,可以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二)中国内债式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判断
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关注的地步了(曾康霖,2010)。[11]如果债务管理不慎,势必成为中国内债式金融危机的豁口。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2010)统计,2008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仅为1.7万亿人民币,而到了2009年底,在中央政府的反周期政策鼓励下,源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及债务压力,地方政府依托的3800家投融资平台债务急速膨胀,负债总额增速高达250%以上,其负债总额升值为5.26万亿元,占其9万亿元资产的60%,相当于全国GDP的15.7%,全国财政收入的76.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61.35%。[12]另据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和2011年,地方投融资平台将增加后续贷款约2~3万亿元,2011年底总负债将达到10万亿元。
地方政府依托投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大大超过了本级财政收入所能够承受的债务风险极限。这就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按照目前地方政府6万亿元债务总额以及现行的5年以上期限的贷款利率5.94%计算,那么每年还款额为5206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6.3%。如果其中的一半发生违约,则依照2009年银行业的盈利总额和贷款余额,银行机构资产不良率将提高7个百分点,此时中国内债式的金融脆弱性势必凸现出来。
(三)中国金融监管的邦联格局雏形:制度脆弱性分析
2003年启动的农村信用社机构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得其所。各级地方政府的金融工作(服务)办公室应运而生,其职能之一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区域金融资源乃至其他区域的金融资源,为地方经济服务;其职能之二是促进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其职能之三是竞争对于区域金融的监管权。其中第三个职能的结果必将是,中国金融业监管制度将形成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协调下的地方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监管区域金融的邦联式监管制度。但是,一方面,地方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并不具备金融监管的能力,更不具备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作为监管部门,更加容易被俘获。基于后者,其职能实施的短期表现是,在解决金融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下,区域金融资源在短时间被过度开采,导致了金融资源的枯竭。2009年,全国有15个省(市)地方政府要把金融业发展定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而更多的地方政府要把金融业发展成为服务业的龙头,由此形成了遍布全国26个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地理分布格局,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出现了非常规的结构转换和突击性升级。其逻辑后果必将是,中国的区域金融首先暴露出地方金融机构的资产不良化,然后需要政府填补资本金。其结果是,为解决金融危机留下的债务,必然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成为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导致地方金融机构首先爆发危机,然后传染给区域性股份制银行机构,并继续扩散。如果不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即便是中国式“次贷”问题能够捱过,脆弱的邦联式金融监管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所引致的金融危机也会在中国的银行机构爆发。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能简单地运用描述市场经济运行状态的教科书上的精致工具,来判断中国强势宏观调控能力下的金融经济运行态势,金融危机应该具有中国自己的指标体系。中国的股票市场,因为其价格形成中的市场竞争特性,决定了其最具市场经济品格,因此其指数波动幅度可成为判断中国金融运行态势是否陷入金融危机的典型指标。他国金融危机扩散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营企业的“辟谷”应对策略,再次提醒政、学、业各界深入思考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重拳,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穷人”住房梦的破灭,引发中国式的“次贷”问题,而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则会导致中国GDP增长的衰退,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外来传染所采取的反周期式的宏观调控猛药,又会成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引子;至于赋予地方政府金融工作部门以金融机构监管职责,笔者认为,尚需审慎之。
注 释:
① 当然,中国没有作壁上观。无论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向被染国家通过实地购买以扩大进口方式伸出援手,皆以发展中国家之能力,超负荷承担起了大国责任。
② 诸如粤、浙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微观层面并未明显好转。
③ 2008年11月设定2008-2010年财政投资计划4万亿元,其中2008-2009年分配额度近3.5万亿元。
④ 我们无法得出准确数据,因此使用左小蕾(2008)的匡算结果。[3]
⑤ 对于2010年初东莞等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我们的解释是,不是企业用工量比2007年前增加了,而是返乡农民工惯性滞留的结果。另外,“农民工荒”了,大学生毕业就待业了,以至于“刘易斯拐点”问题在中国变得不清晰了。
⑥有学者的计算结果(李世凯、杨公齐,2009)[6]与本文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可能是计算口径不同所导致的。
⑦外汇储备增加表现出其巨大的居民生活水平的吸瘪能力,中国经济只见GDP增加不见居民生活水平对应提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⑧当然,“央企”利润可能构成中央财政收入一部分。
⑨2008年东莞市的经济增长率是-2.3%。就东莞经济增长而言,定性陷入了“经济危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⑩直到2009年第四季度,PPI微破零点,2010年第一季度才开始攀升。尽管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动效应已经达到了“关注”级别,但统计显示,第一季度CPI仅为2.7。
:
[1]蔡卫平.直击华尔街风暴新闻传播特色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4):68-71.
[2]李 扬.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所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J].当代财经,20098,(6):15-16.
[3]左小蕾.4万亿投资可保GDP年增长10%[N].中国证券报,2008-11-12.
[4]唐 旭.论银行业的股东掠夺与经理人掠夺[A].唐 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三辑)[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1-19.
[5]刘 源.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配额货币体系的创建[J].科学决策,2009,(9):73-85.
[6]李石凯,杨公齐.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5):5-13.
[7]佚 名.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困境调查[N].北京晨报,2008-10-27.
[8]张成思.中国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启示[J].经济研究,2008,(2):33-43.
[9]吴敬琏.近期不可能马上出现通货膨胀[R].“2009浦江创新论坛”发言稿,2009-10-24.
[10]中国建设银行课题组.经济增长“保八”无悬念,股市上行债市趋弱[N].中国证券报,2009-02-02.
[11]曾康霖.地方政府过度负债蕴藏中国金融业风险[R].“完善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理论研讨会发言稿,2010-04-25.
[12]张茉楠.地方债务膨胀:中国经济安全堤坝最脆弱点[N].上海证券报,2010-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