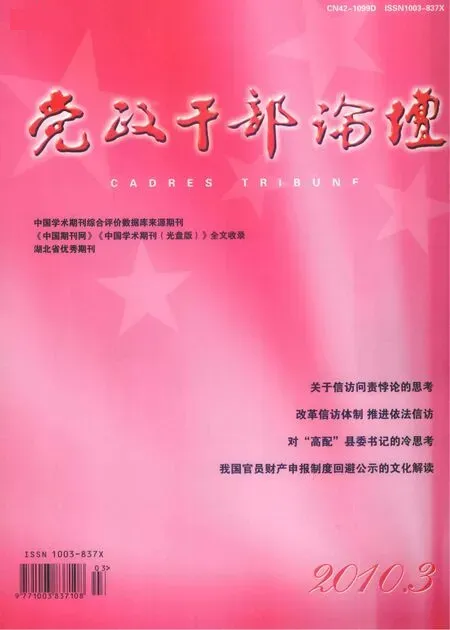关于信访问责悖论的思考
2010-04-05徐敏宁陈安国
○徐敏宁陈安国
关于信访问责悖论的思考
○徐敏宁陈安国
信访问责制施行以来虽已取得很大预期成效,然而,部分无理信访者却有恃无恐,无理信访急剧攀升,越级访、缠访等现象也并未削减;基层领导压力过大,甚或谈访色变,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人财物进行围追堵截,“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的心态悄然而生。本文首先指出信访问责悖论的客观存在性,然后从职能定位、权责关系、程序设计三个维度来剖析其成因,并提出定位大信访职能、构建椭圆型信访机构的对策建议。
一、信访问责悖论的客观存在性
信访问责悖论是指现行的信访问责制在客观的行政环境运行中出现的一种与其本意相反的结论。信访问责目的是更大程度上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规范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然而,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指引下,信访问责制在地方运行时往往出现不细化责任、不管有无责任,出现重大信访问题就追究的一刀切现象。在问责重压之下,基层政府和信访机构往往采取能立竿见影、简单易行的然而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围追堵截的方法。责任压力越大,围追堵截力度越大;围追堵截力度越大,越级上访越多;越级上访越多,围追堵截力度越大……这样往往陷入无穷的恶性循环。
同时这种问责制也易于助长无理信访的现象。一些觉悟较低的信访者为了自身私利,利用问责制弹性空间及领导者怕乱求稳的心理,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信条,往往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来要挟基层领导,而目前又缺失对无理信访者进行约束与规范的政策。在责任重压之下,基层领导无奈之处就会采取“花钱消灾”的办法。而这短视行为不仅易于丧失党的政治信仰和公信力,而且易于诱引另一批无理信访者效尤,进而滋生下一轮无理信访,这样又易于形成另一个恶性循环。从这两种角度看,问责的结果与问责的初衷极易背道而驰,既易于给基层领导带来太大的心理压力,花费基层大量的人财物,易于产生“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的无奈心态;又没有抑制住越级访、缠访等现象,反而加大了无理信访。同时又易于给那些真正利益受损的信访者在围追堵截中增加痛苦,易于使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仰和合法性流失。
2009年9月8日,笔者对江苏省委党校第28期乡镇党委书记进修班的36位乡镇党委书记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其中88.88%的人认为,上级领导对基层领导信访问责时,有一刀切现象,即不细化责任、不管有无责任,出现重大信访问题就追究;80.55%的人认为信访问责制给基层领导的压力太大;75.00%的人认为目前地方基层最棘手的问题是信访问题;91.66%的人认为信访问责制施行后,他们得花费更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来处理信访问题;91.66%的人认为其所在的基层有对越级上访人进行截访现象;91.66%的人认为,在现行问责制下,他们是基层领导一把手他们要对所属区的越级上访人进行截访;97.22%的人认为,在现行问责制压力下,基层对信访问题必然出现“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现象;83.33%的人认为,自信访问责制施行来,地方无理上访的人越来越多;80.55%的人认为,自信访问责制施行来,地方越级上访的人越来越多;100%的人认为,应制定相关政策来规范无理信访者。这一组与信访问责初衷相背道而驰的数据说明了信访问责悖论不仅在理性分析上客观存在,更说明了它在现实运行中的客观存在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二、信访问责悖论的成因
(一)职能定位有问题
在现行《国家信访条例》中,并没有对信访的职能作明确界定,但其总则第一条指出:“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制定本条例。”可见国家信访主要功能是民众的利益表达与利益救济以及维护信访自身秩序的功能上。其实,信访的功能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柏瑛认为,如果把我国的行政体系看作一个运转的系统,信访处的位置应该是末端,公共政策出现了问题才会在这里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界定信访职能时,应将信访放到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中考量,应将信访放到公共政策运行的系统中,既要注重信访本身固有的民众的利益表达与利益救济功能;更应注重它的推动中国特色的动态民主建设的导向功能,即用处于政策运行系统的末端的信访与民众的监督来反推政策的科学制定与规范执行,反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客观事实上,信访这一功能并没有得到体现,民众的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没有得到更大的激发。往往将信访与政策的系统运行割离开来,孤立地看待信访问题;往往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信访本身问题,将更大的政策缺失、政策滞后、政策不当和政策执行偏差等政策问题束之高阁。民众的维权意识也主要集中在与自己联系密切的利益上面,而对那些与己无利益相关的政府不当行为则缺乏监督意识与监督能力,抑制政府的围追堵截等不当行为的能力更是低下。这就更易诱发和助长政府围追堵截的不当行为。简言之,信访职能定位短视易于使民众的监督意识、监督能力以及抑制政府不当行为的能力短缺,而民众的监督意识、监督能力以及抑制政府不当行为的能力短缺又易于助长政府对信访者围追堵截等不当行为,易于助长问责悖论产生。
(二)地方与中央信访机构职能错位
机构设置应以职能为导向,以解决事务为准则;反之,职能定位是否准确,也可以从机构设置状况得以体现。地方基层是处于管理金字塔的底端,是信访问题的井喷之处。由基层向中央信访问题的源发数量应逐级递减。而目前我国信访机构却出现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即地方基层信访机构太小,人员编制少,而国家信访局规模大、人员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地方政府难以应对大量信访问题,难以将督察、协调、办理的职能落到实处。这必然吸引大量信访群众越级上访,进京上访,也容易给老百姓以“上面解决问题、下面不解决问题”,中央都是“青天”、地方都是“昏官”的错觉。在问责重压之下,基层领导必然对越级访与进京访的信访者进行围追堵截,围追堵截力度越大,越增加信访人的敌视心理,越可能迫使进一步越级上访,进而加速问责悖论的产生。
(三)领导干部的权责不对称
领导干部的权责不对称是指处理信访事务时拥有的权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对称。一是有责无权。处理信访事务是按属地管理的原则,而有些事务是由上级部门不当行为或不合理的政策引发的,但信访人是在基层,即信访人所属地和涉访事的地点不一致。基层领导有时是很难甚或无力解决上层组织引发的这些问题,但责任却完全落到他们的头上。二是权力越位。政府与法院及检察院的关系是平行的,应该互相制约。但目前两院的信访例并不健全。政府信访机构是主导的信访机构,当涉访事是介于行政与两院之间,甚或就是两院的事,在地方考核制度不健全或一刀切的情形下,责任往往还是地方政府和党委负责。这样势必易于导致行政权扩张和行政权侵犯司法权,易于导致司法扭曲变异。司法权的扭曲变异又将加大信访工作的难度,加大基层政府履行职责的难度。
(四)信访机构的权责不对称
无论是行政机关的信访机构,还是两院的信访机构,它们都是其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而它们却要承担督察、督办等职能。倘若是平行部门之间督办还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如果涉访事务是那些重要部门或重要领导人身上,他们在权力甚微的情况下,如何去督办?在面对越级上访或难缠信访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围追堵截甚或“花钱消灾”的方法,这样既可减轻自身的工作难度,又可以减轻领导的问责重压。问责悖论的产生就有一定的必然性。
(五)信访人的权责不对称
信访人的权责不对称是指信访人拥有的信访权力和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对称。目前信访条例和相关制度着重强调信访机构和相关领导人的责任,对信访人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信访秩序要求上,而对他们的越级访、缠访和无理上访缺少相关的制度来规范。那些越级访、缠访和无理上访更易制造事端影响稳定,这也是目前基层领导干部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在信访问责和考核一刀切的重压下,地方政府极易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或不当措施。如,围追堵截、关押、逼问、变相罚款等。在信息网络化的今天,这些信息又极易被进一步放大甚或扭曲变异,人们往往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长此以往又易于使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仰与公信力流失。这与我们的问责本意背道而驰。
(六)程序的欠正义性
公共政策程序正义,罗尔斯提出可以从完善和不完善程序正义的比较来理解。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条件是:“有一个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独立标准,和一种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不完善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1]目前我国的信访程序设计在权力不对称和信访机构职能错位的条件下,其程序不完善或欠正义性主要体现在中央允许而地方堵截的越级访的程序设置上。由于地方信访机构太小、人员编制少、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信访人长期信上不信下的思维定势,地方政府既是信访问题的制造者又是问题的仲裁者的双重角色等诸多原因,信访者更多的会选择越级访。而越级访最易引发不稳,引发地方政府的围追堵截。这是信访中最棘手的问题。现行信访条例允许信访人向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进行信访,然而,它同样也默许地方政府对越级信访者进行围追堵截。因为国家信访条例和2008年制定的一系列问责制度中,只字未提对信访围追堵截的惩处。地方政府在问责重压之下,对于那些最易引发不稳最易暴露问题的越级访,他们势必进行围追堵截。这种“明扬暗抑”的越级访程序势必产生系列问题。信访人在越级访中常常饱受痛苦,往往对地方政府或地方领导产生敌视心理,这不仅使地方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而且使党或国家的政治信仰流失,这与问责本意完全背离。
三、破解信访问责悖论的对策
(一)定位大信访职能
1.定位大信访职能首先要跳出“民意表达、利益救济、维持稳定及为信访而信访”的功能圈子,将推动中国特色的动态民主政治建设放到最大高度。美国学者M·麦克拉夫林在他的《互相调适的政策实施》著作中提出了互动理论模型,认为“政策执行的成效与否取决于执行者与受影响者之间互适的程度”[2]。从这一理论角度看,我们可将信访问题纳入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估、反馈等政策运行的系统中,将信访问责纳入整个行政问责的系统中,加大信访督察、督办的职能力度,加大对信访问题的量化分析与归纳整理,以信访来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2.建立整改的倒逼机制。将问责与考核指挥棒侧重倾斜于涉访的政策与行政行为的整改上,以整改行动逐步推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建设及其政策的规范执行。倒逼机制的力度越强,不合理的涉访事件将可能变得越少,人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越能得到有序地激发。这种判断的逻辑源于塞缪尔·亨廷顿的假定,即政治开放、政治发展的速度应与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相匹配,这样才能使政治博弈过程中新成长的力量被有序地吸纳,而不至于导致政治秩序结构的失衡,并瓦解社会稳定的基础[3]。当人民的民主意识越强,越能把民众单一的狭隘的利益信访向无自我利益可求的带有强烈民主意识与主人翁意识的信访转变;人民的无利益需求的信访意识越强,又越能推动倒逼机制的建设。这就构成一个闭路良性循环,其运转速度越快,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越快。可以说,倒逼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疏通信访渠道和走出围追堵截的怪圈;有利于民众的利益表达与利益救济,能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等落到实处;有利于构建政策执行的系统,激发民众的民主意识与主人翁意识,既能避免民众的无理信访与缠访等现象,又能从源头上逐步减少涉访事件,从政策执行的末端来反推我国特色的动态民主政治建设。
3.准确定位行政、立法、司法与人大等信访机构的职能。既要突出行政机关信访机构的功能,又要发挥人大信访机构的主导作用,也要彰显立法与司法信访机构的独立性。这就能避免行政权的扩张,将部分涉法信访引向法制渠道,还能增强整个信访的系统性,便于从根源上消解信访问责悖论现象。
(二)构建椭圆型模式信访机构
椭圆型模式信访机构是指解决某地重大难缠的信访的数量以地级市信访机构为中心向上下两级信访机构逐级递减的信访机构构建模式。构建椭圆型模式信访机构主要目的:避免信访问责悖论现象产生;避免现行的“头重脚轻”的信访机构引发大量的越级访与进京访现象产生;避免权责不一致无法问责的现象产生;避免乡镇政府与县政府的“信访事件的制造者”与“信访事件的解决者”的双重角色易于作出违规行为的现象产生。具体的构建措施如下:
1.各地市构建大信访机构。整合信访资源,创建市级大信访办公厅,扩大信访机构的权力,使之具有督察、督办、提议罢免、干部考核权、统筹调度、表彰通报等权力;设置城市拆迁、企业转制等常规性的行政执法部门;实行“一站式”接待处理,将法院、检查机关引入信访接待大厅,设立信访涉法事务代理登记点;制定联席会议、行政仲裁、信访听证等制度。着力解决本市重大难缠的信访事项,保证本市满意的结案率达98%以上。
2.中央与省信访机构基本保持不变,但应加大量化分析的技术性研发,突出处理重大难缠的信访能力建设,突出督察督办职能,保证每一级政府的信访机构达到要求的结案率,保证各项整改措施能有效地贯彻落实。省政府信访机构应保证本省信访的满意结案率再增加一个百分点,使之达到99%以上,基本解决本省的信访问题。中央信访机构主要任务是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与法规和对各地信访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并处理极少数的特别难缠的信访问题。
3.重新定位乡镇信访机构。首先,在各乡镇设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化解本地区的各种矛盾,从源头减少涉访事件发生。其次,取消以信访数量为标准的一刀切的考核办法,取消涉访事件引发者的问责制度。严格意义上说,乡镇不设专门的信访机构,它的主要信访事务是执行上级政府作出的涉访事件的整改措施,以及逐步实现本地区行政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从源头上逐步根治涉访事件发生。再次,设立乡镇一级信访数量弹性预警线。该线由县信访机构结合本地实际自主确定,但标准应逐年提高。预警线内不考核,超过预警线,设立地方一把手问责制。设立预警线目的:一是从宏观上要求该级政府加强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建设,既能达到减轻地方的信访压力,又能防止信访数量增加;二是以信访为突破口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的动态民主政治建设。弹性预警线就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预警线,以民众的信访汇总情况不断地推进政府提升考核标准,不断给地方政府提出新要求。它迫使行政人员必须将“三个代表”、服务型政府与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不断地规范自身行为,从源头上减少涉访事件的发生。最后,设立围追堵截的问责高压线。虽已取消以信访数量为标准的一刀切的考核方法,取消涉访事务引发者的问责制度,但弹性预警线的设立也会给其带来适度压力,因此必须设立围追堵截的问责高压线,坚决惩治对信访人员的围追堵截行为,必须保证弹性预警线能有效地贯彻落实。
4.调适县政府的信访机构。县级政府继续设立专门的信访机构,适当增加人员编制,但其基本格局大体保持不变。其主要职能是“收、转、督察与督办”。将县信访机构作为信访的第一站,信访者越过乡镇直接向县信访机构上访。其目的是避免乡镇机构处理涉访事件时其双重角色易于带来的不公行为和对信访人员的围追堵截现象发生。乡镇涉访事务的整改要求由县信访机构直接落实到相关责任人,并对整改的结果进行考核。同样,取消县的信访数量一刀切的考核方法,取消涉访事务引发者的问责制度,同样设立信访数量弹性预警线,其预警线由市信访机构确定,其目的与考核方法与乡镇的相同。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3]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作者单位 江苏省委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
(责任编辑 崔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