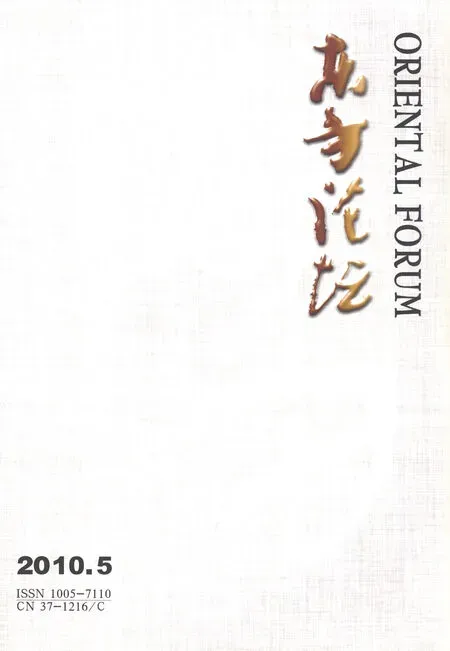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2010-04-05赵树国
赵 树 国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赵 树 国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的水神信仰传承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呈现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等特点。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水是人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该地区层峦起伏的地形,以及温带季风性气候的作用,容易造成降水不均,形成旱涝灾害。于是,当地便围绕水产生了一系列的信仰。明清时期的鲁中地区水神信仰,既对前代有所传承发展,同时因其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又与周边有所不同。本文采用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对明清鲁中水神信仰概况、特点及其原因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鲁中地区水神信仰概况
(一)自然神
1.山:久负盛名的泰山、沂山,早就成为人们祈雨的对象。宋宣和间,徽宗遣张所代祭沂山,提到:“春来及夏,魃鬼复加为虐。谷未播,麦枯焦。……朕躬省深念,惟王镇中区,国所恃,民所倚,特遣官赍香帛牲醴,祈告于王,……布甘霖,驱旱魃,以成丰年”[1](P229-230),即为一例。除岳、镇外,普通山神也主降雨。金泰和间,章丘县“炎沴流行,自冬徂春,雨旸愆期,田禾枯槁,农家困窘”,知县刘某,“斋戒精洁,引咎自讼,躬率其属遍祷于境内山川之祠”,最后于女郎山之巅,致祭天神而获雨。[2](卷十三《甘澍亭记》)此外,新泰敖山之孚泽山神庙,“祷雨有应”[3](卷十九《敖山记》);东平县金螺山顶有白云洞、黑云洞,“每起云如盖,或旋绕四侧,辄雨。旱岁祷雨多应”[4](卷三《山川》)。
2.水:自然界的水也是人们祈禳的对象。长清隔马山神君祠前有一潭,“祷雨辄应”[5](卷十《祠祀志下》);章丘西龙洞,“有泉一,自上滴下,下有石盆盛之,四时不竭。遇旱,取水祷雨,辄应。旁石壁有龙形隐隐可见”[2](卷三《山水考》);东平芦泉山下有珍珠泉,“祷雨取水于此,甘霖立沛”;东平凤凰山下有寺,四周皆石,中有巨泉,清澈涌沸,旧传“祈雨有应”。[4](卷二《山川》)
3.石:石本与降水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被赋予某种神奇功能后,也可主降水。长清县清河西纪家庄侧有“鸡含店”,坑中有大石,刻佛数千如莲花状,天旱土人掘之,“方漏顶,有水自内出,即大雨”;长清县石佛屯庙内石佛旁有王三公石像,“祷雨辄应”。[5](卷十《祠祀志下》)
4.灵物:当地人们普遍认为,凡遇大水一般均伴随有灵物,即传说中的“水精”,它们可以操纵水流的方向、规模、程度等。据《聊斋志异》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山东大旱,自春至夏,赤地千里。至六月,方才下雨。一日,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羊斗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携家播迁。村人共笑之。无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6](P234)此处的羊即管水的灵物。
(二)龙神
这一时期,龙因其传说中所特有的行云布雨的功能、以及长久以来人们对龙文化的崇拜,成为职业化的降雨之神,充当了降水的主要角色。在鲁中地区,其祠宇所在多有。人们多认为龙神具有“倏隐倏见,能大能小”的特点,龙王庙亦可“不梁不栋”、“不黝不垩”、“不甓不甍”,甚至可以“不必庙不必不庙”。[7](卷十三《龙王庙碑记》)所以,这一地区的名山大川、抑或乡野村落,甚至一般靠近水湾、泉水、河流之处,经常有或大或小的龙王庙。
龙神崇拜较为复杂,龙神中有自然神,也有人格神。作为自然神的龙,是龙的具体化身,是与水直接相关的灵物。弘治十年,益都县“有龙斗于阳水,漂没人物甚众”。[8](卷六《五行志》)顺治十年,颜神镇大水灾“山谷皆涨,其水每在高处流,下处反无水,又或中流如脊高立,两边乃下”,人们以为有龙。[9](卷十下《杂志•神异》)作为人格神的龙神,则是“龙”名义下的具体个人。如莱芜县旧寨龙王庙,“祠宇三间,置神像,南向二妃祔,风雨神西向,雷电神东向”,龙王家属、僚属一应俱全[10](卷三十五《新建龙王庙记》),显然已把龙王当作活生生的人。再如临朐县禅堂崮,崮下有泉,自白龙洞中出,洞侧有龙神祠,岁旱祷雨多应。此“白龙神”也是活人,“相传神生于元末,姓钟名玉秀。父世太,字安邦。母张氏。住城北五里庄。明洪武中于六月十三日尸解成仙,栖白龙洞中”。[11](卷十五《礼俗•白龙神庙》)
当然,不管龙神属性如何,其在降水中的主导作用是无可置疑的。蒲松龄曾描述龙神显灵的事迹:“泉最久,故其神最灵。每旸亢,远迎舁柳辇驻其下,呼神者三,谷渊渊有应声,其声彻,雨则立澍”。[12](卷十《满井募建龙王庙序》)
(三)人格化水神
1.专职水神:由于当地对水的需求较大,龙神不能完全满足人们需求,一些与水沾边的人格神,也纷纷加入到降水神的行列中,成为专职水神。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在博山一带广为流传的颜文姜。据宋熙宁六年《重修顺德祠记》记载:颜神镇(博山)所供“孝感泉水”之颜文姜的顺德祠,早在后梁乾化间就有“岁旱祈祷,即日获雨”的记载。[13](卷三《飨祀》)后世记载更多。清代,昌邑县抚安社圣水池顺德夫人祠,池冬夏不涸,每大旱淘之即雨。[14](卷一《山川》)此外,二郎神虽非鲁中所产,但有些地区也将其作为水神崇拜。如天顺年间莱芜大旱,知县伍礼派人祈祷于二郎神庙,果获大雨。[10](卷三五《祷雨有感记》)长山县,二郎神庙建于金代以前,又称感应公庙,“旱潦螟螣疾疫,祷之辄应”。[15](卷二《庙观》)肥城大封乡也有二郎神祠,乾隆年间恩贡尹统撰《重修二郎神祠碑记》推断:“乡之中,其始必以水患蒙神力而获福惠焉,乃庙而祀之”,[16](卷二《重修二郎神祠碑记》)显然也把二郎神当做水神。再如,昌乐孤山夷齐庙,久有降雨之功,“夷齐庙祷雨之灵,古有明征”,后来附近又修建了龙神庙,但民众仍然认为其“清圣之惠被斯民固与广陵侯同,有合于祀典者也”,[17](卷十六《重修孤山庙碑记》)认可其降水功德。
2.兼职降水神:一些人格神,本不专司降水,但在特殊情况下,也能施以甘霖,客串水神角色。观音就因其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性格,和解民于倒悬、拯苍生于苦难的精神,一度被赋予降水的职能。淄川县西峪普陀洞,“数年来水旱、疾疫,有祷辄应”[12](卷十《西峪修普陀洞碑记》);康熙辛丑春夏间大旱,济南卫守备朱士豸步祷于胡山圣水井,忽见“观音大士像历时没,回未数里,沛泽遍野”[2](卷十五《轶事志》)。均认为观音可主降雨。此外,博山禹王庙,“遇旱祷雨,迎神设祭,有司主之”[9](卷二《祀典》);昌乐朝阳洞泰山神,“遇旱干疾疫竭诚祈祷,辄蒙神庥”[17](卷十六《重修朝阳洞碑记》);甚至虫神八蜡,也可降水,万历甲辰春,长清县“弥月不雨,稼穑维艰,民感不宁,公率僚吏徒行诣(八蜡庙)祷,不逾时而甘霖三日,炎夏魃虐,祷之复雨”[18](卷九《重修八蜡庙记》)。
3.职能转变之水神:一些本不属于降水系统的神灵,因机缘巧合,也可能具备行云布雨功能,并逐渐转化为降水神。如郑康成,本“以儒术润色教化、启迪后学,使万世咸赖其功”,属道德人物崇拜。至元代,“此土间遇水旱、螟蝗之灾,民往祷之,未尝不旋踵而应”,具备了降雨、祛灾的功能。虽然正统人士对此颇有非议,认为“若夫牵合怪诞、惑乱众听,以求黍稷牲牢之丰腆,是玷公之德,非神之望也”。[12](卷七《重修郑公庙记》)不过,这时郑玄能被普通民众广泛信仰,其降水之功起了很大作用,诚如当地诗中所谓,“霖雨苍生又响应,祈年更祝汉司农”。[12](卷七《郑公祠筑楼》)此外,流传于益都、淄川一带炉神姑,这时也成为降雨之神,并能“祷雨辄应”。炉神姑本为冶铁业行业神,“南燕立铁冶于商山,而鼓铸之事起至元不废。冶工因庙炉神以祈福利”。[8](卷十三《营建志上•炉神庙》)元代以后该地铁冶业废弛,炉神信仰的基础不复存在,如果这一信仰仍要存在、发展的话,必须通过新的灵验事件获取民众的支持,其降水职能便应运而生。淄川十里庄民众,曾经“举议往祷,即沛甘霖”,于是“募化四方,各捐资助力为修行宫”。[12](卷十《十里庄炉神庙碑记》)
4.社区神:作为社区神的城隍、土地等神,有时也能承担降水的职责。万历年间,新城知县因“旱干祷神(城隍神),雨泽灵应”。[19](卷二十三《重修城隍庙记碑》)康熙五十二年,长山县“时逢润夏,雨泽愆期”,孙衍率僚属,设祈场,禁止刑牲,以求雨,于是大沛甘霖,此处所求之“邑神”就是城隍。[15](卷十二《酬邑神文》)乾隆中期肥城县尚无龙王庙,大旱之际“乃假城隍庙于六月初六日,设坛展拜”,获大雨。[16](卷四《创修龙王庙记》)光绪十一年,淄川城隍因官民“祈祷,获沛甘霖”,而被“敕封利民,并赐御书匾额一方曰‘般阳绥佑’”。[12](卷九《三续祀典》)甚至官卑职微的土地爷,也负有降水职责。这从小说《醒世姻缘传》中所述劣秀才严列星之忤逆行为可以得到反证,“若是该雨不雨,……他走去那庄头上一座土地庙里,指了土地的脸,无般不识的骂到。——再不就拿了一张弓,挟了几枝箭,常常把那土地射一通,射得那土地的身上七孔八穿的箭眼”[20](P338)。在临朐西北地区,也一直流传着“土地爷还有二指雨”的说法。
5.仙人:仙人也负责降水。齐东县之麻姑仙庙,“农夫祷雨,无不雨降”。[21](卷八《修麻姑仙庙碑》)传说中斩蛟的许真君,成为人们信仰的司水仙人。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写道:“玉帝檄召江西南昌府铁树宫许旌阳真君放出神蛟,泻那邻郡南旺、漏泽、范阳、跑突诸泉,协济白云水吏,于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决水淹那些坏人。”[20](P364)
(四)方术、祈禳行为
鲁中地区人们大多认为,有时长期不雨是妖孽作祟,倘若施以方术,铲除妖孽,即可得雨。顺治十七年,长山县大旱,贾知县认为“果有旱魃者为虐”,一方面虔心求雨,一方面令属吏起草檄文,“檄城隍,且执神前二土偶,械而系诸谯门之左,曰‘速返吾雨’。不,且磔女矣”,果然大雨。[15](卷十三《贾侯祷雨记》)
在民间,民众除祈求神灵降水外,还组织各种祈禳行动。博山县,“凡遇旱祷雨不应,无夫老妇挈箕帚,叩祝于秋谷龙王之庙,以帚刷箕毕,收泉水轮箕飏之,谓之‘刷簸箕’,往往有应”[9](卷四下《风俗》);长清魏里庄西北里余,“一阜突起,高丈余,广十余亩,俗呼为‘狗冢’,值岁旱,土人以草秉然火,旋绕其阜,辄得雨”[5](卷十六《杂事志•义犬冢》);昌乐县西菜园庄北之唐埠,“天旱用火燎之辄雨”[17](卷三《山川志》);长清龙泉寺内有坑,坑内有亭,谓之“方石亭”,亭中有井,天旱土人掘之,即雨[5](卷十《祠祀志下》);临朐西北逄山北麓村庄,逢久旱不雨,便组织少女、或已婚妇女,携带工具爬逄山顶挖饮马池,据说不等下山,雨就已经降落。
水神是鲁中地区信仰最为直接、分布最为广泛的神灵,从神格上讲,既有自然物、自然神,又有人格神,其中尤以各种类型的龙神为主。从信仰群体讲,是非常广泛的,既有地方官吏、士绅,也有平民百姓。
二、鲁中水神信仰的特点
明清时期,鲁中地区的水神信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范围广、神灵全。其范围广体现在,求雨行为涉及官吏、士人、普通民众等,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如地方官吏,临朐县尹陈仲祥,“操履端洁,政事修举,遇旱祷雨辄应”[23](卷十三《宦迹》);康熙年间,长山县“时逢润夏,雨泽愆期”,知县孙衍率僚属,设祈场、禁止刑牲,以求雨,于是大沛甘霖[15](卷十二《酬邑神文》)。如乡村领袖,在临朐西北逄山爷信仰区,一遇较重旱灾,六社社首就会带领人们赴逄山庙求雨。如普通百姓,一遇大旱,则“父老子弟相率而奔走于丛祠之间。凡所为索虵医、祈龙子、暴虺而诚求者,不遗余力矣”[15](卷十三《贾侯祷雨记》)。由上可见,求雨行为涉及面非常广,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与此同时,由于水的至关重要性,加之人们在面临困境时“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使得鲁中地区的“水神”体系非常广泛。由本文第一部分可见:在鲁中地区,自然神、龙神、人格神、神职人员等均可降雨,降水神灵非常完备。可以说,降水行为几乎牵涉到神界、人界中的各个层级。
(二)祈雨动机功利化。风调雨顺是各阶层求雨的一致目的。当然,在这一功利化目的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如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其求雨行为大多是出于生计考虑的无可奈何的虔诚;对于地方官来说,则求雨既可能是“为民请命者”在灾难到来之际,与民同甘共苦的一种政治姿态,也可能是“沽名钓誉者”为维护一己之私的假仁假义。但总体而言,所有的求雨行为都将归于一个中心,那就是“灵验”。为达到灵验的目的,民众可以“惟灵是从”地去求各路神灵,而不管其是否专职降水。如上文所引之虫神八蜡,本为专职灭蝗神,与降水无涉。万历甲辰春,长清县“弥月不雨,稼穑维艰,民感不宁”,知县率僚吏徒行诣祷,“不逾时而甘霖三日,炎夏魃虐,祷之复雨”[18](卷九《重修八蜡庙记》)。此外,民众对降水神灵是否虔诚和尊重,基本上也是以灵验为标准。如上文所引《醒世姻缘传》中劣秀才严列星,每遇到旱情,就到土地庙中大骂土地,或者拿弓箭射土地神像[20](P338)。其行为固然忤逆,但其目的的功利性也非常明显。再如,康熙间章丘知县钟运泰,数次求雨不得,撰《祈雨文》对降水神进行恐吓、挖苦。他先针对长久不雨指出,“夫以为土木形骸,果不知之,是无神也”,并大胆责问“知民之颠连而不为之请,是神溺其司而不职也”、“吾神职守有亏,徒享常祀不能御万民之灾患”,最后更进一步威胁道:“将易此土木之形骸”[2](卷十《祷雨文》)。威逼利诱之态,一目了然。由上可见,尽管各阶层民众均参与到祈雨活动中,但在貌似虔诚的背后,功利性是其主要目的。
(三)政治色彩浓厚。这体现在信仰群体上,是地方官、士绅积极参与、并主导祈雨行为。如嘉靖十二年临朐旱蝗,知县褚宝祷于沂山,“甘澍立降,蝗尽飞去”[23](卷十三《宦迹》);康熙辛丑济南大旱,济南卫守备朱士豸步祷至胡山圣水井,于洞中忽见观音大士像,历时而没。回未数里,沛泽遍野[2](卷十五《轶事志》)。此等事例不一而足,兹不赘述。体现在神灵行为上,则是部分降水行为,需要一个完整的行政程序。如成化年间莱芜大旱,知县伍礼先是派司吏王辅、里老人魏良友至魏家庄迎请二郎神入城隍庙。有小民傅真入庙昏眩,醒后曰:“神白马黄袍,真及从者十二人行空至东海,见高城铁门内若王者居,曰:‘此龙宫也’,神入于宫”,“须臾取故道归庙,……庙之中则城隍与神会议良久”。[10](卷三十五《祷雨有感记》)通过傅真的奇遇,展现了一场牵涉到二郎神、龙王、城隍神三者的降水过程。这次降水由二郎神与城隍神决策,龙王负责实施,行政程序非常完善。又如,临朐西北一带,每逢天旱,人民便去求逄山爷,然后抬逄山爷之法身,往东数里外珍珠山玉皇庙去“朝玉皇”,以求得降雨法旨,然后再由逄山庙西南数里的郝坛村白龙王爷负责降雨。降雨后,在逄山庙唱戏酬神,请白龙王观看,逄山爷作陪。(一说:逄山爷朝过玉皇后,就到北溜胡家庄其外祖家等雨,民众则于降雨后唱戏感谢逄山爷)在这一求雨过程中,逄山爷的角色是居中调度,求取圣旨、调度降雨,真正实施降雨行为的则是白龙王爷,体现了较为严格的行政程序和明确的职守观念。
(四)道德倾向明显。随着“天人感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对程朱理学的大力推行,人们普遍认为:上天对世间事了如指掌,即“神以聪明正直而在此位,则官之贪廉、政之得失、民情之喜怨,靡不熟计而详察之”,[21](卷八《祈雨文》)并通过赐福、或是降灾,表现对于地方官是否满意。如康熙二十九年夏,章丘大旱,知县钟运泰“斋心步祷,直至山颠叩谒神祠,甫下山取水,即密云四起,疎雨廉织,及归甘霖大沛”。[24](卷一《山川•胡山》)最为典型的当为李化熙所述长山贾知县祈雨之事。贾知县为祷雨,首先下令“减刑罚、停输纳”,而后“退而沐浴洁斋,布席于庭,身自曝烈日中。明日,复往祷于长白之五龙塘……侯上下山坂往返百有余里,悉屏车盖、彻驺从,膝行稽首、鹄望屏息,质明而往,未晡而返,迄终事无少懈也”,展现了他作为一方父母为民请命的诚意。上天也给予了非常奇妙的“答复”,即贾知县所辖之长山县境内“数百里沾足若一,而它邑之壤相错者无有也”,以高度精确的灵验,突显了贾知县挺身而出、为民祈雨的功劳。李化熙肯定了贾知县的功劳,“自侯之来,而狱无穿墉之鼠,家有牦足之厐。不以一胥督催科而税集,不以一圜取钩金而颂清”,认为祈雨之所以成功,是“侯之意,非侯之术也”,[15](卷十三《贾侯祷雨记》)强调了道德在求雨行为中的重要性。此外,“降水”还是上天对孝子的奖赏。明代益都郑墓店人冀琮,居官清廉,且能克尽孝道,其母去世时“天久旱,葬之日,大雨如注”,明年父卒“天又大旱,比葬,亦大雨”。[8](卷四十一《孝义传》)
(五)具有特定的地域特色。明清时期,鲁中地区的水神信仰,具有特定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具有山、水特色。鲁中地区多山的地形,使得当地围绕“山”的信仰较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大到泰山、沂山,小到女郎山、逄山,其神灵均在降水中承担了重要职责。当地民众在长期的生活中,还形成了观山貌以窥雨情的习俗,如沂山,天欲雨则山颠有云如冠,“故土谚云:沂山戴笠,雨不一日”。[23](卷三上《山水上•沂山》)此外,该地区多河、泉,因此与河、泉有关的水神特别多,其主要职责几乎均为降水;其二,具有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鲁中地区人类文明源远流长,从上古至明清,中间并未断绝。一些具有当地历史特色的神灵一直流传下来,如逄伯陵是商以前居于齐地的诸侯,颜文姜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他们均代表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鲁中水神信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继承表现在,当地水神信仰体系具有延续性,降水神灵与前代一脉相传,如逄伯陵、颜文姜等,均在当地有悠久历史;其发展表现在,明清以来,随着程朱理学的普遍深入人心,朝廷官吏、普通民众在水神信仰中,对道德的要求日益严格。同时,由于朝廷对民间社会控制日益严密,当地水神信仰较之以前政治性色彩更为浓厚。此外,由于鲁中地区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该区域水神信仰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
三、鲁中水神信仰流行的原因
鲁中地区水神信仰中展示出诸多特点,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一)在鲁中地区,石灰岩低山地貌、石灰岩丘陵地貌分布较为广泛。石灰岩溶蚀裂隙发育,地表水多渗漏转入地下,形成干谷,俗称为“漏河”。[25](P57)鲁中地区多山,且山多为单面山,加之溶蚀洼地及漏斗群、岩溶泉广泛分布,容易形成一些“冬夏,不溢不竭”[26](卷一《山川考》)的积水湾,它们或在高山之巅、或在峻峰之下,较易引发人们的遐想,使其产生对水的崇拜。如仰天山黑龙洞,“相传有龙潜其中,能兴云雨”[23](卷三上《山水》),宋元丰三年封灵泽侯,崇宁五年改封丰济侯,香火颇盛。此黑龙洞“即是一个发育在小溶斗底部的落水洞,洞阔如厅,垂直向下,洞深不详”[25](P74)。于慎行在阐述龙王与山水关系时曾说:“云雨者,龙之所凭。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则山川者龙之所自,即山川云雨之交而求龙以事之”,田叟、里老,也往往因“云雨之所兴,山川之所聚,立为庙貌,以备不岁之雩,而号之曰龙君”[27](卷七《平地泺重建龙王庙记》)。此外,在鲁中地区,人们经常将降雨与一些山貌联系起来,如沂山,天欲雨则山颠有云如冠,“故土谚云:沂山戴笠,雨不一日”。[23](卷三上《山水上•沂山》)昌乐方山东麓之雨信埠,“每阴雨前,辄有声隆隆如殷雷然,远闻数里外,三日后必雨”[17](卷三十八《杂稽传》)。这种种降雨的征兆,更使人们坚信山川与降雨有莫大的关联。显然,鲁中多山、水的地形,为龙王等水神崇拜奠定了基础。
(二)鲁中地区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人们对水的需求尤为紧迫。因此,祈雨行为便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官吏、士人、普通民众等,均有重要关系,所以水神信仰范围较广。此外,由于农业社会对水需求的极度迫切性,民众在求雨中,必然会“惟灵是从”,这既加深了水神信仰的功利性色彩,客观上也需要更多的水神以供其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降水神灵的复杂。更重要的一点,传统农业经济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业经营仅依靠小家庭协作即可完成,根本不需要大规模的相互协作,这就使得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如《醒世姻缘传》中描述的游秀才,“除了岁科两考进到城里走走,不然,整年整月,要见他一面也是难的”[20](P314)。康熙《颜神镇志》也说,“村下细民,山栖谷汲,女织男耕,深居简出”[13](卷二《风俗》)。同时,这一地区山峦起伏、交通不便,加之政区限制,容易形成小的地理、文化单元。每个小单元内必然有自己的水神,所以水神体系非常全。
(三)鲁中地区靠近京畿,受政治影响较深。传统的等级观念、行政程序等,既影响到地方官,也影响了民众的观念。体现在水神信仰中,就是祈雨行为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并与地方官、士绅相结合。这一时期,统治者出于“神道设教”的观念,也在扶持、参与民间信仰活动,他们认为:“若夫庵观寺院……虽非经制之宜,然劝善惩恶,俾民不佻,亦神道设教之一助也。”[21](卷二《坛庙》)至于这点,康熙《章丘县志》说得更为露骨:“嗟乎,淫祀不经。章丘之祀,不浸浸近淫乎?然庄语不如狎语,张耳、陈余不如厮养。率匹夫相怒,持券冒刃走死地如鹜。或语之以如来柱下至必袖手屈膝,相戒不敢犯。假令颜曾周程揖让劝论于其侧,宁渠足听?夫民之不可户说渺论尚矣,神道设教何必素王之宫,乡先生之社哉?”[24](卷七《秩祀志》)显然,地方官已经认识到民间信仰对于稳定统治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不遗余力的参与祈雨等信仰活动中来。同时,由于靠近政治中心,民众较为向往官场生活,也会在可能的范围内刻意加以模仿,体现在水神信仰中,就是求雨行为按照人世间的官场形式,有一个严格的行政程序。
(四)鲁中地区历史悠久,许多上古时期的水神等神是如逢伯陵,颜文姜等在水神信仰民俗传承中一直没有消亡,只是随时代不同发生了一些变异。另外,鲁中地处孔孟之乡,民众崇尚道德,并将道德因素与神灵行为联系起来,认为神灵可以赏善罚恶。如同治年间,青州知府王汝讷上任伊始就面临“惠泽未遽沦浃”的严峻考验,他“慈祥恻怛,为民请命,不越日甘霖大沛,稿润枯苏”,时人感叹“天地与人心相感通也”,王死后,百姓建祠纪念[8](卷十三《王公祠碑记》)。如崇祯九年,淄川县石工边某,“兄弟皆不孝,边每上山凿石,其母饷之稍迟辄诟詈,一日雷击死于石坑中,兄弟对坐如凿石状,但其一帽落耳。”[12](卷八《轶事》)在这种观念下,出现以道德因素影响求雨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时,植根于儒家传统的天人感应观念,不但为熟读儒家经典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士绅奉为圭杲,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醒世姻缘传》中说道:“那明水村的居民,淳庞质朴,赤心不漓,闷闷淳淳,富贵的不晓得欺那贫贱,强梁的不肯暴那孤寒,却都象些无用的愚民一般”。因为这一时期的乡民非常质朴,于是便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却道数十年,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夜湿昼晴,信是太平有象”。当数十年后,“那些前辈的老成渐渐的死去;那些忠厚遗风渐渐的浇漓;那些浮薄轻儇的子弟渐渐生将出来;那些刻薄没良心的事体渐渐行将开去;习染成风,惯行成性,那还似旧日的半分明水!”于是上天示警降灾,“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什么轻飚清籁,不是摧山,就是拔木。七八月就先下了霜,十一二月还要打雷震电”[20](P309)。可见,以道德标准赏善罚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这一地区在水神信仰中非常注重道德因素。
明清鲁中水神信仰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明清鲁中地区当地水神体系较为发达,各路神灵纷纷参与降水,祈雨行为成为一场牵涉各个阶层的社会性活动,并引起官方的重视。这一时期,当地水神信仰呈现出一系列特点,如水神体系完善,政治、道德因素浓厚,功利性色彩明显、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传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息息相关。
[1] 潘心德.东镇沂山[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
[2] 吴璋.道光章丘县志[M].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3] 江乾达.乾隆新泰县志[M].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4] 左宜似.光绪东平州志[M].光绪七年(1881)刻本.
[5] 舒化民.道光长清县志[M].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6] 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 王荫桂.民国续修博山县志[M].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
[8] 张承燮等.光绪益都县图志[M].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9] 富申.乾隆博山县志[M].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
[10] 李钟豫.民国续修莱芜县志[M].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11] 周钧英.民国临朐县续志[M].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12] 王康.乾隆淄川县志[M].乾隆八年(1743)刻本.
[13] 叶先登.康熙颜神镇志[M].康熙九年(1670)刻本.
[14] 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M].乾隆七年(1742)刻本.
[15] 倪企望.嘉庆长山县志[M].嘉庆六年(1801)刻本.
[16] 凌绂曾.光绪肥城县志[M].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17] 王金岳.民国昌乐县续志[M].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18] 李起元.民国长清县志[M].民国二十四年(1925)铅印本.
[19] 袁励杰等.民国重修新城县志[M].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20]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0.
[21] 余为霖.康熙新修齐东县志[M].嘉庆八年(1803)增刻本.
[22] 宋宪章.民国寿光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23] 姚延福.光绪临朐县志[M].光绪十年(1884)刻本.
[24] 钟运泰.康熙章丘县志[M].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25]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自然地理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6] 魏礼焯.嘉庆昌乐县志[M].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
[27] 李敬修.光绪平阴县志[M].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
责任编辑:郭泮溪
A Study of the Worship of Water God in Central Shando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O Shu-guo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China)
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entral Shandong was a typical agricultural society where there were numerous worshippers of Water God. Their system of worship was complete, and their rain praying was utilitarianism, with rich political, moral and regional features. It was inherited from former times and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All these features we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natur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entral China; worship of Water God
K207
A
1005-7110(2010)05-0022-06
2010-08-16
赵树国(1981-),男,山东青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