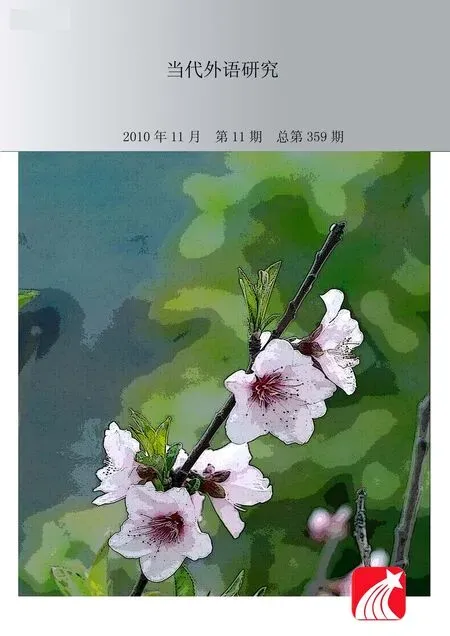构式语法与二语习得:现状、问题及启示
2010-04-05徐维华
徐维华 张 辉
(1. 国防科技大学,长沙,410094; 1. 2.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210039)
1. 引言
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种句法理论,构式语法是多个理论的统称,有几个重要的分支,如Fillmore和Kay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以Lakoff和Goldberg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为CCxG)①、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还有Lakoff等人最新发展的体验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Sag等人致力于使构式语法形式化的基于符号的构式语法(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为SBCG),等等。虽然各家理论有所不同,但其基本主张一致,即“句法结构的基本形式是构式,即复杂结构与其意义的配对”(Croft 2007:463),而且都认为构式是以网络结构形式组织起来的。与传统语法中构式的概念大相径庭,作为生成句法组合模式的反动,“构式”已成为一个代表所有语法知识的统一概念,包括句法、语义、词形、语用等知识。
构式语法最初起源于对一些特殊的“边缘”(peripheral)现象的研究,如熟语。这与乔姆斯基以常规的符合语法规则的所谓“核心”(core)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正好相反。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简称为UG)的组合理论(Compositional Theory)对熟语、半熟语等现象无能为力,而构式语法对此现象却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构式语法认为对特殊构式的研究同样可以揭示语言的普遍规律,从而全面解释各种语言现象。90年代以来,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以下简称构式语法)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近年来的理论更新和应用更引人注目,Croft(2009:157)称赞Goldberg的构式语法“对句法的理解有重要贡献,它从基于使用的(usage-based)构式视角对具
体构式进行分析,并将它们与生成语法的分析批判地进行比较”。与其它认知语言学理论一样,Goldberg的构式语法也是一种基于使用的语法理论,即语言使用决定语法表征,正是这一模式使得构式语法不仅关注语言的现状和实际使用,而且也关注语言变化和语言习得。以构式理论指导语言习得有其自身优势,如构式分析有助于区分相似结构的细微意义差别,如load the wagon with hay与load hay onto the wagon之间的语义差别,但如果用转换生成规则解释容易掩盖这种细微差别,而这种语义区分对于外语的掌握非常重要。对母语者构式的心理现实的论述和证实(Goldberg 2006)也引发了人们对二语构式的研究兴趣,研究者提出种种相关问题,如构式是否属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库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语构式是如何习得的、与一语构式习得相比有何异同,等等。本文主要论述的是Goldberg的构式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
2. 构式语法的语言习得观及二语教学观
首先,Goldberg对Chomsky的UG假设提出质疑。UG的语言天赋论(innateness hypothesis)认为语言的代表性或原则是天生的,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Goldberg强调语言是经后天学习得到的。在其新著《工作中的构式》(ConstructionsatWork)中,Goldberg认为可以将构式主义方法(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包括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她指出构式主义方法强调语言是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认为语言是作为一种范畴习得的,语言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由构式组成的,构式是用于交际目的的规约化的形式—意义/功能配对,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只要它的形式或功能不能从它们的组成成分或其它的构式中预测出意义,就可以被称为构式(梁君英2007)。语言的学习即构式的学习。
构式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语言构式有其自身的意义,构式义不等于构式各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符合心理学上的“格式塔”原理,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此构式义是独立于具体词汇而存在的。构式可以同时以抽象程度不一的几种不同形式进行表征和储存,成人的语言知识是一个复杂程度和抽象程度不同的由语言构式所形成的连续统,词汇与语法之间无法严格区分,语言是在输入和普通的认知、语用和处理限制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Goldberg 2006,2009a,b)。通过多个新奇构式(新奇形式、新奇意义及其配对)的实验,Goldberg(2002)证实,即使是在少量输入的情况下我们学习构式的速度也很快。
语言在本质上是与人类认知、记忆、感知、注意力、范畴化和原型化等相联系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是普遍认知机制起了作用,而概括的能力是语言学习的关键,单个例子的记忆随着时间会消退,而概括则在加强,人们将知识以格式(patterns)的形式组织起来,同时保留许多具体信息。语言知识不是由一条条互不相关的事实构成,而是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包括具体的和普遍的知识。因此Goldberg等人(2007)指出,学习者如何形成概括应该是语言习得研究的中心话题。关于构式的知识和其它普通的知识一样,构成一个综合的有其内在动因的网络。构式主义方法允许广泛概括和更受限制的格式都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释。Goldberg(2006,2009a,b)成功地解释了儿童初期的学习和如何进行概括以及如何避免过度概括。
基于使用的构式语法认为语言结构是在特定语境的使用中产生的,高频构式比低频构式更容易处理,这证实了学习和使用之间的联系(Ellis 2006)。构式的习得是由输入驱动的,并且依赖于学习者关于形式-功能关系的经验,同时,在语言习得研究中确立语言使用的首要地位使得语料库方法和语境化的功能话语的研究大行其道。
以构式主义方法研究二语教学通常认可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的基本原则,但是二语习得毕竟与一语习得有较大差异,如:在概念的发展方面,儿童习得一语过程中,他们的世界知识与语言知识是同时发展的,而成人的语言知识是在已存在的概念知识之上发展的,成人有复杂的形式化思维方式,能显性地进行学习;一语习得是自然的语言输入,二语习得往往是通过课本、教师、影像资料等途径接触语言;语言迁移也不容忽视,成人在习得二语时,其母语对二语中介语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Ellis 2001:9)。因此二语习得比一语习得增加了一层复杂性,再次建构一门语言比学习第一门语言更为复杂,在发展过程中二语构式会直接与学习者的一语构式进行竞争,而且二语习得代表着以另一种方式建构同样的现实,跨语言的影响无法避免(Ellis et al. 2009:112)。类似于索绪尔的符号,构式作为形式与意义/功能的结合体,形义的结合是任意的,不同语言的结合方式不同,这也体现了语言任意性的原则。学习第二语言意味着掌握一种不同的形式与意义/功能的结合方式。总之,构式的二语教学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完全照搬一语习得的研究成果。
3. 构式语法在二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1 研究的现状
目前构式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主要包括二语词库中的构式及其对习得的影响、构式在二语中的出现频率和语言形式对习得的影响,还有语言类型差异或母语迁移的影响等。下面介绍几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3.1.1 构式与二语词库
索绪尔的象征单位(形式-意义配对)的概念不仅涵盖词汇层,而且也适用于从音位、词语到更复杂的句法构造的各个层面的构式的语义表征。在构式语法中,高频句法结构被认为是与词汇一起作为象征单位储存在心理词库中的。那么,二语学习者是否也将构式储存在心理词库中呢?二语构式是否存在?研究者可以通过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和行为实验来证实构式的存在。
Gries和Wulff(2009)比较了英语动名词和不定式的两种构式的表达差异,如:She tried rocking the baby和She tried to rock the baby,其中to-构式通常描述比较具体的、潜在的、将来的事件,而-ing构式描述的大多是普遍的、现实的事件,一般指向与话语相同的时间。但是出现在两种构式中的动词并非明确地分成两组,动词后接的是动名词还是不定式往往给二语学习者带来不小的困难。此研究考察了母语为德语的英语二语学习者是否也将这两种不同的格式以构式的形式储存在二语词库中。作者通过结合语料库和行为实验证据证实了二语构式的存在,通过句法启动、补充完成句子和句子可接受度判断等语义分类实验后发现:二语学习者表现出句法启动效应和语义分类偏好,支持了“构式是中介语词库的一部分”的观点,启动效应与英语母语者非常接近,因为与母语者动词的次范畴偏好高度相关,而与这些动词的德语对应词的次范畴偏好完全不相关。
二语句法启动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多(见McDonough等人的研究),结果均支持“构式存在于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库”的论断。
3.1.2 频率与二语习得
构式在语言输入中出现的频率对习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个人的语言发展依赖于语言输入中特定构式出现的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和示例频率(token frequency)。Goldberg等人(2004)对CHILDES语料库中的儿童早期言语的查询发现,每一种构式都有一个动词的出现频率特别高。Goldberg提出自然语言中动词的类型/示例频率是呈Zipf分布的,之后进行了成人习得新奇动词(以o作为后缀)和新奇构式(SOV-o句型,如:the king the ball moopo-ed.)的实验,实验对整体的类型频率和示例频率都进行控制,结果显示被试在接触一个新奇构式在接触三分钟后就能对其进行概括,输入倾斜的实验组对构式的概括比输入平衡的对照组更精确,证实了通过提供具有原型意义的高频词范例可优化构式的学习。
Ellis和Ferreira-Junior(2009a)查询了ESF语料库(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Corpus)中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语料,包括VACs、VL、VOL、VOO等构式,发现二语习得的语言输入的类型频率和示例频率也同样呈现Zipf分布,而且学习者首先习得最常见的、原型的例子,因而支持了Goldberg的高频词例子有利于构式学习的论断,得出了例子的频率及其分布影响二语习得的结论。Ellis和Ferreira-Junior (2009b)进一步分析了频率、频率分布和例子的原型性对二语习得的影响,认为动词论元构式的类型-示例频率分布及其原型性、普遍性与形式-功能映射的可靠性共同作用优化了语言的习得。
3.1.3 母语迁移问题
母语迁移是影响二语习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母语迁移会影响二语的音位、词汇、词法、句法和语篇等各个子系统的学习(转引自唐承贤2003)。构式语法的二语习得研究也重视母语迁移的影响。
Cadierno和Robinson(2009)从语言类型学和心理语言学视角分析了表达移动的二语构式的习得,以期提供教学法参考。他们的文章“语言类型、任务复杂度及描述移动事件的二语词汇化发展”对母语分别为丹麦语(类型学上与英语接近)和日语(类型学上与英语不同)的英语二语学习者进行了跨语言研究,考察二语学习者掌握接近于目的语的词汇化模式和适当的表达移动的二语思维方式的情况。结果表明:二语水平的高低能预测母语为丹麦语和日语的学习者是否产出类似的二语移动构式;母语为丹麦语的学习者比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使用更多表达移动的构式;在认知复杂度高的任务中,接近目的语的词汇化模式的产出更多,但此现象只出现在同类型的丹麦语学习者中。虽然母语类型不同的学习者能渐渐学会二语的表达移动的方式,他们还是会表现出一些母语迁移的影响。
Gullberg的文章《在二语中重新建构动词意义》研究了母语为英语的荷兰语二语学习者在何种程度上重建放置动词的意义,发现英语致使-移动构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中表示放置的动词是通用的put,而在荷兰语中是两个具体的致使姿势动词zetten和leggen,相对应于英语的set和lay,没有一个上位词与英语的put相对应。作者还研究了一语中存在的低频同源词(即set和lay)是否会减缓重建的问题。言语和手势的证据表明,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在荷兰语的具体动词使用上有困难,开始时通过过渡概括寻求类似于母语的普遍方式来表达致使-移动构式。手势的数据进一步表明,目的语形式常用于表达类似于母语的意义。然而,学习者能区别表达垂直放置的zetten和表达水平放置的不及物动词(zitten/staan/liggen,“sit,stand,lie”),并具有与目的语相似的手势,这表明学习者对二语动词语义特性有了敏感性及重建的可能性。
自从构式语法被介绍到中国后,人们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既有介绍和理论阐释(见纪云霞、林书武2002;董燕萍、梁君英2002,2004;严辰松2006等),也有理论探讨和应用于汉语语法的研究(见沈家煊2000;张韧2007;陆俭明2008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董燕萍、梁君英对构式在中国学生英语句子意义理解中的作用的实证性研究,其主要发现是初学者更容易受动词的影响,而中级和高级水平的学习者则倾向于依据论元构式来理解句子意义(董燕萍、梁君英2004);胡学文(2007)进行了关于中国学生英语双宾构式习得情况的研究,该研究基于语料库进行英汉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英语双宾构式的发展模式与英语母语儿童该结构的发展模式相似,而意义范围要小于学者,该构式使用的错误主要源于母语的影响。黄莹(2006)对have使役结构的语义限制条件及其习得进行了研究,发现出于学习环境、母语迁移等原因,无论学习者英语水平高低,对该使役结构的语义限制条件均不敏感,因此提出英语使役类动词的教学不仅涉及动词语法形式的教学,还应涉及动词构式意义的教学。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也有一些将构式语法应用于教学的研究,如王海峰(2009)对汉语离合词教学模式的探讨,苏丹洁(2010)对现存句“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验研究等。
3.2 主要的问题
构式语法发展迅速,但毕竟是一种新的理论,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提炼和发展。构式语法在二语教学中的应用更是刚刚起步,理论和实践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构式语法研究本身还不够完善,如儿童早期句法发展研究成果较多(见Tomasello,Goldberg等人的研究),而对其后的发展研究较少,这也自然影响了构式语法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对正式的、通常在教室中进行的二语教学来说,可以直接借鉴的研究成果更少。构式的应用研究受Goldberg等人的影响,往往以几个主要的特殊句式研究为主,如双及物构式、致使移动构式等。构式实际上可视为从语素、部分固定词语构式(partially filled words,如post-N、V-ing)到短语直至语篇的连续统②,两端研究的极少,而不论是小的单位如语素、语音、词汇,或是大到语篇,都是二语习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偏颇。
其次,多数的应用研究只注意到了某一构式的个体性,研究缺乏系统性。如Matsumoto(2008)通过对比日本二语学习者语料库与CNN Larry King Live Corpus分析了find一词后接补语和从句的情况,发现日本二语使用者的一些问题,提出应如何教授这一构式(针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有不同的建议)。该研究至多也只能解决一个构式的学习问题,而且针对的只是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至于如何推广到其它构式以及如何形成系统以供实际教学用或编写教材参考则并未提及。
此外,从目前构式语法在二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来看,主要的研究方法有语言对比、行为实验和语料库方法等。我们认为还可以应用更多的方法,如,神经语言学实验方法、话语研究的多模态分析、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方法等,还可以借鉴Goldberg实验范式3,即结合新奇意义和新奇构式的研究方法。
4. 应用研究对二语教学的启示
构式语法理论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二语教学视角、方法和启示。
首先,要同等重视所有语言现象的学习。二语教学不能只注重那些有规律的、“合乎语法的”采用“核心”语言现象,我们同样需要重视日常用语中大量存在的、并不一定能用通常语法规则解释的习语表达,因为熟悉它们也是掌握一门语言的重要一部分。Goldberg(2006)指出,这些具体的表达显然不是由普遍原则决定的,而且必须逐个学习掌握。她从基于例子的抽象概念(exemplar-based abstraction view)出发,指出语言学习必须从记忆具体的例子出发,然后再逐渐形成一般化的规律。Ellis(2002)也认为语言学习是范例学习,学习者流利使用语言的决定因素是存储在学习者大脑中的大量言语范例,而非抽象的语法规则。不论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学习都需要学习者在反复出现的语言材料之间建立联想并给予不断强化。“核心”语言现象大多有规律,出现频率高,因此较容易学会,而“边缘”的、较难掌握的语言项目则需要在输入基础上通过归纳习得(Goldberg 2006)。比如,习惯用语就属于“边缘”范畴,掌握更加困难,因此二语教学中更应充分发挥构式语法理论对高习语化(idiomaticity)构式的解释力,帮助学习者轻松掌握习惯用语。
其次,要遵循构式习得顺序与频率的规律。语言输入的形式和频率对语言学习起着决定作用,语言学习就是构式的学习,二语习得依赖于学习者语言使用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运用经验;从惯用语、低域格式(low-scope pattern)到构式的发展顺序(Ellis 2003)也是二语学习需遵循的习得顺序,因此,我们应按照习得的顺序进行教材编写和二语教学的安排。语言结构产生于特定语境中对语言的使用,语言发展是缓慢的、渐进的,从具体事物到更为抽象的语言图式,这一过程相当程度上是依靠特定构式的类型频率和示例频率,整体语言结构在学习者心理词库中的存储依赖示例频率,图式化依赖类型频率(Ellis & Cadierno 2009)。既然语言结构的存储和图式化都依赖高频(不论类型或示例频率),这说明语言输入必须达到一定频率才能储存和图式化,即语言学习需要反复接触和反复练习,这意味着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追求速成是不现实的。
第三,要注重一语和二语构式的对比分析。母语迁移对二语构式学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一语和二语构式相近的情况下,一语构式可以作为二语构式学习的基础,但即使是相似的构式也有细节上的差别,二语构式的习得也会由于一语的影响而受阻。与儿童语言学习不同,成人习得二语构式是在一语构式的基础上重新学习,因此二语教学中一语和二语构式的对比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成人学习外语也有其优势,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都已完善,适合采用构式主义的方法学习,对于两种语言的异同,既可以通过学习者自己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也可以通过显性的方式来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教学中增加一语和二语构式的对比分析能够帮助学习者克服母语的负面影响并发挥其正面的促进作用。
第四,要强调构式的系统教学。目前从构式视角对二语教学进行的研究大多只注意到构式的个体性,教学和研究缺乏系统性。我们提倡注重教授构式的多义性和层级性。一种语言的构式清单(inventory)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具有层级性的网络结构,一类句子是一种构式,正如语言中有无数的表达式一样,具体的构式实例是无限的,而且可以创新。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才是决定其性质的根本,不能把符号看成自治的独立实体,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系统的一部分。理解构式的意义需要把构式看作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比如,要理解或习得致使移动构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需要把它与其上级构式(如SVO句型)、同级(如双及物构式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以及下级构式(如动结构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联系起来理解和学习。二语构式的教学只有让学习者了解构式的整体状况才不至于见木不见林,而且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第五,要培养对构式的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目前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构式的语法结构形式的分析上,对构式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只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如Wee和Tan二人(2008)对So TIME构式(如Podcasts are so last year. E-mail is so five minutes ago. That’s so today.)的研究。他们指出该构式反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了全面理解这一构式应考虑社会-文化语境,这是具有普遍性的思路,由此作者提出构式语法与社会语言学结合的建议。在教学中除了讲述构式的语言结构,还应分析其文化内涵,强调语用知识的习得和运用,培养学习者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
附注:
① 在比较几种构式主义方法时Goldberg(2006)将Lakoff和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命名为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CCxG)。
② Goldberg对构式的定义和范围作了适当的调整,参见刘玉梅(2010)。
③ Goldberg和Casenhiser(2008)等称他们的实验方法为“新的实验范式”。
Cadierno, T. & P. Robinson. 2009. Language typology, task complex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2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for describing motion events.AnnualReviewofCognitiveLinguistics(7): 245-76.
Croft, W. 2007. Construction grammar [A]. In Dirk Geeraerts & Hubert Cuyckens (eds.).HandbookofCognitiveLinguis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63-508.
Croft, W. 2009. Constructions and generalizations [J].CognitiveLinguistics(20): 157-65.
Ellis, N. C. 2003. Constructions, chunking, and connectionism: The emergence of second language structure [A]. In C. J. Doughty & M. Long (eds.).TheHandbook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C]. Oxford: Blackwell. 33-68.
Ellis, N.C. 2006. 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SLA [J].AILAReview(19): 100-21.
Ellis, N. C. & T. Cadierno. 2009. Constructing a second language [J].AnnualReviewofCognitiveLinguistics(7): 111-39.
Ellis, N. C. & F. Ferreira-Junior. 2009a. Construction learning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J].TheModernLanguageJournal(3): 370-85.
Ellis, N. C. & F. Ferreira-Junior. 2009b. Constructions and their acquisition: Islands an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ir occupancy [J].AnnualReviewofCognitiveLinguistics(7): 187-220.
Goldberg, A. E. 1995.Constructions: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berg, A. E. 2002. Surface generalizations: An alternative to alternations [J].CognitiveLinguistics13 (4): 327-56.
Goldberg, A. E. 2003.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J].TrendsinCognitiveScience(7): 219-24.
Goldberg, A. E. 2006.ConstructionsatWork:Thenatureofgeneralizationin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berg, A. E. 2009a.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J].CognitiveLinguistics(20): 93-127.
Goldberg, A. E. 2009b. Constructions work [J].CognitiveLinguistics(20): 201-24.
Goldberg, A. E. & D. M. Casenhiser. 2008. Construction learnin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P. Robinson & N. C. Ellis (eds.).HandbookofCognitiveLinguisticsan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C]. New Pork/London: Routledge. 197-215.
Goldberg, A. E., D. M. Casenhiser. & N. Sethuraman. 2004. Learning argument structure generalizations [J].CognitiveLinguistics(15): 289-316.
Goldberg, A. E. D. M. Casenhiser. & T. White. 2007. Constructions as categories of language [J].NewIdeasinPsychology25(2): 70-86.
Gullberg, M. 2009. Reconstructing verb mean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J].AnnualReviewofCognitiveLinguistics(7):221-44.
Gries, S. T. & S. Wulff. 2009. Psycholinguistic and corpus-linguistic evidence for L2 constructions [J].AnnualReviewofCognitiveLinguistics(7): 163-86.
Matsumoto, N. 2008. Bridges betw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pedagogy: The case of corpora and their potential [J].SKYJournalofLinguistics(21): 125-53.
Sag, I. A. 2010. 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 an informal synopsis [A]. In H. Boas H. & I. A. Sag (eds.).Sign-BasedConstructionGrammar[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39-156.
Wee, L. & Y. Tan. 2008. That’s so last year! Constructions in a socio-cultural context [J].JournalofPragmatics(40): 2100-113.
董燕萍、梁君英.2002.走近构式语法[J].现代外语(2):142-152.
董燕萍、梁君英.2004.构式在中国学生英语句子意义理解中的作用[J].外语教学与研究(1):42-48.
黄莹.2006.Have使役结构的语义限制条件及其习得[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49-54.
胡学文.2007.中国学生英语双宾构式的习得——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外语研究(5):48-53.
纪云霞、林书武.2002.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构块式语法[J].外国语(5):16-22.
梁君英.2007.构式语法的新发展:语言的概括特质——Goldberg《工作中的构式》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1):72-75.
刘玉梅.2010.Goldberg认知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反思与前瞻[J].现代外语(1):202-09.
陆俭明2008.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142-51.
沈家煊.2000.说“偷”和“抢”[J].语言教学与研究(1):19-24.
唐承贤.2003.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迁移研究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37-42.
王海峰.2009.离合词离析形式AxB的构式特征[J].汉语学习(1):31-35.
严辰松. 2006.构式语法论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7-11.
张韧.2007.认知语法视野下的构式研究[J].外语研究(3):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