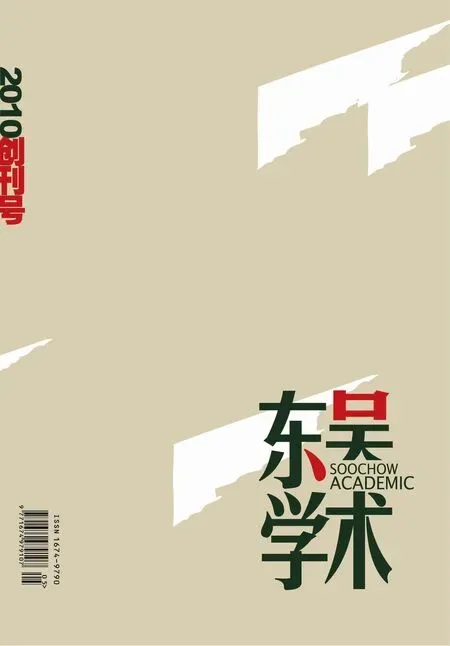天人合一的文化地标——从赵宧光寒山轶事折射太湖文化精华
2010-04-05徐伟荣
徐伟荣
苏州研究
天人合一的文化地标
——从赵宧光寒山轶事折射太湖文化精华
徐伟荣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换言之,人类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而且惟有文化的存续和发展才因此而有了历史的记忆和积淀。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沧海良田,物是人非,有许多文化会被湮没或毁灭,于是就会导致历史的缺失甚至断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太湖三山岛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以及在太湖流域相继发掘出来的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遗址,填补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一大空白,把长江流域的文明史至少上推了三千年,证实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吴文化、越文化等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可能同样也是由于文化的湮没抑或历史的缺失,到目前为止的区域文化研究,依然面临着不少疑团和迷茫。诸如,同样发源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和越文化,为什么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包容性和扩张性;吴文化又为什么会发生先是尚武后又崇文的变化;民间广为流传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因何而起又所谓何意等等,有的往往是语焉不详,更多的则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显然,这些文化遗传基因的信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损或丢失,这就导致了一个时期以来的区域文化研究尽管取得了重大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但再往前走似乎又是困难重重。
一本《赵宧光传》的问世,为晚明高士赵宧光掸去了厚重的历史尘埃,重要的是还在姑苏城外太湖之畔树起了一座醒目的文化地标。清帝乾隆六下江南六幸寒山决非幸致,这位“天授神权”的真龙天子,在孜孜追求“满汉一家”境界的同时,恐怕还在不断探索“天人合一”的真谛。他所御制的《寒山千尺雪》长诗的末句“雪香在梅色在水,其声乃在虚无间”,除了表达对名山高士的仰慕之心和留恋之意而外,也透露了内心深处的一些若明若暗的信息。这似乎为吴文化研究,其实也是为整个太湖文化的研究从边缘处切入理出了一个全新的线索。
“谢家青山”之谜及其南渡文化背景
据考证,赵宧光为宋太宗第八子赵元俨的后代。宋皇室南渡时,其一脉便流落到了姑苏太仓繁衍生息。赵宧光家学渊源,自幼苦读,“泛滥经书,贯穿百家,策名上庠”,本是个经天纬地的济世之才,不想乃父含元公临终一句遗言:“非谢家青山不葬”,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谢家青山”如同佛家箴言,一度引起了家人的迷茫和混乱,只有赵宧光心有灵犀,理解了个中深意。乃父作为皇室后裔,尽管早已改朝换代,其内心深处的家当仍然是赵家天下之家,空有报国之心,却是终身不第,临终之时不免有“壮志未酬,怒目苍天”之憾。故而,其口中之“谢家”,一可作辞世之解,二当有归隐之意。他是希望借其归葬之机为后代提供一方遁迹山林的风水宝地。
赵宧光终于在吴郡西部寻觅到了位于支硎山西、花山东、高景山南、天平山北那一块乃父所谓“谢家青山”、后命名为寒山的风水宝地,买山葬父,完成了父亲的临终遗愿。此后的三十余年,赵宧光便隐居于此,精研学问,广交朋友,教化山民。更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宧光穷其毕生之学识和精力,在这里叠山理水,筑园造林,阙者使全,没者使露,秽者使净,坡者为阿,宜高者防以堤阜,宜下者凿以陂沱。意欲其塞者,除蓁而石现;意欲其通者,疏脉而泉流。“稍加力役,百倍其功,果出天人,若非人力。”携妻率子,历经寒暑,栉风沐雨,胼手砥足,精心营造了目前尚可资查考的峰岗、奇石、坡道、石台、丘壑、泉池、楼阁以及摩崖石刻等融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景观百数十处,在方圆不过数平方公里的空间范围内形成了一块世所罕见的自然形胜的微缩图和人文历史的密集地。这应该就是在其身后百余年居然还能吸引贵为天子的乾隆名为巡幸实质瞻仰而六上寒山的魅力所在。
世界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发展往往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文化现象则更是如此。倘若赵宧光的寒山轶事仅只是历史的偶然,那么称之为文化地标就有哗众取宠夸大不实之嫌。事实上,只要稍稍对照吴地的历史文化就能发现,赵宧光现象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而其中最为直接和浅显的当为史称“宋室南渡”的背景。在外族入侵和兵连祸结的情况下,宋皇室被迫仓惶南渡,但由此而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毕竟是中国历史尤其是江南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无序的大转移过程当中,势必有一部分人,其中也不乏失势失意的达官显贵或文人墨客未曾到达目的地而中途择地隐居起来,贵为皇室成员的赵宧光的祖辈流落太仓只是其中的一例。因而,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南渡文化”现象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对于杭州周边以及更广泛地区的越文化而言其影响当然是主流的和直接的,并且隐隐然还带有皇家的霸气和张力;而对于以太湖周边地区为核心的吴文化的影响其实也不可小看了,只是相对而言属于支流的和间接的,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包容性,因而就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略。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太湖周边地区,特别是在洞庭东、西山等相对封闭地区的民居建筑、民风民俗、方言俚语等各个方面找到“南渡文化”所留下的鲜明印记。
这里有必要追溯到已经尽人皆知的 “泰伯奔吴”这段历史公案。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记载又极少,就有许多语焉不详之处,只能靠大胆而严谨的推理。诸如,“奔吴”一说就值得推敲,一个“奔”字至少给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长途跋涉,而且行程很急;二是目的地明确,直奔吴地。但当时尚无“句吴小国”,又何来“吴地”之一说?可见,这里应为“湖”解(吴语中至今吴、湖不分)。再如,泰伯、仲雍贵为王族,“奔吴”之时绝不可能形单影只,尽管已经无从查考,但完全可以推测,他们必然携带着一大批追随者和大量的生活和生产必需之物,所谓的北方文明也绝不是靠泰伯和仲雍的个体力量,而是靠了大批的无名英雄和大量的物质载体才得以广泛传播的。更重要的是,泰伯奔吴,脱离原先熟悉的生存环境以禅让王位是其本意,到完全陌生的“蛮荒之地”建立句吴小国却绝非初衷,这可能也是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必然结果。而从思想文化本质上分析,泰伯及其追随者们所带到江南的其实也只是一种隐逸者的文化,这与两千多年以后的“南渡文化”存在着许多颇有意义的相似之处。
从隐逸文化中透析“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
隐逸文化作为一种边缘化了的非主流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其实也是源远流长。孔老夫子就明确提出过“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隐”的主张,但同时也因把“隐”与“无道”联系在了一起,而从此给“隐”涂上了一抹消极的色彩;《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只是因为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被视为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形象。其实,世俗之人最终成为隐逸之士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此而形成的隐逸文化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的。纵观上下数千年,滚滚红尘中,历朝历代的隐逸之士,有惊世骇俗的愤世之隐,也有韬光养晦的蛰伏之隐、黯然失色的失意之隐;更有寄情山水的怡情之隐、待价而沽的钓饵之隐;还有眷恋名利尘缘未了却又心向山林志归禅道的亦僧亦俗、亦官亦隐。隐逸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道隐、心隐、酒隐,还有官场之隐、市肆之隐、壶天之隐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见,对于隐逸文化确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固然有悲观遁世等形形色色的消极色彩,却又始终闪耀着探索追求开拓创新的积极内核。
隐逸文化的积极内核,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释、道、儒三家之精华,但最终却未能自成一家,这恐怕也是其最终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隐逸文化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哲学基础和人格精神,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种有序的统一体,把自然当成最高的法则和规范,从而开启了隐逸文化对自然天趣的崇尚和追求以及一以贯之的田园情怀和山野情趣。在此过程中,又不断地吸收和丰富了儒家和佛家的人格精神和文化影响,如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则尽忠,退则思过”;佛家的“放舍心身,令其自在”,“无相、无念、无在”等等。虽然尚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体系,但已经体现出一种独到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在联系到赵宧光买山葬父及其叠山理水的世俗之人所无法理解的怪异行径,其有诗曰“云山常满目,破产不为贫”,我们就不难理解他那寄情山水、天人合一的至高思想境界和独特人格魅力了。
由隐逸文化到天人合一思想,似乎跳跃性大了一点,其实里面有着较强的思想基础和逻辑关系。“天人合一”,是老庄道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核,汉代董仲舒则将其发展成为儒家的基本哲学思想,所谓“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并因之而演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易经》有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曰阴阳,地道曰刚柔,人道曰仁义。是故,道家有“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万物与我为一”之说;佛家有“明镜本无台,何需勤擦拭”,“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之说;儒家则有“主客合一,天人合德”,“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而所有这一切,其实并非是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而是讨论人的精神价值的来源问题。《礼记·中庸》中说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提倡人只要恪守诚信之道,以诚待天,以至诚至信感天动地,就可与天一致,亦即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然则,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上述思想似乎已经很难对号入座,尤其是舍弃了人的精神本源问题,而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直接探讨人与自然的利害关系,就导致了舍本而求末,显得貌合而神离了。西方的工业化浪潮创造了超过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总和的现代文明,在此进程中对资源环境无度的索取和破坏,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大自然的惩罚之剑已经高悬于人类的头顶,但时至今日人们一方面仍然不肯放弃无穷的索取,另一方面却奢谈什么 “保护地球”、“回归自然”,甚至不断上演“天体”、“裸奔”之类的闹剧,其实与东方文明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相去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有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出现的本身就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因而,地球的毁灭是必然的,人类的自我毁灭当然也成了必然。诚然,人类本身应该是自然造化的产物,但人类一旦形成社会,即自然人进化成了社会人,也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就是在承认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客观关系之上,提倡一种超越自我的兼爱思想,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以博爱主义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起来,提倡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在尊重“自然的尊严”的前提之下赢得人类自身的尊严,在“天人相分”的客观条件下找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途径。
文明的对话:太湖文化基因的遗传变异及其精华
在区域文化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的冲突和碰撞是显而易见的,具有一定的阳刚性和扩张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非主流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则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具有隐蔽性和包容性,因而就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本文之所以把赵宧光的寒山轶事称之为文化地标,其实倒并不在于其本身有多么大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地标式的载体获得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并据此探索区域文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这样一种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直接对话的方式,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明大交融的大背景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即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有关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疑团和迷茫之处,亦可因此而找到答案或破解谜团的途径。
比如,关于吴地文化因何会出现先是尚武后又崇文的截然相反的转变?其实,由尚武而崇文,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由野蛮而文明的漫长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轨迹,只是吴地文化更具典型性罢了。远古时代,人弱自然强,北方水土丰肥,南方则洪水滔滔,水环境比之陆地环境更加复杂更多凶险,是故吴地先民多断发文身,强悍尚武。大禹治水只是确立了“由堵而疏”的治水理念和解决了大范围的洪水出路问题,至于流域性的水利建设则有待于后辈子孙的不懈努力;“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文明,同时也激化了封王争霸的纷扰,民心一度更加强悍,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而一直要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掌握了变水害为水利的规律和达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识,才有可能实现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而“南渡文化”现象则正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之中,并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前文提到的那些南渡人士,虽为“隐逸”,但能量不小,同时也仍然需生存和发展,于是舞文弄墨、务农经商各展所长,明清时期风靡一时的“钻天洞庭”,其中就不乏南渡人士的后人。而这一时期太湖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文化繁荣,乃至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摇篮,与这样一个转变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逻辑关系的。
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尽管出于何典确已很难查考,但很显然的应该是泛指整个太湖地区。而所谓的“天堂”,又显然不是指纯粹的“原生态”的原始风光之美——否则,如可可西里等无人区才更有资格称为“天堂”——而应该是指被人格化了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与文化相映生辉的最适宜于人居的天堂。就此角度讲,这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毫无疑问应该是最有资格享此殊荣的。这里且不去赘述这里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四季分明的太湖小气候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还有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等等基础性条件,重要的是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经过吴地先民祖祖辈辈不懈的努力和探求,加之各个历史时期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所形成的“和合文化”——寒山、拾得其实也是隐逸文化的代表,而实际上应该是太湖文化的精华所在——即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兼爱精神已经把这里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历史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才是“天堂”的本质内涵所在。
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风靡全球并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共十七大也将之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相提并论写进了党的决议。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并未能囊括生态的全部内容,人类的生存环境关涉到生物与非生物、物质与非物质的全部关系。生态文明与精神、物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文明也并非平列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容的关系乃至覆盖的关系,它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这正好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的人格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兼爱思想,同时也检讨了现代文明中物欲横流的人格缺陷和“战天斗地”的畸态文化。
在这样一个历史潮流和文化背景之下,太湖地区的历史积淀及其子民身上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了。早在“十五”期间,正值工业化城市化大开发大建设的时期,位于古城西部和太湖之滨的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出了“生态立区”的行动纲领并积极付诸实践,这在当时来看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恰恰正是传统文化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弘扬。寒山赵宧光这座一度被历史所淹没的文化地标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而整个环太湖区域也将随之而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加深广意义的文化地标。
徐荣伟,苏州市政协调研员、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江南研究院院长、苏州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