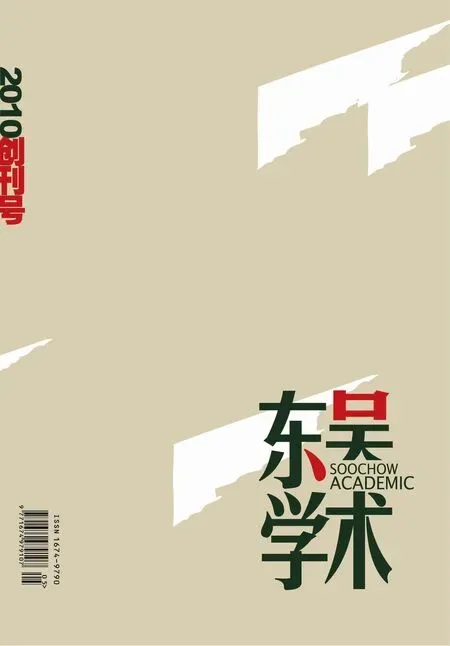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战略转型
2010-04-05潘家华
潘家华
经济与政治
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战略转型
潘家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进程跃入快车道,规模扩张可谓史无前例。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发展品质亟需提升,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健康、稳定、均衡发展。“十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规模扩张的制约和品质提升的压力日渐凸显。展望“十二五”的城镇化,无论是自然演化还是宏观调控,中国必将进入一个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整体转型时期。
一、强劲的经济增长助推城市规模扩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在百分之九以上的年增长率,非农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载体。过去三十年,中国城镇化年均提高幅度接近一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九点七二增加到二○○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九。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一速率和水平并不算高。①例如:日本1950-1955年的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3.8个百分点,韩国1965-1970年年均提高2.08个百分点。罗志刚:《对城市化速度及相关研究的讨论》,《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6期,第60-66页。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位置。从每年新增的城镇人口数量上看,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五年,平均每年超过一千万;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每年超过二○○○万;二○○六年至二○○九年,每年大约一千五百万。②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二○○九年,中国城镇人口总量已经达到六点二亿,为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比欧盟二十七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四分之一。③2007年,美国人口总数3.02亿,欧盟27国人口总数4.96亿。尤其是通过“十一五”期间“突击性”的大规模、高速度建设,城镇用地规模和城镇道路体系、房屋建筑、工业得到超常规发展。上海的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经达到工业革命发源地的 “世界城市”伦敦的规模。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城市硬件设施在许多方面似乎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二、城镇化进程出现明显失衡
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存在不平衡,而“十一五”的快速规模扩张,使得这种失衡呈加剧态势。
首先,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地域空间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对于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速度明显滞后。一九九六-二○○六年,中国城镇化人口年均增长百分之四点四六,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百分之五点二三,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增百分之五点二七。如果考虑农民工的不完全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率的情况更加突出。中国非农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降至二○○九年的百分之十点六,但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仍然大大超过百分之五十。二○○九年底,城镇就业人口只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第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中国工业产品产能过剩。因为农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其消费仍然以农村模式为主,消费理念和能力严重偏低,难以匹配工业产能的扩张,只能过分依赖出口,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妨碍城市的健康运行。根据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关系的一般模式,城市化水平接近百分之五十时,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百分之七十七点二,非农产业就业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但实际上,我国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在二○○九年已占近百分之九十。城市化水平滞后工业化水平十五个百分点。如果按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的对应关系,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八个百分点。①程开明:《当前我国城市化速度的争论与审视》,《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第1-6页。
第三,城市社会融合程度偏低。在全国六点二亿城市人口中,农民工数量达到二点三亿。而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边缘,就业、收入、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被城市化。例如,其子女要返回原籍参加高考,多数就业岗位、低保等要求本地户籍。北京市廉租房和经适房管理办法规定,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房子已成为两极分化的分水岭,农民工被排斥在外。②周天勇:《户籍拉大收入差距》,《新京报》2010年6月5日。
第四,城镇化发展地域不平衡。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快,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地处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二○○八年的城镇化水平已达百分之六十三点四;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江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十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五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则要低十-二十个百分点。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城镇化水平只有百分之三十六,西部的甘肃、云南不足百分之三十五,贵州低于百分之三十,西藏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点六。东部地区技术先进、能效水平高。平均每万元工业增加值,东部地区所需能源消费只有中部地区的一半、西部一些省区的四分之一。例如,二○○八年上海平均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只需消耗能源零点九六吨标煤;江西、安徽、湖北在二吨左右;内蒙、甘肃、贵州则超过四吨。二○○八年,东部地区每百户居民汽车拥有量达到十四点四辆,而中部地区只有四点一辆,东北地区三点八辆。
第五,城乡差距依然在扩大。尽管“十一五”期间,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大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家电下乡”,农村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中国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二○○八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十七点三万亿,其中城镇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一,农户只占百分之三点四。农户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只有城镇房地产开发形成资产的百分之十九点一。二○○九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点三倍。城镇居民所享用的教育补贴是农村居民的二倍,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种隐性补贴甚至高于农村居民所获得的人均收入水平。③李实:《城镇居民补贴甚至高于农民收入》,《新京报》2010年6月5日。
三、体制因素强化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城镇化出现区域分化失衡的原因涉及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体制等诸多方面。从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上讲,东部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自然生产力高,承载力强,而西部地区的高原地貌和干旱缺雨的气候条件,生物自然生产力十分有限,正常社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刚性制约。西部地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但受自然气候条件限制,产业链条延伸有限,多限于简单采掘,加工转换和服务业发展难以深化拓展,城市发展缺乏自然条件尤其是水资源的支撑。从经济区位上看,西部处于内陆,与国际市场和国内生产、消费中心空间距离远,交通运输成本高,因而缺乏竞争优势,城市扩张经济源动力较为有限。从社会文化条件上看,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比较开放、竞争意识较强。从体制上看,中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资源的分配、使用具有比较高的行政色彩,特大城市的政治、文化、教育资源显然首都优于区域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优于非省会城市和中小城市。由于中国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力强,经济对政治的依附性较强,因而经济活动必然在大中城市、省会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政治、文化、教育资源集中的特大城市表现出“极化”特征。北京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城市定位表明,北京不宜也不必“以工致富”,但传统上高耗能、高耗水的钢铁化工企业,依旧布局北京。北京大中型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不多,但超大规模的企业总部多集聚北京,形成中国特色的“总部经济”,更准确的讲,是“首都经济”。不仅如此,在一个城市内部,资源也相对集中,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核心区,而外围城市区域则处于相对弱化的地位。例如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北京,每千人汽车拥有量全国第一,四环路以内交通拥堵不堪,但在五环以外,道路交通状况较为宽松。
中国城市社会分化失衡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惯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农业资助工业,农村资助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化、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出现变化,不再是产品剪刀差,而是土地利用方式转换的巨额价差和农民工的低价工资红利。城市和工业需要占用农村用地,对土地占用的补偿多采用行政性的计划经济补偿模式,经城市地方政府一转手,用于城市商业、工业和房地产开发,地价决定机制则采用“市场经济”模式,“拍卖”价格是补偿额的数百乃至数万倍。没有合理的经济补偿,失地农民不可能有经济能力主动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在体制上没有被接纳进入城市社会主流。中国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成为可能,但这种制度的延续使农民的身份标签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人在城市,就业在城市,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处在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等方面,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工资从改革开放到“十一五”中后期,长期停留在每月千元左右甚至更低,一年的劳动所得难以在所在城市购买一个平方米的商品房。经济增长的红利没有惠及给这些创造财富的底层工人,东部地区用工荒频现。农民工群体在总体上教育程度偏低,在劳动技能上竞争力不强,这是农民工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个表象原因,而农民工占用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资源与市民不匹配才是真正原因。“十一五”期间,天价地王频现,不断刷新于一线和部分经济发达的东部都会城市,处于高位,农民工维权缺乏制度性保障。
四、城市从外延扩张向品质提升的转型势在必然
展望“十二五”中国城镇化进程,必将出现并加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转型。首先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趋缓,已经接近或即将达到峰值。二○○九年中国粗钢产量已达五点七亿吨,占全球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八,水泥产量达到十六点五亿吨,占全球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中国的家用电器和许多主要产品产能均已达到或接近饱和,有的已经出现过剩。就发达国家经验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化的外延扩张趋于减缓甚至终止。目前,中国工业化快速扩张的动力已趋弱,因而对城市空间扩张的拉动力已经有限并将愈来愈弱。第二,城市可用土地资源也已接近极限。中国粮食安全需要保持耕地红线。中国必须要保留自然生产力高的土地。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可用土地已开发殆尽,这些城市即使想外延扩张,也没有土地空间。这样,城市发展只能被动转型。第三,中国城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城市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城市服务功能增强,因而城市发展整体转型的经济阻力得到了弱化。第四,中国城市社会矛盾成为中国城市整体转型的内在动因,收入差距拉大表明收入调整与社会保障已迫在眉睫,两亿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处于边缘化境地,显然是一个社会稳定难题。只有城市发展整体转型,才能不断减少由于社会资源的极化配置产生的区域和城乡差异。第五,城市资源保障、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也要求城市发展从粗放式向集约转型,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