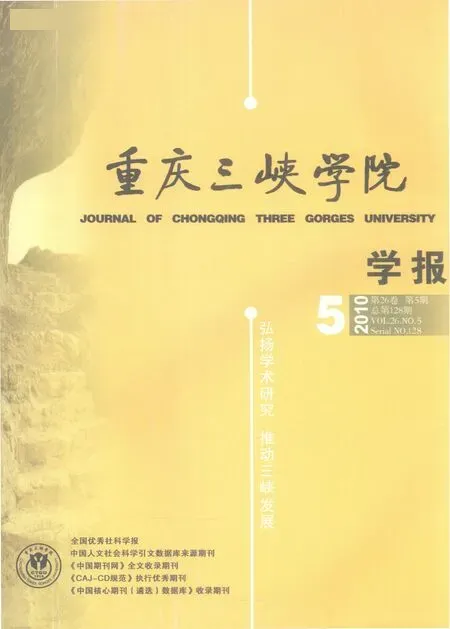论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的切身性
——从“身份认同”角度
2010-04-04俊郑宗荣
李 俊郑宗荣
(1,2.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1.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 610068)
论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的切身性
——从“身份认同”角度
李 俊1郑宗荣2
(1,2.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1.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成都 610068)
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中,不乏身为作家、城市人、病人、农民、失落文人等诸种身份的认同以及认同过程中各种身份的彼此错位;诸种身份认同以及认同中的各种错位使得贾平凹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叙事具有直抵作家个体生存经验的切身性质;小说叙事的切身性具有独特的价值建构意义。
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个体生存经验;身份认同
小说叙事作为对现实生活的精神创造,作为特殊形态的文化,它应该“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的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5)因此,小说叙事就不应该局限于一种外在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支配,给接受者展示一种在此种观念支配下的模式化生活图景,小说叙事应该抵达作为现实参与者与体验者的个体生存经验事实,并叙述这样的事实,而这样的叙述,作为话语的虚构,就自然而然地让叙述话语与个体生存体验具有深刻的相切性质。
正因其如此,便不乏好事者将贾平凹的生病作为他们研究其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视角。应该说,这种视角的切入不无根据。因为贾平凹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写作正是在他感到鬼魅狰狞的40岁时开始的,对他来说,这个时候最大的鬼魅应该是乙肝不愈的生存体验:“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心;吃过的大包小包的中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在谈到《废都》及以后的创作体验时,作者是这样描述当时置身病痛的心境的:“作完一个《废都》,长时间去生病了,小说已不能再写,就一边守着火炉熬药一边咀嚼些平常人的平常日子,像牛在反刍……”,“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作不是一种灰色和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越。走出激愤,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幽默由此而生。爱情的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驭,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意象,这合于我的心境。”[2](533)这部作品除了那头睿智的哲学牛患了肝病之外,并没写到病人,倒是这头奶牛颇像作家自况,在病毒浸染躯体之后,推己及彼,从文人的聚会、文人的心态、文人的行状以及社会上的种种斑驳陆离的文化现象等等,看社会人生的种种病态,体悟文人如何由名人成为闲人、又成为病人、最终成为废人的过程,这种叙写体悟出自作家的真实经验,其警策力量无疑是巨大的。除《废都》之外,关于“病”的类似感受散见于作家的各种文字,几乎不可胜数。于是我们在贾氏的作品中,便不难找到对于各种患病与治病的描写。《白夜》故事构成的内在动力是祝一鹤生病导致夜郎城市生存困境的生成,而那个不问世间喧嚣只管诗意栖居的虞白,实际上也是因病困顿家中而无奈于世事,与汪宽囿固于不合时代潮流的雷锋精神相应的是愈来愈严重并最终角质化的牛皮癣;《土门》中所供奉的神是无师自通的治肝高手云林爷,仁厚村财源滚滚的直接原因是众多的外乡人患了肝病,融入城市中的老冉是性无能而且兼有龌龊的痔疮;《高老庄》中,任潮涨潮落、云卷云舒,不问世事的是神医蔡老先生,标志这个村庄唯一清醒的石头却没有一双健康的支撑肌体的脚,引起乡间火拼的导火线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博弈,但群体心理的唤起却是工业化带来的生态恶化,以及生态恶化导致的村民身体上的癌变。
也有人以贾平凹出身农村、且身矮貌拙生发出来的对于城市的自卑心理为视角研究其1990年代的长篇小说,这同样不无道理。因为作家本人对这样的自卑心理的存在也并不讳言,但在这里我并不想强调作家这种自卑心理是否存在,因为我宁愿相信作家在这几部长篇中细腻地展现了这样的尴尬:秉承了农村的文化因子,接受了高等教育,又终于成为了万人仰慕且能够站在云端俯视芸芸众生的文化精英,栖居于城市,又割舍不下农村,因此集各种身份于一身后,在身份认同上时时错位。贾平凹1990年代前的小说,作家的笔触大都伸向农村,1983年开始的对商州农村生活的真切体验,加上过往的来自农村的童年经验,不可磨灭地在其印象中深刻起来,并溢于笔端。自《浮躁》开始,置于城市的现实身份与“我是农民”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开始在意识中呈现,于是就有了金狗带着农村印记的城市闯荡。而真正让作家感到农民与城里人这两种身份认同错位的应该是1990年代,在这一时期,作家真正产生了写作城市的冲动,“我试图真正地写一下都市生活,阐述古城里的一种‘废都意识’,内容是写古城里一些当代人的生活。我常常想,《金瓶梅》、《红楼梦》也写的是城市生活,但是现代人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为什么总没有这两部作品的那一种味儿呢?当然,封建时期的城市毕竟和现在的城市不是一回事儿,但如果能表现出现在城市人的生活,也能传达出像古典名著中的那一种味儿,那就太好了。基于这种考虑,正是为要寻找到这样一种感觉,我寻了几年,迟迟没有动笔,现在感受到,在写作的过程中,心里很畅美。”[3](122)在这样的冲动下,始有《废都》的写作,但正是这部作品的写作,才让我们看到作家在兼具农民、城里人身份时,那种经常处于身份错位状态中的尴尬体验。比如在《废都》的叙事中,作家一方面在叙事中让人物、环境带上浓郁的城市标记,如在投机钻营的周敏、投怀送抱的唐宛儿、柳月诸等人物身上,投射进极力融入城市的企图与热望,来表现带着自身印记的对于城市的某种认同。另一方面,则在他们的身上及置身的环境中烙下乡村的记忆,比如作家刻意设置的奶牛与埙乐,便使小说时时流露出浓郁的乡土情感和乡土精神,埙乐让这座城市的上空始终萦绕着土声土气,而那头睿智的哲学牛则对终南山的自然风光留恋不已,它们代表着乡村文明的两个极致与废都的城市文明相参照,显示了作家的苦心经营,流露了作家情系乡土的内在真诚。这种真诚在对照融入城市的期求时,不仅传达了转型期城市化中人们的复杂心态,而且也传达了作家身份认同错位的现实处境。在《白夜》中,也不乏这样的处境展示。比如来自农村的夜郎、颜铭,爱极了城市,不惜以攀附权贵、同城里人联姻、整形美容等方式融入城市,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眷恋着农村纯洁的亲情、温馨的人际,所以当夜郎在追求受挫时,总是不忘来到城墙,烧一叠冥纸,追思长眠在乡野的父亲,并一如《废都》中周敏,用鬼魅般的埙,吹进西京的夜色,表达对乡村的无限眷念。另如汪宽,也在被城市反讽了其兢兢业业践行的道德之后,重新回到乡间,去寻找自身的意义。稍后的《土门》、《高老庄》,则更是显示了作家类似的生活镜像,因为《土门》直接将一个固守、保护传统的村庄推到城市的面前,刻画了一幅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心态的浮世绘,《高老庄》似乎带有对这种人生经验进行总结的意味,全书的构成是以来自农村的教授返乡——回城为结构框架的。
另外,在这四篇小说中,文人心态的表露也是一览无余的。对于世纪之初的贾平凹来说,其文人处境的特殊性正在于:在遭逢了一个物质至上、精神沦落的社会现实之后,他不得不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自身价值失重、被社会冷落、几乎变成废物的薄命文人的无奈;在幸运地碰到一个市场化背景之后,文学作为商业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又使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把握被人捧场、包装、成名、赚钱、得到实惠的机遇。特殊的处境决定了贾平凹四十岁后的文人心理状态是十分复杂的。人文价值的衰落和物质欲望席卷一切的裹挟,不能不使苦苦追求对现实进行精神超越的贾平凹在心灵深处笼罩上了一层阴霾。一方面是参与商品大潮,一方面是让文学承担历史的、当代的精神价值。作为一个一直在培育、唤起并张扬自己主体意识的文人来说,贾平凹便被置于这两者之间。《废都》之类作品的市场化写作与出版发行的商业炒作表明了作家对商品大潮驱动下的物欲的靠近,但“安妥灵魂”的写作命意又表现出他对物质的拒绝,这样的靠近与拒绝我们可以从其作品中叙述声音的复调表达中见出。比如庄之蝶,就作者命意来讲,是要借这个人物的形骸来批判知识分子用情欲的放纵弥补精神的失落的,但在作家对庄之蝶情欲放纵的不乏品味欣赏的笔触中,我们分明看到其中有因物质条件优裕而纵情享乐的现代商品消费意识。《白夜》中的夜郎,在一次次被城市戏弄也一次次对城市的戏弄中,看惯了城市中人在物质至上的名利场中的可笑嘴脸,但隐藏在其下的,却是融入名利场的野心。《白夜》中虞白的设置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因为祖产的遗馈,虞白在无所事事中并不缺少物质方面的优厚享受,作为一个精神探索者,与《废都》中的庄之蝶在拜物教诱惑下的精神沦落不同的是,虞白并不沉溺于物欲之中,她依然保持了精神的高标,在优厚的生活之外,她更钟情于在精神对接层次上的古典恋爱,以及审美前提下对于剪纸、古琴、古玩的痴迷,在物质的丰裕与剪纸、艺术、古琴之间,显示的正是作家想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转型期文人的心态。《土门》中的成义、梅梅的形象同样显现了作家复杂的文人心态。成义、梅梅一方面钟情于传统宗教、制度、音乐、各式各样的旧式床,并以此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但他们在固守传统时却采用了现代商品经济最流行的金钱法则,开办大药房,取得巨大收益,并以金钱开路,打广告、拉关系,力图在金钱的魔力下取得仁厚村的保全。尽管这样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但却显示了作家在商品经济背景下试图贯通传统与现在,并在这二者间找到妥协的文人心态。《高老庄》中这种心态的显现同样是复杂的,如果说前几部小说更多的批判是给了商品大潮中物质至上带给人们的喧嚣,那么在《高老庄》中,作家则主要是对传统文化带给现代人的精神销蚀作了深层的审视。子路这个城里的教授,回到乡间后,做爱不洗身子也不制造前奏情趣,睡觉前不刷牙,还偏好就地大小便并因此就地浇庄稼,而且还和以前认为没有精神追求的前妻保持暧昧的关系……置身于高老庄的是非之中,子路终于看到了自己被销蚀的危险处境,于是决定离开,以表示对这种传统的决绝,但作家在面对这样的决绝时则显得有些犹豫,因为他对传统有着深深的眷念,于是,一个能够让高老庄男人都仰视的人高马大、高鼻深目的城里女人——西夏便留了下来,这不仅包含了作家用异质文化改造传统的希冀,使转型期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人心态毕现无遗。
因此,当我们一次次轻而易举地在作家的叙事话语中找到诸如疾病患者、农村人、城市人、畅销书作家、偏好传统审美情趣的文人等现实中的贾平凹诸种镜像之后,我们发现,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较之以前的作品,其重大的转变正来自于对话语切身性质的赋予:注重讲述个人生存状况与生存经验,让话语直达这种经验。这种个体化的书写,正表现了作家对自己主体意识的张扬,对自我心灵的贴近,对外在意识形态的悬置。对象直抵经验并贴近内心,文学叙事的真实性、可靠性便因此而生,这也正是其叙事价值建构的重要前提。
[1][法]维克多•埃尔著.康新文等译.文化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贾平凹.后记[M]//废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3]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新玲)
Abstract:There are various different identities as writer, city folk, patient, farmer, unsuccessful literal man etc. created in the novels in the 1990s by Jia Pingwa, and in the proc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those identities are misplaced each other.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identity misplacement displays that Jia Pingwa’s narrative in this period shows writer’s own living experience, which has unique significance of value construction.
Key words:Jia Pingwa; novels in the 1990s; narrative; personal living experience; identity
On the Author’s First-hand Experience Features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s in the 1990s by Jia Pingw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LI Jun1ZHENG Zong-rong2
(1,2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404100, Chongqing, China, 1,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Sichuan)
I206.7
A
1009-8135(2010)05-0090-03
2010-05-21
李 俊(1971-),男,重庆开县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
郑宗荣(1975-),女,重庆万州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