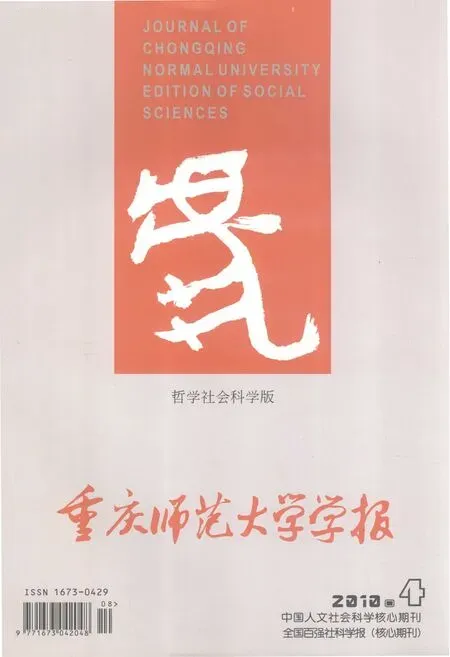巴蜀“竹枝”的酒香
2010-04-04王子今
王 子 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巴蜀“竹枝”的酒香
王 子 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历代竹枝词因包涵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被看作社会史料的宝库。发掘其中有关酒的生产与消费的资料,对于酿酒史和饮酒史,以及相关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的回顾和总结,是有积极意义的。巴蜀竹枝词有体现酒与节令礼俗的关系、酒与休闲生活的关系的篇章。农家自酿酒在民间消费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城乡“酒市”的繁荣,也表现了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竹枝词中也有反映酿酒业之产业史的内容。“载酒”舟船浮江远行,则体现了商品酒的流通以及巴蜀酒业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
巴蜀;竹枝词;酒;酒业;酒船
竹枝词是来自民间的诗歌形式。唐代诗人开始吸收这种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生动清新的因素,用于诗歌创作,并且多仿作“竹枝”,使得诗坛注入了新的生力。此后历代诗作都包括大量的竹枝词。世态和时风、乡俗和民情,都因此得以记录。竹枝词因包涵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被看作社会史料的宝库。[1][2]
巴地是竹枝词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蜀地亦得竹枝词的早期传播。清嘉庆举人、成都人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所谓“莫道北人不识唱,‘竹枝’原是蜀中词”[3](第3册1845),正体现了这一文化史的重要现象。巴蜀“竹枝”遗存所透露的历史文化迹象,已经为学界所关注。[4][5][6][7]发掘其中有关酒的生产与消费的资料,对于酿酒史和饮酒史,以及相关文化演进历程的回顾和总结,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酒与节令秩序
清代梁山 (今重庆梁平)人涂宁舒《竹枝词二十四首》题下附注“每月二首”,最后二首应是说腊月风俗。前者说到年节的“酒”:“美酒肥豚一岁终,年货安排处处同。”看来“美酒”在“年货”中是最为重要的。最后一首言及家人团聚“守岁”时倾杯情形:“烛热香温腊鼓催,紫薇灯照望春台。今宵守岁陈新酒,按月同倾十二杯。”(《高梁耆英集》)[3](第2册1226-1227)清人程伯銮《桂溪四时竹枝词》记述了同一风习:“爆竹声多向晓催,一家人上祖茔来。拜年比户陈春酒,按月宜消十二杯。”[3](第3册P1869)一说“守岁”,一说“拜年”;一说“陈新酒”,一说“陈春酒”。然而都是“按月”饮尽“十二杯”。
清人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中《拜年》题下有十首诗,其九说到“酒盘”:“茶点才过又酒盘,共连摆饭是三餐。腌鸡腊肉尝俱变,尚说连朝胃不安。”[3](第5册3916)清乾隆举人、双流人刘沅的《蜀中新年竹枝词》,也涉及“年酒”使年节热烈气氛得以升温的意义:“整顿冠裳色色新,年糕年酒馈亲邻。”而新年重要礼仪祈神祝天也要用酒:“只鸡尊酒算奇珍,祭罢财神又上神。”又如:“愁听长街击磬声,惊心岁短倍伤情。可怜案上无杯酒,也向神天祝太平。”这里是说“贫人”情形,一般人家应当都不能轻易改变以酒祀神的礼俗。
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另一首则是描写元宵节热闹情势:“月团圞处贺元宵,花满灯棚酒满瓢。不费千金闲觅得,夜深还上七星桥。”[3](第2册1517-1520)清道光进士、达县人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写道:“上元灯火舞龙狮,锣鼓喧阗爆竹随。村酒几瓯须立饮,看他会首醉归时。”[3](第3册2192)“灯火”、“锣鼓”、“爆竹”、“村酒”,同样的热烈场面,也有同样的欢情和醉意。又如天全人杨甲秀《徙阳竹枝词》:“六街三鼓息喧阗,到耳声高欲废眠。知是猜余灯谜后,围炉酌酒复猜拳。”[3](第4册2664)在街市已“息喧阗”时,所谓“围炉酌酒”,大概也是“闹市后”的接续节目。
与前引“爆竹声多向晓催,一家人上祖茔来”情形相同,南溪也有岁首上坟的风习,届时往往也得一醉。清道光时南溪人万清涪《南广竹枝词三十六首》对这一情景有所记述:“岁头珍重新年坟,壶榼归来独醉醺。不比清明携内里,淡红香白一群群。”作者原注:“俗以岁首登墓,为‘上新年坟’。清明则携眷同往。士人谓妻妾为‘内里’。”[3](第3册2150)
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说到“春酒”:“年景花开兰草香,家家春酒帖来忙。无多腊味有春饼,冬笋椿芽间韭黄。”[3](第3册1834,1836)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有文句颇为相似的一首,题《请春酒》:“年景花开兰草香,家家春酒客来忙。腌鸡腊肉尝俱遍,冬笋春芽并韭黄。”[3](第5册3914)“请春酒”,大概是民间共同的春节时尚。清人杨甲秀《徙阳竹枝词》关于“春游”,则有“清凉古刹景清幽”、“提壶日日唤春游”诗句。[3](第4册2668)所谓“提壶”者,推想应当是酒壶。
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说到有一种鸟,名为“清明酒醉”:“惊闺页响刚临镜,卖花声过正把梳。淘井挖泥街上唤。‘清明酒醉’树间呼。”原注:“春时有鸟呼‘清明酒醉’四字,第二声即呼‘清明酒醉死’五字,其音清越可听。”[3](第3册1836)鸟得名“清明酒醉”,自然也是清明时节民间饮酒风习的一种反映。清明扫墓备酒,见于清人山春的《灌阳竹枝词》:“鹃声不住北门悲,三月清明上冢时。最是官山人似海,男携酒榼女携儿。”[3](第5册3947)清人陈在镤《合阳竹枝词》:“清明风景数城西,上冢人多路欲迷。落日泉台一杯酒,几家欢笑几家啼。”[3](第5册3963)也记叙了酒和“清明风景”的关系。新繁 (今四川郫县东北)人吕燮枢《渝州竹枝词八首》写道:“春来扫墓踏青行,翠翠红红尽出城。多少少年游侠子,纸钱灰里醉清明。”[3](第2册1693)清明,事实上成为青年男女春季郊游的节日,“少年”一“醉”,也是欢娱的重要内容。
南溪有三月十二日“设祭城隍庙”的传统,也设酒席相祝。万清涪《南广竹枝词》:“阑干十二数芳辰,可与轩中聚众宾。酒祝宋公筵四座,书差绅士并街民。”作者原注:“可与轩、宋公祠,三月十二日额办酒筵四席,设祭城隍庙。值年首事,无论书差、士民一体同席。”[3](第3册2151)
端午用酒,也是历史悠久的风习。宋代诗人范成大《夔州竹枝歌》写道:“五月五日岚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云安酒浓麹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回。”[3](第1册16)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写道:“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3](第3册1838)其中“艾叶菖蒲烧酒香”一句,反映了“酒”在端午节庆时的作用。又如灌县人王昌南《老人村竹枝百咏》中的诗句:“士女儿童底事忙,为游百病乘端阳。沿街饮罢蒲觞酒,约伴偕行好下乡。”[3](第5册3944)可知“菖蒲烧酒”又称“蒲觞酒”。清末四川资中人卢寿仁《资阳端午竹枝词》也写道:“酒后雄黄满脸摩,东门争出小阿哥。双双粽子来提起,准备今年走外婆。”[3](第5册3916)前引“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此处则说“酒后雄黄满脸摩”,强调了“酒”的功用。而“雄黄酒”之说,见于涂宁舒《竹枝词二十四首》。
万清涪《南广竹枝词》记述了“中元各家陈酒祀祖”礼俗:“截边正路纸分行,码数买来不计张。备着中元烧袱用,酒兼家酿饭家常。”作者原注:“‘截边’,黄表纸也。‘正路纸’出夹江,一码约四百张。中元各家陈酒祀祖,尽先买纸作袱。”[3](第3册2153)清末成都人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中《七月》一首应是写述鬼节风习:“纸钱风起月昏黄,儿女庭前罗酒浆。自是金银魄力大,阴曹人世两心香。”
《锦城竹枝词百咏》题《八月》则记述中秋节令民俗,也说到饮酒情节:“茶半温时酒半酣,家人夜饮作清淡。儿童月饼才分得,又插香球舞气柑。”(作者原注:“成俗中秋夜,儿童以神香插满气柑而舞,名曰‘流星香球’。”)[3](第4册3456-3457)
有的地方每年八月二十七日行“学师”“瓜代”“签换”仪式,需“设席”备酒。佃户纳租事宜,也往往在这时“招集”通告。这就是万清涪《南广竹枝词》所谓“每年庚子陈经日,瓜代惟延酒一尊。”作者原注:“每年八月二十七日设席,延学师签换,首事并招集纳租各佃。”[3](第3册2153)
重阳饮酒民俗,亦见于涂宁舒《竹枝词二十四首》:“无端风雨满江皋,黄菊花开引兴豪。烧酒酿成蔬菜熟,相携明日好登高。”[3](第2册1226)清人王履吉《合阳竹枝词》:“满城风雨菊花黄,酒熟家家扑鼻香。惟有诗人消受得,白华山上醉重阳”[3](第5册3961),也描写了“菊花黄”时家家户户“醉重阳”的情形。又颜汝玉《建城竹枝词》:“登高佳节菊花香,落帽风来扑面凉。旧酿已空新稻熟,家家造酒趁重阳。”[3](第4册3248)所谓“旧酿已空”,可知用酒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二、酒与礼俗传统
在民间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礼俗生活中,酒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共同作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神异饮料。元代诗人孙嵩《竹枝歌八首》中“荒祠歌舞与招魂”、“万里还乡酾酒樽”,以及“黄牛庙前鸦鹳棲,黄茅宫外枭鵩啼;估客酹神巫妪醉,青林日转风凄凄”(《千首宋人绝句》卷七引作“黄陵庙前鸦鹳棲,黄陵宫外枭鵩啼”,《宋诗纪事》卷八 ○引作“黄牛庙前鸦鹳棲,黄魔宫外枭鸣啼”。)诗句,[3](第1册24)体现了“神”“祠”和“酒”、“巫妪”和“酒”的关系。清人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写道:“当年后主信神巫,近日端公即是徒。锣鼓喧天打保福,包头斟酒会招呼。”[3](第3册1889)在“神巫”表演的节目中,“酒”是营造神秘气氛的重要条件。
婚礼用酒表现喜庆和欢乐,是天经地义的事。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玻璃彩轿到华堂,扶得新娘进洞房。挑去盖头饮合巹,闹房直到大天光。”[3](第3册1890)“合卺”是借“酒”完成的表现夫妻情意长久的庄严的宣誓。酒同时又是不可或缺的增益婚礼喜庆气氛的强化剂。清时曾经三任绵州知府,主持重修同治《绵府志》的文棨,在《左绵竹枝词》中描写婚礼热烈情景:“花烛辉煌待席开,争夸女貌与郎才。支宾先向门前坐,让客须倾三百杯。”[3](第4册3035)清乾隆进士、曾知南溪的翁霪霖在《南广杂咏二十四首》中也写道:“压领村间各斗妆,朱陈门户说相当。儿家斟酒双双对,不是平常并长娘。”作者原注:“女人以银串挂脰,名曰‘压领’。娶亲,谓‘斟酒’。抱媳,则谓之‘并长娘’。”[3](第2册1369)所谓“娶亲,谓‘斟酒’”,反映婚礼必须酒宴的情形。而“并长娘”风习体现的童养媳民俗形式,也是社会史研究者不宜忽视的。清康熙年间任成都府督捕通判的陈祥裔著有《蜀都碎事》。所收《竹枝词二首》写道:“邻姑昨夜嫁儿家,会宴今朝斗丽华。咂酒醉归忘路远,布裙牛背夕阳斜。”[3](第1册855)诗句体现了民家婚礼亦往往不免一醉的情形。
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彩亭锣鼓送南瓜,送到人家一片哗。吃罢酒宴才散去,明年果否得娇娃?”[3](第3册1890)所谓“彩亭锣鼓送南瓜,送到人家一片哗”,记述了一种求子方式。清人徐志的竹枝词作《送瓜》写道:“桂子盈盈白露凉,育儿心切晚添妆。蓬门少妇金闺女,并作瓜田一夕忙。”范锴补注:“俗于中秋之夕,锦彩饰棚,设瓜其中,灯火鼓乐,群送与戚友家,谓之‘送瓜’。受之者必备酒食,以犒来众。妇女欢迎,咸庆多子之兆,盖取瓜瓞绵绵意也。”[3](第3册2379)这是一种社会上下“蓬门少妇金闺女”共同的民俗。笔者以为值得注意的,还有“受之者必备酒食,以犒来众”而“来众”往往“送到人家”,“吃罢酒宴才散去”的风习。
丧礼用酒,亦见诸巴蜀竹枝词的记录。如王正谊《补达县竹枝词》:“庆吊仍须走一回,人家酒席要追陪。头缠白布鞋如雪,守孝缘何送礼来。”[3](第3册2193)
以酒送行,是古来社交方式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清光绪年间任汉州训导的富顺人宋时湛有《竹枝词二十二首》,又题《广汉竹枝词》。其中写道:“把酒临歧别有情,愧无一物送公行。柳枝欲折休教折,留待归时听好音。”[3](第4册3197)欲折不折句别有意趣。而笔者以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送别友人时“把酒临歧”的风习。
传统农耕生产程序中,也有需用酒的礼俗形式。如杨甲秀《徙阳竹枝词》说到“才祈雨罢又祈晴,官吏拈香日再行”,以及“万顷新秧绿渐匀,豚蹄麦饭祭田神”。又写道:“腊肉堆盘酒满卮,田畴正是插秧时。商量作个祈苗醮,打鼓前村去竖旗。”作者原注:“州人插秧,用腊肉饷工。田家作秧苗醮,前三日竖旗。”[3](第4册2664)
与“社”有关的崇拜意识和祭祀规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春日赛社”用酒,亦见于杨甲秀《续增徙阳竹枝词》:“歌声袅袅鼓冬冬,坐饮沿溪兴正浓。赛社风光饶乐岁,移尊携酒笑相逢。”[3](第4册2674)
三、酒与休闲生活
从体现巴蜀民间社会史的竹枝词作品中可以看到,酒在社会日常休闲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蜀社会传统民俗生活的每一寸空间,都弥漫着酒香。
宋人冉居常《上元竹枝词和曾大卿》收入《全蜀艺文志》,其中写道:“青春恼人思蹁跹,女郎市酒趣数钱。不道翁家留客久,红裆幔结赛秋千。”[3](第1册21)明人高启《竹枝歌》有“蜀山消雪蜀江深,郎来妾去斗歌吟”,“妾爱看花下渚宫,郎思沽酒醉临邛”。[3](第1册138)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笑语纷纷佐酒尊,天明犹记是黄昏。”说“守岁”风习。“彻夜不眠”、“达旦不休”的年节表演,是需要“酒尊”作道具的。相互贺年道喜,也借助“酒”以增益喜庆气氛:“队队衣裳簇簇新,相逢道喜贺阳春。无愁百岁惟今日,醉里何须谢主人。”[3](第2册1518)日常休闲生活中“当歌对酒”情形,南江人岳凌云的《春日锦江杂咏仿竹枝体》有所体现:“远山娇黛隔层云,酒忆临邛尚待醺。芳草天涯春寂寞,含情独上薛涛坟。”“阆苑城南春复春,桃花能笑柳能颦。如何濯锦江边月,不照当歌对酒人。”[3](第5册3831)诗句中“郎思沽酒醉临邛”,“酒忆临邛尚待醺”,既表现了对司马相如、卓文君临邛当垆故事的历史追忆,同时也是诗人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的反映。
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写道:“醉语喧于石路车,娇音多似毀巢鸦。妇人送客浑身胆,少见低头不语花。”另一首又有“尖声刺耳酡颜妇”,“细腰长千自风流”句,也说女子醉酒情形。又如:“嫁得红人多在衙,呼卢会酒自当家。玻璃窗轿归来晚,三炷燃香护奶娃。”作者自注:“俗以老爷、师爷二爷之得时者为‘红人’。其内眷出入,作自家大玻璃轿,婢仆群从,多有饮赌为常事者。”[3](第3册1840-1841,1843)豪家女子所谓“饮赌为常事”,固然不可看作社会常态,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风景,也是值得注意的。民间下层劳动者的“饮赌”习惯,近代人曹宦庥《汉源岁时竹枝词》中“老稚呼卢乘酒兴,荒郊野岔掷金钱”诗句也有所反映。[8](第5册3491)
富家闲暇,往往以酒为生活情趣的重要点缀。出身彭县的清代诗人吴好山《成都竹枝词九十五首》写道:“中年便喜服长袍,一朵花簪鬓二毛。镇日斗牌无别事,偷闲沽酒醉陶陶。”[3](第3册2439)“斗牌”“沽酒”成为某些社会阶层主要的消闲方式。又如“肆外衣裳亦美哉,携他一个大壶来。分明贮米归家去,却道街前打酒回”,似乎饮酒也是家境殷实的一种标志。不过,下层劳苦民众其实也有借“酒”稀释困苦、消散愁情的情形。清乾隆年间曾任盐源县令的王廷取在《盐源杂咏竹枝词》中的“蚁聚蜂屯豹子沟,砂丁沽酒更椎牛”,说到生活异常艰苦的矿工们“沽酒”“椎牛”的情形。他们平时的生产和生活境况,诗人有“费尽工夫石益坚,葱汤麦饭亦艰难”的描述。[3](第2册1146)
明代诗人王叔承《竹枝词十二首》其一:“月出江头半掩门,侍郎不来又黄昏。夜深忽听巴渝曲,起剔残灯酒尚温。”[3](第1册245)说到女子于心有期待而对方终于“不来”时的心境。江上“夜深”,“残灯”冷月,一缕寂寞情思,隐隐收藏于“酒尚温”句中。清人吴德纯《锦城新年竹枝词十四首》:“椒盘献瑞紫烟凝,饮罢酴酥力不胜。最恼娇痴邻小妹,强人呼雉剪银灯。”“花月春宵宴赏新,同行姊妹递邀频。红闺思斗新妆束,细语萧郎点黛匀。”[3](第4册3081)都说到女子面对美酒的香艳情态。清乾隆举人、合川人张乃孚《合阳竹枝词》:“云鬟堆首步生莲,夜夜人家闹庆坛。进酒不容空手过,席中捧出白磁盘。”[3](第2册1420)也涂绘了色调类似的宴饮图。
吕燮枢《渝州竹枝词八首》写道:“两鬓蓬松簪珥黄,齐纨摇动满身香。弯弯月子年年好,可惜飘零在异乡。”“香水桥头一笑过,蕉园风景近如何。举杯试问貂裘客,露冰风寒孰按歌。”[3](第2册1693)“举杯试问”句,反映了烟花生涯中“酒”的意义。又如王正谊《达县竹枝词》:“杨花又逐柳花飞,深碧钗荆浅碧衣。郎自进烟奴进酒,大家看遍醉人归。”作者原注:“土娼俗名‘杨花子’。”[3](第3册2192)又《补达县竹枝词》:“只著长衫不著裙,归来红粉酒颜醺。肩舆到处无帘笰,饱看双钩亦任君。”这些醺醉“红粉”,似是特殊职业的女子。又如:“声咽樽前不忍听,辞娘一饭泪零零。可怜十七如花女,富贵人家赋小星。”[3](第3册2193)作为竹枝词作者描述对象的,虽然在热烈的酒宴上“齐纨摇动满身香”,其实却是一位“樽前”卖唱的“可怜”少女。而窦絟《益州竹枝》:“一尺纤腰一束绫,醉为细步一轮冰。东门桥上悄声约,明日相邀到惠陵。”[3](第2册1692)其中“醉为细步”的女子的身份,则不易确定。
四、城乡的“酒市”“酒楼”“酒家”
以提供酒的消费条件作为主要经营内容的服务业,在巴蜀地方很早就已经兴起。明人薛瑄《效竹枝歌》写道:“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作锦城游。”[3](第1册157)清乾隆举人、崇庆人谢攀云《蜀州中秋竹枝词》也说:“夕阳西下月东升,罨画池边酒气蒸。莫诮游人归步晚,街帘初卷上红灯。”[3](第2册1472)“酒气蒸”一句,颇有声势夺人的商业气焰。又如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北人馆异南人馆,黄酒坊殊老酒坊。仿绍不真真绍有,芙蓉豆腐是名汤。”[3](第5册3492)说到“北人”“南人”“老酒”“黄酒”的不同消费倾向,都可以得到满足。近代曹宦庥《汉源岁时竹枝词》所谓“六月炎威酒市繁,梨园歌舞倍声喧”[8](第5册3492),则直称这种以酒为主的营业设施为“酒市”。
吴好山《成都竹枝词九十五首》:“鲜鱼数尾喜无穷,分付烹煎仔细烘。九眼桥头凉意足,邀朋畅饮一楼风。”[3](第3册2441)写述酒楼经营,笔调也是鲜活生动的。同一作者的《灌县竹枝词》写道:“危城半壁帯江缠,走集行人欲暮天。好客来时沽酒急,解衣无处典青钱。”[3](第4册2953)也说到城市中“沽酒”之处。清嘉庆庠生、彭山人袁怀瑄《游江口竹枝词》写道:“夜泊春江短竹篱”,“花港层楼隐翠微”,江港街市一派繁华,“烟街一带挂青帘,亚字栏杆倚画檐”,游人于是有“解得腰钱沽酒市”的行为。[3](第3册2095)达县人耿如菼的《宣汉竹枝词》有形容饮食市场的诗句:“绕郭酒楼经里余,可人风味暮春初。满江艇泊桃花水,争买新鲜丙穴鱼。”[3](第5册4132)也说到“酒”与“鲜鱼”合成的“可人风味”。而“绕郭酒楼经里余”的形势,值得研究者关注。
清人王培筍《竹枝词》:“明月楼头且醉眠,从来富贵亦徒然。邓通坟近铜山在,寒食无人挂纸钱。”[3](第3册2101)所说“明月楼头”应是酒楼。邢锦生《花市竹枝词》说到女子亦有以“上酒楼”为消遣方式的情形:“锦江儿女爱春游,联袂看花上酒楼。生长绮罗娇养惯,只知欢喜不知愁。”[3](第5册3869)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写道:“同庆阁傍薛涛井,美人千古水流香。茶坊酒肆争先汲,翠竹清风送夕阳。”又:“每逢佳节醉人多,都是机房匠艺哥。一日逍遥真快活,酒楼酌罢听笙歌。”[3](第3册1891-1892)说到“酒楼”的服务对象也包括手工业劳动者。酒家以妙龄女子“当垆”吸引顾客的情形,清光绪举人、曾任户部主事的什邡人冯誉骧在《巴江竹枝词》中有记述:“娉婷玉貌亦当垆,罗绮丛丛认彼殊。赢得路人开口笑,东川风景赛成都。”[3](第4册3422)
范成大《夔州竹枝歌》形容山区果农的经营形式:“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回。”[3](第1册16)在他们的生活中,“酒”竟然有与“盐”相当的地位。“沽酒”的所在,可能是与乡间保持密切经济联系的城市的酒家。
明代诗人王叔承《竹枝词十二首》言及“白帝城”、“十二峰”、“嘉陵江”、“万里桥”及“西川”、“成都”、“荡漾红妆下锦川”等,应是描述巴蜀风情。其六:“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其八:“郎今晒网桃花渡,奴把鲜鱼换酒来。”其十一:“绿酒娟娟白玉瓶,酴醿花发语猩猩。”[3](第1册246)都说到“酒”作为商品的情形。清康熙举人、温江人李启芃《邑竹枝词四首》写道:“麦草挑齐满屋叉,好将灯下绩新麻。帽成亲手交郎卖,莫把些钱付酒家。”[3](第1册542)这里所说的,很可能是村镇的“酒家”。
有一组《钓鱼竹枝歌》,作者是清乾隆进士、绵州人李调元。其中最后一首写道:“钓客将虾为钓饵,塘翁以酒作塘媒。既施鱼肴兼施酒,落得朝朝醉饱归。”[3](第2册1189)笔者不太清楚这里所说的“塘”的具体经营形式,而“鱼肴”和“酒”的享用,“落得朝朝醉饱归”,则是探讨酒的消费史时应当注意的。
五、“村酒”的醇香
明代诗人曹学佺《虁府竹枝词》有这样的诗句:“沿江坎上即田畴,满店烧香酒气浮。峨眉五月雪消水,刚让侬家割麦秋。”[3](第1册261)清乾隆举人、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写道:“闲是闲来忙是忙,劳劳车马走银珰。午餐更比晨餐早,野老微醺卧夕阳。”[3](第2册1518)以一幅“野老微醺”画图,描绘出乡间由酒香所烘托的平和气象。
前引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可见所谓“村酒几瓯须立饮”。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中有“家家春酒帖来忙”句,又说到“村醪”的制作和享用:“欢喜庵前欢喜团,春郊买食百忧宽。村醪戏比金生丽,偏有多人醉脚盘。”农户向地主奉礼,也包括自酿村酒:“佃户入城送年礼,黄鸡白酒主人贤。芭蕉叶大贴甜饭,味似年糕方似砖。”[3](第3册1834,1836,1844)农家自釀“白酒”可以“入城”,消费层面得以扩大。
另一例反映“佃户”和“主人”的关系以“酒”为中介情形的,是清人何人鹤的《佃户竹枝词》:“不计人牛受苦辛,押租钱扣更加贫。鸡儿啄黍偏难长,得酒无肴请主人。”作者自注:“佃田种者,有押租钱。少租,主人扣其钱。”[3](第2册1584)笔者虽不十分清楚“佃户”“得酒无肴请主人”的具体情形,但是“酒”在这种阶级关系中的作用,可以隐约得知。
以村酒“开筵”,是农户聚会乡亲邻里的通常方式。如杨甲秀《徙阳竹枝词》:“腊尽呼屠宰腊猪,开筵都为酌乡闾。席间竞说完粮早,幸免催科到里胥。”诗人又写道:“水绕山环竹树高,人家聚饮献羊羔。怪来此处名安乐,满眼青畴雨润膏。”[3](第4册2666-2667)所谓“人家聚饮”,也许是传统农人生活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清乾隆贡生、曾任芦山县令的朱黼有《芦风竹枝词》记录芦山乡俗,其中一首说到饮酒风习:“贸迁无计只屠沽,食肉人多半酒徒。每到场期一五八,酡颜攘背共欢呼。”[3](第2册1196)乡间“酒徒”们每逢赶场时节都不免一醉。西昌人杨学述《建昌竹枝词》描述乾隆年间西昌民习:“海滨村落半闲人,终日醺醺为惜春。若问酒钱何处觅,无庸播种但垂纶。”“楚语吴音半错讹,各乡场市客人多。日中一集匆匆散,烧酒刀头马上驮。”[3](第2册1204)也说乡间市集因酒而导致的热烈场面。“场市”散去,又有驮酒而行的“客人”将酒香带到远方。
陈祥裔《竹枝词》记录蜀地风习。其中写道:“竹架低檐草半堆,竹柴烧饭响如雷。灶边揖罢随人坐,笑道贫家只旧醅。”记述了“贫家”以“旧醅”酒待客的情形。他的《巴渝竹枝词》中“花布春衫白布裙,斜阳牛背醉醺醺”句,也说到乡村人家酒的消费。[3](第1册856,858)康熙举人、曾任江油县令的彭阯有《江油竹枝词十二首》。其中说到衣不蔽体的穷困者对酒的迷恋:“寒生肌栗计如何,丈布斤绵便可过。怪不觅衣惟觅酒,酒钱结算较衣多。”[3](第1册782)诗句对沉醉于酒者有批评之意。
六、少数民族饮酒生活
在巴蜀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也有早期酒文化萌生的迹象。川酒的精彩,不排除来自少数民族文化之积极因素的可能。
浙江嘉善人钱召棠,清道光年间曾经任巴塘同知。他的诗作《巴塘竹枝词四十首》中写道:“蜀疆西境尽巴塘,重叠川原道路长。地脉温和泉水足,何曾风景似蛮荒。”其中有少数民族饮酒形式的记录。如:“笼头小帽染黄羊,窄袖东波模格长。满饮葡萄沉醉后,好携纤手跳锅庄。”作者原注:“妇女穿小袖短衣,名‘东波’;细褶桶裙,名‘模格’。每逢筵会,戴黄羊皮帽,联臂歌唱,以足踏地为节,曰‘跳锅庄’。葡萄酿酒,色红而微酸。”[3](第3册2262,2264-2265)所记述的,应当是藏族生活。清末新津人陈经《炉城竹枝词》有题为《跳锅庄》者:“袅袅婷婷绕席游,红巾一幅喜缠头。漫歌一曲拼成醉,醉把锅庄当翠楼。”[3](第5册3900)也许“漫歌”“翠楼”一句,是诗人自己没有什么根据的漫想。
清人李瑜在道光、咸丰年间曾经在绵州等州府任地方行政长官幕僚。他的《雷波竹枝词》写道:“箐林风静月轮高,醉拥氍毹弄宝刀。木碗劝郎斟椰酒,愿郎莫作石飘飘。”作者原注:“‘石飘飘’,夷地名。”[3](第3册2435)“石飘飘”句,如果不是诗人刻意修饰,则意境不逊于古“竹枝”“道是无晴还有情”[3](第1册1-2)等。
清人石德芬《叠克杂咏》,又题《边俗竹枝词》,其中有关于“蛮家”饮酒风习的内容。作者写道:“蛮家薄薄酒,味淡人意浓。拖且使君妇,殷勤捧玉锺。”作者自注:“‘拖且’,即‘多谢’之声转,蛮音与汉音最近者。”作者解释说:“‘叠克’,即‘德格’也。《杂咏》即《竹枝词》也。不言《竹枝》者,边俗与内地不同,不须假借也。”[3](第5册3872,3870)德格,地在今四川甘孜。作者这里所说的“蛮家”,应当是藏族。
从竹枝词中的相关文字遗存,可以看到“咂酒”这种特殊的饮酒方式。垫江人程伯銮《桂溪四时竹枝词》写道:“听来搭斗响连声,咂酒盈缸香到门。晓榼恰完归去也,月明人语散鸡豚。”又如:“看茶随意约亲邻,拼醉丰年酒几巡。归路喃喃谈不了,赶场初散太平人。”[3](第3册1870)前引陈祥裔《竹枝词二首》可见“咂酒”。梁山(今重庆梁平)人蓝选青《梁山竹枝词》也写到“咂酒”:“新醅咂酒味偏醇,留与生期款众宾。小火炉中刚捧出,大家相让请头巡。”[3](第5册3959)由“小火炉中刚捧出”句可知,这种“咂酒”是取热饮方式。明代学者杨慎《昭化饮咂酒》诗说到“咂酒”:“酝入烟霞品,功随曲糵高。秋筐收橡栗,春瓮发蒲桃。旅集三更兴,宾酬百拜劳。苦无多酌我,一吸已陶陶。”[9](卷一九)清代学者查慎行有《咂酒》诗:“蛮酒钓藤名,干糟满瓮城。茅柴输更薄,挏酪较差清。暗露悬壶滴,幽泉借竹行。殊方生计拙,一醉费经营。”[10](卷三《慎旃集下》)现今彝族、土家族、羌族都还保留“咂酒”习俗。这种饮酒方式据说早先有更广阔的分布空间。杨慎考论,杜甫诗句“黄羊饭不膻,芦酒还多醉”,所谓“芦酒”,就是“以芦为筒,吸而饮之,今之‘咂酒’也”。[11](卷二二引《升庵外集》)杨慎又说,这种酒又称“钓藤酒”,引宋人朱辅《溪蛮丛笑》“钓藤酒”条:“酒以火成,不醡不蒭,两缶东西,以藤吸取,名‘钓藤酒’。”[9](卷六九“芦酒”条)
七、早期酿酒产业史迹
私酿,可能曾经是酒这种饮品早期发生的方式,也是酒业惯常的发展路径。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写道:“三莲池判上中下,三较场分西北东。玉带桥名人易忽,铁圈井酒味难同。”作者自注:“‘铁圈井’在成都县署旁,井泉清冽,暑月酿酒不坏。”[3](第3册1836)可知成都市民以泉水自酿酒,至清代依然形成民俗。
清人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再续竹枝五十首》:“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绸。西来氆氌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3](第3册1893)说各地物产经销成都者,包括“郫筒酒”。史次星的《自流井竹枝词十章》则称之为“郫酒”:“门前树树水林檎,屋后山田种靛青。昨日成都王大舍,寄来郫酒醉初醒。”[3](第2册1195)何人鹤《郫县竹枝词》:“郫筒井上桐花开,幺凤飞飞绕树来。妾似桐花郎似凤,花开端的望郎回。”[3](第2册1584)所谓“郫酒”、“郫筒酒”,或许与“郫筒井”的井水有关。
吴好山《成都竹枝词九十五首》:“酒数‘森山’与‘玉丰’,别家香味总难同。‘泥头’好又‘陈年’好,引得人人困此中。”[3](第3册2438)可知好酒已经在市场上形成了名牌效应。王昌南《老人村竹枝百咏》:“佳酿泉香气味清,漫夸吸海赛长鲸。山翁屡醉泥相似,酒出‘烧刀’旧有名。”[3](第5册3946)名为“烧刀”的酒,亦是一时名产。杨学述《建昌竹枝词》“烧酒刀头马上驮”诗句中所谓“烧酒刀头”,不知是否与“烧刀”有某种关系。前引曹学佺《虁府竹枝词》“满店烧香酒气浮”说到“烧香”,也是很有意思的信息。
酿酒讲究水泉的品质。西昌人颜汝玉以对于当地风土物产的熟悉,在《建城竹枝词》中说到酿酒业的经营:“城东河水绕城南,城右西河带远岚。城左香泉推第一,城前龙眼井泉甘。”又写道:“芋麦高粱酿酒多,无论糯稻是嘉禾。怪它大曲饶香烈,择地偏宜马水河。”[3](第4册3249)其中“芋麦高粱酿酒多,无论糯稻是嘉禾”一句,值得酒史研究者特别注意。诗人列举酿酒的“嘉禾”,计有五种,恰恰正合于后来酒业成功人士们所艳称的“五粮”。
“高粱”作为酿酒主要原料,很久以来即成为好酒的牌号。四川眉山人刘鸿典曾任西充县训导,作有《西充竹枝词》。其中写道:“街头风景问如何,饭店门前豆腐多。更有高粱烧酒好,散场人尽醉颜酡。”[3](第4册2627)所谓“高粱烧酒”,长期成为许多好酒的通常称号。
八、川江“载酒”船
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大佛寺前放画船,薛涛井畔汲清泉。回船买得薛涛酒,佛作斋公我醉仙。”[3](第3册1838)所谓“回船买得薛涛酒”,或许是说回程时买酒,也可能体现的是岸上买酒而“回船”一醉情形。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画船”有售酒服务的内容。
诗人乘舟远行,往往以酒为旅伴。杜甫曾作《不见》诗,以“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的名句概括李白的一生。[12](下册417)与行旅历程相始终的“飘零”生世同“酒”的关系,显然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李白也曾经写道“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13]中册686)。“明湖涨秋月,独泛巴陵西。”“曲尽酒亦倾,北窗醉如泥。”[13](中册953)杜甫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关于回归中原的行程计划,也写道:“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12](卷一二)陆游曾经创作的行旅诗中,有《溪行》一篇,其中写道:“买鱼寻近市,觅火就邻船。愁卧醒还醉,滩行却复前。”“逢人问虚市,计日买薪蔬。”“枕书醒醉里,短发不曾梳。”[14](第1册36-37)也具体描绘了江溪泛舟之时其行旅生活的饮食内容。鲜活鱼蟹,新嫩菜蔬,都十分方便,而酒醪之充备,也足以使旅客于亦“醒”亦“醉”之际,轻舒浪漫地行历水程。
显然,“酒”在行旅生活中,绝不是只作为一般的饮料而仅仅具有物质的意义,而实际上发挥着行旅者精神伴侣的作用。[15](157)类似的意境,我们读新繁人刘希正的《五日竹枝歌》时也可以有所体味:“青蒲绿艾短篷支,帆饱舟轻浪自移。我欲壶觞诗酒去,不知作楫可如伊。”[3](第5册4075)赵熙《下里词送杨使君之蜀》中“醉中一浣银河笔,丈瀑如龙落九天”[3](第4册3424)句,则鼓励友人旅途中在酒的陪伴下有诗的丰收。
一如陆游《荔枝楼小酌》“病与愁兼怯酒船,巴歌闻罢更凄然”[14](卷三,第1册P305),清人赵熙的竹枝词作品《下里词送杨使君之蜀》也说到“酒船”:“乌尤山是古离堆,沫水沙明一镜开。竹外三峨九秋色,劝君莫棹酒船回。”[3](第4册3426)清人文棨《左绵竹枝词》则有“载酒遨游意自豪”[3](第4册3035),读来可以感觉到酒气和雄风共同充溢着旅人的心胸。
江船“载酒”,可能有多种意义。清人龚维翰《川船竹枝词》:“嘈杂乡音入耳中,掌家籍贯半川东。衅船鸡酒人人醉,一揖而来有太公。”说“鸡酒”“衅船”,应是出航前具有神秘意味的礼俗仪式。而“人人醉”者,反映礼仪参与的形式,可能包括所有的出航者。又如:“宽分大小酒分香,割肉酬劳三寸长。醉后休忘是潮水,灯花剪向太平舱。”前一首说到“蜀道愁过百八滩,滩滩险处觉心寒”情形,又说:“骇人最是三峡石,乱掷金钱乱打宽。”自注:“赏酒钱曰‘打宽’。多者谓之‘大宽’,少者谓之‘小宽’。”则所谓“宽分大小”得以说明。而“宽分大小酒分香,割肉酬劳三寸长”句,是说船工经历险滩之后得到犒劳的情形。又:“万变篷窗景莫穷,青山名字问篙工。马门又说传餐饭,火老丁哥颊映红。”[3](第5册3949)最后一句,似乎也是说船工饮酒。
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写道:“绍酒新从江上来,几家官客喜相抬。绍兴我住将三载,酒味何曾似此醅。”[3](第3册1895)则明确是说江船载运酒的情形。不过,说的可能是“绍酒”逆江西运事。诗人似乎是在批评商品假冒情形。联系前引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所谓“仿绍不真真绍有”句,可知确有“仿绍”进入民间消费生活。如此则“绍酒新从江上来”未必来自长江下游。张乃孚《巴渝竹枝词二十四首》也说到“载酒”情形:“载酒纷纷香国去,阿谁画壁睹歌鬟。最嫌小艇沿江叫,白昼摊钱送上关。”[3](第2册1417)所谓“摊钱”,指一种相当普及的赌博游戏,有时是和饮酒同时进行的。[16]
川酒随船远运,是更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华阳 (今四川剑阁)人顾印愚《府江棹歌十二首》有反映江行“载酒”的诗句:“五两风微五粄轻,春江滟滟縠纹平。沙头宿鹭莫惊起,凭借烟波载酒行。”据作者序文,“甲申乙酉之间,砚食戎州。中间数还成都。每遵陆取资州、简州而归。复买舟出清溪三峡,清江白石,即物流连,水宿星饭,每有佳语。”诗人 1884年至 1886年间往来成都与戎州(今四川宜宾)、资州(今四川资中)、简州(今四川简阳)间,行旅感受,集成佳句,成《府江棹歌》,“体仿‘竹枝’之遗,词则‘折杨’之陋尔。”诗作有“锦城南下寄篷艭”、“行尽青衣三百里”、“江口逶迤百里间,麦苗风里见彭山”句,又可见“眉州”(今四川眉山)、“嘉州”(今四川乐山)字样。[3](第4册3156)“凭借烟波载酒行”的航道,可知是既漫长,又沿江飘送着酒意和诗思,因而情趣盎然的。
[1] 王振忠.竹枝词与地域文化研究——评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J].历史地理,21.
[2] 王子今.“竹枝词”的文化意义[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3] 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4] 王慎之,王子今.唐代三峡“竹枝”: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J].商务印书馆,1999.
[5] 王慎之,王子今.四川竹枝词中的盐业史信息[J].盐业史研究,2000,(4).
[6] 王子今.四川竹枝词客家文化史料研究[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1).
[7] 王子今.明人竹枝词中有关“巴盐”的信息[J].盐业史研究,2008,(3).
[8]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M].北京出版社,1997.
[9] 杨慎.升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陈元龙.格致镜原[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 李白.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7.
[14] 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 王子今.中国古代行旅生活[M].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
[16] 王慎之,王子今.清代竹枝词反映的民间赌博风习[J].紫禁城,1997,(3).
K89
A
1673-0429(2010)04-0011-09
2010—06—22
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校外专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