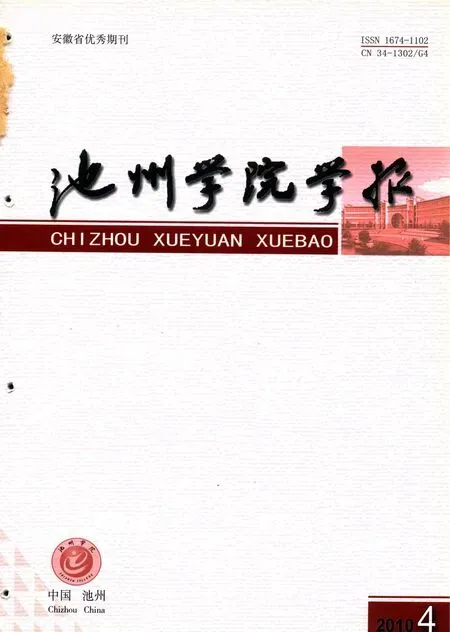古代诗词教学与审美能力的培养
2010-04-04渠红岩
渠红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阅江学刊》编辑部,江苏 南京 210044)
古代诗词教学与审美能力的培养
渠红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阅江学刊》编辑部,江苏 南京 210044)
对诗词作品进行审美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与人事使作家产生感发,并运用某些艺术手法,遵循某种规范,将其内心的感触用文字表达出来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是诗人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的结果。想象和情感是形成美感的两个主要因素,因此,解读古代诗词作品,必须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抓住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分析其使 用的艺术性。第二,将自身情感投入作品中,去分享诗词中的生命和情趣。第三,分析诗词中的修辞手法,从而正确理解诗词中的形象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关系。
古代诗词;自然物象;感触;艺术;想象;情感;意象;修辞
《文心雕龙·序志》云:“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①。这段话鲜明地说明了“文章”的实际价值,当然,刘勰所言"文章"是指经世致用之文。其实,其他文体之文,如诗歌、词、曲等莫不具有欣赏和教育等价值。毋庸置疑,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是作家对现实生活和社会进行审美的结果,而想象和情感是形成美感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对于读者而言,要真正获得文学作品的价值,则离不开想象能力和丰富的情感。中国古代诗词作品以变异了的生活形式、生活情态、色调以及更为深邃的内涵令读者陶醉,给读者以启迪。究其原因,是作家的想象艺术创造和浓浓的、真切的情感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教师能在古代诗歌教学中注意挖掘作品的想象艺术和情感因素,生动、深刻地解读作品本身,则能逐步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那么,如何较为客观地、深入地理解古代诗词作品从而更好地体悟其美感呢?
第一,抓住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分析其使用的艺术性。诗歌和词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精心选择的意象去创造内心情感和思想的世界,这些意象往往通过作家的想象而失去了生活原型的一部分性状而获得了感情的特征,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家赫斯列特《泛论诗歌》说:“想象是这样一种机能,它不按事物的本相表现事物,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绪把事物揉成无穷的不同的形态和力量的综合来表现它们。这种语言不因为与事实有出入而不忠于自然;如果它能传达出事物在激情的影响下,在心灵中产生的印象,它便是更为忠实和自然的语言了”②。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排除白描手法也常常会为诗歌带来新的生命,如《诗经》汉乐府、陶渊明的诗歌等,但是,从艺术上说,同一个表现对象,两者的表达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两首以杨花为题材和的作品为例既可以明白。
首先是宋代章楶《水龙吟》:
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清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霑琼缀。绣床旋落,香球无数,才圆又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③。
再看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④。
显然,两首词都是闺怨作品,借春日纷飞的杨花表达女主人公的伤春意绪。从艺术表现上看,章质夫对杨花的描写可谓是曲尽其妙,“轻飞乱舞”、“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等词句,将杨花的情态惟妙惟肖地写了出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章质夫词中,是以写实的手法表现杨花的,没有发生与实际所见杨花的任何变化,只是以一些较为形象的动词将杨花的情态表现出来了。而在苏轼词中,杨花则别具一番意趣,而不再完全是实际所见的杨花了,“似花还是非花”、“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像花又不像花,是离人的眼泪,苏轼以比喻的手法将杨花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在“杨花”和“眼泪”这两个本来不相关联的事物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暂时的相同点,点点的杨花像滴滴的眼泪,这样,本来不具有情感的杨花就具有了人的感情。另外,我们再看,为什么苏轼看到杨花会想起“离人泪”呢?因为杨花所能让人引起的联想很多,它可以使人想到杨柳的栽种,或者想到杨柳依依的小河,或者想到轻盈的纱等,那么,讲到这儿时则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为什么苏轼仅仅将“离人泪”与杨花联系起来了呢?原因就在于,作家在选择意象时是凭着情感去决定取舍的,同一事物,在这个境界会唤起人们这种情感,唤起这种意象,在另一境界里又会触动另外一种情感,从而唤起另外一种意象。又如,同样是杨柳,不同的情境下所触发的作者的心绪是不一样的。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⑤。“杨柳”可以唤起无穷的想象,但是,“夫婿”的形象对于“春日凝装上翠楼”的少妇来说具有很强的情感倾向性,这种倾向就是使“夫婿”形象油然浮上心头的最好动力源。《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来我思,雨雪霏霏”的杨柳则是触动征人思乡的媒介。而唐代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⑥。诗中的“柳”则是目睹六朝繁华与今日衰败景象的意象。可见,情感因境界而产生,境界不同,所引发的情感也就不同,情感的相异从而引起作者选择意象的不同。
第二,“体物入微”,将自己的情感投入作品中,去分享"物"的生命和情趣。生活的主要特征实际上是作家的主导感觉,这种感觉之所以生动、形象,不是由于它准确地反映客观生活对象的主要属性,而是它超越了客观对象的主要属性,这种超越的、非常态的、变异的感觉知觉就以它的强烈性和生动性而成为内在情感微波的一种索引,而这种索引则反过来能使读者明晰地、深刻地感受作品中作家的情感。白居易《与元九书》:“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感是构成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作品的根本因素。美国著名文艺美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将这一观点阐释得更加详尽,她认为,艺术就是一种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并不是直接地表达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而是表达他所领会到的某些人类情感的本质,或者说是被符号抽象化了的人类的情感⑦。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吧,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情感的独特性;(2)情感传达的清晰度;(3)情感的真挚度。而这三种因素的艺术效果归根结底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在抒情性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古代诗词作品中,作家常常通过主体与客体相互融化为意象的方式,将主客体在现实环境中交融起来构成一种混沌的整体,这种整体好似生活本身的原生状态,创造出“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共生”,或者“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艺术境界。例如,陶潜《饮酒》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诗人所见所感,不是有意寻求,而是不期而遇,南山的美景与采菊时的悠然心境相映衬,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苏轼称道此句:“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此时,如果我们引导学生试着将“见”字改为“望”字,然后再来体会一下其中的情感艺术表现,则可以清晰地表现出“见”字用得巧妙。如果再结合诗歌结尾处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含蓄表达则更能体会出诗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人生态度。当然,这些理解离不开我们对陶潜的生平与经历的了解与认识,离不开对那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特征的把握。由此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陶潜这首诗歌所表达的感情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声音,是通过一些精心选择的意象,如“飞鸟”、“山气”、“菊”等将自身情感与大自然密切地融和起来,从而达到了真率质朴、 天然无雕饰的艺术效果。
第三,通过分析诗词中所用的修辞手法,从而正确理解所用的形象与诗词情感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不仅是自然界的“物象”可以引起人的内心感发,人们的活动等也可以引起人的内心感触。自《诗经》开始,中国古人就根据外物与内心情感相互作用而总结出了一些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毛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无曰雅,六曰颂。”所谓“义”,即一些重要的道理,而其中的“赋、比、兴”就是写诗歌时所用的一些基本方法。这些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词。因此,在解读这些诗词作品时,只有分清楚作者是采用了赋、比、兴中的那一种方法而带领读者进入感发的,才能进一步理解诗词中的意象或者形象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之间的关系,从而体悟出诗词作品的美感意蕴。在“赋”、“比”、“兴”这几种手法中,“赋”较为简单直接些,也容易理解,而“比”、“兴”则相对难理解些,它们的作用是以一组或者一系列的形象和事物来间接地某种情意,而这种情意永远都不直接说出来。我们以李商隐《燕台四首》中的《春》为例加以分析。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⑧。李商隐《燕台四首》组诗共分为春夏秋冬四首,每一首都写得扑朔迷离,令人难以读懂。诗人始终都未说明他想要的是什么,然而却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中,我认为,解读这组诗的关键是正确分析其中的修辞手法。
在这首诗中,“风光”指的是大自然的景色,这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是因为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将本已不新鲜的事物变为新鲜的,“冉冉”二字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写出了春日气象万千的姿态。“陌”是人行的小路,“东西陌”是一种对举的手法,实际上包括了东西南北所有的道路。这句的意思是到处都有冉冉的春光,活泼盎然。这一句并不完全是视觉感受,其中还带有一种心灵深处的触动,所以,接下来就说“几日娇魂寻不得”。诗歌中感发的生命是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好诗人和坏诗人的差别就在于这种传达的能力的不同。一个大诗人,总是能够选择出恰当的语汇,并将其组织得恰到好处,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往往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包含着他心中的感受,在李商隐这句诗中,“娇”、“魂”就是如此,美好可爱、灵动自在。这种灵魂也许就是诗人心中美好的追求,或者是那种超乎物质之上的某种精神?这一切,都是诗人留给读者的无穷的想象。下一句中,“蜜房”就是储藏蜂蜜的地方,“蜜房羽客”就是蜜蜂了。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把白日飞升的神仙叫“羽客”,所以,这句诗就产生了拟人的效果,表现了一种飞翔和求索的情致,而“遍相识”三字则表达了一种执著的追求。苦苦的追寻似乎真的看到了他所要寻觅的“芳心”,所以,诗人接下来又用了一些形象,“辉”是日光,春天白天渐渐变长,太阳移动得很慢,因言“辉迟”,而当太阳的影子移到桃树之西时,就出现了 “高鬟立共桃鬟齐”的美妙的情景,“高鬟”是一种女子的发式,极显女性的端庄成熟之美,本句言美丽的女子头上簪满了花朵,站在桃树旁边。这就给读者一种亦幻亦真的感觉。其实,这确是一种幻觉,诗歌的最后一句即言:“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古代常用龙凤结合表示美满的婚姻,然而,诗人说不但没有雄龙,也没有雌凤,更谈不上二者的结合了,而这种迷惘就像春日天空的纷乱的丝絮,蒙蒙的令人惆怅。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用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形象,表现了一种怅惘缠绵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是不可言说的,隐隐的,这也正是诗歌的妙处所在。
诗歌是自然界的物象、人事对诗人内心产生了感触,诗人通过一些艺术手法将这种感触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而形成的。《礼记·乐记》言:“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⑨。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而作为读者来说,欣赏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作品进行审美判断,审美判断的基础就是审美感受,这就要求审美主体具有较强的悟性,将对作品的理解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并且靠妙悟来作出审美判断。综观中国诗歌意象,自然界的物象占据显著位置,而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某一方面看,就是自然界的物象不断意象化的过程。再从汉语语法方面看,汉语的句子往往靠意合而不是形合组织在一起的,古代诗歌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将介词、连词等省略,直接把意象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强了诗歌的多义性,从而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富于跳跃性,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在教授古代诗歌或词作品时,就要引领学生分析其中的意象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理解诗词作品所表达的、蕴含的情感,形成审美感受,进而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人生阅历等作出审美判断,完成作品欣赏的全过程。
注释:
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②《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0-61页。
③清朱彝尊《词综》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苏轼《东坡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全唐诗》卷十六。
⑥《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七。
⑦[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⑧李商隐《李义山诗集》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章建文
G642
A
1674-1102(2010)04-0139-03
2010-05-18
渠红岩(1970—),女,江苏徐州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阅江学刊》副主编,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编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