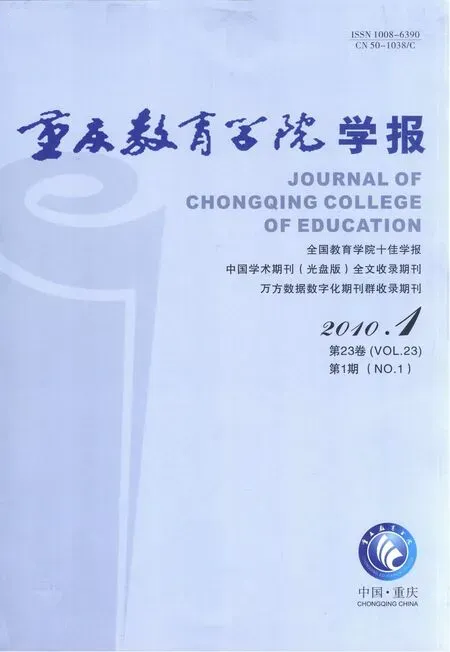符号论与主客观化合论视角的抒情诗——兼及鲁煤文学语言的美学个性问题
2010-04-04赵心宪
赵心宪
(重庆教育学院 中文系,重庆,400067)
一、符号论美学视角“抒情诗最值得注意的特点”
美国当代美学家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有关抒情诗的论述,是与其提出文学语言“思维与情感生物性统一”[1](P299)的美学难题同步的。 立足于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视角,对抒情诗的认识,就是对抒情诗语言(符号)美学功能的理解,涉及艺术哲学、艺术语言(符号)学到文学文体学等系列诗学问题,概括言之,主要导出关于抒情诗的两个重要论断:
(一)强调抒情诗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先天”的情/思合成表现力
苏珊·朗格说:“各种现实的事物,都必须被想象力转化为一种完全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作诗的原则。进行诗转化的一般手段是语言。”在我们看来,上述“作诗的原则”,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的一般美学原则;“诗转化”即生活形态向语言艺术形式的转化;“一般手段是语言”的艺术创造,特指文学创作语言形式运用的情感价值:即“述说某件事情”,应“使得这件事具有一种或是漫不经心地,或是郑重其事地;或微不足道或至关重要;或好或坏;或熟悉或陌生的外在形式……每一个给定的事实、假设或者幻想,则主要从它被表现和接受的方法中获取其情感价值。”[1](P299)“它被表现和接受的方法”,就是文学创作的语言形式运用方法,从而体现文学语言情/思合一表现的美学功能。
在苏珊·朗格看来,文学语言符号形式的情/思表现能力“十分惊人”。仅就其发音“就往往能影响人们关于词汇原意的情感。有韵句子的长短同思维结构长短之间的关系,往往能使思想变得简单或复杂,使其中内含的观念更加深刻或浅显直接。赋予语言以节奏的强调性发音,发音中元音的长短,汉语或其他难得了解的语种的发音音高,都可以使某种叙述方式比起别的方式来显得更为欢愉,或显得倍加哀伤。”[1](P299)抒情诗语言为代表的文学语言的韵律节奏,好象有一种神秘品格,暗示着人类思维与情感“先天”统一性的存在,因此倍受美学家关注。
(二)认定抒情诗主体性突出的语言(符号)形式运用特点
抒情诗作为符号论美学文学语言的首选研究对象,因为“它是最直接地依赖着口语根源”的文学形式,是文学语言“最典型的语言创作”。苏珊·朗格说:“抒情诗所以如此大量地依靠语言的发音与感情特征,原因在于它非常缺乏创作材料。一首抒情诗的主题往往只是一缕思绪,一个幻想,一种心情或一次强烈的内心感受……抒情诗人所以运用语言的每一种特性,就是因为他既没有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往往也没有任何使诗歌得以继续的理性的论述。致力于字句的准备和完成不得不取代一切。 ”[1](P300)这也是抒情诗文体主体情 /思张扬表现的根本动因。
上述引文所谓“运用语言的每一种特性”,在我们看来,存在着两个对立互补的基本面。首先是语言作为符号活动的特征。苏珊·朗格《哲学新解》有关符号与信号的本质区分中,明确了符号活动的两个事实:“第一,符号活动已经包含了某种抽象、概念活动,已经不再停留在个别之上,它经过了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过程。第二,人类所具有的全部原始本能中,必然有某种本能自发地进行了理性实践活动,人类的抽象思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本能的智力活动就是符号活动。”[1](P5)语言就是人类符号活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次,艺术作为语言符号补充的符号活动特征。因为人类的情感特征充满着矛盾与交叉,处于一种无绝对界限的状态中,只能强调其区别的语言符号描述,严格地说并不能表达人类情感。人类的符号能力,因此创造出服务于情感表现的艺术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比较,“语言能使我们认识到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周围事物同我们自身的关系,而艺术则使我们认识到主观现实,情感和情绪……使我们能够真实地把握到生命运动和情感的产生、起伏和消失的全过程。 ”[1](P7)艺术这种独特的哲学美学认识功能,说明艺术充当了一种特别的人的经历认识“概念”,成为“标示情感和其他主观经验产生、发展和消失过程的概念,是再现人类内心生活统一性、个别性和复杂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就是艺术形式的内涵,艺术正是那种将这些概念细腻而深刻表现出来的符号手段。语言无力完成的任务,即呈现情感本质与结构的任务,艺术完成起来却得心应手。”[1](P11)抒情诗作为语言的艺术,与其他文学类型不同的地方,在于“既没有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往往也没有任何使诗歌得以继续的理性的论述”,正处于从日常生活的语言转化为艺术符号——语言的艺术符号化阶段,创作主体必须竭力“运用语言的每一种特性”,而使其文学语言的情/思符号功能可能得到全面实现。所以朗格这样评价说,“抒情诗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诗人正在抒发着自己瞬间的情感与思绪”,“现在时态”[1](P301)文学语言的语言形式运用。
二、胡风“主客观化合论”的美学视角及其“诗”本体的论断
无独有偶,20世纪中国最有争议“第一义诗人”的美学大师胡风,一生有关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也同苏珊·朗格一样,给予抒情诗美学视角的特别观照。当下仍然是理论热点的胡风文艺美学思想,虽然涉及多个重要的哲学美学命题,但其主干就是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主客观化合论”。了解“主客观化合论”的建构过程,才能理解作为现实主义美学视角的“主客观化合论”,从而认识胡风抒情诗有关论断的美学意义。
胡风美学层面的主客观化合论原则,贯穿文学艺术的批评论、接受论、创作论和本体论等文艺美学的各个理论层面,有一个发生、发展、完型的完整过程。王丽丽博士指出:胡风主客观化合论“原生性”的生成轨迹,呈现为清晰的三个阶段,即“主客观化合论的形成、主客观化合论获得现实主义命名,主客观化合论表现出社会学与美学结合的样态”[2](P22)。第一阶段:《张天翼论》中首次出现“肉搏”“突进”等,构成“主观战斗精神”内涵的关键词;《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赋予主客观化合论 “基本的唯物辩证法的品格和双向出击的批判功能”;《文学与生活》评论集开始为胡风所有理论阐述,盖上主客观化合论这个 “胡记标志”;《略论文学无门》将“主客观化合”过程具体化,析出人生、作者、艺术三要素,提出三要素间的“化合方程式”,强调“作者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受难(passion)的精神”主观性,到此,表明胡风“主客观化合论”思想在发生期所具有的“胚胎”特点。
现有的文献资料已经充分证明,胡风主客观化合论的美学思想,其实是在1940年代“民族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步入成熟”,即“获得现实主义的命名”的,这是主客观化合论进入第二阶段的主要标志。最重要的文献,是1940年《七月》发表的胡风与读者关于田间诗歌的通信。胡风于信中将主客观化合论,作为达成现实主义诗歌“诗的理想境界”的基本理论依据,从而将其提升到全新的美学阐释高度:要求作家最后争取达到和现实对象的“完全融合”。胡风解释说“那就是作者的诗心要从‘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更前进到对象(生活)的深处,那是完整的思想性的把握,同时也就是完整的情绪世界的拥抱”。因为能否“获得向生活深处把握的力量,也就是把握生活的思想性和拥抱情绪世界的力量”,作家的主观精神作为整合作品素材的要素,推动主客观互动,是决定作品世界整一或四分五裂的关键,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2](P38)。这个时期的其他文献,《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对文学创作中作家主观精神倚重的自觉程度,作家高昂而强旺的主观精神已被胡风作为现实主义的突出特征;《一个要点备忘录》所记1941年文协小说晚会的发言要点,同样显示出胡风现实主义理论与主客观化合论合二而一同步发展的美学思想特点;现实主义等同于主客观的化合,从而让胡风现实主义精神的美学阐释获得明确具体性的 《现实主义在今天》;《关于“诗的形象化”》批评“形象化”理论对诗人主观精神的漠视等文,都是胡风主客观化合论获得现实主义命名的重要证明。
1943年底,胡风为田间诗集《给战斗者》撰写的《后记》,显示出主客观化合论思想进入第三阶段的思维逻辑:“当主客观的化合获得最理想的条件时,诗歌作品就可以达成‘浑然’的理想境界,‘社会学的内容’就可以获得‘恰恰相应的,美学上的力学表现’。由此,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又转变为社会学与美学的结合。”[2](P51)胡风在《给战斗者·后记》中,沿用主客观化合论追述田间诗歌的战斗历程,认为诗集中的各辑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但都是诗人田间将他的情绪和心“投向了作为整个生活世界的战争”的产物。这样,早在《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建构的“主客观互动”文学创作论模式,被重新提升到哲学美学层次给予新的理论观照,赋予其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论内涵,而且于创作实践更具有指导操作性。不管是《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两个层次体现的社会学与美学的统一,或者《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提出“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作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引起广泛争议的观点,其实都能够回到“主客观互动”,这个精辟概括文艺创作普遍规律的理论思维模式上,从而让主客观化合论的美学阐释具有永恒的理论生命力。换言之,如果不总是被不相干的原因强力干扰、影响,无限放大胡风主客观化合论自我阐释体系的若干不周延处,遮蔽其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创新贡献,只要全面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重视主客观化合论形成过程中与创作实践的血肉联系、互动生成的经验理性风格,就会高度认同胡风主客观化合论在创作论层面特别有效的实际指导意义,欣赏其阐释艺术创造规律的理论穿透力。
例如抒情诗本体特征的认识。胡风有关诗歌美学特征的阐释,与其主客观化合论的生成过程是合二而一的,当时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家的创作,往往就是引证主客观化合论思想,上述发展过程中内涵认识的主要例证。下列胡风战争时期关于“诗”的系列论断,都可以读到这个特点:
1.“诗是作者在客观生活中接触了客观的形象,得到了心的跳动,通过这客观的形象来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体验。”(《略观战争以来的诗》)
2.“诗就是作家在现实这火石上面碰出的自己的心花。”(《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
3.“诗应该是真情,在‘抓住现实的一瞬间’触发的真情。”(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与导师》)
4.“诗是作者被客观世界所触发的主观情操的表现。”(《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
5.“(诗)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的感动里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田间的诗》)……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胡风上述论断所说的“诗”,不是一般的徘徊于文体知识层面、日常生活常识的普通“诗歌”概念,而是类似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抒情诗”范畴的运用——在哲学美学层面思考艺术的普遍规律,又具体关联创作实践规律体现的认识、领悟,是对于艺术本体内涵的特别审视及其概括阐释。从偏重于描述主客观一般“互动”的《略观战争以来的诗》,到强调主客观“化合”及其创作主体语言运用的《田间的诗》,胡风依据田间抒情诗美学特征的本体分析,在《给战斗者·后记》中,将其主客观化合论思想,从“诗”的创作论层面,成功建构、提升为艺术本体认识的哲学美学原则,胡风抒情诗观念形成过程的美学意义及其学术价值是有待学界深入研究的。
三、鲁煤:抒情诗与剧本相关文学语言的美学个性问题
苏珊·朗格说,抒情诗创造出的“在记忆中形成的”“虚幻历史”的现实,“是一种充满生命力思想的事件,是一次情感的风暴,一次情绪的紧张感受……是一段真正的主观的历史”[1](P300)。胡风说“真正的艺术是从生活现实产生的”,“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只能是:作家得深入作为题材母胎的生活现实,紧张起他的全部精神力量和生活现实搏斗,使生活现实里面的历史真理变成他自己的血肉的要求,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作家才能够反映现实。”[2](P83)两位美学大师所论话题并不一致,但是,胡风所论“真正的艺术”,如果特别指代他最喜欢的抒情诗,两个论断的美学内涵不但完全相通,而且互为补充。这种类似“超级链接”的美学思想关联,是因为近期连续阅读《鲁煤文集》,由鲁煤创作文学语言的美学个性问题,所触发的理论思考内容之一。
鲁煤是中国解放区著名剧作家、七月派诗人。收入《鲁煤文集》的诗集《在前沿》、话剧卷《红旗歌》,文学博士蒋安全分别为之写了《序言》和《代前言》。《在前沿·序言》论鲁煤的诗,题为“这是一座沉寂的火山”[3](P1)。鲁煤诗集《扑火者》(曾列入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1月初版的《现实诗丛》),收入诗人1937年到1948年在国统区、解放区的重要诗作,是经胡风亲自辑录、严格筛选、认可的作品。引起笔者深长思之的问题是,有着出色审美判断力并且抒情诗创作经验厚实的胡风,读到鲁煤写于1939年夏(时年16岁)的《难童之歌》时,就深为其中托付河水(淅水)表达作者对家乡和母亲思念朴实的诗句感动,下了“又一个小天才”的评语:“静静的淅水,尽情地流吧/请你绕道流过/被日寇侵占的我的故乡/把我滴在你胸前的/思乡的热泪/带给我亲爱的母亲……”胡风“小天才”评语的根据,大概应运用苏珊·朗格“抒情诗最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美学原则,关注“诗人正在抒发着自己瞬间的情感与思绪”,“现在时态”文学语言个性表现的成功运用与否,以及胡风主客观化合论的抒情诗论断,来认可这首抒情诗语言形式的“天成”表现;而不是斤斤计较于诗的建行、用韵等外形式后期工夫的语言技巧。
诚如蒋博士的评述:“1944年初,鲁煤来到河南伊川县白杨镇的知行中学教书。由于在国民党四十军中当官的同族长兄向他披露了国军的种种投降、腐败行为,以及他受已去延安的大哥的影响,鲁煤心中深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具备了战士与诗人的特质。在这个时期,他依凭真实的生活,并借鉴自己读过的别人的诗(主要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中艾青、田间、阿垅等人的诗),本能地写出了《表》这首相当成熟的诗。鲁煤的诗友徐放曾对我说:‘《表》写得多好啊,结结实实的。’《表》是怀念因中共河南地下组织遭破坏而潜伏延安的大哥的,由大哥留下的一块怀表,将‘我工作的世界’与‘大哥工作的世界’连接起来。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故作高玄的警句,但每个平常的方块字里都流溢着令人无法抗拒的思念亲人和向往革命的情愫。”[3](P3)《表》之成为“相当成熟的诗”,“结结实实的”,主要在于诗人思念哥哥“瞬间的情感与思绪”,自然借助于“表”的核心意象及其口语形式,真实而饱满地得到了表达,同时抒情诗体式的外形式完整,而文学语言的情/思表现非常符合抒情诗人的心理特征与年龄个性,抒情诗的艺术美得到完美的表现。
鲁煤1944年9月考入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政治上加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东北救亡总会”,参与组织艺专的抗日、民主学生运动,是年轻的“精神战士”和“站在实际政治斗争最前沿的战斗者”,“业余”的新诗写作得到胡风认可和直接的创作指导,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抒情诗作品。从史实来看,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和小说是《希望》的两个占有很重分量的版块。绿原说过:“《希望》时期胡风文艺思想更成熟更完整,他所反对的目标也明确了,那时候关于所谓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意见,在《七月》上还找不到,到《希望》时明确地提来出来”[2](P283)。由于刊物相关的“‘文化批判’过多地吸引了读者的视线,尽管《希望》上刊登的诗歌和小说总体上都较《七月》时更成熟,但除了路翎、绿原等后来成了‘分子’的作品之外,其余的均未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2](P285)。 鲁煤“七月派”风格的抒情诗,一般读者感到生疏,原因即在于此。写于1945年春的抒情组诗《牢狱篇》,鲁煤将其作为自己诗作成功与否的试金石[3](P4),就在于明确认同胡风做“第一义诗人”、“作家主体与表现对象完全融合”主客观化合的创作原则;抒情诗组诗《在一九四六年的恐怖中》,《希望》第六期准备全部刊用,被国民党报刊检查官抽掉所谓“时局不容”的三首,仅《在一九四六年的恐怖中》《默悼几只扑火者的死》《爱花》《喜悦》等四首得以发表。如《默悼几只扑火者的死》:“箭 /射向靶 /你 /射向火 //小河 /奔突、 冲撞、搏击/追求海/你/奔突、冲撞、搏击/拥抱火//火/火呵/以它兽性的贪婪/吞食你的生命//你/你啊/以你心血的异彩/爆破这寂寞的黑夜//呵,死了/你——/那么残酷/又那么宁静//死了,你/甘心瞑目——死于追求/死与理想……”[3](P38)。这首诗有一个副标题,引用鲁迅《野草》的散文诗句:“对着灯默默地祭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理想、信念、抱负;奋斗、追求、抗争;痛苦、死亡、牺牲;大爱、大恐怖、大恨……1946年中国人民抗战救国的时代情/思,“生活现实里面的历史真理”,如此这般借助内涵深沉、丰富诗的语言,转化为诗人“自己的血肉要求”,可见鲁煤接受胡风抒情诗观念的实际影响,其早期抒情诗语言的美学个性,值得深入研究。
《天才的种子 坚劲的老松——为鲁煤话剧集说几句话》,是蒋博士为《鲁煤文集·话剧卷》写的《代前言》。文章开头的三段话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
即使放在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文学通史上看,像鲁煤这样一批作家也是无法回避的。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理想是最光辉的,其创作也是最美好的。轰动也罢,沉寂也罢,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无疑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况且,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发端。
鲁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执笔完成了具有轰动效应的戏剧作品,这就是被收入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出版的《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的《红旗歌》。胡风、周扬这一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冤家对头”,因为同样具备“观千剑而识器”的艺术慧眼,都曾对这个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戏剧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果人们有兴趣,不妨打开尘封的历史,感受一下这个戏从解放区走向北平(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创下的几多记录、赢得的几多好评。
“我好像天生就是写戏的!”有一次,在与鲁煤讨论其话剧创作时,朴实谦和如陋巷野老的他,突然兴奋地冒出了这么一句“狂话”。他的含意是:他根本没有专门学过戏剧创作,更不要说什么戏剧理论,充其量当初也就是读了几个中外名剧而已。但为了给剧团提供上演节目,他竟敢于拿起笔来写戏,并一写就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喝彩。这情状,能不说是天才么?但是,他事后又嬉笑抵赖,不承认自己会说这样的“狂话”。而我觉得那正是他心迹真实的流露,即使他真的没说出口,心里肯定这样想过。[4](P1-2)
蒋博士认为鲁煤从抒情诗创作到话剧创作,似乎一出手就得到美学大师的首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迄今没有进行 “科学总结”、“准确评价”,“无法回避”的“文学史现象”[4](P2)。在我们看来,作为学术问题,最能展示鲁煤文学成就的话剧创作,戏剧大师的评价可能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看了 《红旗歌》。不错。”这是老舍看了《红旗歌》舞台演出后,当晚日记中写下的评语。“台词儿写绝了!那些台词是怎么写出来的呀?”[4](P384)这是参加剧本创作讨论后,《红旗歌》导演陈怀皑转述曹禺阅读该剧剧本印象最重要的一句话。两位戏剧大师的评语,一位着眼于舞台演出的艺术效果,一位画龙点睛指出剧本成功关键所在的剧本语言特点,互相印证《红旗歌》文学语言,作为“红色经典”的美学价值。
《红旗歌》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鲁煤曾对创作伙伴陈淼总结过写作此剧的主要体会:“我能执笔写出《红旗歌》来,主要靠两条:其一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其二是胡风强调和人物融合的理论。 ”[4](P376)周扬在领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时代的文学精神方面,给予鲁煤剧本创作以正确引导,让他“懂得应该这样地生活和写作”[4](P371);胡风则在戏剧人物创作的美学原则方面,帮助鲁煤打开舞台艺术话剧剧本台词写作的大门。《红旗歌》剧本语言的基础,首先是抒情诗等创作积累的文学语言写作经验,其次是多个话剧剧本写作的积累。鲁煤说:“我是河北农村长大的,熟悉家乡农民语言。后来,在蒋管区读中学、大学,说的是知识分子语言,并用它写诗。1946年进入解放区后,开始为工农兵写作 (特指剧本——引者),马上就学习、运用群众语言……在写《反对三只手》《里外工会》时,请工人同志来坚定、修正、丰富工人人物的台词,把刻苦学习发挥到了极致。到后来接着写《红旗歌》时,我不但对所要描写的工人生活已了如指掌(那都是自己参加过的),想象、虚构起来能随心所欲,而且运用语言也已得心应手了。”[4](P370)从生活语言到抒情诗的文学语言,鲁煤显示了他的语言天赋;从抒情诗的文学语言转型为舞台艺术《红旗歌》剧本台词的文学语言,鲁煤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语言才能。鲁煤创作受外力扭曲而终止的残酷事实,怎么不会让惜才如命的胡风痛心疾首,愤激写入文艺政策建议的《三十万言书》呢?
[1][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鲁煤.鲁煤文集(1)诗歌卷·在前沿[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4]鲁煤.鲁煤文集(2)话剧卷·红旗歌[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