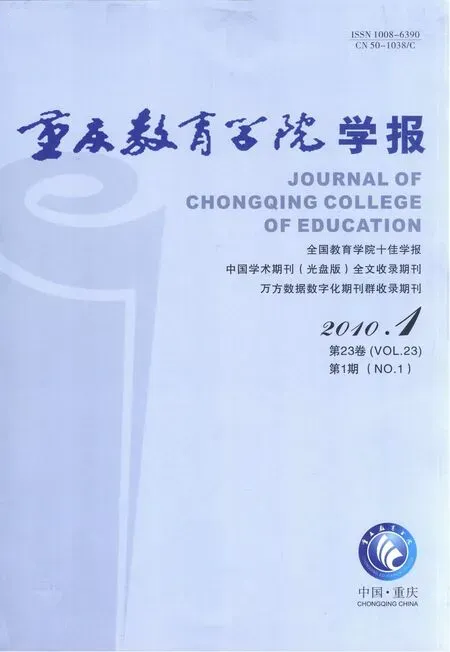如何重新理解“五四”
2010-04-04周伟薇
周伟薇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时间很快,充满了激情与理想以及在后来的岁月中被争论不休的 “五四”,如果以其被命名的那一年(1919年5月4日)算起,竟有90年。“五四”因为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其诞生之初至今就被不停争论且被不断重估,褒之者谓之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贬之者认为“五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大灾难,甚至将“五四”与文革并提。“五四”,在物理时间上,是过去了;但其影响至今连绵不绝。理解“五四”、整理“五四”,至今仍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一、理解“五四”
对于“五四”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是其中一个角度,我们不妨把|“五四”放在历史文化交汇的语境当中去,并在这种语境中去贴近、去理解那些看起来激进的“五四”人物。
(一)历史文化交汇语境中的“五四”
“五四”,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无论现在对它的褒贬与否,都不可否认它巨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外域文化输入,一次是汉唐时期佛教文化输入,另一次就是明万历至今的西方文化的输入。“五四”的新文化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中的一次高峰。
第二次的文化交汇不同于第一次的文化交汇,第一次的文化交汇是中国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因为自己国力的雄厚与文化的同等发达,而有了宏阔包容的文化气派。但是,第二次的文化交汇的情况却是中国要面对文化水平远超过自己的西方文化。这是一股波及范围更广的文化交汇,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整个非西世界被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现代化”进程,说得露骨一些就是“西方化”进程。第二次文化交汇在接触的初期,即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的耶稣会士他们带来了欧洲神学的同时,还带来了西方文化,打开了部分中国人的眼界,近代人士如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甚至康熙大帝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西学。但是很遗憾,随着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西学东渐”的进程在雍正之后中止了,清帝国的大门对外关闭,但是很又被打开了,而且是被武力强行打开的。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正如当时其他非西世界一样,以一种血和火的形式,情愿或不情愿地被卷入西方化进程。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候不再陶然于天朝帝国的地大物博,随着与西方接触日深以及西方侵略加强,民族危亡和文化落后的危机感加剧。凡尔赛合约的签订打破了国内人士对西方的幻想,“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时候爆发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了一种焦虑感,尤其是“五四”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焦虑夹杂在一起。用杜维明的话来说,就是中华民族气不顺,“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局促不安的无力感,但这种压抑之情在知识分子身上显得特别严峻。”[1]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落后的焦虑,尽管也有人在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去寻找自信的基石[2],却难以掩盖整个民族的失落、自卑与焦急,而知识分子因为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来自传统与西方的信息,无疑是承担更多的民族焦虑。这种焦虑感直接催生了“五四”的激进主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先锋人士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对传统的批判、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以及白话文运动是过于激进了。有时候,时代形势的峻急并不给我们坦言一切的机会,在某些情形下,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策略。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曾过一个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3]鲁迅在《随感录》也说过要在一个黑屋开窗,必遭反对,但要说把整座房子拆掉,那么也许可能开出一个窗户来。当我们在批判“五四”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并把这种断裂与中国当代的道德滑坡视阈的平面化与单维化等问题结合起来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当代与“五四”的历史处境不同,能不能对“五四”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二)中西文化交汇语境中的“五四”人物
当我们回过头看“五四”那些在今天称之为激进主义者的那些人,比如鲁迅、胡适等人,难道我们没有发现他们这些人正是学贯中西的人物?对于传统文化,他们不似今天的我们如此陌生。郭齐勇教授说“今天,像我们这些忝列高校文史哲教席的‘教授’、‘博士’们尚不得不借助工具书才能勉强读懂《尚书》、《诗经》,大学生们尚分不清《四书》与明代小说中的‘四大奇书’,还有所谓著名青年诗人不知《老子》、《庄子》为何物,到德国去大闹笑话。”[4]在1919年之后,中国的经典和历史研究,在清代汉学研究的今文学派以及西方所引进的怀疑主义与考证的方法之后,中国古史观念改变相当大。这正是在胡适、梁启超和其他学者的努力。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正是有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功底。(胡适在这方面的贡献,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开端,其贡献有:(1)他最先运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2)他比旧式学者更注意古代哲学家的生卒年代和他们著作的真实性;(3)他对墨家学派,尤其是它们的逻辑思想的卓越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是独一无二的;(4)他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作者、版本以及其故事演化的考证,激发了公众对文学的兴趣,为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传统树立了榜样[5]。鲁迅在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较今人深厚许多,在1908年鲁迅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以近半生之数校阅《嵇康集》,研究过佛经,刻印《百喻经》,编纂《唐宋传奇集》,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之时仍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墓志拓本,其50岁之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为经典著作。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激进主义者,其传统的背景不仅体现在学术上还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中国是一个以孝为先的社会,胡适和鲁迅都十分顾念母亲的辛苦,对母亲都非常孝顺,在一些人生大事上不敢违背母意。当他们提出建立新文化,有其中学背景,提出反对旧道德,有其受传统的伦理纲常束缚之背景。这些在今天看似不可接受的激进提法,有其深刻的背景。如果因为今天的我们对传统的陌生而去指责 “五四”是传统文化的大灾难,是不是我们没有从历史地同情理解“五四”,我们仅仅从“五四”的口号来断定“五四”?这种不考虑背景的理解,又能多大程度理解“五四”呢?而我们这种看似保守实则偏激的情绪,是不是也与“五四”的焦虑感异曲同工呢?
自80年代后期林毓生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和余英时先生的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两文发端以来,对于“五四”的激进与反传统,学界对于“五四”的看法骤转,与80年代复兴“五四”、提倡新启蒙相反,90年代学界开始反思“五四”、批判“五四”,新保守主义泛起。对此,邓晓芒先生指出,“当人们众口一词地指责 ‘五四’思想的浮躁时,自己却如同一个顽童拂去一盘下输了的棋一样,堕入了另一种情绪的浮躁”。[6]姜义华与陈炎先生也指出“激进主义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则又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一旦风行起来往往暗藏着危险。因为,将学术研究简化为一种主义的做法,本身就是危险。”[7]
二、整理“五四”
“五四”,如果仅仅对此有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那么还停留在理解的粗浅阶段;如果不去整理“五四”的成就与不足,那么一来无法深刻地理解这个特殊的运动对于历史的影响与效力,二来也无法应对来自保守主义者的进攻。
(一)关于“五四”研究的整理现状
对于“五四”,人们历来是争论得多,而整理得少。2008年,“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近90年的历史,研究的资料不可谓不多,但是很多是分散型或专题型的研究,缺乏一种全景的整体性的研究。周策纵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英文初版《“五四”运动史》中就曾慨叹“有关‘五四’的文字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然而这些书刊却都是争论性的居多,描述史实的极少。”[8]时间在周策纵先生说这话时,又过了近40年,我们现今的“五四”研究状况还是如此,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我们还是更多地将时间与精力放在争论上,而很少去做全局性的整理性工作。
当然,“五四”作为一种涉及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一个多面性的历史事件,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整理、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曾有一段时间对“五四”的研究有一些政治禁区,很多研究不能与政治对“五四”的定位冲突太大,而政治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的政治倾向而对“五四”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现在研究政策有所松动,而且专题性的研究也为全局性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面对新保守主义对于“五四”的诘难,我们是有必要重温也有必要整理“五四”了。新保守主义的诘难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温“五四”、整理“五四”、反思“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二)“五四”是否调整了原有文化传统?
在“五四”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后,在走过近90年的历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五四”看作传统的一部分?在更往后的将来,人们是不是以看待佛学汉传一样看待“五四”对西学的引进以及“五四”对原有文化传统的调整?
传统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是不乏交流与变动。从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20世纪初1000多平方公里国土,华夏的文化在民族内外地域内外都展开过文化的交流,甚至是文化的冲突。在内,以中原的农耕文明为主,与北方游牧文明、南方游耕文明长期的交融与冲突一直存在,中原的衣食坐行乐都受到影响与改变;于外,佛教的传入,其思辨的缜密与繁富、教义的精深与不可思议对中国的哲学与伦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汉化产生了禅宗,佛教的转化生成了宋明理学。这其间的交流与融合历经了千年,当我们急急地指责“五四”的激进,是不是我们也太激进,没有给“五四”留够时间去转化出新的文化生长点?更何况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五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成效在政治、文化、社会、文学上的效果尤为显著。
“五四”它给了一种原来传统所不曾有的或者说历史上曾有的但在“五四”之前以及当下都相当式微的某种精神和行为方式么?
邓晓芒先生认为“五四”精神有:1.怀疑和批判的精神;2.自我忏悔的精神;3.对进化论的超越[9]。邓先生所提出的这三种精神,我们都可以在佛教哲学或儒学中找到近似的精神或观念。佛教反对迷信,要求知而后信,这就是一种怀疑精神;佛教有经忏的仪式,也就是一种自我忏悔精神;儒家也讲求一日而三省吾身,这同样也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自我忏悔;佛教的观念与进化论是相反的,它是一种循环的观念;而儒家是好古,美好之事往往追至尧舜禹,孔子一生克己复周礼。这些精神尤其是前两种精神在明清之际到“五四”之前是近乎被遗忘的,当然不排除在个别的人身上存在。“五四”它尤其带来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概念的细分,那么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个性解放、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打到孔家店等等,这些“五四”时期关键词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即精神的独立。这是“五四”时期给我们的丰厚馈赠。王元化先生认为个性解放后来成了一个讽刺。个性解放后来被扭曲与压抑究竟是“五四”所暗含的趋向还是原来文化的积习太重?这是值得讨论的。但如果把时间限定在“五四”期间,仅仅从意图上去分析的话,并不做一种过于苛刻的要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在当时确实成为了一种时代的目标取向。
(三)“五四”对原有文化传统的调整
“五四”后来被定义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不独包括精神层面,还包括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五四”的独立精神,通过报纸、期刊等大宗媒介以及自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的传播,直接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文化由精神层面扩散并进而向制度层面扩张。这些文化层面是相互交融。
“五四”的成就,以下主要从精神内部、社会后果以及制度方面来谈。
1.精神内部
精神内部,这是内涵最丰富也最富争议性的一个部分,绕开还在争论不休的碍地,比如“五四”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10],比如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实用理性的世俗关怀等等,我们直达“五四”所提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所直接引发的两大文化事件:一是文学革命,二是整理国故。文学革命当中,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1]文学革命实乃独立思想之产物,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使思想有了较为轻盈的翅膀,而让下层百姓都可以乘着语言的翅膀飞翔。“五四”之后,几乎所有的杂志、报纸、期刊都开始使用新文学语言。而杂志、报纸、期刊甚至教材,这些大众媒介和教育媒介语言方面的革命带来了又进一步带来了思想的大交流、大解放。重估遗产和整理国故中,把传统的权威性打破,依据新思想重新批判传统,这也正是批判怀疑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即使是有一些反对者,也在客观上指出了传统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一文中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12]中国出产的太监和女人的小脚,便是恶习的例子。三纲五常发展到极端就是对个体的极端不尊重。袁伟时先生指出:“五四”时期对人格的尊严,对人的自由,对学术的独立探讨精神,这些价值正是当前我们开发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发展有创见性的理论思维、道德理性和精神价值的必要条件。”[13]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集权是日趋严密。商周尚是狭义上的封邦建国的封建国家;自秦之后,中国的形态变转为中央集权;而在唐代所开创的科举制之后,天下读书人就被尽揽网中;纲常伦理在宋代理学之后就相当地束缚人,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仅是极少数人的事。“五四”是撕开了这一道口子,在一个由个人意志统治的社会,给了民众以自由交流与思考,文学革命所提倡之白话文正是这一自由交流与思考的工具;整理国故,又给了民众反思本土文化的契机与过去相异的思考方式。独立精神与自由思考,这正是讲究纲常伦理的传统文化所欠缺的,无论后来的道路如何改变,“五四”的这一初衷以及在随后的社会后果中是显而易见的。
2.社会后果
社会后果,这是“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最显而易见。“五四”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已经由知识分子布传给青年学生,政府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已经不易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王土”的意识已转成“国土”的意识。在“五四”运动中,学生提出了“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外抗强权”的口号很快地有了效果,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总统提出辞职,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自那以后,这些口号很快就被各地政党采用,在后来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主义的运动。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了 “反帝国主义大同盟”,24个支部很快在全国的主要城市建立起来,社会各界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它的纲领是:通过联合抵制、罢工、和其他被压迫民族合作的方式,废除和取缔一切租界、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驱逐所有外国军队,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14]后来影响中国政局的两大政党(国共两党)在这种氛围下开始合作,北伐和国民革命由此有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社会基础。“五四”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让商人和城市的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得到了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工会正是在1919年成立的,由26个归国的工人组成。那个时候,工会组织和商会组织遍地开花,街道联合会、工业协会、电器工业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全都在那几年迅速地冒了出来,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运动和罢工。
这些民众的运动可以如此公开,并影响到政府意志;工人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自发地举行组织和活动,这些在传统社会,要么是被视为叛逆,要么是不可想象;而在“五四”,这些都成了现实,甚至是潮流。这些民众运动的出现,当然有政权不稳固的因素,但新文化运动在其中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3.制度层面
“五四”运动再一个硕果即制度上的妇女解放。自宋以来,汉族人看到少数民族的舞姬裹脚而舞姿态娉婷,就要求汉族女子也缠上脚,自那以后,中国的女子基本上就是男性变态审美观念左右下的半个残废。“五四”时期,三纲五常被打破,女子裹足缠脚的被放开,这是身体上的解放。随着三纲五常打破的还有家长的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的提倡,让女子有了人身与婚姻的自主权(尽管这有很长的路程,但“五四”开了个好头)。妇女不再作为附属品而开始作为独立的人出现在家庭和社会中。“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15]在那个时候,妇女开始了要求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受教育权,甚至对政治事件有了浓厚的兴趣,比如当时以战国 “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 “四公子”。1920年,长沙妇女参加游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1921年湖南女界联合会提出实现妇女的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选举和被选举权、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以及婚姻自主权利(后来被称作“五权运动”)这些运动在湖南、浙江、广东都有发生,甚至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比如,湖南省立法中指定了妇女参政和人身自由的条款,并有一妇女被选入了省立法机构。[16]
当我们今天一夫一妻地婚姻受到制度的保障的时候,当女子可以平等地接受教育,平等地参与政治和工作之时,我们是否知道这正是“五四”在那个时代的努力之一?传统社会的一夫多妻制,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传统社会女子的无才无职,这些是我们内心想要的么?我们是否对“五四”心存感念?“五四”的这些成果化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生活其中,并因为习惯此种生活方式,也不再追问什么时候一夫多妻被废除了,因何而废除?我们真的是很善于遗忘,以致我们在生活中碰到道德滑坡、出现对传统文化的隔膜就开始抱怨”五四”。
以上的三个方面仅是最显而易见的,“五四”作为一个影响面极广的运动,其成就要远远超过以上所概括的。
“五四”是未竟之业,“五四”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继承被超越,这正需要保守主义、启蒙主义、新批判主义的共同完成,守成与创新始终是相伴随的。
那个时代没有给“五四”足够的可以从容承接传统的空间,而现代的历史语境给了我们超越“五四”的平台。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化的要求,过于西化的现代,对传统文化陌生的现代,以及现代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企望,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重视我们的传统资源。“五四”的不足,可以在今日加以弥补与超越。
[1]杜维明,袁伟时.“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J].开放时代,1999,(2):26.
[2]对这种现象,冯友兰先生曾有过描述:“中国民族,自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见冯友兰.三松堂学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4.
[3]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A].独秀文存[C].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564.
[4]郭齐勇.评所谓 “新批判主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3):1.
[5]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447-448.
[6]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J].科学经济社会,1999,(4):12.
[7]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J].开放时代,1997,(2):37.
[8](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英文初版自序[A].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5.
[9]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J].科学经济社会,1999,(4):14-16.
[10]王元化先生将“五四”的思维模式概括为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其中意图伦理和功利主义这是一种激进思维模式还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姜义华先生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见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 [J].开放时代,1997,(2):38-41.
[1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N].新青年,1917-01-01(2).
[12]吴稚晖.箴洋八股化的理学 [J].科学与人生观,1923,(2):8-9.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449.
[13]杜维明,袁伟时.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J].开放时代,1999,(2):20.
[14]高希圣.社会科学大词典[S].上海:1929:116-117.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370-371.
[15]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1928.365.又见林语堂.吾国吾民[M].纽约:1935:69.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372.
[16]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译.岳麓书社,1999.372-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