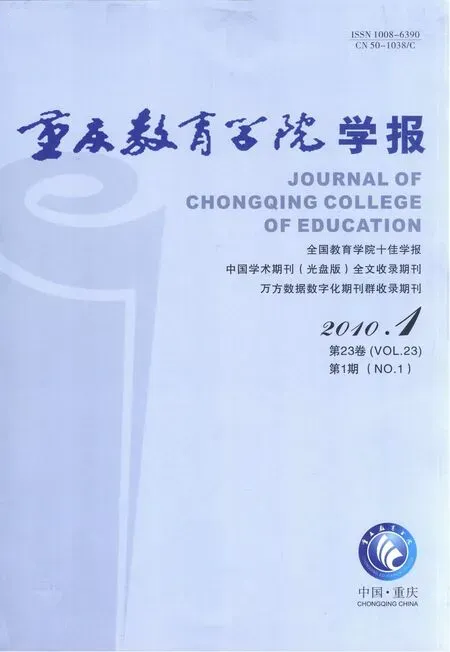服饰象征理论视野下的悲情秦良玉——赵藏本《秦良玉》京剧剧本之女性主义研究
2010-04-04聂树平陶永莉
聂树平,陶永莉
(重庆市长寿区龙溪中学,重庆 400000)
一、赵桐珊藏《秦良玉》京剧剧本说略
(一)《秦良玉》京剧剧本版本情况
京剧剧本《秦良玉》,为赵桐珊藏本[1],收入《京剧汇编》第 23集,由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北京出版社1957年1月出版。共计21页的篇幅,一共22场,大致表现了秦良玉平台召见、回川杀贼、断臂全贞几个事件。作为传统京剧剧本,探讨其与史实相去几何,非本文所关。本文意欲关注在于民众喜闻乐见之京剧艺术中,秦良玉形象之嬗变及哲学意味。
(二)赵藏本《秦良玉》与尚小云之紧密关系
在戏曲中较早以秦良玉为题材的有《芝龛记》[2];在京剧中创排秦良玉剧目的有尚小云[3]。此处赵氏所藏剧本与尚小云有相当紧密关系。一是因为藏者与尚小云共有“正乐三杰”[4]之称号,两人艺术渊源甚深;二是此书出版于1956-1959期间,此时尚小云任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应与尚小云这样的京剧大师有着联系;三是经过笔者比对《尚小云专集·秦良玉》[5]中“本事”与“唱词”,发现尚小云所演秦良玉有唱词“恨李闯贼流寇为患,他要夺我主爷锦绣江山”等,在此本中就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此种版本之与传统秦良玉剧本有大量保留,但是个别唱词有微调的关系。
(三)解读赵藏本《秦良玉》之学理资源
焦菊隐说:“小说是引起想象的艺术,而戏剧是引起感觉的艺术……一切人物思想行为,一切时代生活环境,都要由它们自身以具体形象、以行动,出现在舞台。一切都要演出来,叫观众看见,而且叫观众一下就完全看懂”[6]。但是,眼见未必皆可坐实,感觉只是戏剧接受时的起点,其后还需鉴赏、分析等,正如伟人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此,对剧本《秦良玉》我们也有必要深入剖析,使此剧得到新的演绎、发展可能性。而该剧,从女性主义角度深入分析,至少可得益于如下学理资源:
1.妇女史研究
杜芳琴指出:抗日战争“反映到妇女史的研究方面,延续前一阶段张扬妇女贡献的传统,不是对才女的表彰,而是对历代女英雄的呼唤。像……危急时率兵解围的秦良玉……等故事都编成了出版的热销书,时代要求妇女或希望通过宣传妇女英雄激励人们的民族精神,投入抗日救亡战争”,但是当时所得成果——“对妇女史在理论、概念、解释框架方面的发凡起例,……成为后来希望有所突破的障碍”[7]。当前,对秦良玉研究的拓展、突破,如果缺乏社会性别理论的介入,是难以有其重大推进的。
2.文学史研究
王德威说:“男扮女装,这一舞台艺术及欲望,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持续上演。其盛况造就了梅程荀尚等‘四大名旦’”[8],该说法导源于其晚清小说研究,但对本研究有可资借鉴之处。因为,秦良玉本为女性,但是既称“巾帼英雄”,则已具“女扮男装”/“女行男事”意味,而由男性演员表演的旦角戏,是以“男扮女装”而凸显其独特意义,于是造成实质上的“双重反串”,这是颇值得关注的。
3.思想史研究
葛兆光指出:“用流传的小说话本戏曲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讨论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很有效的途经。……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国家处境、流行的故事主题、它所涉及的观念,各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一般阶层的感受、焦虑、紧张、情绪,而这些感受、焦虑、紧张、情绪所呈现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和经典思想的一个背景与平台,证明他们思考的合理性和紧迫性”[9]。
(四)赵藏本《秦良玉》的时代定位
对《秦良玉》的深入解剖,有利于深入了解秦良玉这位英雄在后代的形象变迁。该剧本虽初版于20世纪50年代之中国大陆,由于特定原因,已删除指责流贼造成公众不安的那些唱词。然而毕竟在总体上继承了尚小云所演《秦良玉》的剧情、唱词等,故此我们可以认定,《秦良玉》剧本塑造了20世纪中期及其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秦良玉形象。对于秦良玉文化在未来的研究拓展方向,拙文《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综述》提出“引入女性主义”等设想,这里姑引如下:
西方学者琼·W·斯科特认为:“将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10]。就秦良玉研究来说,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将会对我们的研究换取更多的阐释空间。迄今已有文献注意到秦良玉的女性特质,如相抱轮对秦良玉的称呼直接是“英雌”而非习见的“英雄”,“秦良玉的英勇行为,竟能提高妇女的地位,不特能使和男子平等,甚至使男子生愧,真可谓伟大的人物”、“伊并不像今日新潮流的号称新女性的女子,专在爱情上用工夫,甚至在虚荣的观念下找结婚的出路,伊不是这样”[11];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说,秦良玉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认知。传统中国文化对男性的扩张型人格,女性内敛型人格在其身上似乎失去了效用,因此秦良玉能得以以女儿身得到 “诚可谓有丈夫风矣”[12]的高度评价;清初诸多史学界人士都认识到:“石柱秦良玉,以妇人而列武臣之传,嘉其义切勤壬,不以寻常土司例之”[13];“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14]——这可进一步认识到证明秦良玉对女性固定形象的挑战是比较成功的,并得到了官方 的认可。[15]
二、《秦良玉》剧情之 “服饰象征理论”解读
(一)“立主脑”与《秦良玉》之“其人其事”
1.“立主脑”之说
李渔说:“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16]。就《秦良玉》而言,此人即秦良玉,此事即其“服饰象征”具体内涵之变异。
2.“服饰象征理论”之引入
“服饰象征理论”,学界国内学界提者尚不多见,现略作阐释如下:
对源远流长之中国文化而言,“服饰象征理论”有其服装史学、儒学思想史双重依据。韩国学者成秀光研究服饰的起源时,提出:“象征理论认为,服饰历史是从人类最初佩带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的时候开始的。原始人类中经常有一些人佩带某些战利品来显示自己勇敢、强健和有技能的形象,这就是最初的装饰品。……在某种意义上,服装是一个人内心的表白和个性的表示。原始人类中的一些人为了充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地位、身份和力量,经常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来装扮自己,而人类对服装的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现在”;葛兆光谈“‘儒’注重服饰的象征意义”时也深刻指出:“注重服饰的象征服饰的象征意义,本来正是早期巫祝史宗所形成的习惯……服饰象征人的身份,修养甚至状态,而象征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的身份、修养和状态,通过这种‘垂衣而治’的象征系统,儒者相信可以整顿秩序。”[17]“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象征的意味是极其重要的,一些人相信,这套象征的符号就是事实世界本身,他们整饬有序,就可以暗示和促进事实世界的整饬有序,而它们的崩溃,就意味着世界秩序的崩溃。当人们越来越相信‘名’对‘实’的限制、规范和整顿作用时,人们就常常希望通过‘符号’的再次清理和重新确认来达到对‘事实’的清理和确认。 ”[18]
既有之学界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因此,我们认为,服饰象征理论,既是关于服饰起源、同时也是关于服饰功能的理论。就其起源说,原始人类基于原逻辑思维的“灵魂互渗”、“万物有灵”等观念,未知世界中诸多神秘力量和权威需要用服饰来暗示自己的存在,于是产生服饰中的诸多严密的规则,从颜色到形制,都成为重大问题;就其功能说,服饰在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融合了儒家之阴阳、五行等思想等学说,参与到现实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斗争中,此时服饰之价值绝不限于形而下之保暖、蔽体等功用,而更多体现为政治等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限制、规范、整顿以及表现、监督、控制等形而上之功用。
3.秦良玉传世遗物——“蜀锦征袍”
“秦良玉的遗物:蓝缎绣金蟒袍、黄缎绣金蟒凤衫、镏金铜胄(头盔、甲衣)、象牙朝笏、朴刀、缎绣花鞋、牛皮盔等,这些珍品现存于重庆市三峡博物馆”[19],这些都是来自昔年四川省石柱文化馆(现为重庆市石柱县文化馆)之传世实物,其中崇祯皇帝赠袍本有两件,但是剧中只有一件,可见虽源于历史,但并未受史实局限。剧中之袍,仅称“征袍”,其原型未必能坐实到具体哪件上,但此袍得与失、完与残,所伴随之主人公性别身份等象征意味之增减、变异则是解读此剧深层意蕴所宜用力之处。
(二)由“服饰象征理论”分析《秦良玉》剧情
由“服饰象征理论”而言,此剧围绕“蜀锦征袍”而展开。在此我们浅析如下:
1.“平台召见”:服饰之获得与象征之预实现
全剧情节三大部分。其第一部分即第一场至第三场,“平台召见”:为服饰之获得与象征之预实现。此几场戏涵盖司礼监王承恩上台自报家门、秦良玉营中接旨、崇祯帝平台召见秦良玉等剧情。其中,重点在第三场。第一场、第二场主要是叙述性的交代而非表现性的刻画。
在第二场中,秦良玉上场自道:“巾帼英雄,扫群凶,西川望重”[20],其中“巾帼”,本指“一种首饰,宽大似冠,高耸显眼,内衬金属丝套或用削薄的竹木片扎成各种新颖式样,外紧裹一层彩色长巾而成。……先秦时期,男女都能戴帼,用作首饰。到了汉代,才成为妇女专用。”[21]在这里,巾帼一词已暗示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英雄”,是秦良玉一切作为的概括描述,“扫群凶”是其战斗行为,西川望重是其战斗结果——“我本巾帼彦,奇谋胜伟男;功名标石柱,女将震西川”——“巾帼”、“女将”中的女性色彩,“奇谋”、“功名”中的英勇业绩,在这首上场诗中包含张力的表现。四句诗中,第1、4句都表明了女性身份,第2、3句都体现了男性本该拥有的业绩,如今却被秦良玉所取得,这首看似波澜不惊的定场诗中夹杂着一种性别对峙。
然后,秦良玉念白:“这几日闻阁帅杨嗣昌有驱贼入川之计。本帅急于回蜀,因朝命未下,故此迟延,叫人好生焦虑也”,此时正好接到圣旨:“秦良玉平贼有功,特赐蜀锦红袍,以示旌赏”,崇祯皇帝深感秦良玉功劳之大,故欲借此服饰之象征意味加强秦良玉之责任感;而王承恩之吩咐:“秦将军,今日召见,可穿万岁所赐之袍”,尤见此袍之象征意味,在神圣高远之庙堂更显突出,可谓妇孺皆知。
秦良玉临行有令:“众将不许离营。众女兵,带马入朝”,此与一般将领之不同,在于所带之女兵。众女兵本位普通女性,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跟着主帅秦良玉,舍家别子、背井离乡,而今走上战场,实属非常,她们是秦良玉部队的成员,也是秦良玉的情同姊妹的老乡。她们虽未得到皇帝亲赠的红袍,但是一样实现了从家庭妇女到疆场战士的角色转变。她们的角色转变,以及相应的易服,都为后面陆逊之挑逗埋下伏线,正所谓草蛇灰线,伸达千里。
第三场戏,秦良玉上得平台,崇祯口占一诗,以表其功:“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里依然有男女两性之对比与反讽存焉。蜀锦,自古有名,征袍,既是对其已有战功之肯定也是对其未来战绩之期许。“男子”,在此戏中至少含左良玉、陆逊之之流——在此,两者已经或将被推到女英雄的对立面。其后唱词:“可敬可敬真可敬,可敬良玉女将军,愧煞男子无血性,都是贪生怕死人”,正因男子无血性,引得秦将军回川退贼,才引出下文之戏情。
2.“回川杀贼”:服饰象征功能之实现
第二部分“回川杀贼”:表明崇祯皇帝所赠之袍象征功能之充分实现。前面说过,“服饰…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地位、身份和力量”、“服饰象征人的身份,修养甚至状态”,在这部分第四场至第二十场中,主要是叙述性的动作居多,联系到全剧二十二场,在这部分就花了17场,可见观众及编剧对此部分之重视与酷爱。
这17场中,流贼于二郎庙设地雷埋伏,秦良玉识破诡计,将计就计,诱其前来劫营,乘势杀贼,进入夔州城,扫清流贼。除以几处说白展示筹划计之外,本部分特重武打。联系到创演京剧《秦良玉》之尚小云曾“把‘杨派’武生的精湛表演,吸收融化,用在自己的旦角戏里…特别适于表演巾帼英雄人物”,这17场中的武打似为适应尚派而设。
这部分戏中,红袍在身,给了秦良玉杀贼的智慧与力量。在前一部分的秦氏与左良玉等之男女对峙在减轻,秦氏与流贼的对立是正邪对立,而非性别之对立。其中秦良玉曾安排众人“各归讯地,只留女兵在此伺候”——可见,在休息等非军务时期,秦良玉与女兵在一起,虽有休息时光,无复闺阁生活;而张凤怡的自陈:“媳妇在临洺关改装追贼”,固属智举,亦能凑效,说明改装即能增添斗争之力量与勇气。
秦良玉在此关于红袍之说白不多,亦即对自己的性别身份甚少关注,其台词:“众女兵,开城杀!”,联系前场戏,可见秦氏之兵,在其眼中先是女性、再是兵,因此在下令之时,必示性别。
本部分收场时,流贼被擒:“身入陷阱难逃走,好似曹操到中牟。进得帐来用目瞅,女将威风贯斗牛”——表现出了败军之将见到对手时的震惊,此时所见秦良玉,虽是女性,但是“威风贯斗牛”,在其眼中,秦氏之力量、智慧,高抵云霄。
此部分虽未写红袍,但是所有的战斗,都是表现前一部分征袍、战袍中的“征”、“战”二字,故可见,此部分是前部分象征功能之实现。
3.“断臂全贞”:服饰象征功能之丧失
最后两场,第三部分“断臂全贞”为其服饰象征功能之丧失。其中包含陆逊之奉命犒军、陆逊之见色起心、陆秦等军中冲突、秦良玉断臂全贞等环节。
其中,陆逊之初见秦良玉之子媳,疑为男子,并猜度道:“好一个少年美男……妙哇!怪不得人言秦良玉帐中,多有男妾,原来他帐下有这样美男。想我陆逊之也是个风流人物,此番前去,用言语挑逗于她,若得天缘凑巧,也是我祖宗阴功,父母的德行啊。人言女将风流甚,不知她心是我心?”这其中包含着服饰身份与真实性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服饰看,是男将军,就实质言,是女英雄,矛盾在听信谣言中更加挺进——“人言秦良玉帐中,多有男妾,原来他帐下有这样美男。”
于是陆逊之试探道:“这位少年将军,他是何人?”;秦良玉答:“此乃儿妇张氏,因军中不便改装,改穿男服”,此说可为有理有据,然而陆逊之假痴不癫:“真是巾帼英雄。怎么贵虞侯都是美少年?”——秦良玉感到了难堪,但是她仍能化解这种性别危机:“使君,她们是男子么?侍女们快快换了女装,再来伺候。”——再次可见,秦氏将“众女兵”改称“侍女们”,是为了让陆逊之之流不生闲话。只得让这些女孩子褪下戎装,换上女装。这一安排大有讲究,其一,此举客观上让其属下暂时性放下武器、恢复平静生活的静穆之感;其二,此举主观上自己是为自己只清白作证,孰料此举换来更大危险,从而导致她黯然离开战场。
陆逊之已明白秦良玉非蓄妾好色之人,但却并不死心:“秦良玉这样一个绝色美人,就轻轻放过不成?”于是他以按行营垒为名,以退为进,欲行非礼,顿遭惊天霹雳般的怒斥:“使君作事不思忖,你将良玉当何人?用手拔出青锋刃,斩断左臂表真心。”“我这臂膀一定要斩断的了”,一见秦良玉要自残明志,陆逊之的色胆早已吓飞到九霄云外,只得跪求:“元帅果是贞操凛,不该起下不良心。没奈何只得来跪定,元帅不可自伤身。”
此时一干众人欲杀好色陆氏为主帅出气,秦良玉却委曲求全,自白:“我还替朝廷出力,不敢伤残肢体,这个袍袖却不能留它,可惜御赐锦袍,毁于你手”,此时,情节达于高潮,负载秦良玉战斗象征功能之锦袍被自断袍袖,这意味着其象征意味随之瓦解,即杀退流贼、保境安民的智慧、力量被这残袍所击溃。
此行为实出无奈,不断袖,则有违“男女授受不亲”“女子从一而终”的古训,如自残,则无以尽忠报国;因此秦良玉只能自断袍袖。该戏的最后,秦良玉总结一生战斗,顿生悔意,并要求儿媳等本家族女性不再关注公共生活:“任你巾帼有本领,要比男儿总不能。抬头我把苍天问,因何生我是妇人?……媳妇,从今以后,再不可男装打扮,明日你回石砫司,看守故园,不用随军效力。这军旅之事,原不是妇人本份。”然后秦良玉唱曰:“悔不该习兵法亲身战阵,学男子我忘却身是妇人。今日里恐难免旁人议论,断袍袖洗不了不守闺门”——这似表明秦良玉并未使自己平静下来,还是得回到庭院,避免再生是非:“我是个妇人,军旅之事终非所宜。不如回往石柱司,闭门自守,免遭物议”。
(三)《秦良玉》“主脑”与哲学意味层
1.《秦良玉》的“主脑”
通观此剧,自始至终含一“主脑”,即作为女将军之秦良玉的战袍之象征意味之获得与失去。如果说崇祯皇帝之赠袍为其杀贼行为赋予了国家层面的肯定意味,那么陆逊之的挑逗则瓦解了这种肯定的神圣性,此种神圣事业毁于男性色胆的悖谬,暗示着明朝灭亡之乃至秦良玉悲局之难免。
2.《秦良玉》的哲学意味层
“这些作品深藏着超越时空的人生精义和心理蕴含……就会长久地保持着艺术的魅力”,作品想“流传下来”需要“靠其人生精义和心理蕴含,即其中有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未来的东西。”[22]该戏中的上战场还是回家的争执,男性还是女性,是短袖还是断臂的种种纠葛,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值得后人思考。
三、对《秦良玉》悲壮结局的总结
正史云:“良玉竟以寿终”,而此戏则突出了其悲壮结局,下面结合有关材料进一步分析。
(一)从思想史角度看
从思想角度观之,戏剧中如此表现,是为了满足民众对秦良玉作为公共人物的私人道德上的苛求心理。后人固然不必为真实秦良玉担心遭遇上司非礼的具体处置,编戏者,似只是为了反映以秦良玉为代表的德行与陆逊之为代表的欲望之间的斗争。陆逊之的欲望,未能实现,而秦良玉的德行,从其对丈夫的贞,对国君的忠,都得以充分体现。正如王德威所言:“‘欲望’,我指的是一种对未竟的人、事的向往;而所谓‘德行’,我指的是一套被认可的行为体制与思想规范,它将欲望限制在某一既定的社会文化藩篱之中。 ”[23]
(二)从社会性别角度看
从性别分工理论看,这个情节说明尽管秦良玉在当时的“公共领域”做出贡献、大出风头,但是一个异性上司见到他,还是从个人私欲出发,暴露了其猥琐心理,渲染了男性的危险性色,后人叹曰:“陆知州,诚可耻,肉眼不识奇女子,抽刀断袖应羞死”[24]!戏末,秦氏称自己“我是个妇人,军旅之事终非所宜。不如回往石柱司,闭门自守,免遭物议”——这个情节似乎表明男权社会对女性走向公共领域、从军打仗的担忧,一忧内眷外出,影响家风;二忧女性一旦出门,男性只得回家。“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生育是她们的特权,正如战争是男人的特权一样”[25]。
(三)对照史实本身看
当秦良玉热心征战,引起部分男性官员妒忌。天启三年,秦良玉因与官员不和上疏云:“总兵李维新……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静夜思之,亦当愧死。”皇帝为此“命文武大吏皆以礼待,不得疑忌”,此时尚有皇帝平息纷争;其后,“绵州知州陆逊……见良玉军整,心异之”,此处虽无非礼之事,但其颇为“吊诡”的“异之”二字似被现代人放大、变形,才有此剧之两人失和!
[1]dickjia.京 剧 汇 编 .http: //blog.xikao.com/2005 /07/27/147,2005-07-27/2009-09-0.
[2]邓涛,刘立文.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163.
[3]皮簧客.尚小云的艺术和生平[EB/OL].http: //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 =3303&jouRsid =1301,2000-11-27/2009-09-01.
[4]佚 名 .京 剧 大 师 尚 小 云 [EB/OL].http: //www.heb.chinanews.com.cn /lsrw /shangxiaoyun.htm l,2009-09-01.
[5]玉带墨客.尚小云演明代女将军秦良玉[EB/OL].http://
tieba.baidu.com/fkz=487177804,2008-10-7/2009-09-01.
[6]焦菊隐.导演·作家·作品[A].童庆炳,马新国.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新编 [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54.
[7]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27-228.
[8][23]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4.104.
[9]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C].北京:三联书店,2005.110-112.
[10][美]佩吉麦克拉肯,艾晓明,柯倩婷.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9-180.
[11]相抱轮.千古英雌秦良玉[J].现代青年,1936,(5).
[12]张文柏.秦良玉以家财助饷论[A].学生文艺汇编,1926.上集.
[13][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五·明史体例[Z].http://tieba.baidu.com/fkz=332843597,2008-3-3/2009-09-01.
[1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Z].http://tieba.baidu.com/fkz=340216988,2008-3-16/2009-07-10.
[15]聂树平.明清以来秦良玉研究综述[Z].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课程论文,未刊稿.
[16] [清]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立主脑[Z].http://tieba.baidu.com/fkz =229278078, 2007 -7 -16 /2009-09-01.
[17][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172-173.179.
[19]李良品,冉建红,吴冬梅.石柱“秦良玉文化”的类型、成因与保护[J].重庆社会科学,2007,(11).
[20]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京剧汇编第 23集[Z].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年.本文所引,未经说明者皆出此处.
[21]weertfox 等 .巾 帼 [Z].http: //baike.baidu.com/view/127211.htm,2009-8-8/2009-09-01.
[22]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10-211.
[24][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第一七八条[Z].成都:巴蜀书社,1987.91.
[25]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 [M].北京:三联书店,200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