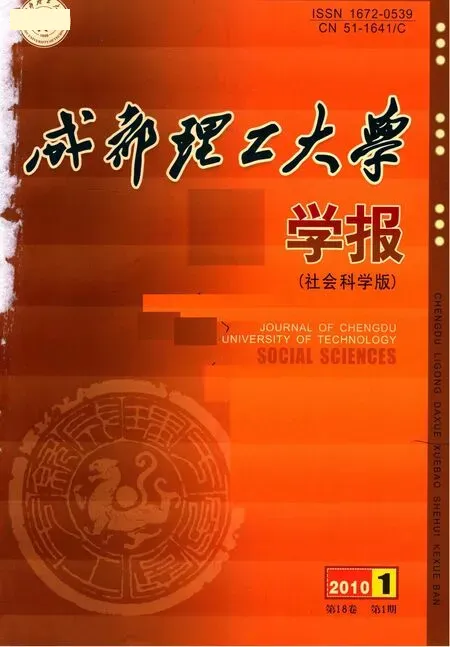文学史研究的“回到现场”
2010-04-03赵卓
赵 卓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桂林 541004)
文学史研究的“回到现场”
赵 卓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桂林 541004)
“回到现场”意味着文学史研究抛弃“宏大叙事”的叙述和阐释方式,避免跨越式的霸权主义口吻强加“历史规律”于具体史实。保留社会文学生活的本有状态并搁置文化精英的傲慢态度,放弃狭隘的“文学进步”观念和囿于高雅沙龙的单一审美趣味。文学史应该通过文学呈现社会精神——心灵史。
现代文学;研究;回到现场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回溯“五四”和研究北京大学校史时多次提出,研究历史要“回到现场”,并发出感慨“‘回到现场’之艰难”![1]历史研究要“回到现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对这一观点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强调收集背景资料的重要性上。我认为,“回到现场”,尤其是回到文学史的“现场”还有更深层次的潜在理论空间。
一、回到历史事实
“回到现场”意味着文学史研究从理论上抛弃“宏大叙事”的叙述和阐释方式。宏大叙事的弊端在于总是把具体的文学事实与“时代精神”直接建立起联系,以一种跨越式的霸权主义口吻强加“历史规律”于具体事实,结论空疏、大而无当,导致这种“规律”飘浮于历史事实表面。
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历史事实,政治——主题先行地“框范历史”,只能是“历史为我所用”,即中国传统文人早已发现的严重弊端“六经注我”并由此形成人文学术“曲学阿世”为当前政治服务。文学史研究不该跟着时尚走,更不该跟着政治权术需要走。它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内积极创新,在不断挖掘文学史史实的基础上,引导我们从高层次理解和解释前人的文学实践。“文学作为一次事件的一致性基本上是在当代和后代的读者、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界内实现的。能否以其独特的历史性理解和再现文学史取决于这个期待视界能否具体化。”[2]“宏大叙事”不提供历史“现场”,它以不符合历史必然规律和非本质的偶然现象之名掩盖“现场”,以此手段“先验性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先入之见。尤其是在长期遭到政治色彩涂抹之后的研究领域,只有刮垢磨光,即“回到现场”,才能求得学术研究更上层楼。
韦勒克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要么是‘文学史’。当然,‘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在应用的时候,经常是将文学理论包括在内的。我曾要求将这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它们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很难想象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怎能有文学理论;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怎能有文学史。’”[3]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文学批评实践改观和文学史改写提供机会,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所“发现的”文学史会截然不同。在思想经过重大的“解放”之后,文学批评已经发生了显明的变迁;文学理论视野也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在此情形下,文学史研究必将有实质性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应该从“回到现场”开始,而不是简单地与过往的“文学史”争吵。数次的“翻案”——对鲁迅的评价是典型案例——争吵证明,在固有平台上的辩论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与其说是理应促进学术研究的辩难,不如说是意气用事地唱对台戏。轰轰烈烈的争吵之后,曲终人散,只是一场热闹而已。
“回到现场”就意味着从历史事实出发,最大限度地把历史研究拉回到学术的正常轨道上来。历史的现场早已开始被慢慢淡忘,更经过恶意破坏,而且持续地遭到篡改,历史的碎片飘零散落,犹如被安排好的毁尸灭迹。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回到历史的现场是艰难的!“几十年后的追忆,难保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污染’。”[4]39回到现代文学的“现场”,“遗忘”和“污染”会给我们造成诸多困难,但最关键的或许是让历史成为历史,让现实政治影响退出这一研究领域,勇敢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重新评价,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即将在一个更符合理想的气氛中展开学术活动的信号。
“回到现场”包含着两个因素:一是“现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复原;二是“回到”现场的人,他带着怎样的洞察力和工具。近三十年来,欧美的各种哲学和思潮一浪一浪地涌进,我们往往把这些当作简单的工具,顺手抓来使用,似乎从没想过其中包含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回到现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象学的色彩,这种倾向产生自对“宏大叙事”的深刻怀疑。以此为出发点是可以接受的。“选择对于‘五·四叙事’来说至关重要的三个案,强调‘回到现场’,暂时搁置‘伟大意义’、‘精神实质’之类的论争,目的是突破凝定的阐释框架,呈现纷纭复杂的‘五·四’场景,丰富甚至修正史家的某些想象。”[4]27“现场”永远是我们研究的坚实的出发点,也是辨认其他研究者的结论正误和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逼近真理的唯一真实。
二、让“缺席”的读者归位
“回到现场”将复活当时真实的文学生活。在以往的文学史描述中,“当代的”读者完全被忽略了,所提供的几乎完全是后代批评家以自己的标准和爱好对作者和作品的筛选。社会生活中的文学生活层面读者缺席是难以理解的。
不知这里所要阐述的观点是否逸出了陈平原先生的原意或逸出有多远,但是,严格地说,从“回到现场”可以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回到现场”肯定会遭遇读者反应的问题,即当时社会文学生活的实际状况。根据我们现在已经基本接受的文学理论,读者不是被动的文学消费者,而是文学完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读者的审美需要对文学生产有着强大的左右和选择功能,就像物质消费市场对生产厂商的作用一样。
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史中读者成为了临时演员,而不是一个“常在”的角色?当文学史家需要提及社会公众反应时,读者就会被镜头扫描一下,而在更多的场合中读者是缺席的;文学史家既是消费式读者,又是作家作品的坐在法官席上的历史审判者。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弊端:一、历史事实——陈平原先生所说的“现场”——被涂抹了,取而代之的是今天的文学史家的阅读反应;二、文学史家的精英意识不仅合理合法,而且是唯一的欣赏和评价文学的标准。借用一句话说:“这里,文学史实的概念很广,既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品,还包括与作品相关的环境、读者等,作品完成前与之有联系的因素、作者以及作品完成后的接受和影响情况。”[5]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读者因素,即“接受和影响情况”,这也是此前文学史研究中所缺失的。
涂抹历史,或称忽略甚至驱逐读者,用“回到现场”的方法限制、矫正文学史家的狭隘、偏执和个人好恶的机会丧失了!我们看到的文学史是不包括文学最终消费者反应的文学史,而是最大限度的后代文学研究者的审美趣味表现的场所。更何况我们曾经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强解文学史!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20世纪前半叶几乎是独霸文坛,畅销不衰,虽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就连“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也羞于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但是,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生活就是以“鸳鸯蝴蝶派”及其衍生流派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市民大众的审美与精神状态就表现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欣赏活动中。周作人说得夸张但不无道理:“我想这黑幕的发生,是中国社会自然的趋势;社会上对于这黑幕的需要与供给决非偶然的事。一篇文告,有什么效力?他们那班黑幕家,怎肯听人劝告?即使听了,黑幕也不做了,仍于社会毫无益处。因为那些做黑幕看黑幕的人,依然存在;他们的思想,也依然如故;将来自有别一种‘欧洲写实小说的新潮流’出现……譬如一个害梅毒的人,全体组织都有了毒,如今说怕他传染,劝他割去脸上的小疮,补上鼻子,无论这事十分为难,即使勉强办到,也仍然是一个梅毒患者。中国社会的情状,正是如此,所以我说不必劝告;至于办法,则若无六O六对症药将他医好,惟有候其以天年终而已。”“黑幕”(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6]但启蒙运动者和新文化的后继者们似乎没有以作家作品为个案做细致分析的工作热情。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创作中没做什么,没做好什么,无力做什么,与他们的作品表现的反动、腐朽、梅毒是两回事。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通俗文学,它肯定隐喻着读者的社会心理状态,简单地斥之庸俗低劣,甚至喻之为“梅毒”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社会文学生活的事实,更无助于提升文学生活的质量。
鲁迅先生的文字在当时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呢?文学青年丁玲看不懂所以不喜欢,鲁迅的母亲的评价很有保留,“左联”的青年同志也(对《倒提》)发生严重的误读……“回到现场”也许会提供史料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的广泛影响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生前乃至到1949年之前,影响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回到现场”才能克服“宏大叙事”和政治干预给人们造成的错觉,使后人对“五·四”时期的启蒙阵营以及后来的左翼文化的奋斗与孤寂全然不知。
“回到现场”并不意味着“演义式”地描述众多历史故事,不是演义,而是真实又生动地再现文学生活史,记述各个时代的社会大众精神史!“回到现场”要勾划“现场”的实际状况:哪些作家、作品占据着舞台的中央?社会公众为什么陶醉于这些作品?哪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忽略?我相信,社会接受——读者阅读状况将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文学史不再是作家作品的清单,更不是寥寥几个名作家和寥寥的几部名著的年表。毕竟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要由接受做必不可少的环节。读者反映着社会文学生活的实际情况,反映着一个时代广大社会公众的审美趣向。
鸳鸯蝴蝶派小说、蒋光慈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在文化人圈子里的崇高地位,背后肯定存在着先于作品存在的社会心理需求。作家通过作品“创造”了读者,广大公众的追捧也造就了“著名”作家。读者的阅读期待影响并决定着一个时期的文学生活主层面。用后来的眼光描述文学史,很有可能发现长期默默无闻的天才作家和优秀作品,揭示的则是优秀作家存在和文学名著产生史,而不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生活史。
世界 ——作家 ——作品 ——读者 ,四要素缺一不可,才能构成完整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活“现场”。此前的文学史,对作品所产生的“世界”往往做大而无当的空疏的交待,由此证明该作品的真实或虚假,读者反应只是文学史家对作品评价的佐证,从没有成为研究的对象。即使这种研究思路不是僵硬无生气的,也是明显偏枯的。
三、拷问“精英审美”的合理性
“回到现场”将考验“精英审美趣向”的偏见。如果在其它场合坚持“精英”而拒斥“大众”只是捍卫高雅的传统,只是一种审美价值取向;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无疑这种偏好就是偏见,就是局限。
就如同不能用“诗史”、“女性文学史”或“儿童文学史”取代整体的文学史一样,精英审美趣味狭隘视野中的“文学史”同样不能代替整体的文学史。胡适等人曾经大力倡导“俗文学史”,并认为“俗文学”才是中国真正的文学主流。这是矫枉过正的说法。但是,以“社会进步”为取舍尺度的“政治文学史”似乎又回到了“文以载道”的老路。新时期以来的不懈努力虽然已经大有改观,文学史中的精英意识仍需探讨。近年来的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成为了一时的热点,显示出学者们的宽容,但只是宽容而已。“回到现场”去,把读者的审美经验当作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撰写出复活当时社会文学生活“现场”的文学史,还有待时日。“然而,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却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从这样一些规则,即必须提出一整套连贯一致的变量说明体系,各种假设也必须统统纳入十分简明的模型之中,这样的模型还必须说明可在经验中观察到的大量事实;要想推翻这种模型,新的模型也必须符合同样的条件:逻辑连贯性、系统性和经验可证伪性。仅就此一点来看,我以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系统的建构之所以如此困难重重,与此一问题关系甚大。”[7]
大众的、通俗的文学艺术到底有多么空洞、“堕落”、低劣甚至反动,需要就具体作品给出结论;即使它们确实是低劣的、腐化的,怕那也是人性中的一部份,从最原始的文学作品中就已显露出根苗。我并不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文化的激进思想是绝对正确的,以为大众通俗文化是未来理想文化的必然方向。“当然,那些深信应该认真看待大众文化的人也掀起了有力且激进的革新潮流。大众文化非但不应被当作粗糙庸俗的东西加以排斥,相反应像对待更奇异的‘原始’社会文化一样进行细致的探索,因为毕竟对许多人来说,民众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基础,后者将克服资本主义的显而易见的失败。”[8]4至少大众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而且确实长期被统治阶级所蔑视和打压。即使我们认定通俗——大众文化是人类文明中的某种“症候”,史家如果忽略了它,其记述的文明经历中当然也就包含着“误诊”!
正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带来的工业文明,使得劳动者得以享受文化娱乐,即专门为他们提供的文学艺术产品。文化精英们认可的“纯文学艺术”在文化生活中越来越处于边缘的、小集团的地位,大众文化生活则日益喧哗。至少从人群的规模和场面来看,大众的文化已经取得“主流”、“主旋律”的位置,恝置不屑或一味地声讨,其声音也细,其效果也微。“鲍曼指出,对知识分子来说,更糟糕的是意识到,随着国家权力不再控制他们的特权领域——文化,这个领域开始被新的大众消费产业所控制:‘让他们受伤的……不完全是被侵犯,更是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来担当这一惊人扩张的掌舵人。’”[8]5精英知识分子处于悖论之中,隐约地怀有一点酸酸的心理。对大众文化的积极、主动关注,应该是解决这一悖论的唯一途径。或许陈平原先生的言论中已经包含着这一解决方案。他说:“重建现场、回到本原当然是一种策略,而且很基本,但这只是第一步。能不能从这里面走出来,取决于你自己的眼光和立场。回到现场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再来表达自己的观念。”[9]我们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搭建这样一个新的平台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满足于高雅沙龙的文学谈论的描述,局限于反映或促进社会进步的作品,只能体现出文化精英的审美偏好,呈现的却绝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回到现场”就要打破精英与大众的隔阂,淡化进化论的文化观念,回到生产——消费这个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来。用“生产——消费”这种说法形容文学生活当然过于简单化,就像说通俗文学“商品化”一样;在学术目光的审视下,必会发现其中隐含着相当丰富的人生和历史信息,也会为我们深入研究“审美经验”提供有价值的资料。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等在批判“鸳蝴派”时,也曾提到众多市民读者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需求是此类小说大量产生的社会原因。但他们太不屑于“鸳鸯蝴蝶派”啦,所以把小市民的审美癖好一同斥责为“梅毒”,轻蔑地一瞥了之。我们无需为前人辩护,但是我们知道,矫正时弊与回顾历史有着不同的使命,与之相应的,还要有不同的眼光。
“回到现场”意味着承认作家与作品的联系,作家与世界的联系。文学史不是作品清单,也不是共时性地存在着,因为文学创造本身既包含着对传统的借鉴和继承,又意味着对传统的回避和扬弃,传统先于作家存在,并可论证地影响,进而“决定”了作家。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可能导致文学研究的破产;但历史主义的“世界——作家——作品”理解性诠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里是对仅凭阅读作品边指点前人写作得失(如贬低鲁迅者)的人的反驳——“回到现场”会真正理解。“回到现场”能否启发或引导我们创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的理论话语,当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口号潜存着理论发展的空间。
[1]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回到现场”之艰难[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15.
[2]姚斯.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A]//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4.
[3]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8.
[4]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9.
[5][俄]埃·梅勒坦斯基.社会、文化与文学史实[A]//[加拿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198.
[6]仲密(周作人).再论“黑幕”[G]//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87:81.
[7]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M].上海:三联书店,2000:16.
[8][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4.
[9]阮慧勤,陈岸瑛.我希望学术做得好玩儿——访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J].书评周刊,2000,(06).
L iterary History of the“Back to L ive”
ZHAO Zhuo
(College of Liberal A rts,Guangxi No 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Back to the on-site”means that the histo ry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bandonment of the“grand narrative”of the narrative and to exp lain theways to avoid the tone by tone to impose the hegemony of“historical law s”on the specific facts.To reta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s literature there are state and cultural elite arrogance aside,abandon narrow“literary p rogressive”ideas and confined to a single elegant salon aesthetic.Histo ry of literature should be p resent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the social spirit-spiritual histo ry.
modern literary;studies;back to the scene
I209
A
1672-0539(2010)01-026-04
2010-01-20
赵卓(1984-),女,吉林双辽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