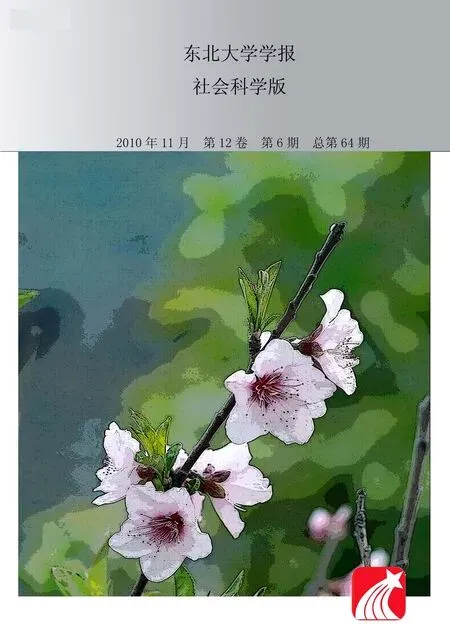论译者的显身性
2010-04-03任蕊
任 蕊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一直以来,翻译界为译者究竟应该隐身还是显身而争论不休。译者应当以何种状态存在,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对于学者和翻译从业人员都同等重要。翻译因语言表达形式不同而分为两个领域,即以书面形式呈现的笔译和以口头形式呈现的口译。同为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均可被称为译者,但正如以书面形式存在的笔译和以口头形式存在的口译蕴涵语言表达两种不同的语体,人们对翻译者的称谓也体现了口笔译翻译活动的语体特点,笔译中他们被称为译者,口译中他们被称为译员。在一篇文章里同时探讨口笔译两个领域中译者的隐身与显身,目的在于展示其全貌、实现对其较充分的认识。笔译界美国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著有《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 ,口译界虽没有类似的专著,但也有Angelelli基于博士论文于2004年发表的从译员隐身出发,借助实证研究成果论述显身的系列书籍。除了这两位学者,还有来自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语言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者,他们都对译者的角色、作用及工作状态作了深入探讨。以上所有研究的目的是要让世人认识译者,同时,这些研究也使译者得以重新认识自身及自身所从事的行业,为这个行业确立正确的职业操守提供理论依据。国内也已有学者就译者的隐身与显身作了论述,有学者提出“译者从隐身到显身”[1],也有学者提出译者的隐身与显身都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本文针对在笔译及口译中同时存在的译者的隐身问题展开探讨,指出隐身与显身的实质,提出译者隐身是人们的主观意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无法作为职业操守被践行,显身才是译者的真实存在状态。
一、 被隐讳的知觉
传统的笔译和口译都要求译者要隐身,然而,这个原则在历经了数百年的实践以后,却越来越被证明与事实相悖。不管笔译还是口译,译者都是显身的。
译者的显身首先是被笔译译者知觉并且表达出来的。笔译翻译的流畅性原则始于17世纪的欧洲,直到今天译者们仍然广泛践行着这一原则。译文要流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与流畅性如影随形的另一原则是透明性[2]1。Shapiro在论述翻译问题时曾经说:“我视翻译为一种努力译出透明文本的行为,译文应当透明,看上去它似乎不是被翻译过来的。好的译文像一块玻璃,它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玻璃上面有小的瑕疵----划痕或气泡。理想状态下的玻璃应当什么也没有。玻璃本身应当永远不被人关注。”[3]这一观点在翻译界非常普遍,具有典型性。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译者和译员应当将翻译的透明性作为职业的最高准则,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个术语来描述透明的翻译行为:隐身[2]5,即在翻译的文本中看不到译者的身影,译者仿佛是人们所看不到的隐身人。人们有一种想法,翻译的文本,不管是散文还是诗歌,不管是小说还是写实文学,都应当行文流畅,让我们感觉不到语言与文体上有被译者处理过的痕迹。这样的译文从表面上看是“透明的”, 鲜明地反映原文作者的个性或意向,或者说反映原文的根本意义。换句话说,从表面上看,译文事实上不是译文,而是“原作品”[2]1。在突显作者原创性这个原则的指引下,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译文中让位于源语的相关表现力。Trask曾在与Honig的谈话中明确地区分了写作和翻译:“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你所写的是某人、某地、某事,你主要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但是,翻译时你所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想法,你仿佛是在做专门的特技表演……。我发现译者必须与演员有相类似的天分,都须要将别人的东西表达得如同自己的一般。我认为你必须有这样的能力。除了专门的技能之外,翻译还须要揣摩(他人的)心理,有些像舞台上所需要的技能。这一切不同于诗歌等的创作。”[4]然而,人的活动具有意向性,虽然受社会规则等因素的制约,但是归根结底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体现个人、社会等方面信息。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尽管受制于不同的主体,“语言的精神”决定言语行为,主体的活动受制于个体的“存在”。语言不可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如果作者是“语言精神”的唯一提供者,那么译文的读者又如何能理解“源语作者的语言精神”,如何能领会“他自己独特的感受以及思维方式”呢[5]?语言精神是一种语言独有的内容与方式。译文若能够被读者理解,译文所呈现的源语信息必然要由目的语的“语言精神”来体现。
在人们所追求的“表面上”的“原作品”,“表面上”的“透明”、“隐身”的翻译活动中,从本质上说译文所呈现的恰恰是译者对于原文最大的干预与显身,译文越流畅,越是译者显身、干预的结果。的确,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被边缘化了,但是,韦努蒂认为不管译者翻译时对语言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原则,译者都不是透明的、隐身的[2]34。Shapiro认为他在翻译时是在与作者协作,“当然,我的自我和个性会体现在翻译之中,但我必须努力以一种不表露自我的方式忠实于原文”[3]。尽管他须要将自我和个性隐藏在译文中,但是他始终知觉自己的显身,他始终支配、操控着源语文字。虽然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是以不表露出自我和个性的方式来忠实于原文,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时时刻刻都是显身的。在口译界,译员一直被要求在口译中隐身。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译员唯有隐身才能彰显他的职业性。显身一直被认为是行业禁忌,职业译员对此讳莫如深,很少谈及,更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显身。然而,学者Angelelli在对从业译员的调查中发现,“聘用译员的组织总是希望译员是职业的,不管译员的出身、性别或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行为应该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对这个领域的直觉、经历和观察使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6]84。她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译员们始终知道自己是显身的[6]98。
译者,从出现之日起,在翻译中的显身就是确定无疑的,这是客观存在,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但是,无论译者还是翻译活动涉及的各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的。译者的隐身与显身问题,在口译中呈现出较笔译更为复杂的情况,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且论述颇多。译者的显身在口译员身上较之笔译的译者更明显,然而,一直以来,人们试图从观念上忽略显身的存在,大力推崇隐身。在当下,这种错误认识仍然在口译职业机构的职业要求中、口译培训中、从业译员的思想中广泛存在。
理论上,隐身的译者被认为是运用不同的语言重复相同信息的个体。在实践中,践行隐身原则的译员,多半会忽略语域的差异,不是控制信息而是随着信息流动,不在意各方对信息的理解或共建。他们往往对于谈话双方是否获得信息或获得的信息是否充分漠不关心,在跨文化交流中并不积极,只在语言学层面处理信息,更确切地说,是语义翻译。然而,在早期的口译研究中,学者们就明确指出口译不是源语与目的语间的逐字翻译。Kondo在有关口译和跨文化交际的文章中指出:“源语与目的语之间一字一字地对应翻译在口译中无立锥之地。”[7]Davidson指出:“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可能会假设同一表达会被以同一方式译出,但是这种假设却不一定成立。”[8]Gile也指出:“一种语言中运用特定类型的词或结构表达一个意思,在另一种语言中这个意思可能变成了其他意思,在又一种语言中则可能是社会无法接受的了。”职业译员做的事情是洞悉外行经常忽略的文体学或语用方面的细微差异,适宜地进行翻译。他举了一个用日语表达个人情感的例子:当表达A有B的想法时,日语说话人可能会说诸如“我猜A可能是有B吧”的或然性表达而不是作出断言。在日语中,这样的做法反映的是“教养方面的谦恭有礼”。在西方语言中,这句话反映的是说话人对所说的话拿不准、不确定。而在西方语言中完全可以被接受的直陈观点的话,对于讲日语的人来说,可能是唐突的,甚至到了粗鲁的程度。西方人习惯表达观点时,态度鲜明,语言较日语直接。同样的信息,日语用贬低自己来表示有教养的谦恭[9]。如果没有译员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根据相应的语言文化对信息进行处理,谈话双方的交流便无法达成。House在对一则简报进行翻译时发现,英语译成德语时,译文要比英语原文言辞更有力,更活泼,更直接。英语原文则较抽象、间接,话语中似乎含有微妙暗示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在德语的译文中这个暗示则变成了要求[10]。上述例子不是个案而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如果说,一个隐身的译员所做的事情是对信息作语义处理,那么在他显身地将日语的猜测语变成英语的直陈语,在他将英语的抽象、间接转换为德语的更直接表达时,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是隐身的了。
译员隐身观认为译员是言语转换的操作员,译员要高度注意会谈各方信息的意义,不要对其有任何增减。以会议口译为参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意义,因此这个意义不能够被共建,即一句话只有一种解释。对口译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翻译得精确至关重要,精确高于信息的传递及其他方面(如谈话各方的意图,语言交流行为的目的,或语言互动的语境等等)的体现。隐身观假定:①译员与说话人之间无相互作用(即译员的参与仅限于语言转换);②说话人之间无相互作用(如身体语言);③口译可以在“真空”中进行(即译员可以不受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地进行翻译)。持隐身观的人们认为译员以及谈话双方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彼此产生的影响可以被忽略[6]7-8。然而,近期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译员隐身观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的一句话,它的意义不只有一个。维特根斯坦向我们证明了意义具有社会性[11]。一句话意义的产生源于它的社会性。口译不是在社会真空之中完成的[12]。如果说话人与译员三方对于相同的社会文化因素所持观点各异,对于同一句话,他们就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句话的意义就不只一个了。为了使交流能够顺畅进行,三方须要共建这句话的意义,须要达成一致。译员是跨文化语言交流的真正操控者,是针对一句话确定三方共享的意义的人。近期的口译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学者们改用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领域的方法研究经由口译员完成的语言交流活动,研究的焦点由隐身的译员转到了显身的、作为共同参与者的译员。研究结果表明译员在语言互动中与其他参与者共建一个概念时会融入自身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构建、阐释现实[6]10。
其次,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有译员参与的跨文化语言交流是由三方存在的语言共同体完成的,译员是其中的一员。然而,译员的角色还不止于此。学者们还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对译员作为语言交流的共同参与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Roy深入分析了一位教授与一名聋哑学生在一位手语译员帮助下所进行的会谈,揭示了译员对于语言互动所起的积极作用。她指出在翻译时发生了“译员由转述信息到管理、协调对话”的角色转换[13]。Hymes的研究表明,每个交流活动都涉及权力纷争[14]。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译员对于权力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①译员要研究谈话双方各自的心理状态。译员不断地与说话人及听话人产生语言互动,以便谈判、协商、澄清问题。译员在这个过程中是主力队员。他甚至是守门员。如果译员不这样做,谈话双方就可能无法顺畅交流。即便在单语语言交流中,有时也会出现说话人、听话人不能彼此理解,须要磋商以澄清语言信息的情况。因此,在跨文化语言交流中译员经常须要为了实现双方的顺利交流,对语言信息作必要的澄清、解释。②译员作为不断进行着语言互动的三方中的一方,其角色是不可预测的,时而是信息流量的控制者,时而是教育者,时而是概括人,时而又是经纪人。③文化、语言方面的差异可能影响交流,三方的想法和交流的预期结果不一定会被共享。译员的参与为交流的结果增添了新的可能性。④在交流中译员试图发现、发掘他们不熟悉的说话人的语言能力。译员有可能在处理说话人的信息内容、形式时也将自身融入进去。在交流中,各方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三方共享的,只有译员同时与谈话双方共享一种语言。译员在引入自身言语形式的同时,还要顾及谈话双方的言语形式。⑤在交流中,两个单语说话人要经由译员协商语言理解和互动的标准,各方的标准会增大语言互动的复杂性[15]34-40。在有译员参与的语言交流活动中,译员不但是活动中的一员,而且还是真正处于强势地位的谈话方,有能力改变语言交流的结果。他可以将自己的能量与权力物化为不同的交际行为[6]10,左右交流的进程与状态。
口译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过程,涉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信息处理,涉及对于社会因素的权衡。译员的显身是口译活动本身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坚持译员隐身,其结果必然是与事物本质相悖,必然影响跨文化语言交流的质量,影响口译的效果。
三、 难以践行的职业操守
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隐身被认为是译者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如上所述,笔译中的译者、口译中的译员时刻都是显身的。隐身的职业操守是人们的主观意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以口译为例,“隐身的译员”只能在某些场合下勉强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在隐身地做着翻译,更多的情况下,他是被自己时时刻刻的显身行为折磨着。译员显身最明显的例证来自于医疗口译。译员必须偏袒弱势即患者一方。医疗口译的背景通常是当事人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化迥异。只要有需要,为了使双方能彼此理解,译员就须要对信息作必要解释,而不能只是用目的语重述源语信息[15]75。他必须以患者为中心,显身地干预交流进程和状态,控制话轮,以患者最终能够得到良好救治为目的,为患者和医生充当语言文化中介。Davidson研究了由译员作为交流中介的医疗语篇,他发现,对于医生来说,译员是使患者定位的工具,对于患者来说,译员是与其对话的共同对话者。他指出,译员不是只充当语义会话的机器,而是诊断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译员与医疗提供者站在一方,为他们的口译对象充当看门人[16]。但是,正是因为在医疗口译中译员偏袒患者一方,“充当了患者的辩护者”或者“站在患者一方翻译”,“某些译员及组织提出医疗口译译员要注意操守问题”[15]77。然而,医疗口译译员若不能保障跨文化语言交流的顺畅进行,不能保障医疗质量,他就会不被需要,进而失业了。为了所谓的职业操守而失去职业,这显然是荒谬的。这恰恰反映了隐身在翻译实践中不仅是难以被践行的,而且还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隐身被作为职业操守提出来,呈现了除译者之外的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方对于译者行为的一种担心、忧虑。人们担心译者肆意改变源语作者或说话人的表达意图。的确,译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Metzger运用框架理论及基底(footing)概念来研究译员能否在翻译时隐身、不掺杂自身对于语言互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翻译中的确存在译员以自己的解释来歪曲信息源基底抑或是译员脱离源语产出话语的情况[17]。这样做的译员无疑是在篡改源语的表达意图。如前所述,译者可以操控跨文化语言交流,左右话轮,掌控谈话的进程,维系谈话双方的关系。如果没有职业操守,译者足以颠倒黑白。有人戏称世界大战之所以打起来是由于译员翻译时言语处理不当造成的。关于对话语的处理问题,Irvine举了一位唱赞歌歌手的例子。歌手是被雇来唱赞歌赞颂一个世代为皮革制作者的家庭。因为觉得拿到的报酬太低,这个歌手就用过度称赞的方法来嘲讽这个家庭。听众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歌者称这个家庭的祖先是帝王,这是与事实相悖的。于是,溢美之词就成了羞辱[18]。话语在此呈现了其复杂性,这一点是话语的本质,也正是人们对译员的担心之处。诚然,如果译员没有责任感,在措辞时有能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控制谈话的结果。但是,职业译员鲜有这样的行为。译员对于语言的操控以及在交流中的作为体现了显身性,但是绝不等于他可以脱离语言文化事实歪曲一切。译员的显身的确揭示了译者对于跨文化语言交流的操控,但不是对语言文化事实的歪曲。译者的显身在于推动语言互动。
在没有认清译者的本质之前,人们从思想上规定译者要隐身。外界对译者隐身的要求更造成了译者对于自身是否应当显身始终存疑。大多数译者的做法是,虽然知道自己是显身的,却努力掩饰显身,展示所谓的“隐身”。这样做被误认为是译者职业性的体现。然而,事实证明译者的隐身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直以来隐身被盲目推崇,无疑是人们为了成就隐身的主观愿望而掩盖了显身的事实。隐身作为职业操守并不存在,显身才是译者在翻译时的真实状态,是译者的本质属性。
四、 结 语
译者的隐身与显身,向我们揭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隐身最初是被作为译者的职业操守提出的,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不要对源语意图产生影响。然而,如上所述,译者的确显身地对译文产生影响。其次,在探讨译者的隐身与显身这个问题时,事实上我们已经承认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存在,探讨的实质在于他的存在对源语的改变、影响能否从视觉上、感官上被感知。译者,作为具有社会性和意向性的人,不管他在翻译中的存在对于他人或译文来说能否被意识到,译者的确在翻译活动中对于译文进行着处理,施加着影响,产生着作用,即显身于翻译之中。再次,译者的隐身与显身不是一种和谐,而是一种冲突。有学者说隐身与显身都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隐身与显身似乎在译者身上是一种和谐。如果说,隐身存在,它也不是指译者真正地隐身,更准确的表述和理解应当是,它指译者被要求忠实于源语信息,不要凭借个人意志任意篡改其意义。显身是指译者作为语言文化的中介,要在翻译时,以交流成功为目的,呈现源语在目的语中应有的状态。
诚然,翻译遵循忠实原则,忠实于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与文化,让源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或谈话双方,在有译者参与的语言交流情况下,实现仿佛没有译者存在的单语交流,这是译者职业追求的最高境界。正是为了这个目标,译者在不同语言与文化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充当跨文化语言文化交流的纽带。因此,如果隐身与显身真地可以同时存在于译者身上,也是显身驾驭隐身,在翻译时用译者的能动作用显身地本着忠实于语言交流双方、忠实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原则,以不同的语言形式、文化表达完成语言信息传递工作。隐身,这个要求是人们的主观规定,看似明确,但实施起来存在困难,作为职业操守十分抽象也不宜践行。译者的隐身与显身的论断体现了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过程。全面地认识隐身与显身,由最初的隐身观,到目前的显身观,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可以进而得出以下两点启示。其一,翻译培训者们不应当再错误地要求受训者要隐身,不应要求其在翻译活动中不露痕迹地工作。其二,翻译从业人员从本质上认识了译者的显身之后,可以更好地架设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宫钦言. 译者:从隐身到显身[D].上海: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4.
[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3]Kratz D. An Interview with Norman Shapiro[J]. Translation Review, 1986(19):27-28.
[4]Honig E. The Poet's Other Voice: Conversation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5:13-14.
[5]Lefevere A.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M]. Assen: Van Gorcum, 1977:69-70.
[6]Angelelli C V. Revisiting Interpreter's Rol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7]Kondo M. What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Do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990(3):62.
[8]Davidson D. Radical Interpretation Dialectic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125.
[9]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Training[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75.
[10]House J. Politeness and Translation[M]∥Hickey L.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66-67.
[11]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12]Wadensj ? C. Interpreting as Interaction[M]. New York: Addison Welsley Longman Inc., 1998:8.
[13]Roy C. Interpreting as a Discourse Proces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111.
[14]Hymes D.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M]. New Jerse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53.
[15]Angelelli C V. 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Davidson B. The Interpreter as Institutional Gatekeeper: The Social-linguistic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Spanish-English Medical Discourse[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4(3):379-405.
[17]Metzger M. S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Neutrality[M]. Washington, D. 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Irvine J. Insult and Responsibility: Verbal Abuse in a Wolof Village[M]∥Hill J, Irvine J. Responsibility and Evidence in Oral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