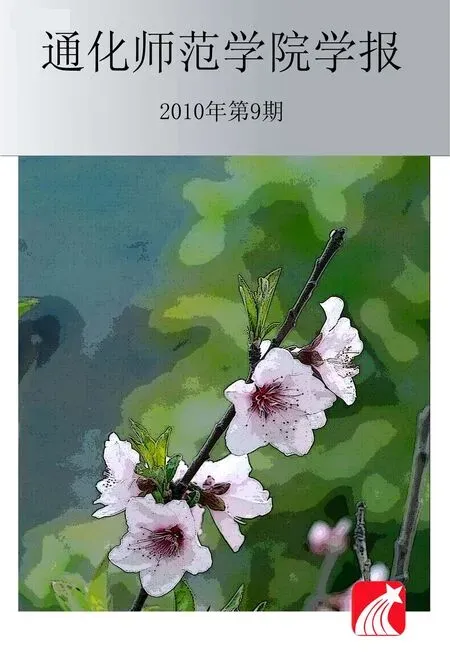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体裁的美学价值研究
2010-03-23王冰
王冰
(通化师范学院音乐系,吉林通化134002)
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体裁的美学价值研究
王冰
(通化师范学院音乐系,吉林通化134002)
世俗声乐体裁是文艺复兴时期与宗教音乐并行发展的一种音乐体裁,通过对世俗声乐的起源探究,了解世俗音乐在不同国家发展的形式特点,以及它所表现的情感和内涵,挖掘出世俗声乐体裁所具有的美学价值以及在欧洲音乐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
文艺复兴;世俗声乐;美学价值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深受当时的绘画、文学和哲学等思潮的影响,尤其是随着世俗声乐体裁越来越繁荣,更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
一、世俗声乐的起源
所谓世俗声乐,是相对于宗教音乐而言的,指那些表现世俗人民的愿望,反映世俗民众的生活,歌颂世俗人间的爱情,赞美奇妙大自然等题材的音乐。世俗声乐是以抱持发现艺术、释放情怀的观念,以原创的诗歌为主,采用单声部方言歌曲的形式,面向农民和市民等不同阶层大众,优雅与质朴并存。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成为音乐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音乐语言使各国的世俗声乐呈现出百花齐放、绚丽多姿的发展景象。
早在以宗教音乐为主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反映民间的世俗声乐就已经在发展了。大约在十二世纪建立的大学,吸引着各个国家许多神学士前去就读,在用功学习的学生当中也不乏有倜傥不羁、赌博冒险、喝酒大醉的人,他们在学习生活阶段度过的是无忧无虑、充满世俗享乐的生活,并且不愿意再回到“清规戒律”的隐修院和做乡村牧师,而成为整天四处游逛,招摇撞骗的“流浪汉”,但他们确实是诗人和音乐家。“他们歌颂爱情和春天,诗兴优雅、语气柔美;但酗酒和赌博时,却又写出最放浪不羁的诗行。他们的艺术并不限于古典来源,他们的创造活动范围也不囿于自己的原创作品。他们侵入到宗教的神圣领域,将那些优雅得体的诗行转用到各种各样的凡人俗事上。他们的歌词有时采用圣经的片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祭礼崇拜的形式——赞美诗、连祷文、甚至弥撒——无一能逃脱被篡改的命运。”[1]64可以说当时的世俗声乐并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与宗教音乐的发展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界限很模糊甚至分不清,常常用同一个曲调来唱两种不同性质的歌词含义。世俗音乐不仅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幻想,同时能够寄托和释放人们的情感,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绪,因此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喜欢,伴随着中世纪后期法国游吟诗人、游吟艺人,德国恋诗歌手等世俗音乐传播者的出现和增多,世俗音乐的发展非常迅速,影响广泛,为文艺复兴时期世俗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受到活跃于当时的绘画、文学和哲学的思潮影响,要求摆脱宗教的禁欲主义束缚,在关心灵魂得救的同时,也向往着世俗的享受,音乐在发展中获得了与绘画、文学和哲学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世俗声乐的发展促使许多新的音乐体裁出现,如意大利的牧歌、德国的利德、法国的尚松、英国的康索尔特歌、西班牙的比良西科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形式和音乐内容,更是为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文艺复兴时期多样化的世俗声乐体裁
鉴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感受不同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即使音乐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但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人群会有其特定的感受力、创造力和欣赏力。“人的内在世界由于对现实世界的掌握而愈加丰富时,人表现这个内在世界的形式就愈加丰富。”[2]11由于音乐能提供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会有多样化的形式来表现内心的自我,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声乐体裁体现尤为突出,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风格的兴起推动了民族音乐的发展,各式各样的民族语汇逐渐崛起,建立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之上的世俗声乐在每个国家都各自特色鲜明。
(一)意大利的世俗声乐体裁
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意大利,受到来自文学的影响,民族风格的兴起最为明显,最早出现的世俗声乐对其他各国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意大利世俗声乐牧歌出现之前,活跃于意大利宫廷的世俗声乐体裁的先行者是弗罗托拉。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弗罗托拉风靡一时,属于意大利分节歌曲,有明显的节奏型和简单的自然音体系和声,按照音节配成四声部乐曲,具有明确的主调音乐风格,旋律在高声部,表演方式通常是用人声唱出旋律声部,器乐演奏其他声部来伴奏,歌词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它的创作特别集中在意大利的费拉拉、曼图瓦等宫廷中,其影响不仅波及后来的牧歌,而且还对法国的尚松产生过影响。例如马尔科·卡拉创作的弗罗托拉《我不再期望》,“这是一首失恋者的轻松的诉怨,收在彼得鲁奇的第一卷中。琉特琴符号谱的一小节4拍划分法有时会使一小节6拍的舞曲节奏不清楚,使它时而成为两拍一组,时而成为三拍一组,形成了整个16世纪流行的坎左内典型的以及后来17世纪单声部歌曲所采用的赫米奥拉比例。和声配置法几乎全部是在低声部诸音上构成和弦,这一和声风格对于16世纪在意大利所创作的音乐有其深远的意义。”[3]22716世纪的意大利牧歌正是从弗罗托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弗罗托拉的风格为主,同时融入经文歌的模仿、对位手法,形成复调、主调相结合的形式,这便是意大利牧歌音乐的基本雏形。通过牧歌意大利初次在历史上成为欧洲音乐中心,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的牧歌发展大约为1520——1550年,这一阶段的作品多半是四声部的,具有主调风格,作曲家们在用对位手法谱写牧歌时,给予了歌词较多的尊重,甚至因突出歌词而牺牲对位。此时的牧歌是供人声演唱的室内乐曲,通常是在各种高阶层的社交集会上演唱,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器乐的独立,也常见器乐取代其中的人声声部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部来演奏。“大多数牧歌唱词的题材是多愁善感的或色情的,并且有取自田园诗歌的场景和借喻。歌词通常以最后一行或两行中的警句式高潮结束。”[3]239早期的牧歌主要活跃在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城市,主要代表作曲家有罗勒、阿德里昂·维拉尔特和雅各布·阿卡德尔特等,其中作曲家雅各布·阿卡德尔特创作的一首著名世俗音乐《啊,美丽的容貌在哪里》,一方面体现了主调音乐的进行,方整的节奏,严格的遵守诗节的形式和韵律;另一方面,运用平行六度和弦及模仿等复调手法,不再将深奥的赋格作为主要创作手法,而是更注重通过音乐来交流感情。歌词大意:我亲爱的珍宝,至善至美……也是直白的述说内心的情感和爱恋,这些创作手法让我们对早期牧歌的风格特征一览无余。
第二阶段牧歌的发展大约在1550——1580年,这一时期以威尼斯为中心,音乐结构以五声部为主,当然四个、六个、八个、十个声部也不罕见,既有主调风格,又大量运用复调手法,着重把握诗歌情绪的变化,更注重声音的效果。此时的牧歌多半是供表演者自我陶醉,并不是为听众而创作和演唱的,是种自我情感的释怀。重新受到推崇的14世纪诗人比特拉克在诗中寻求的两种对立的特性——“动人和严谨”,此时通过音符半音变化以及大小三六度音程的转换,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并且完全服从于所配的歌词。重要的代表作曲家有罗勒和维森蒂诺等,尤其是半音体系的倡导者维森蒂诺,为比特拉克十四行诗《劳拉,绿色的月桂树》谱曲,一处用了下行一个小三度和两个半音的希腊半音四音列作为模仿的动机,充分表达出作者忧郁悲伤、柔情似水的情结。扎里诺在论和声如何配合歌词时指出:“如果作曲家想要表达粗暴、苦涩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感,他最好把作品的声部进行安排得没有半音,例如可与用全音和两个全音的进行;如果作曲家想要表达忧郁悲伤的效果,他应该用半音、全音和类似音程的进行,要常在作品的最低音上方用小六度或小十三度,这些音程在本性上是甜美柔和的,特别是用正确的方式把它们谨慎合理的结合起来时。”[3]244
第三阶段牧歌的发展大约在1580——1620年,进入成熟时期的意大利牧歌,实现了意大利人创造新的自由而充满激情的艺术的梦想和抱负。这时期的牧歌更注重表现人物感情,通过运用戏剧性的手法,使音乐更接近人文主义者们理想中的古希腊音乐。作曲家中的奥拉齐奥·韦基具有大胆而色彩绚丽的戏剧性场面,戏剧性音乐刻画的能力,表明了世俗合唱复调的极限已走近戏剧;卢卡·马伦齐奥具有强烈的表现力、高度个性化的语气以及喜剧热情,尤其是自由地运用变化音的描绘性手法,描绘他所钟爱的田园诗歌,音乐抒情优美;卡洛·杰苏阿尔多的牧歌将半音的应用达到了高峰,音乐创作将半音与织体、节奏的剧烈变化相结合,深刻动人的反应歌词的内涵,充满了悲剧性的半音音响;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牧歌作曲家,成就了意大利牧歌创作技巧大师的风范,不仅关注歌词的表现,同时还注重作品整体的戏剧性,将主调与复调风格完美的结合,运用富于表现力的和声,并且通过牧歌从复调重唱的写作转到器乐伴奏的独唱和二重唱曲。除上述的世俗声乐体裁,意大利还包括世俗合唱曲体裁,如维拉内拉是一种三声部的、分节歌式而且活泼的主调风格,歌词和音乐常常模仿牧歌;小坎佐纳和芭蕾歌都用整齐、快速的主调风格写成,和声清晰,段落均衡等等。意大利世俗声乐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的音乐创作技巧,被同时代和后来的音乐家所使用,对器乐音乐、经文歌和法国复调尚松等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二)法国的世俗声乐体裁
源于法国的行吟诗人的世俗歌曲是民族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理性的世俗音乐体裁——尚松,一直反映着法国人民的民族性:幽默、敏感、潇洒、调皮、持重。在法国,世俗音乐与文学的发展并驾齐驱,法国人采用与时代精神相符的文学诗歌,主要表现为人文主义倾向的抒情和个人感觉的表达。杂彩纷呈的尚松分为主调和复调两种音乐风格,诗歌与音乐结合时,以法文诗歌为主,歌词指挥音符,借鉴吸收法国民歌的主题,按音节谱曲,强调规则的重音,诗歌的韵律对音乐旋律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决定了音乐的曲式,也决定了旋律的节奏,音乐活泼欢快,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尚松多为四部织体,主旋律在高声部,下方各声部基本上以同样的节奏陈述歌词,主要代表作曲家之一克莱芒·雅内坎的尚松最具特色,新的因素将合唱音乐构成地道的“交响性”小音诗,擅于把生动的模仿与情景描绘相结合,《百鸟图》模仿百鸟齐鸣的景象通过巧妙地对位、灵活的装饰音,表现得惟妙惟肖,如身临其境般置身于美妙的大自然之中,展示了大自然中的种种美好与和谐;《巴黎街头叫卖》模仿街头商贩各种叫卖的声音,描绘出热闹的街市景象;《战争》中主要运用模拟战争中的声音的手法,用响亮的喇叭声来表现号角长鸣,以标注重音记号的音符来表现炮火轰隆,又通过变换节拍中强拍的位置来表现战场上的混乱,如实的勾画出战争场面等等。法国的尚松是众多作曲家关注的体裁,通俗明晰的歌词,采用各种复调写作的技法,明快的风格,构成了法国音乐发展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德国的世俗声乐体裁
利德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世俗歌曲体裁,融德国的严肃与意大利的柔美于一体,将弗兰德斯乐派的复调手法与德国中世纪以来的独唱歌曲相结合,形成四个声部,其中一个声部为旋律,其它三个声部围绕旋律声部构成复调或和声织体,广泛吸收德国民间音乐素材,富于青春、生活的气息,歌词内容不是美丽的虚构,而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城市中的业余音乐家——名歌手为代表,他们肩负着德国世俗声乐的创作与传唱,如纽伦堡的名歌手汉斯·萨克斯作有歌曲1000多首,歌曲多角度、多方位的表现人世间生活琐事,优美的旋律唱出广大民众的心声,本民族的德语通俗易懂,是广泛流传世俗声乐的基础。
(四)英国的世俗声乐体裁
16世纪的英国国内政治安定,上层社会生活富足,大大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此时意大利牧歌的英译本《阿尔卑斯山南的音乐》推动了英国牧歌的兴起和发展。英国牧歌受意大利的影响,较意大利牧歌更重视音乐总的音乐结构和自身的完美,采用英语歌词作词,具有本民族特征,以五声部为主,属于对位风格,和弦式的段落与对位式的段落交替出现,音乐节奏与诗歌节奏相符合,常变换拍子,多为田园性和抒情性的诗。重要作曲家托马斯·莫利擅长创作轻快类型的牧歌,主要是主调织体的歌曲,曲调在最高声部,由完全终止式分成明显的段落并带有重复,他强调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这样才能创作出悦耳动听的音乐,充分体现了音乐创作中人是主体、以人为本的精神思想。康索尔特是产生于英国的一种室内器乐合奏体裁,康索尔特歌曲这一世俗音乐体裁是由康索尔特这种室内合奏伴奏的独唱或重唱歌曲,后期阶段发展还加上了合唱。歌词通常为格律诗歌,内容既有严肃的,也有欢快的,形式上既有分节歌,又有通谱体,吸收本民族音乐因素,音乐以抒情见长,较少带有意大利牧歌的影响,威廉·伯德创作了大量的这一体裁的作品。
(五)西班牙的世俗声乐体裁
16世纪西班牙的世俗歌曲体裁——比良西科,它以西班牙同名的诗歌体裁谱曲,是一种反映田园或爱情内容的短诗。音乐具有纯朴的民歌风格,内容涉及爱情、警句、政治、史实等世俗内容,也有涉及宗教内容,以三或四个声部为主,主旋律在高声部,其他声部以乐器伴奏形式出现,以西班牙的琉特琴-维乌埃拉伴奏的独唱歌曲最为多见,揭示的是一个无比优雅精美的音乐艺术,最重要的西班牙作曲家路易斯·德·米兰创作这一体裁尤为出色。“比良西科的价值不体现在歌曲本身,而在于它的器乐伴奏部分,它的伴奏常常是一连串固定的和弦连接,这些固定的和弦序列,后来演变成帕萨梅佐和罗马内斯卡等器乐体裁中的著名低音主题。”[4]91
三、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体裁的美学价值
(一)世俗声乐的发展促使主调音乐的回归与和声体系的完善
欧洲中世纪音乐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复调音乐的出现,其统治地位达千年之久,甚至到文艺复兴时期经文歌都是非常重要的复调体裁。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音乐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体裁形式,尤其是单声主调风格的世俗声乐,常采用乐器伴奏的形式,结构清晰,节奏规整,注意明确的歌词和清晰的音乐织体的相互关系及如何表达,促使了主调音乐的回归与和声体系的完善。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声乐体裁,不同的国家将其发展的各具特色,无论是主调风格还是复调织体,更注重的都是诗歌的内容,注重音乐对歌词的细致表达。众所周知,复调声部越多,对歌词的表达就会越模糊,这是因为每个声部都在描述,每个声部都在表达,都很重要也就都不重要,音乐压迫了诗句,模糊了诗句的表现力。世俗声乐将各个声部以相同的、较为单纯的节奏在一系列的和弦基础上进行,突出最高声部的旋律,形成主调织体的效果,突出了诗句的表达。世俗音乐要表达的内容多是歌颂爱情、社会事件、风俗人情、自然风光等题材,音乐要服从题材的需要,采用的主调风格音乐,将人声唱的声部为主要声部,器乐为伴奏的声部,这样既能突出声部的主旋律所揭示的主要题材和内容,同时器乐伴奏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琉特琴、维奥尔琴、竖笛、肖母管、横笛等乐器都可作为伴奏乐器,其中琉特琴是当时流行最广、世俗声乐伴奏应用最多的乐器,经常采用的一种伴奏技巧——法索伯顿,即为四声部根音位置的三和弦织体,或是复调音乐与和声的混合运用,对和声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瑞士学者格列利安将自己的音乐审美价值观念建立在世俗音乐生活的基础上,强调“不论是单声旋律也好,单声部的调式也好,都比多声部歌曲的应用广泛。……带有适当的歌词、出色的、辉煌的单声部旋律,可以对大多数人提供愉快。格列利安认为主调音乐比复调音乐更优越。”[5]53
(二)世俗声乐的器乐伴奏加快了器乐独立的步伐
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器乐都是从属于声乐,是声乐的配角,可有可无,甚至在宗教音乐中只有管风琴有参与音乐生活的特权。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中的器乐伴奏,大大提高了器乐在音乐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为器乐的独立提供了有利基础条件。西班牙的世俗声乐比良西科的器乐伴奏,“常常是一连串固定的和弦连接,这些固定的和弦序列,后来演变成帕萨梅佐和罗马内斯卡等器乐体裁中的著名低音主题”。[4]91文艺复兴时期手工业、金属冶炼等方面的发展都为乐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家庭音乐生活的需求成为器乐发展的动力,这些都大大推动了器乐的发展和创新。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逐渐丰富,一些乐器还形成了乐器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演奏技法用于独奏、重奏或声乐伴奏,在给世俗声乐伴奏时,器乐有时可代替人声,有相互问答的形式,形成别样的风格、情趣,器乐逐渐凸显其独立发展的倾向,逐渐摆脱了对声乐的依附,朝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器乐的‘客厅’演奏更是社会阶层的风气。买不起斯皮耐琴或楔槌键琴的人可以在英国的理发店里买到一把便宜的琉特琴。乐器根据贵贱分成‘贵族’、‘平民’两类。上等人应该会弹精巧的乐器,风笛、簧管、喇叭和声音尖利的笛子不适合有教养的高雅人士吹奏。琉特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流行的乐器,犹如今天的钢琴。”[1]189
(三)世俗声乐中音乐与诗歌结合的倾向导致了歌剧的诞生
歌剧是在16、17世纪之交文艺复兴的最后阶段产生的,是人文主义艺术家把诗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综合艺术体裁。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重视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主张以诗歌为主,音乐根据诗歌的韵律和需要来谱写,有器乐伴奏,具有主调音乐风格,人们在世俗声乐中感受情感的抒发和畅想,刻画和表白自己的内心世界,使诗歌在音乐旋律的装饰下栩栩如生,扣人心弦。歌剧同样主张以诗为主,音乐为辅,具有旋律清楚的主调音乐风格,乐队伴奏不仅仅起到支持作用,还能表达演唱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更注重追求对人内心世界与情感生活的揭示,这些都与世俗声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16世纪牧歌中音乐与诗的结合,以及牧歌又渗透到戏剧表演中,音乐在戏剧中的配音作用越来越大,也促成了两者在新艺术形式中的结合;16世纪声乐与器乐作品中主调和声风格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如果没有复调音乐向主调音乐的过渡,没有和声观念以及相应的数字低音,从音乐织体的纵向关系去构思音乐,也就不可能产生歌剧音乐。”[5]4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横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两个时期的伟大音乐家蒙特威尔第,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位伟大的世俗声乐作曲家,在巴洛克时期又是一位卓越的歌剧作曲家,集文艺复兴世俗音乐之大成,开巴洛克歌剧之先河,在欧洲音乐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一席。由此可见世俗声乐导致歌剧诞生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四)世俗声乐具有大众化和娱乐性的美学价值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艺术追求而实现的是健全的感官享受,所以整个希腊精神所包含的是乐观主义,爱好的是健康、自然、恬静、和谐和秩序等属性。文艺复兴所谓再现古希腊、古罗马的时代,其实已大大超越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范畴,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人文主义,即“人乃万物之本”。主张认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重视人的价值和个性自由,提倡人权和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世俗声乐遵循这一发展规律从宫廷和贵族中走向市民和大众,使更多的人们都能够接触、欣赏、创作音乐并享受于其中,“朗迪尼早已抱怨人人都想作曲,对专业音乐家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合格的业余作曲家之多,使专业作曲家难以立足。”[1]188乐观主义精神是人类永恒的渴望,音乐带给人们的愉悦不言而喻,因此音乐生活成为市民家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聚会、沙龙、庆典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有不满足于听隆重庆典或宴饮娱乐的音乐伴奏,要听专为欣赏而举办的演唱演奏,更甚者往往还亲自参加表演;女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恢复,可以参加音乐生活并备受男人的称羡和赞许,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队伍在不断的壮大,世俗声乐的表演不受时间、场地、形式的约束,内容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可进行更改,更贴近人们的心灵,与人产生精神的共鸣,备受大家的推崇和喜爱,在娱乐的同时,更享受心灵的慰藉和愉悦。乐谱的印刷为音乐的普及和大众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熟人间的‘社交’音乐的流行是伟大的牧歌艺术昌盛的主要原因。每一个有修养的人都要参加即兴的音乐晚会,否则被认为是粗俗,缺乏风度。”[1]189由此可见世俗声乐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意义。
世俗声乐犹如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发展中一朵瑰丽的奇葩,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追求以及审美价值取向,同时也提供了当时音乐家们的创作手法、创作精神和创作理念,因此说,对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声乐体裁的美学价值研究,不仅能够体现当时的音乐创作越来越臻于完善,还表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及具有大众化和娱乐性等美学价值,这为更全面的把握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发展、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和判断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为迎接宏伟辉煌的巴洛克音乐奠定了基础。
[1]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于润洋,译.卓菲亚·丽莎[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3]唐纳德·杰·格劳特.西方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4]沈璇.西方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5]修海林.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徐星华)
J601
A
1008—7974(2010)09—0058—05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创作的美学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9B297
2010—06—25
王冰(1972-),女,吉林通化人,现为通化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