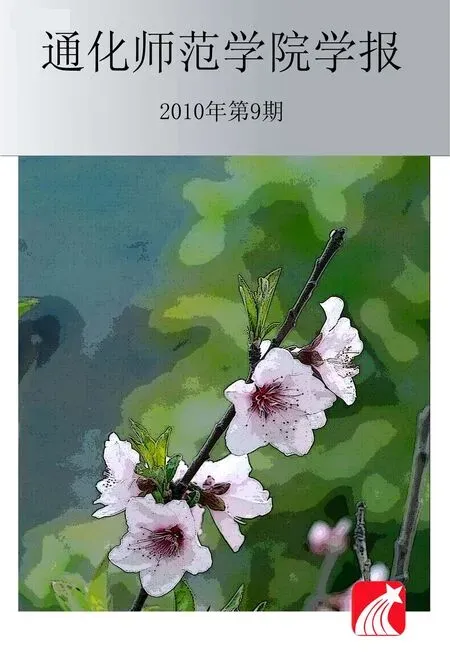童年的穷苦创伤经验对郁达夫艺术创作的影响
2010-03-23刘丹
刘丹
(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童年的穷苦创伤经验对郁达夫艺术创作的影响
刘丹
(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穷苦心酸的童年经验使其艺术创作表现出“生的苦闷”的郁式哲学,尤其是作品中“零余者”形象的塑造更表现出作家的自身气质。本文试以《茑萝行》为蓝本,展示其童年的穷苦创伤经验对郁达夫艺术创作的影响。
郁达夫;童年经验;苦闷;零余者
童年是是一个梦,七彩缤纷;童年是一首诗,妙不可言;童年是一段音乐,优美舒展;童年是一条河,明净清澈;童年是理想的摇篮,童年是记忆的风车……快乐安逸的童年令人回味,酸楚痛苦的童年更让人难以忘怀。
尽管童年在人生旅程中短暂而初始,但它却往往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终生不渝的印象。既然文学是作家反映人生的一种精神活动成果,那么童年经验对于作家而言更是刻骨铭心的,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作家的童年经验中找到印迹。所谓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1]84美国作家凯琴指出:八到十五之间是一个作家一生的个性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他不自觉地收集艺术的材料,他成熟之后可能积累许多生动有趣的印象,但是形成创作主题的材料都是在十五岁以前获得的[1]87。尤其是创伤性童年经验更能成为他们创作的强烈“动力源”。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弗洛伊德也认为,文艺创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中国当代作家张炜则讲得则更为具体:“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外部世界对他的刺激,常常在心灵里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差不多所有成功的艺术家,都在童年有过曲折的经历,很早就走入了充满磨难的人生之途。这一切让他咀嚼不完。无论他将来发生了什么,无论这一段经历在他的全部生活中占据多么微小的比例,总也难以忘怀。童年真正塑造了一个人的灵魂,染上了永不褪脱的颜色。”[2]28-29那么,郁达夫的童年经验又给他的创作以怎样的动力源泉呢?
(一)穷苦心酸的童年经历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而又充满忧郁感伤的作家,他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出世,伴随他而来的就是悲苦交加的命运。他甚至把自己的出生称为“悲剧的出生”。3岁丧父,母亲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更别说购买其它物品。当他以优异的成绩跳级之后,看到周围许多同学都穿着皮鞋,尽管家境困窘但他还是不自觉地央求母亲也为他买一双新皮鞋。为了不伤年少的郁达夫的心,本已四处筹款、经济困顿的母亲仍然带着他跑了一家又一家鞋铺请求赊账。但是结果得到的却是商家的一番番羞辱。童年的郁达夫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自从这一次的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的仇恨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还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3]28-29正如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中写道:“儿时的回忆谁都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可见经济上的贫困对郁达夫的影响是致命的,性格中的极端敏感、孤独、表现自我、忧郁感伤都是由于童年时代的穷困生活所致。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在创作文本中就以“生的苦闷”的情绪体验得以抒发。从他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篇左右的小说中,表现“生的苦闷”的作品就占了大部分,特别是小说《茑萝行》更是对贫困遭遇的坎坷倾诉。
(二)“生的苦闷”与“零余者”原型的塑造
《茑萝行》中的“我”和妻是出于旧式婚姻而结合的,虽然婚前不曾有过爱情,但婚后还是建立了相互爱怜与同情的夫妻感情的。如果不是经济上的拮据,二人本可以朝夕相处、互敬互爱,但是严酷的生存问题却严重影响了二人感情。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我”是官费生,每月还有一些中国政府提供的几十块钱的官费津贴,“虽则每月所得不能敷用,是租了屋没有食,买了食没有衣的状态,但究竟每月还有几十块钱的出息,调度得好也能勉强免于死亡。”但“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来,缚在我周围的命运的铁锁圈,就一天一天的扎紧起来了”。“我失了我的维持生命的根据”,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不善交游,又不会钻营,因而四处奔走都找不到职业。这种巨大的失望只能使“我”或徘徊于公园放声痛哭,或徘徊于黄浦江边试图自杀。后来“我”终于谋得了一份最苦的教职,把妻接到A地同住,但失业的恐怖却时时在内心颤抖,因此,当得知妻已怀孕,这种职业不保的恐怖就更加强烈了:“一想到辞了教授的职后,就又不得不同六月间一样,尝那失业的苦味。况且现在又有了家室,又有了未来的儿女,万一再同那时候一样的失起业来,岂不要比曩时更苦。”于是“我”粗暴、烦躁,经常对妻谩骂,然而骂了以后又立即痛责自己,陷入深深的懊丧和悔恨之中,上前去爱抚妻,以至两人相视对泣。孩子出生后,“我”果真失业,天天在家中喝酒,喝醉之后就大骂妻儿。妻走投无路就投江自杀,幸而被人救起,不久后体谅“我”的妻为解除“我”的负担独自带着孩子返回浙江老家去了。《茑萝行》使我们看到,一对年轻夫妻正是由于没有经济权没有工作权,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所以不能不成为人生舞台上受人摆布的傀儡。“我”的暴躁、妻的自杀,一切的不幸都源于经济上的贫穷窘困。作品中郁达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爱情和夫妻生活并不是梦境,并不总是鸟语花香,而是人类的现实生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也会渗出痛苦的血泪来。经济的窘困给这对年轻夫妻的爱情生活投下了多么巨大的阴影。日本留学回国后生活上的困顿,唤起了郁达夫童年时代的灰色记忆,穷苦生活又一次复活于其创作文本中,强烈地表现出“生的苦闷”。
如果说,在《茑萝行》里,好胜的“我”不愿意演一出失意的还乡记,只好让妻子带着幼儿独自回乡,自己还想留在上海奋斗,那么,仅仅过了三个月,“我”仍然不得不成为这出失意的还乡主角。《还乡记》和《还乡后记》所叙写的就是“我”从上海回富阳老家一路上的经历。“我”在上海奋斗了几个月,仍然是一个“有识无产者”,一个“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于是只得带着“两袖清风,一只空袋”和满脸愧色,返回故乡去见老母妻儿,“想去看看故乡的景状,能不能容我这零余者回家高卧”。在另一篇题为《零余者》的散文里,我们也看见这样的话语:“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又是郁达夫笔下一个突出的形象表现。《茑萝行》中的“我”自怨自艾是“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沉沦》中的“他”怀着“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南迁》中的伊人厌世忧郁、衰颓沮丧、有感于飘零身世,最后感风寒而病入膏肓;《迷羊》中的王介成犹如一只在人生中迷了路的羊不知所终;《过去》中的李白时只落得飘零一身,颠沛流离;《烟影》中的文朴哀痛自己的妻离子散,终借烟麻醉、借酒浇愁而自戕;《十一月初三》中的主人公更是以零余者自况,叹息“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冷颤”……这些众多的人物形象都有着共同的特征:“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于世无补”。他们的性格复杂多元,敏感多疑又麻木不仁,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愤世疾俗又随波逐流。在这些“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零余者”身上,显然投射着作家自我的身影和个性气质。作品中忧郁、孤独、凄切、哀婉、感伤的基调也正是作家的童年创伤经验在作品中的突显。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亨利·特洛亚曾说:“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之所以不得不写作,并非为了尝试某种未曾有的表现方式,而是出于内心的冲动。”[4]467郁达夫曾说:“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络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5]85他的这些“零余者”显然是从屠格涅夫创造“多余人”形象以表现忧伤情绪中受到的感悟与启迪。然而这个“零余者”形象虽受屠格涅夫的影响较大,但通过对郁达夫童年的考察我们却从他穷困、孤苦的生活找到了促使他进行创作的更强大的内驱力。尽管我们在这个“零余者”身上看到了郁达夫的身影,但是正如荣格所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无数次重复的悲欢的残余,而且总体上始终循着同样的路径发展。它犹如心理上的一道深掘的河床,生命之流在其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因此,从这个“零余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普遍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这种意象已深深镂刻在我们记忆的深处任凭激流的冲刷。我们看到贫穷是郁达夫生活的主旋律,所以它作为一种童年创伤经验,在郁达夫的记忆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除了知识分子形象,郁达夫还为我们展现了许多劳苦工人和穷苦的风尘女子形象,我们同样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和物质贫困给他们造成的“生的苦闷”:《薄奠》中的人力车夫由于社会的压迫,自己买一辆人力车的希望而随落水身亡成为泡影;《茫茫夜》中的海棠为生活所迫靠出卖肉体换钱过日子,早年卖笑的翠云即使是嫁人,但男人的早死又使她无所依从,重操卖笑的生涯,等待她的结局依然悲惨。令人窒息的“生的苦闷”就像一幅厚厚的黑色帷幕,笼罩在郁达夫的生命中,成为“郁达夫式”的哲学。
结语
童年经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真味和深厚的人性内涵。也许正源于此,人们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缅怀已经逝去的童年时光。艺术家更是执着于全部情思,追忆和叙写自己的童年时光和经历。鲁迅的童年记忆复活在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巴金的童年经验使大公馆的少爷深切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萧乾的童年经历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寄人篱下的阴影;莫言童年的饥饿、孤独、忧伤在《五个饽饽》、《石磨》中得到了艺术再现。事实上,艺术家的童年生活已经作为一种潜意识,渗透在这些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凝结成为作品的形象和风格等深层意蕴。孤苦的童年使萧红作品表现出悲美情结;女性生活氛围形成了王统照《童心》的阴柔美风格取向;父慈母爱的和谐生活使冰心接受了“爱的哲学”;封建家长的严酷压制,使曹禺形成叛逆的探秘心理;毫无父爱又使张爱玲蒙上可怖的心理阴影。迥异的童年经历会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诗文风格,复杂的童年经验必然会形成每位作家各具特点的创作心理。
穷苦心酸的童年创伤经验赋予了郁达夫感伤忧郁、浪漫自卑的人格特征,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困扰着他的一生,也影响着其笔下的艺术创作。弗洛伊德就认为创作动机的形成与作者的童年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创作家对早年经验的回忆(通常指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了实现。[6]8-9郁达夫正是将潜意识中的童年创伤经验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创作动机,表现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而在这种独特的童年经验的影响下,郁达夫的作品也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1]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楼肇明,志愚.禁锢的火焰色——理性与反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郁达夫.书塾与学堂[G]//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崔道怡.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92.
[5]郁达夫.闲书[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6]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G]//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章永林)
I206.6
A
1008—7974(2010)09—0056—03
2010—07—20
刘丹(1978-),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教育学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