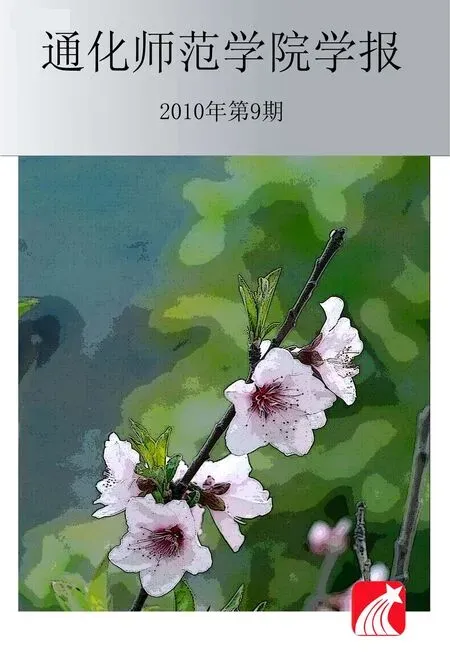《诗经》重章叠沓艺术新论
2010-03-23任树民
任树民
(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诗经》重章叠沓艺术新论
任树民
(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重章叠沓是《诗经》重要的抒情体式之一。塑成《诗经》这一复沓艺术的质素有三,即民间性、表演性以及场合性。这三个方面不仅共同塑成了《诗经》这一叠咏复沓艺术的反复使用,尤其是表演性与场合性决定了风诗与小雅反复叠咏。
重章叠沓;表演预设;演奏场所
就抒情体式而言,《诗经》除采取四言句式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显然要属它大部分诗篇都采取了重章叠沓这一艺术形式。根据夏传才先生在《诗经语言艺术新编》一书中的统计,《诗经》中采用复沓章法的诗歌有177篇,占305篇的58﹪,而这占了305篇一半以上的叠咏体又多集中在《国风》与《小雅》部分。[1]42-43由于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认为十五国风是民歌,而复沓又“主要体现的是民间作品的特色”,[2]因此,在夏先生这辈学者看来,集中保存在“《国风》和接近《国风》的《小雅》”当中的这一复沓艺术主要是由这部分作品的民歌性质所致。[1]43
新时期以来,论者罕有再把《国风》视为民歌了。“且不论《风》诗里有大量的诗作可以被证明是贵族阶层的作品,即使假设它们是从民间流传出来的,也至少需要有这样的基木认识:它不是某个民间百姓随口唱出,就能够唱得如此整齐、精致的,而一定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传播,并经历了一个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加工、提炼的经典化过程,才最终完善、定型的,这样的歌曲才能够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3]68在笔者看来,这一意见较为通达。我们认为《诗经》当中,尤其是十五国风,有一部分诗篇来自民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部分诗篇当中也着实表现了许多来自民间的风情风俗。但是,正如上述引文所指出,并不能因此即把风诗视为民歌。于是,当下的一部分学者便抛弃了从民歌这一视角来寻绎这一复沓艺术的渊源塑成。但是,“诗为乐心,声为乐体”,[4]墨子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5]《诗经》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显然,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已是古今学术界的共识了。因此,近十年来,以赵敏俐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人鉴于《诗经》的这一特征即把它定质为歌诗,进而从歌诗这一角度来探讨《诗经》的相关艺术特质。本文不揣鄙陋,亦拟从歌诗角度来探究一下《诗经》的重章叠沓艺术。
一、歌诗表演与重章叠沓
据王靖献博士的意见:
《诗经》中的“诗”与“歌”已经获得它们各自的意义。《大雅·卷阿》已表明,“诗”指题材内容的文字表达,而“歌”则指唱“诗”的行为:“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其它许多地方也如此:一说到“歌”,即指唱“诗”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召南·江有汜》、《卫风·考槃》、《魏风·园有桃》与《陈风·墓门》等诗中找到显著的例子。[6]
在我们看来,王博士的这一意见颇为中肯。但很显然,它与《诗经》的歌诗定质并不龃龉。而且王博士还以此告诉了我们歌与诗的一个区别所在,亦即歌与诗虽然都是用以来抒发情感,但歌并非是用于案读,歌“指唱‘诗’的行为”,也就是说,歌具有表演的特征。诗人说:“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歌的也是诗。但是,歌与诗是有区别的。歌是用来表演的,即便是个人的自娱自乐:“我歌且谣”,显然也有自我表演的成份。那么表演又有何特点呢?就抒情文学而言,在我们看来,表演就是把情感充分展现出来以供观众欣赏进而引起共鸣。笔者拙见,《诗经》歌诗的这一表演特点是促成诗章之中重章叠沓反复使用的重要塑成要素之一。
赵敏俐先生剖析时下的流行歌曲对照《诗经》以寻绎其中的重沓艺术:“虽然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看起来形式变化很多,不必拘于常法和定式,但重复仍然是最基本的手法。这说明它是一种符合人的审美心理需要的表达方式,是为了演唱的便利,满足于乐歌欣赏的需要而形成的。书面文学所忌讳的重复,在歌唱中形成了有力的表达形式。”[3]65赵先生颇有眼光地在比较当中发现了重沓手法的审美特质及其在表演文学当中所承担起的作用。寻绎古今,在表演文学当中,复沓着实是“一种符合人的审美心理需要的表达方式”。而《诗经》歌乐舞三位一体的这一表演性质也就决定了复沓不会缺席于我们的早期诗情抒发。
按照当下的接受美学理论,任何一部作品其实都预设了一个读者,但很显然,表演文学的这一观众指向是最为突出的。诗情涌动的伊始之际,《诗经》是用来表演的,它不像后世的案头文学那样可以被仔细地咂摸、反复地咀嚼以寻求理解,是时它必须在当下感染观众以寻求一种理解与共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复沓本就是“一种符合人的审美心理需要的表达方式”,是故,就像当下的流行歌曲运用了诗章与乐曲的复沓,反复层染情感以使观众充分理解那天马行空而又稍纵即逝的情感一样,《诗经》时代的乐师们也在运用着,并且还不少。例如《召南·摽有梅》。诗写少女盼望求婚的男子及时前来,别让自己等得青春消逝。“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梅子零落,象征女子青春渐渐消逝。第一章说树上的梅子还有七分,姑娘盼望小伙子快找个吉日来求婚;第二章说树上只有三分了,姑娘盼望得很急了啊,可小伙子还是没有来;第三章梅子凋零,要用簸箕来收了,时间在流逝,可那小伙子来没来啊?!我们急,姑娘更急,急得只要对方开一开口,她就可以嫁给他。可是,小伙子到底来了没?这样,诗中的情感,就通过换用几个具有表现力字眼的章节复沓,不但充分展现了抒情主人公焦急的心理,同时也把观众的情感调动起来,一颗心提到嗓子眼,我们急,姑娘更急,最后在双方互动中形成一种巨大的具有审美落差的心灵张力,从而把诗歌的情感抒发推向高潮。赵先生认为,复沓是“为了演唱的便利,满足于乐歌欣赏的需要”,通过上述分析,很显然,赵先生的这一意见是颇为中肯的。复沓不仅能够使诗人的情感得以尽情抒发,而且还能够以此更好地感染观众,唤起观众共鸣。我们认为,正是表演文学的这一观众预设,致使诗人在展现情感之时,予以了反复的章节复沓。
二、表演场所与复沓叠咏
通过寻绎,我们认为,歌诗文学的表演预设特质直接塑成了《诗经》这一章节复沓艺术,那么,何以同是歌诗,《国风》与《小雅》反复复沓叠咏,而颂诗与大雅却很少运用呢?
在我们看来,塑成《诗经》这一复沓艺术的质素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民间性、表演性以及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场合性。
诗有三体,风雅颂是也。关于其歌乐场所,郑玄说:“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矦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7]清孙诒让正义《周礼·春官·磬师》“教缦乐燕乐之钟磬”说:“燕乐用二《南》,即乡乐,亦即房中之乐。盖乡人用之谓之乡乐;后、夫人用之谓之房中之乐;王之燕居用之谓之燕乐,名异而实同。”[8]雅,朱熹解释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羣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徳。”[9]115关于颂,郑樵《通志》卷七十五《昆虫草木略·序》云:“宗庙之音曰颂。”[10]朱熹说:“颂者,宗庙之乐歌。”[9]260这就告诉我们,风雅颂的演奏是有场合要求的。风诗与小雅用于乡之宴饮,“王之燕居”,而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颂诗用于宗庙已经没有疑义,朱熹说大雅:“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徳。”显然其演奏场所也不可能是歌乐的宴饮场合。《礼记·乐记》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11]1086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郑玄解释说:“《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耳。”[11]1081对此,赵敏俐先生剖析说:“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12]我们认为,这一意见颇为精警。宗庙是一个“凝重、肃穆”的地方,那么与之相配的乐与诗也一定要有“凝重、肃穆”的特质。简单的章句配以迟缓的音乐,显然是这个场合所要求的用乐。那么由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诗之三颂是这个样子,而不会像风诗与小雅那样,显然这里已经毋庸置言。因为,复沓叠咏带来的是情感的冲击,生命的欢快,生活的苦恼,这是一个情感四溢的言述体式,而这,显然与宗庙的庄重场合是不协调的,相反,宴饮作乐,酒酣耳热,情感的热烈动荡正是此时所需。试想,今天,如果你去KTV,你会唱什么歌呢?如果你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你会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呢?再如果,如果我们在社稷坛祭天祭地你会唱妹妹你坐船头吗?大雅的歌乐场合虽然还不能确指,但其或述民族之历史,或记国家之大事,或谈朝政之得失……“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徳”,[9]115显然,重章叠沓的这一言述体式与其风格也是不相符合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正是基于这一不同演奏场合的不同表演预设,促使复沓成为风诗和小雅的重要言述体式之一。
综上所述,塑成《诗经》复沓艺术的质素有三,即民间性、表演性以及与前两者密切相关的场合性。这三个方面不仅共同塑成了《诗经》这一叠咏复沓艺术的反复运用,尤其是表演性与场合性决定了风诗与小雅反复叠咏。
[1]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新编[M].北京:北京语言出版社,1998.
[2]褚斌杰.《诗经》叠咏体探赜(提要)[C].第五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658.
[3]黄冬珍,赵敏俐.《周南·芣苢》艺术解读[J].文艺研究,2006(11).
[4]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5.
[5]毕沅.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88.
[6]谢谦.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35.
[7]李学勤.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5.
[8]孙诒让.周礼正义[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00.
[9]朱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980.
[1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赵敏俐.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J].社会科学战线,2002(5):94.
(责任编辑:章永林)
New Points on Usage of Rhetorical Device:Repeti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REN Shu-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BeiHua University,Jilin,Jilin 132103,China)
The repeti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express emo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Basic reasons leading to this feature are the civil character,performabilty and occa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These three reasons,for which the ode and Daya seldom used,not only caused the widespread use of repetition,but also determined the abundance repetition of Guofeng and Xiaoya.
repetition;presupposition of performance;performing site
I207.2
A
1008—7974(2010)09—0049—03
2010—06—11
任树民(1979-),辽宁葫芦岛人,北华大学文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