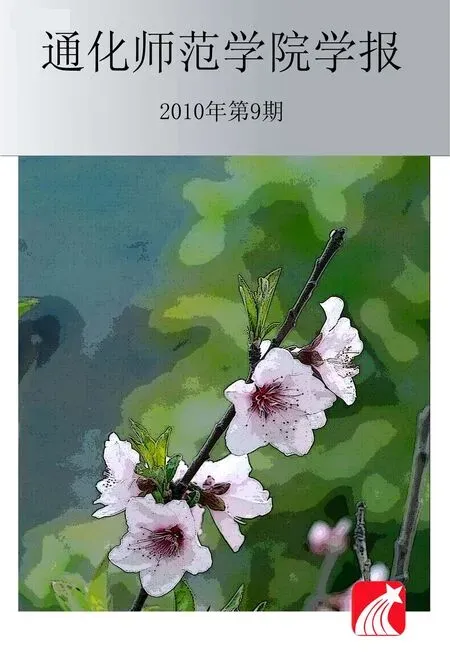从张謇和涩泽荣一的义利观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转型
2010-03-23杨延峰
杨延峰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7)
从张謇和涩泽荣一的义利观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转型
杨延峰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7)
张謇和涩泽荣一分别是日中两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实业家,两者的义利观在同时代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文中以近代化程度为基准,比较两者的义利观在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相异性,并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日中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内在文化传统与外来近代化思想的融合的。
儒教理论;文化传统;义利观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远东。中国和日本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同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危局,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契机,迈开了近代化的艰难步伐。通过明治维新,日本顺利的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三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日本则从此挤身于资本主义列强行列。中日这两个曾站在近代化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何以三十年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与两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笔者从张謇和涩泽荣一的义利观的近代化转型这一角度来粗浅的探讨一下:像中日两国这样的儒教文化圈中的后发展国家,在近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儒教伦理观进行近代化改造的一些经验教训。
一
众所周知,实业伦理化的核心就是“义利之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謇主张“言商仍向儒”,“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他对以追求私利为第一目标的西方价值观念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强调企业活动和营利行为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这与涩泽荣一的经济道德合一论非常相似。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首先,张謇很少明确的谈义和利的关系,对这个问题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然而,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涩泽荣一的儒教观念在西洋合理思想的过滤下得到了重新构建。据此,他的义利观较早的摆脱了张謇终生信奉的所谓“中体西用”思想,只是还保留了一个儒教的外壳。涩泽荣一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孔子的义利说进行了系统的重新解释。
具体来说,涩泽荣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即:私利公益说,经济道德合一说,论语算盘说,从而把儒学德育论中强调的“义”和实用教育论中强调的“利”巧妙的结合起来。他论述说:“兴古来之美风求真知于世界并将其归化为我有,两者相辅相成将对我们日本人的东西文明融合之使命有很大帮助”。涩泽荣一试图以“义利两全”来确立明治时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秩序,为资本主义的求利行为谋求合法性依据。他在义利之辨中明确的承认利的正当性,“必须消除那种认为仁义道德必定是吃亏,得利必定不仁不义的误解”。涩泽荣一的所谓义利两全,就是在“义”的指导下求“利”。“道德与经济两者应并行不悖,生产殖利依靠仁义道德得到发展,而仁义道德又依靠经济得到发扬光大”。
同时涩泽荣一还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批判宋代的程朱理学,推崇阳明学,恢复所谓的孔孟之学的本来面目,从而为他的实用主义的义利观找到了理论依据。涩泽荣一认为,孔孟之道的本意是主张致富经国和利用厚生的,只是宋代的学者将其误传才产生了轻视商业的倾向。他指出:“将孔孟之道中的仁义道德与利用厚生剥离这一现象,始于程朱学派中的闽洛派,我虽不才,仍时时痛感该学派之罪”。他进一步阐释说,《论语》、《大学》里有“格物致知”的说法,在孔孟之道的本意中仁义道德与利用厚生也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如此,“宋朝的学者仍然任意的曲解孔子的教义,坚称富与殖利非圣人所云”。
从表面来看,涩泽荣一似乎只是批判了朱子学,但实际上,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教特有的道德观。例如,涩泽荣一经常称呼自己为“买卖人”,其真实用意就是对政治的排斥,是对“以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方为人生之本”这一既定观念的挑战。涩泽荣一指出:“总之,政治是从实业中产生的,政治是实业的辅助机关,实业为主政治为客”;“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会议员,都要依靠实业界的力量。他们就像影子一样,都是依靠我们的反照增加光辉的”。据说涩泽荣一辞去大藏省职务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商业地位低下的状况。因此,涩泽荣一在引用《论语》的时候,实际上是脱离了儒教思维而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解读的。这个现实生活的土壤就是指经营商业的盈利活动。因此,涩泽荣一的“义”与“利”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在涩泽荣一的“义利观”中,“义”与“利”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二
张謇也认为孔子的思想“明伦察物,有用于人治之事”,只是后来被“世主”和“曲儒”加以歪曲篡改,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自世主假其一端之义以为符,而孔子之道晦”,也就是说,由于历代封建帝王出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对孔子思想进行的阉割,使孔子思想变得面目全非,进入歧途。他认为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曲儒”为了功名利禄,扼杀了儒家思想的生机,变得脱离实际,不尽人情。“自曲儒假经义为科举利禄之途,缘之而孔子之道益晦”。所以张謇的“尊孔”实际上是要解除宋儒对儒家思想的束缚,推翻强加在孔子思想中的不实之词,恢复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一点与涩泽荣一的思想十分相似。
但是,他并没有像涩泽荣一那样批判儒教伦理制约近代化发展的根本问题---义利之辩问题,张謇虽然很想从历史书籍中发掘一些可以经世致用的道理,但在思想上始终没有冲破正统义利观念的束缚。而且,他始终未能摆脱对儒家所谓“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张謇最基本的思想和性格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言商仍向儒”。可见,他的基本认同点仍在绅和士,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基,经商逐利不过是他们借以实现人生抱负的方式和手段,并非他们的人生目的。为此,他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商人的身份,而把自己的作用界定为“通官商之邮”。
正因为忠实于儒家的信条和规范构成了张謇思想的基本特征,因此,当他投身历来被士大夫视为末业的商界时,身为士大夫的张謇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难以言喻的。比如他不能对那种视“儒而谋商”为背道行为的传统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作为一介寒士,张謇在病逝前一年(1925),回顾生平时还曾讲道:“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然兴实业则势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以嚼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又如张謇始终“耻言货殖之利”,他反复强调从事企业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教育和实现地方自治。他把创办企业的动机,归结为力矫宋儒只说不做的积弊:“既年轻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由此可见传统的儒教伦理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四书五经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张謇曾经反对儿童读经,(从内容的艰深庞杂,不切实用,不利于资产阶级尽快培养人才的角度来反对)他说:“自成童以至于弱冠,必责以尽读全经,而经乃徒供获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但是后期张謇又自食其言,一反过去反对读经的意旨,认为国体改革之后,道德凌夷,纲纪废堕,是由于“一切经书不复寓言”,因此又赞同加授孔孟经书,提出:“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俾儿童时代即知尊仰孔子道”。这说明张謇的近代化观念意识是比较模糊的。
以上可以看出,在张謇的义利观中,儒教伦理和近代思想的融合是比较肤浅的,其融合过程是缓慢的,且存在着反复。
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这种“义利之辩”中,涩泽荣一打破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所表达的是注重功利价值的新价值观。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对儒家的义利说进行了系统的重新解释,从而使他的儒教的“义”和“利”达到了很好的融合。为此,他不惜严厉的批判朱子学中的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制度。张謇则始终徘徊于“义”与“利”之间,他始终没有摆脱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张謇采取折衷的办法,主张用“中西兼具”的调和思想来应付。与涩泽荣一相比,他对儒教伦理的改造是很不彻底的。他没有像涩泽荣一那样批判儒教伦理制约近代化发展的根本问题——义利之辩问题,在思想上始终没有冲破正统义利观念的束缚,因此在他的义利观中,儒教伦理和近代化思想的融合是比较肤浅的,其融合过程是缓慢的,且存在着反复。可以说,张謇的弃旧迎新是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
如果把张謇和涩泽荣一的义利观看做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那么,通过以上比较,笔者认为可以看出如下问题:
中日两国在吸收外来文明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儒家学说和科学思想常处于保守与革新的相互矛盾之中,没有有效的使两者融合,认为科学教育(西洋文明)是必要的,但是只追求表面形式,从而表现出消极的被动适应性,思想文化的禁锢大大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日本却使儒家的伦理思想与西欧的科学思想巧妙的融合,同等相待。日本不是机械的照搬外来文化,而是显示出了很强的融合性。也就是说,日本是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和融合的基础上将其日本化了。总之,从西方文明引入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虽同属于东亚儒教文明圈,但中国文化属于原生的创造性文明,对待外来文化属于消极摄取型;而日本文化是续发性、摄取性文化,对待外来文化属于积极摄取型。
由于篇幅和水平所限,这里仅就张謇和涩泽荣一个人的义利观进行了分析,关于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对他们义利观的影响这一课题,笔者拟在以后继续研究。
[1]金城.张謇研究论稿[C].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2]周见.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张謇与涩泽荣一[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
[4]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刘厚生.张謇传记[M].龙门联合书局,1958.
[6]严学熙.近代改革家张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7]章开沅.张謇传[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8]张兰馨.张謇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9]曾业英.近代史研究[J].1996(01).
[10]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0(4).
[1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95(6).
[12]谭洛非.中华文化论坛[J].2003(3).
[13]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8(1).
(责任编辑:闻礼)
From Shibusawa Eiichi and Zhang Jian's Justice and Profit Outlooks Looked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of Japan and China
YANG Yan-f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Shibusawa Eiichi and Zhang Jian were the great industrialists in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and China.Their justice and profit outlooks were highly representative in the contemporary.This paper takes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as a benchmark to compare existing dissimilarity of their justice and profit outlook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an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o discuss how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inh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xternal modernization thinking in modern times.
Confucian theory;cultural tradition;justice and profit outlook
B259.9;B313.5
A
1008—7974(2010)09—0021—03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52WR31
2010—06—10
杨延峰(1977-),山东滨州人,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