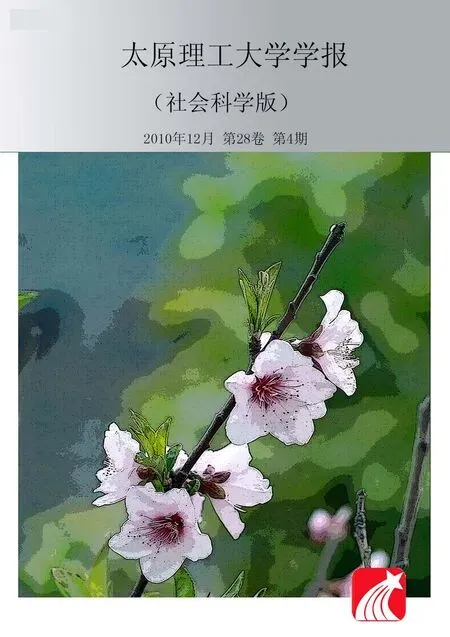解构主义理论观照下庞德翻译思想再研究
——以《神州集》为个案
2010-03-22李言实
李言实
(太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庞德译介中国诗的第一本译集——《神州集》于1915年4月出版,在中西方译学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国内对于庞德翻译思想及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其中蒋洪新、刘军平和祝朝伟译述庞德的翻译理论较为全面。[1]而对庞德翻译的《神州集》的研究,蒋洪新首先做了整体性探讨,谢丹肯定了庞德的翻译创新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本文以《神州集》为个案,从一个新的视角,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来重新研究庞德的翻译思想及翻译方法,继而说明其合理性。
一、解构主义
翻译理论研究的解构主义学派在欧美国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劳伦斯·韦努蒂(Lowrence Venuti)、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解构主义理论主张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其基本观点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它消除了长期占据人们思想头脑的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译者的重要性,阐明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它发现了能指之间的互指、多义和无限延异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文本的开放性和互文性,这样通过译者的创作,原文中不显之处得以发掘,不足之处得以弥补,原文便通过不同的译文逐渐走向成熟。可以看出解构主义的本质并不是拆解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它的创造性或者说重构性。解构主义学者们并不是仅仅停止于拆解和破坏,而是“在把结构拆解之后努力使结构外部的因素与原来结构内部的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多元的重建”[2]。
二、庞德的翻译思想
(一)庞德的翻译目的
实际上,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绝不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而是要从翻译中解决他所处时代文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希望通过翻译达到文学上的创新。通过翻译,“文学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进步,一切复兴都从翻译开始;……人们所谓的诗歌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翻译的伟大时代”[3]。庞德的目的就是要与19世纪末期诗歌中追求华丽辞藻、夸张情感的浪漫主义传统决裂,从而创造出一种更为冷峻、真实、更无所顾忌的现代诗歌风格。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庞德及其所领导的意象派在语言的凝练上,在意象的具体精确上,在韵律的自由流动上,在节奏的构造和强度上,都为英美现代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细节翻译理论
庞德在翻译时并“不强调对原文意义的忠实,或是某些词意义的忠实”[4],他重视细节、意象和变化。根茨勒精辟地将庞德的翻译理论概括为“鲜明的细节(luminous details)”,称其核心在于“精确地表现细节,表现个别词语,表现单个,甚至是残缺的意象”[5]。《神州集》中,庞德将《古风五十九首之十四》中的诗句“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这样的翻译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被认为是因为庞德不懂汉语而对原诗进行的误读与误译。但在谢天振先生看来,这属于“个性化翻译”[6]。因为熟谙中国古诗并了解庞德进行新诗实验的人一眼可以看出,这是庞德的匠心独运,他通过对细节的精确再现及创造性的意象并置,凸现了空旷的大漠映衬下荒凉的古城,由此大自然的萧瑟与人类的渺小一览眼底,形成一副凄凉的画面。
三、庞德的翻译策略
(一)翻译即创作
传统译论中,原作与原作者是中心,是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译作和译者处于从属的地位,译作只是原作的复制品,译者是“仆人”,是“戴着镣铐的舞者”,甚至是“隐形人”。而在庞德的眼中,原作(费氏手稿)只是“信息的提供者”,代表的是过去,是“逝者的声音(a dead voice)”。对于庞德来说,翻译就是创作。正如学者谢明所指出的,在庞德眼里,翻译与创作“似乎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翻译远不仅仅是激发他创作才能的手段,它是诗神缪斯王冠上闪亮的冠饰。”[7]实际上,正是通过庞德的翻译,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英美诗坛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高度的赞誉,并藉此推动了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正是庞德赋予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再生,并且使英美诗歌抛掉维多利亚时代的矫情藻饰,从而使其语言“焕发青春”,这正暗合了本雅明将译作喻为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的观点。
庞德将诗歌分为三类:声诗(melopoeia)、形诗(phanopoeia)和理诗(logopoeia)。中国诗是形诗的杰作。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庞德着力强调保留其意象,以此将“主观呈现于客观”,创造“一刹那间理智与情感的复合”。而中国诗歌最打动庞德的就是用客观物体,即意象来表达个人情感。庞德对李白的诗《玉阶怨》的翻译即是明证。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这是一首“思妇闺怨”诗,但全诗除题目外并无一个“怨”字。它的特征是含蓄而隐晦,表达的是宫女“怨而不怒”。这就需要将情思收敛至极,再转托于外物,也即中国诗歌传统的表达手法“兴寄”。诗人将一切情思托付于景物,以兴喻达意,同时也将解读的任务托付给读者。庞德将之译为:
TheJewelStairs’Grievance
The jewel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with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I let down the crystal curtain
And watch the moon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翻译中庞德突出了几个关键意象:玉阶、白露、水晶帘、秋月。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呈现,庞德基本反映出李白诗的兴寄手法和含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庞德通过意象的客观呈现将“事物本身”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进入诗中的诗性体验,共同感悟诗人那虽富个性但不失普遍的诗性情感。他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帮助西方读者跨越历史、文化障碍,从而给读者以“突然的解放感”和“挣脱时空限制的自由”。[8]
(二)异化翻译策略
一般而言,有无语意单位之间的语法外部连接是英语与汉语的最大区别。由于汉字和汉语的自身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中可以只出现一个个的名词即意象,而省略连接它们的动词、连词等,因此这些意象之间的关系就会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一特点特别适合庞德的意象主义三原则: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或客观的;绝对不使用无益于呈现的词;用音乐性的节奏。翻译中,庞德返回到原诗句的结构中去寻求更有效、更有诗性的表达方式,从中他感悟到汉语语言和诗句的特殊性,并开始欣赏、接受中国古典诗歌无连接的词语(或意象)的排列方式。以下从李白的《送友人》的前两句“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不同翻译进行分析。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Ezra Pound)
Athwart the northern gate the green hills swell,
White water round the eastern city flows.
(W. J. B. Fletcher)
Blue mountains lie beyond the north wall;
Round the city’s eastern side flows the white water.
(S. Obata)
庞德的翻译从句法上看,每一行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只是一个名词短语。这样的表达方式突出了意象的生动性:城北的青山、绕城的白水。而Fletcher和Obata则分别使用了动词“swell”、“flows”、“lie”等。由此可以看出,庞德在诗行中只用名词或名词短语而不用表示逻辑关系的连接成分,是要刻意保留中国诗歌中句法关系的模糊性,以及不同理解的可能性,从而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而这正是庞德所发起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韦努蒂所说的异化翻译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原文的选择,即译什么;其次是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即怎么译。这两个方面只要有一个是异化的,就算是“异化实践”了。由此可见,庞德用最当代化的语言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但在句法及情感表达上,却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不管是在选择“译什么”,还是“怎么译”,庞德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都是韦努蒂所说的“异化实践”。
四、结语
本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作理论支撑,通过对庞德的翻译认识论、方法论进行再研究,发现庞德所主张的细节的精确再现与本雅明的翻译主张不谋而合;而庞德对于词的意义和对文本的解读又暗合了德里达提出的“延异”的概念。庞德所处时代与解构主义思潮在时间上的逆差,恰好说明了庞德翻译观的“先锋性”和“前瞻性”。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质疑和挑战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其偏颇不足之处。解构主义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反拨,带有浓厚的否定色彩。这有可能给各种漫无原则、别出心裁的曲解误解提供理由,使翻译最终陷入混乱虚无之中。其次,解构主义对理论探索较为热衷,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在抽象的理论论述之后,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翻译模式,或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对具体的翻译过程的探索也微乎其微。因此,在承认解构主义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解构主义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及其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切不可盲目追随。
参考文献:
[1] 董洪川.接受的另一个维度:我国新时期庞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外国文学,2007,(5):54-62.
[2] 吕 俊. 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J]. 外国语,2002,(5):49-55.
[3] 谢 丹.意象·语势:庞德神州集译学观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382-386.
[4] 刘 伟,府亚琴.论艾兹拉·庞德的细节翻译理论及其意义 [J].职大学报,2007,(3):78-80.
[5] 陶乃侃.庞德与中国文化 [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6]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8.
[7] Ming Xie.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Poetry[M].London and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99.229.
[8]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