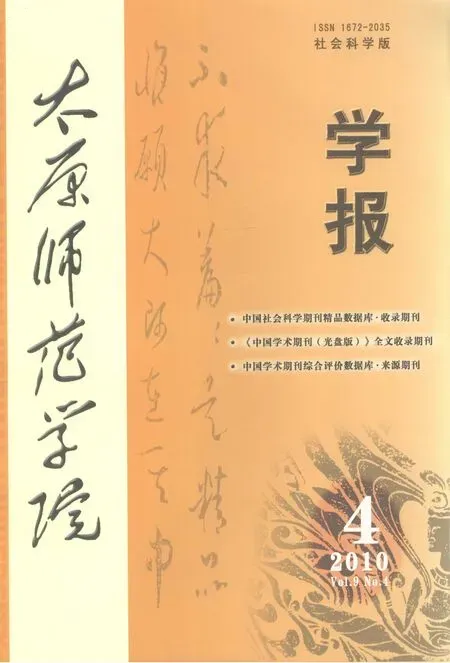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唐传奇中的“化兽”与“化人”故事
2010-03-22黄敏
黄 敏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唐传奇中的“化兽”与“化人”故事
黄 敏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唐传奇中的“变形”故事,大体可分为“化兽”与“化人”两大类。这些传奇故事又常因不同的社会性别主体而显示出不同的意旨及故事形态。由此可见,由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这些故事表达了摇摆在自然与文化间不同的价值与情感取向。
唐传奇;变形;社会性别
在唐人的生花妙笔之下,华美瑰丽的唐传奇之园中,生长着一批诡谲浪漫、摇曳多姿的“化兽”、“化人”传奇故事,它们上承志怪小说,下启《聊斋志异》。其中的主角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但明显以女性居多。且以男性为主体的传奇与以女性为主体的传奇,“变形”的历程相异,“变形”的原因与目的大不相同,意蕴自然也不同。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略谈唐传奇中的“化兽”、“化人”故事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之差异。
一、“化兽”与“化人”故事
所谓“化兽”故事,即传奇中的人类主角变异为兽类外形;相应的“化人”故事是兽类变异为人类外形;还有一类故事,则是由兽类出身变为人类最后又自己回到兽类,这样一个循环历程,可称为“回归”故事。
本文拟略举几例:《河东记·申屠澄》、《崔韬》、《孙恪传》、《焦封》、《原化记·天宝选人》、《李徵》、《补江总白猿传》、《东阳夜怪录》等。试从这些较为典型的“变形”唐传奇文本中,阅读人类成长中的社会性别积淀。
二、以女性为主角的“化兽”、“化人”故事及“回归”类故事
以女性主体完成“变形”的传奇数量众多,本文意不在于传奇中的妖异之氛,而着重于传奇中弥漫的一股山林朴野之气。其实,就主角为女性的“变形”传奇而言,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便是本文拟详述的“回归”类,女主角经历了一个由兽至人又回至兽形的过程;另一类则往往化成人形后,最后仍是由于身上的“兽性”(自然性)被社会所排挤,最后遭致不幸的结局。
就以《孙恪传》、《焦封》、《崔韬》、《河东记·申屠澄》、《原化记·天宝选人》等为例,看看这些来自山林的动物怎样化为软玉温香的女子,又怎样难禁山林诱惑而回归自然。
《孙恪传》[1]叙写秀才孙恪在洛中遇到“兰芬莹濯,玉莹尘清”的袁氏,纳为妻室,却在表兄张处士的怂恿下,怀疑妻子,欲以宝剑除妖,被袁氏斥责并将剑“寸折之”。袁氏为孙恪生育二子,治家甚严。后来孙恪携家赴任经过端州峡山寺,袁氏题诗壁上,与孙恪父子惜别,撕裂衣裳化为老猿呼啸入山而去。
传奇中出现的袁氏,不仅貌美,而且气质高洁,才情不凡。她有能力保护自己,既自强又自爱,在人类社会中也算拥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她始终斩不断灵魂中对山野的牵念,当她看到旧地有“野猿数十,悲啸而跃”时,“恻然题诗,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撕裂了那层于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衣裳外壳,回复老猿的本相随同伴而去,尽管将抵深山尚自不舍地“返视”,她终究还是听从本心的召唤回到自然怀抱中。
《焦封》[1]篇呈现了一个与袁氏颇有相似之处的女主人公形象。士人焦封免官丧妻,在双重打击之下落魄宦游蜀地,于是邂逅了女主人公——知书达理能诗会赋的孙氏(孙者,猢狲也),结为夫妇。然焦封终不脱功名利禄的既定社会框架,为求功名入京求官。孙氏不舍,如倩女一般“奔逐之”,却在途中遇十余猩猩相召,“喜悦倍常”的孙氏亦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去,不知所踪。
孙氏与袁氏一样,才貌俱全,处事端方,能主动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可惜,她们遇到的都是些心志不坚容易动摇的男子。既然这滚滚红尘里条条框框功名仕宦让感情不再纯粹,何不如去除尘世羁绊,脱去一身累赘的“名相”,从此逍遥于青山绿水之间。且看孙氏临去前的话说得多么畅快淋漓:“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亦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正是,道不同者,不相为谋。
《原化记·天宝选人》、《河东记·申屠澄》、《崔韬》则是三篇虎化为女子与人遇合最终又回归虎形啸傲山林的故事。若说猩猩温柔解语,上述几篇的女主人公形象都契合于传统的“贤妻良母”,那么虎女形象显然更加充溢着山林野气,自尊心甚强,也更加危险,投射了男性作家关于女性“魔鬼”、“威胁”之想象的另一面。
《天宝选人》[2]故事发生时期可能较早,篇中叙述天宝年间有选人入京,日暮投宿,于僧院中见一睡美人,却盖着虎皮,选人将虎皮藏起,美人只好嫁与他为妻。夫妻多年后,途经旧地提起相识之事时,选人讥笑妻子的出身,妻子闻之而怒,坦白自己非人,求还故皮。于是觅得虎皮,披之化虎归林而去。在这里,虎皮是美人与山林相联的中介,脱下虎皮这一认同自然的标志,她便是贤妻良母,但只要披上它,她就与这过于“人性化”的社会再无瓜葛。
《申屠澄》[2]篇收在《太平广记》中,情节与《天宝选人》相似,但塑造的虎女形象更为细腻丰满。文中的虎女“雪肤花脸,举止妍媚”,谙熟诗文,一颦一笑间尽是温柔多情。男主人公的俸禄甚薄,虎妻勤俭持家,“情义益浃”,按说应是美满无间不应再生变故了,然而她却在自然景物的感触下,终于吟出自己压抑在心底的想法:“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并且“思慕之深,尽日涕泣”。在发现旧物尚存,那尘埃积满的虎皮(变形必须的中介)后,她终于摆脱贤良淑德的束缚与压抑,“大笑披之,哮吼拿撄,夺门而去”。
而《崔韬》[2]中的虎女形象更进一层,寻得虎皮上身后,“跳掷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虽然叙述不很周详,但让我们觉得有几分残酷的结局却是有象征意味的。人说虎毒不食子,而且此前也没有看到夫妻冲突的场面,为什么虎女要做出如此暴烈的举动?首先,“虎”这一意象的选取本身就具有文化蕴含,这从“母老虎”等民间套语中可见端倪。有研究者认为,杀夫是因悍妒,杀子则为绝念。不由令人联想那手刃爱子而绝然离去的美狄亚,这样的爱恨方式,体现了作者女性想象的另一面,既有波伏娃所言的“魔鬼想象”的影子,又有对于女性力量隐含的恐惧。[3]
三、以男性为主角的“化兽”、“化人”故事
《李徵》[2]是男性化虎故事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它上承《述异记·封使君》,下启聊斋中《向杲》篇,体现了“心为形役”所带来的“异化”结果。李徵作为一个不得意的士子,恃才傲物,却又不得所遇,以致于发展到极端,化成老虎,狂暴食人。但即使性格中暴戾偏执的一面让他化成虎形,虎皮下却依然掩藏着一颗钦羡认同于人世间富贵荣华的“人心”。因此,当同年登进士第的袁参作为监察御史风光经过时,他发出这样的慨叹:“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可见,他对于山林生活的感觉,是出自“异化”的人的视点,把化虎的历程看作永别人世的“天刑”,丝毫没有对自然生活的亲切之感。
《补江总白猿传》[4]是一篇以男性为“兽化人”主线的传奇,大白猿化成人形,抢夺人类女子,在山中过起了王公般的日子。它回复猿形,并非出于本心,而是被人类所报复,临死才露出原相。白猿虽然来自自然,却明显一直在从事着非自然的行为,它化成男性就是为了享有众多艳妻美妾服侍的人间男权生活,也正因为这种自然与文化夹缝中的生活,它把自己的性命也赔了进去。
《东阳夜怪录》[4]相较于上述篇章,可称是众声喧哗,气氛十分热闹。文士成自虚于月夜投宿一个荒凉的佛寺,先后有各色人等来访,高谈阔论,或是抒发己怀,或是一副“文人相轻”之态,穷形尽相。天明时,众人忽然烟消云散,唯剩一群动物,各归其位而已。这是一篇调侃风味十足的传奇作品,然而于行文中,亦可窥见性别意识的折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各种动物精怪,都被赋予了男性的身份;尔后,这些精怪们所孜孜谈论的,并非动物界,乃是人间的种种不平事,他(它)们吟诗作赋,或调笑或绵里藏针地互相抨击,或是抒发羁旅之情,或是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都显露出封建等级社会的诸多框架造成的文化心理。天明,它们不得不恢复本相,然而从头至尾,不见对自然性的一点珍爱之心,充溢着的只是对社会文化结构所排挤的牢骚不平之气。借这些动物之口,抒发的只是“非自然”的意向。
四、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的比较
本文所采取的性别视角即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Gender)是一个与自然性别(Sex)对立的范畴,它指的不是生理上的男女性别,而是后天由社会文化所赋予所建构的性别意识形态。从社会性别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男/女出发,由此相应产生了更多的二元对立,如典型的自然/文化二元对立。[5]有关的社会性别意识理论大多认为,男性对应于文化,女性对应于自然,即男性是更为贴近“文明”的,而女性则更贴近于自然,具有更多的自然性。自然性的流露往往是被鄙视的,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非人”的东西即“自然”的东西总是低一等。只有修身齐家,让自己与他人都合乎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才是真正的“人”。但在唐传奇中,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作者,还是禁不住描写了自然对人性的召唤。可是作为男作者的他们为什么要将这个回归山林的主体性别身份设置为女性呢?这显然折射了一种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想象,试在这种性别视角的框架下对这两类故事进行比较:
1.故事形态的比较。
纵观以上所举的篇章,便可看出故事形态的不同倾向性。以女性为主角的传奇故事都体现出一种回归式的走向,即来自山林最终又归返山林。尽管她们也都曾希望融入人间的生活,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她们也具备这个能力,但最终她们还是把这种生活看成了束缚,义无反顾地撕去人衣披上兽皮,回到山林的逍遥生活中。以男性为主角的传奇则不同,明显缺乏这样一条“回归”的线索,他们如果出发点是人类身份,那经历的“变形”过程即可称为“异化”,由于某种缘故而异变成兽;如果出发点是兽类身份,往往便是站在一种边缘的位置来观看并艳羡社会结构中的上层人物生活,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去模仿和实现这种生活,而兽类身份则是为他们所不齿的出身。
2.“变形”原因的比较。
《孙恪传》等“变形”传奇的女主人公,原本就是来自山林,她们化身为人,只为寻求一种更理想的生活,不料红尘走一遭,却发现做人类社会中的贤妻良母才是对自己本性的“异化”,权衡之下,她们毅然抛弃人类生活,选择了回归朴野与本真。她们在人的外形之下,一颗向往自然的心从未泯灭。她们回归兽形的目的也是纯粹的,只为了享受兽类的生活而变化。而对比之下,男主人公们没有这种抉择。李徵本就是人类,因不得志而异变为虎,从此便陷入对自己“兽类”身份的痛恨中,而不是逍遥于无拘无束的山林生活。还有后来的聊斋中向杲的化虎,亦是借“虎”的身份来达到“人”的复仇目的。更不用说大白猿以及东阳群怪,都不是在人的外形下藏一颗“兽”心,相反,是在兽皮之下藏着一颗“人”心。他们之所以“变形”,正是为了追逐人类所独有的欲求。
3.“变形”情感的比较。
“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这首诗写尽了女主人公们的复杂感情。一面是自己的根,是自己融入其中无羁无绊的乐园;一面是红尘里的情爱与文化里种种制约人性的规范。她们有才有貌,唯一缺乏的就是“出身”,被认为低于夫君一等的“出身”。而“变形”的男主角们,大都认同着人世间的一切,为自己的“异变”而悲恨,为自己能“化身为人”而欣喜,以致于把自己当成超越自然的“人”去追逐文化所可能赋予给男性的最多利益。
还有女主人公们的夫君,虽然只是配角,他们的态度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言行正反映了男子对于女子自然性流露的鄙视,与“变形”男性的思想情感相一致。
总之,在男性的故事中,难以找到女性故事中所存在的那一份两难抉择与向往,而是明显的“人性”倾向与抑郁失意。这种人性恰恰不是老庄理想中的自然人性,而是经过文化规训制约的社会人性。
五、小结
人无论性别都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自然文化以及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更深切的联系,首先由于女性的身体特征以及女性所承担的生育任务,女性与创造万物的自然母亲联系在一起;[5]而且由于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同构于女性/男性的二元对立,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也联系在一起。基于深刻生态学的大地伦理出发,女性有着更强烈的拥抱自然的意识倾向,并对自然有着更亲切的感悟能力。但从唐传奇的文本看来,这样一些推论又可以被解释为女性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一直被“文化”所排挤,无法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找到自我的价值与位置,因而对于自然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唐传奇作为人类成长过程记述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这种社会性别意识。
[1] 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上、下)[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7.
[2]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册)[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 林骅,王淑艳.唐传奇新选[G].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5]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张 琴】
Viewingquot;Animal Transformationquot;andquot;Human Transformationquot; Tales in Legend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Gender
HUANGMin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Thequot;transformationquot;tales in Legend of Tang Dynasty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quot;Animal Transformationquot; andquot;Human Transformationquot;tales.These legendary tales often show different intensions and patterns due to different social genders.Therefore,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gender awareness,these tales expressed different value and feeling orientation between the nature and the culture.
Legend of Tang Dynasty;transformation;social gender
2010-05-15
[个人简历]黄 敏(1988-),女,福建莆田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0)04-0073-03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