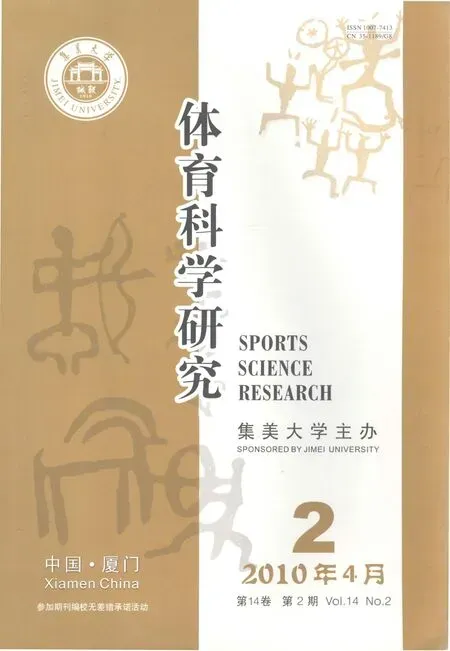乡村节庆体育的社会功能分析
2010-03-22郭传燕
郭传燕
乡村节庆体育的社会功能分析
郭传燕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柳州 545004)
以节庆体育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来探析其社会功能。研究表明:节庆体育是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功能主要包括社会个体、社会文化、社会结构 3个层次,是传统体育根植于乡土民间人民中间而源远流长的主要文化形式,其社会功能是综合的。
乡村;节庆体育;社会功能
节庆期间既有一定的风俗模式,也有不同的礼仪娱乐活动,同时也掺入了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节庆体育是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节日文化活动的形态上发展而来的,是传统体育根植于人民中间而源远流长的主要文化形态。乡村节庆体育活动集中体现了人类多方面的需要,也满足了人类多方面的需要。文化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赋予人类以一种生理器官以外的扩充,一种防御保卫的甲胄[1]。马克思说:“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有许多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乡村节庆体育可以起到调节社会生活,调整人际关系,规约社会行为等重要作用,因此乡村节庆体育活动的功能是综合的。本研究主要从对民众个体、社会文化、社会整合等方面来分析其社会功能。
1 节庆体育作用于民众个体的功能
节庆体育活动对于每个民众个体都具有充分的意义,尤其农民,他们迫于生活压力常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奔忙劳作,生活艰辛,需要有精神的调剂和升华,否则难以忍受生活的重负。按照中国传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节日娱乐和松弛可以冲淡消除农民长久的紧张和疲劳,使他们枯燥漫长的岁月增长许多诱人的生活情趣。
1.1 娱乐功能
体育娱乐一直都是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要表现。节日期间举行的蹴鞠、投壶、角抵 (包括角力、摔跤)舞蹈、以及秋千、舞龙、耍狮、踩高跷等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项目,凝结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活动将体育寓于娱乐之中,提高了欢快的氛围。如新年龙舞本身包含丰富的竞技性、艺术性、观赏性,有强烈的自娱自乐的功能。正如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所言“啊!体育,你就是乐趣,想起你内心充满欢喜……你可使忧伤的人散心解闷,你可使快乐的人更加甜蜜!”人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就会精神饱满,情绪愉快,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体型美、运动美,满足心理上各种欲望。
乡村调查表明,凡传统节日、庆祝集会、新谷登场、商店企业开张、婚寿葬祭都要进行庆祝,其中体育娱乐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一些大型集体性、仪式性体育活动如新年舞狮、庙会龙舞等,给乡民提供了互相接触、彼此交流、增进友谊的机会。对于大多数的乡土民众而言,一年四季在土地上忙碌,似乎没有空闲时间来享受生活,节日是他们唯一的闲暇娱乐时机。节日期间定期举行的民间文艺表演可以把广大农民从枯燥乏味的农活中暂时解放出来,使他 (她)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与满足。届时,村民们遍邀外地乡戚,备酒备饭,招待观看表演。演员表演如痴如醉,观众也随之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乡土民众在参与体育活动和欣赏体育活动中,在无拘无束得欢声笑语中回归自我,获得身心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当前节庆体育中那些简单易行、随意性较强的项目如跳绳、拔河、荡秋千、放风筝、踢毽子、武术等,将成为广大群众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多的乐趣与幸福。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娱乐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人们通过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各种活动,缓解了紧张的生活压力,调节了生活情趣,使身体健康的同时心灵也得到了愉悦。
1.2 健身功能
体育具有“强身健体”的功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农民的观念里,体育的健身的功能还能没有摆到突出的位置,大多数农民认为天天劳作,不用专门进行体育锻炼。所以在农民的健身意识没有多大改观前,着力于健身因素推广体育,可能效果并不理想。长期以来,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体育活动,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形式,迎合民众的心理,对发展农村体育具有潜在优势,对农民健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跳绳的协调,追跑的速度,踢踺子的灵敏,放风筝的野外调适,荡秋千的悠闲等活动都不自觉地提高了身体的各项素质,锻造出健康的身体。尤其大型的节日民俗体育项目舞狮、龙舞、扭秧歌等活动具有很复杂的武术套路、舞蹈动作,一般通过鼓乐将武术和舞蹈有机结合起来,在变化多端的节奏中完成各种造型和表演动作。这种活动集技能、体能、健身为一体,对表演者来说,不仅开发了身体的整体力量,还提高身体的技巧,是一种很好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修炼,对观赏者也不失为一种健康休闲、调节身心的方式。而且其表演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其中有助于培养集体团结、协调能力,使广大民众在娱乐运动中,体验到亲切感、归属感和成就感。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许多节庆体育将成为人民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内容,是他们庆祝丰收及其他各种喜庆活动不可多得的健身娱乐活动,也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多的欢乐和幸福。
1.3 情绪宣泄、调适功能
从发生学的角度,文化发展的迫力是民俗产生的根源之一。节日体育活动是民俗的重要形式,其本身即是文化迫力的结果。人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生存和繁衍,必须有维系群体生活所需要的种种制度,也需要实施这些制度的文化手段,还需要更多的文化条件,这就是文化迫力。这种文化迫力是必需和必要的,但是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生物性;换言之,人既具有社会文化的一面又具有生物本能的一面。因此文化迫力本身是对人本能的压迫与束缚,它使人的本能在文化的框架中受到压制,在制度、规范、礼仪、价值体系中被困厄。文化系统这种源于自身的压力和束缚必然会造成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冲突;此时,文化系统需要一个类似科塞提出的“安全阀”这样的东西来维持系统的良性运行,节日体育即承担着这种功能[3]。借助于节日体育活动,文化系统源于自身的压力和束缚就可以得以缓解。
首先,节庆体育具有调适社会成员生活的功能。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群体为了谋求生存,采取了与自身环境相适应的经济形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谋生方式,在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社会成员都必须付出繁重的脑力、体力劳动,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谋生方式都使社会成员的身心处于紧张状态。显然,长时期地处于紧张状态,对于社会群体成员的生理、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任何社会群体无法承受的。有间隔、有规律的传统节日能创造出一个轻松欢快的文化氛围,有利于社会群体成员身心得到很好地调整。在传统节日里,人们踊跃地参加各种习俗活动,大家都兴致勃勃,感到趣味无穷。竞技性的活动尤其能吸引人。诸如舞狮、耍龙灯、荡秋千、竞渡、赛马等活动不仅能使参加者情绪激昂,而且连旁观者的情绪也都调动起来。人们在节日里,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载歌载舞,大口饮酒,大口吃肉,也是使社群成员心情欢愉的一个原因。总之,传统节日中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节奏明快奔放的歌舞,充足的佳肴美酒,都能使社会成员身心处于放松状态。平时为了谋生而忙碌的社群成员在节日期间的疲劳困倦的身体得到恢复,紧张压抑的精神得到解脱,人们的心理状态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节日的狂欢,可以起到宣泄心理能量的作用。在农村平时除了喝茶聊天,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的单调,长期的劳作,使他们积压的消极情绪较少有排解之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节日体育活动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和娱乐机会,让人们在终年劳碌、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有了适度的放纵自由。在节日期间他们不用农耕,不为柴米油盐事而费心,只管享受生活的轻松与快乐。在这些日子里,儿童尽情的玩耍游戏;青年人通过郊游寻觅情投意合的伴侣,中年人通过各种竞技或民俗表演活动展示自己的技能,老人们则唱说古今;女性们也一反常日的习惯规约,百无禁忌地展示她们的舞姿,整个身心都融入节日活动的热闹氛围中。同时在节日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禁忌全部被打破了,人们可以抛开种种文化束缚,使生物性本能获得必要的张扬,缓解了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此外节日期间村民通过参与或观看具体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内心种种不良情绪,缓解日常生活的压力。正如麦可卢汉所言:“游戏是我们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给各种具体的紧张情绪提供了发泄的机会。”[4]
1.4 归属功能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一直处在一个生存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个体必须依附于某一集团,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归属意识是十分强烈的。赫尔德认为:“归属于群体是人的一种本质的需要。”节庆体育活动,尤其那些经过多年沿袭下来的仪式性节日民俗体育活动,通过周期性展演能不断培养他们的归属感。诸如舞龙、舞狮、踩高跷、荡秋千、划龙船、登高、灯会等节日习俗活动,多是以村庄或部族为单位参加。参赛者除了有强烈的竞争心外,还都有着集体荣誉感,在竞赛中,集体的配合和协作状态如何,往往是集体项目竞赛成败的关键。旁观者也都难以成为作壁上观的局外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社群成员的角色,为本社群的竞赛或竞技活动加油,欢呼或沮丧。研究表明,群体成员相互影响和成员之间的感情对于群体团结起重要作用。传统节日活动中人际交往密切以及社群荣誉感的增强,无疑强化了社会集体意识。节日习俗的趣味性以及节日竞赛活动的配合协作,又提高了群体的内聚性。这就在社会群体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节日期间,群体成员彼此的吸引力增大,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也在增加。平常日子,群体成员接触交往减少,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减弱,群体对成员们的吸引力也跟着减弱。新的节日到来,群体成员彼此交往增多,吸引力相应增加,群体对成员们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加,群体内聚力增强。
在郯城,每到节日或大型庆典,都要举行一些民俗娱乐活动。有的仪式性活动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参加的人员众多。这些活动从娱乐到仪式性体育给民众生活提供了精神归依,成为农村社区演员寻求心理平衡,参与社区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维系社区广大民众共同文化心理的一种粘合剂。通过这种周期性的活动,使社区居民在情感上实现着社群、族群的认同,将本社区、家族中的不同个体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在表演中提高了社区居民的自信心、自尊心、凝聚力和亲和力。
1.5 教育功能
节庆体育活动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曾表述民俗对个体社会化过程的作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民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俗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是他不可能性。”[5]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多数村落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读书,孩子多数任由自己玩耍,所得的知识,不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是自己所生活的周围社会。
首先,节庆体育活动一般是在特定的仪式活动中进行的,通过周期性的仪式表演,如祭祀活动、戒度仪式、成年礼仪等形式不仅保存了体育文化,而且加深下一代对自己的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孩子们通过参加、观看,在无形之中陶冶了情操,帮助他们识别真善美与假丑恶,培养了他们健康、正直的伦理道德,同时了解到许多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
其次,就体育项目看,有些运动技能本身也是生产、生活的技能,如武术、赛马、射箭、射弯、摔跤等,通过表演和竞赛能培养人们的机智、果断、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具有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调节情感的作用。总之许多节庆体育荟萃了民间舞蹈、艺术、风俗、工艺等多方面的精华于其中,人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无形中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
2 节庆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
民众通过民俗活动尤其是节日来认识和了解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节日又不同于书本的说教,它采取了鲜活的民俗形式,借助于大家热爱的民俗活动使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为民众所认定,并促使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维护这些价值观念。例如,在许多传统节日中,祭拜祖先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通过一些庄重严肃的仪式,家庭、家族乃至宗族牢固地凝聚在一起。这里,节日强烈地认定和维护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以及在血缘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节庆体育作为民俗文化现象,不仅保存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在周期性的表演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具有文化的传承和建构等功能。
2.1 文化传承功能
节日体育是社会文化历时性传承的载体和工具,在节日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仪式性、周期性、公共性的民俗节庆体育活动,作为民族文化汇集的“文化集约丛”,[6]它吸附了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传统特色项目,使民族风俗文化习惯在公共性场域中周期性的得到强化与张扬。并能区分异己的文化传统与被历史挑选出来作为社群的标志或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如果成为一种周期性展演的节庆仪式或成为节庆仪式展演的一部分,通过节日活动的展演无疑将不断强化人们的集体记忆,强化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表征,而节庆体育中竞争因素的存在也刺激着传统文化在社群内的传承与发展。在今天的节日中,我们会看到许多自古传承下来的民俗和体育项目,如元宵舞龙灯、猜谜语,端午赛龙舟、挂艾枝,清明踏青、放风筝,重阳登高、插茱萸,春节放爆竹、贴门神、舞狮拜年等,这些活动通过周期性的展演,让年轻一代在心理上、文化上、精神上达到认同、接受传统文化,从而客观上达到传递文化的作用。
伴随着科学进步,文明演进,这些古俗和体育项目本应随着其存在的原初情境逐渐丧失而退出人们生活舞台。但节日通过特定的形式使这些古俗得以保存,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娱乐活动和增加节日欢乐氛围的手段。这样古时的习俗以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代代相传。另外,许多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社会规范亦是依赖节日而得以传承。当前在农村,许多体育项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体育项目活动,它们经过历代的变革尤其是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依然生命力旺盛。如前面所述,春节的舞狮表演在媒体、娱乐文化及其普及的现代社会依然受到村民的喜爱和欣赏,在节日期间给村民沉闷的生活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并对于贫乏的农村体育,可以起到促进和补充的作用,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
2.2 文化建构功能
节庆体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构建功能。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各种风俗活动,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的骨架。节庆体育一方面在民俗背景下进行,另一方面也通过其活动延续和构架农村社区的民俗文化。如农村庙会“迎神、送驾”常以村为单位,有时数村联合,在迎神活动中,乡民组织迎神队伍——“狮子”、“龙舞”“高跷”、“耍大头娃娃”等以配合迎神活动。作为乡村举行的迎神赛社活动,迎神自然是严肃的制约与礼仪,赛社通常是集体行为的竞赛乐趣,而后是吃喝玩乐的献技献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民俗生活通过“迎赛”活动表现出来,并能够构建人们生活的精神取向,形成其文化传统。
节庆体育活动的形式,也具有某些程度的文化构建意义。每个传统节日以约定俗成的节日活动,一年一度的频率,周而复始地强化着村民的集体记忆和社区情感认同。如春节的舞狮拜年活动、清明的祭祖踏青、端午的龙舟竞渡、重阳的登高等,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传统礼俗的建构和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年轻一代体育活动的身体记忆,远比言语的谆谆说教更有效。
3 节庆体育的社会结构功能
3.1 促进社会整合
社区整合的发生包括物质、人力资源和意识三个层面,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其中的关键。从增强社区意识的角度来看,社区整合就是增强社区的团结[7]。格尔茨认为文化对社会的整和是“符合逻辑的、有意义的整和”,具有风格的统一、逻辑蕴含的统一、意义的统一。而社会系统的整合是如同生物有机体的“因果 -功能型的整合”,两种整合既独立变化又彼此依赖。研究表明:那些对历史记忆清晰的村庄往往内聚力也强,村庄公共舆论发达,而那些对历史淡忘的村落社区内聚力不强,村中各色人等自行其事,缺乏公共的行为评价标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功能较强、结构严密的节庆活动,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传统节日的情结早已深深地嵌入中国人的骨髓里,在整合社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能[8]。传统节日可以创造社区居民互动的机会,调节和强化人际关系,并进一步整合社群,强化民众的集体意识。我国的传统节日,虽然通常是由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进行的,但在家人共同欢庆节日的同时又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群体的存在。比如新春之际,人们在合家团圆欢乐之后,便要举家外出,去观看和参加春节期间的各种喜庆活动和游乐,如舞狮,耍龙,踩高跷,划旱船,逛庙会等。清明时节,人们纷纷趋向墓地,祭扫祖墓,也是社群活动行为。另外像重阳节的登高,赏菊,喝菊花酒,采茱萸,也都是很热闹的群体活动。而且这些热闹的群体活动,往往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在人们聚居的地区进行,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时间流向同一地点,汇聚在一起,这种拥挤的场合,使得人与人的交际变得极其频繁。人口密度的相对加大,无疑使人们的社群意识得到加强。人们的言行、礼仪、接人待物的态度都不得不以社群的存在为前提。共同的娱乐和面对面的交流,相互间的问候和馈赠,可以化解人际间的冲突,融洽人际间的情感。
3.2 加强人际交往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社会个体在满足了物质需要之后,就有了安全和交往的需要。所以说,任何一个个体都希望且必将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节庆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群众性的社会活动,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民俗、道德的规范约束下,拓宽人际交往的渠道,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体育运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它可以消除各地、各族人民因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不同带来的隔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感情交流和文化交往的社会媒介环境。节日期间人们通过快乐的文体活动交流彼此间的技艺、文化、思想感情等,有助于改善民众之间关系,增进了村与村之间的联络和互动,促进地方经济与文化交流。
3.3 规约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节庆体育对民众具有规约行为、维护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节庆体育活动的习俗养成方面,习俗是内在心理结构与人情世故的体现,但这种习俗是需要通过多种活动来传承并侵入人们的心灵的。农村社区都有自己的习俗,这种习俗,对广大民众有很强的约束力和规约性。节庆体育活动在形成过程中就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规约,对调节社群矛盾和纠纷,维护社区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归昌陈氏家族自古就有练武强身卫族的传统,整个宗族,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要学会几招把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70年代末。每当秋收结束秋高气爽、明月当空的夜晚,族人们便会在武术教头的带领下,分批分地点地学习武术。在习武的基础上,宗族挑选出一批身强力壮、武功较高的青壮年男丁,组织起自己的舞狮队和保卫队。保卫队的主要活动一是在宗族各村落范围内巡视,防止盗贼、土匪、流寇或聚众闹事、打架斗欧等;一是在与别的宗族发生冲突时,作为主要力量抗击外族。这些都客观上起到保护自身宗族利益、维护宗族所在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节庆体育活动的建设性功能也体现在习俗的养成方面,村落宗族还通过组织自己的保卫队,保护宗族的利益与安全,也达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
[1]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 [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3.
[2]刘守华.文化学通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15-216.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3.
[4]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4.
[5]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5:87.
[6]李强.符号、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EB/OL].(2008-12-03)[2009-03-04].www.china-review.com.
[7]李志清.乡土社会仪式性体育的存在与意义 (二)——仪式中的抢花炮[J].体育科研,2006,27(5):35-36.
[8]许晓辉.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的变迁[J].社会科学, 2001(12):48-52.
[责任编辑 孙永泰]
Study on Social Function of Rural Sports Festival
GUO Chuan-y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Liuzhou Teachers College,Liuzhou 545004,China)
Taking the festival sports as subjects,the author discusseson social function of rural festival sports by field investiga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estival spor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and the main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rooted in people has a long history,and its social function is integrated.
rural;festival sports;social function
G 80-05
A
1007-7413(2010)02-0020-05
2009-04-2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DTY004)
郭传燕(1973—),女,山东临沂人,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