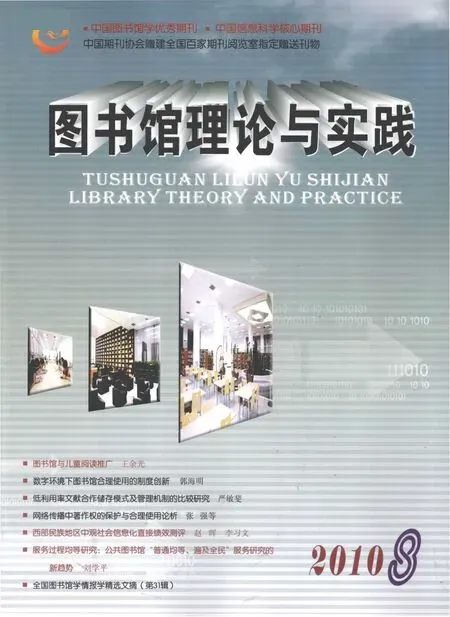论孙星衍的校勘学思想、方法及成就
2010-03-22焦桂美
●焦桂美
(1.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2.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一字渊如,号季逑、薇隐、芳茂山人,江苏阳湖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孙氏治学以博通见长,于经史、小学、校勘、辑佚、金石、方志、骈文诸领域均卓有建树。
孙星衍早年随父读书时即喜校勘,①孙星衍于《孙氏祠堂书目序》中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因按日读学舍官书《十三经注疏》及诸史,朱墨点勘凡数过,几废科举之业。”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1780年—1787年) 在陕西毕沅幕府才华崭露,“毕公撰《关中胜迹志》、《山海经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属君手定”。[1]此后乐此不疲,终生不辍。所校之书主要有:《夏小正传》二卷、《急就篇考异》一卷、《六韬》六卷、《燕丹子》三卷、《牟子》一卷、《黄帝五书》五种六卷、《琴操》二卷、《华氏中藏经》三卷、《千金宝要》六卷、《渚宫旧事》五卷、《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春秋释例》十五卷(与庄述祖合校)、《孙子十家注》(与吴人骥合校)、《三辅黄图》(与庄逵吉合校)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星衍往往将校勘贯穿于辑佚活动中。因此,他的校勘成果远远不止表现在所校诸书中。在所辑《古文尚书马郑注》《仓颉篇》《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古文苑》《尸子》《汉官七种》(《汉礼器制度》《汉官》《汉官解诂》《汉旧仪》《汉官仪》《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物理论》《神农本草经》《孔子集语》《续古文苑》等书中,同样大量体现了孙星衍的校勘成果。以上成果主要集中在他所刊刻的《岱南阁丛书》与《平津馆丛书》中。两部丛书自问世以来一直以精校精注精刻著称,丁丙故有“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皆雠校精审”之叹。[2]但与同时许多校勘名家一样,孙星衍没有留下自己的校勘学理论专著。其校勘学思想、方法、成就散见于校刻诸书序跋及其校勘实践中。此拟对以上问题略作论述。
1 孙星衍的校勘学思想
孙星衍生活在考据学兴盛的乾嘉时期。该时期崇尚实学,反对空疏,研精三代两汉之书,轻视宋以后著作成为一时风气。古书传习既少,传抄踵刻,讹谬愈甚,至不可读。乾嘉诸儒乃广征善本,予以雠校,校勘遂成专门之学。一时之间,名家辈出。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声名最著。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自序》云“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3]当时风气,盖可想见。因此,孙星衍崇尚校勘,积极从事校勘活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学术风尚之所趋。综括孙星衍的校勘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存古书,广流传。鉴于唐前之书,流传稀少而史料丰富,足以信古存真,孙星衍故视若珍宝,校勘以传。其校《李子法经》《文子》《三辅黄图》等皆因重其时代早、流传少。有些唐前古书虽未亡佚,然藏于秘阁,外间难以得见,不便传习、流布。如明梅鷟《尚书考异》是较早系统考辨《尚书》孔传之伪的一部重要著作,孙星衍因其藏于秘阁、传写不易而与顾广圻、钮树玉悉心雠校,“今为流布以广其传且以宣国家表章经学之旨”。[4]
有些古书虽收入《四库全书》,外间仍不得获见,孙星衍因为校刊以传。如《渚宫旧事》于乾隆五十年由纪昀等奉敕校定并为补遗一卷,录入《四库全书》,但外间不得尽睹其本。该书后经孙星衍校注、补遗、刊行,始广为流播。《春秋释例》明以来即藏于秘府,后虽收入《四库全书》,外间仍然难以得见,孙星衍因与庄述祖校雠刊刻,以广流布。
由此可见,保存古书、流布文献是孙星衍从事校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2)证经史,伸汉学。乾嘉考据学以经学为核心,进而以治经之法治史,扩大到金石、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古籍注释诸多领域。证经考史既为考据学之核心,亦为校勘古书的主要目的。乾嘉考据学者校勘古书,范围虽广,然审其校勘对象、校勘方法、校勘目的终不离证经考史、伸张汉学。孙星衍在这方面亦颇具代表性。其于《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校勘该书的目的——鉴于唐前地理著作皆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独存。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诚一代之巨制,古今地里书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5]于《校补渚宫旧事序》中亦云:“书记楚中故事人物,取郢都南渚宫以为名,事起周代,止于晋代……惟此是唐人撰述,引据多后人未见之书,可以证经考史,不独为一方掌故”。[6]1作为乾嘉时期的重要汉学家,孙星衍的学术主张极为鲜明,他在诸书序跋及文集中不仅再三申述对唐前古书的重视,而且毫不讳言对宋后著述的轻视,如于《孙氏祠堂书目序》中言及宋元以来说经之作,认为“至宋明近代说经之书各参臆见,词有枝叶,不合训诂,或有疑经非议周汉先儒,疑误后学,宜别存之,以供取舍”。[7]由此可见,通过校勘古书证经考史、伸张汉学是孙氏学术思想在校勘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3)经世用,惠来学。乾嘉学者尚实学,重经史,经世致用是其治学的终极目标。孙星衍通经、明史,精于刑律、地理,欲以经术饰吏治,其校刊古籍因此具有明确的、强烈的治世目的。孙氏校刻《孙子十家注》即出于当时国家以武经命题试士,而该书世间善本绝少,故校刊之以为国家服务的目的。这一思想在《序》中言之甚明:“国家令甲以孙子校士,所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遂刊一编,以课武士”。[8]
孙星衍校勘古书不仅着眼一时之用,而且希望嘉惠来学,泽被后人。其于《校补渚宫旧事序》中明确指出:“唐人著作存世日少,近人刊《长短经》、《建康实录》等皆有用之书,尚有《开元礼》、《开元占经》、《太白阴经》,所望好事者刊布以惠来学,并为校补此书未备之处。”[6]1孙氏于此进一步伸张了其经世用、嘉惠来学的校勘学思想。
综上所述,孙星衍勤于校勘,终生不辍,究其原因,不外存古书、伸汉学、经世用三端。
2 孙星衍的校勘方法
校勘的主要目的是改正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出现的字句或篇章上的错误,使其恢复或接近古书原貌。在校勘过程中,除学者自身需要具备深厚的学养外,科学、合理的校勘方法对提高校勘质量非常重要。综括孙氏所用校勘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广搜众本,全备为上。一书往往有几个版本,有的片段还保存于类书及他书中,异本及相关资料搜集得越全,越便于比勘异同,判断是非。因此,孙星衍每校一书之前,总是极力搜集众本,力求全备。如《孙子十家注》传世版本稀少,其早年在陕西毕沅幕府,于华阴岳庙《道藏》中读到此书,后有宋郑友贤《遗说》一卷。又在大兴朱氏处见到明人刻本。除此之外,其他版本世间不传。孙氏即用此二本校勘宋吉天保辑本。诸如此类流传较少的古籍,孙氏往往穷搜尽索,希望在尽可能得到所有传世版本的基础上予以校勘,以便得出更客观、更可靠的结论。对流传较多的版本,孙星衍同样广搜众本,予以雠校。如乾嘉时《抱朴子》唯明卢舜治本行世,讹谬甚多。孙星衍广泛搜集,得《道藏》本、自藏天一阁抄本、卢文弨手校本及顾广圻所藏叶林宗抄本、明嘉靖沈藩本进行合校。经其校勘,使得该书成为当时最精善的本子。
(2)精选底本,择善而从。在使用多个版本校勘时,选择底本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只有精选底本,才能事半功倍。因此,孙星衍在选择底本时极为用心,力求以善本为底本。孙星衍在《续古文苑》凡例中有“其诸书皆据善本,如《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唐大诏令》、《开元占经》、《太平御览》等悉系旧抄,《北堂书钞》为陈禹谟未改以前所写,均于俗本大有订正”。[9]由此可见他对善本的重视。孙星衍在校勘《抱朴子》《孙子十家注》时即选用了世人少见、讹谬较少的《道藏》本为底本。同时,孙星衍又坚持唯善不唯古的原则,选择一些遗漏较少、体例较完备的通行本作为底本,如《急就章考异》就是以当时通行的宋绍圣三年帖本为底本。
在求是、择善思想的指导下,孙星衍对任何版本都能一分为二,取是舍非。如他既指出了今本《三辅黄图》存在的错误,如“掖庭宫,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一句,孙氏注云“掖庭宫”后“在天子左右如肘腋”八字今本作注文非。同时,他也看到了《三辅黄图》古本不如今本的地方,如“有玉堂、增盤阁、宣室阁”条,孙氏指出宋王应麟《玉海》本不如今本。即使对讹误甚多的明卢舜治本《抱朴子》,孙星衍也不废其优胜之处,文中时有“今从卢本”字样。可见,精选底本、择众本之长校成善本乃至定本,是孙星衍校勘的最终目的。
(3)运用多种校法,主张校改原文。综观孙氏所校诸书,其校勘方法极为灵活。他总是根据书的版本流传及所占有的资料来选择校法。一书有数个版本单行,各本文字不尽相同,他便以对校为主。如《急就章考异》,当时行世的有唐颜师古注本、北宋黄庭坚刻本、北宋绍圣三年帖本、南宋王应麟《玉海》本、清梁国治临本等,孙星衍便以当时通行的绍圣三年帖本为底本校各本文字之异同,并辨别是非得失。《夏小正传》除有单行本外,还存于诸类书及《月令》郑注、《文选》李善注等书中,这就决定了该书在进行对校的同时,还要进行他校。而对有些书来说,因前后文字多有互见,利用上下文进行本校也是一种极为有用的方法。如《抱朴子内篇·金丹》“其闻仙道大而笑之”。“大而笑之”原作“而大笑之”,孙星衍因后面的《微旨》作“大而笑之”而据改。
除利用对校、他校、本校来正文字、定音义、订句读外,孙星衍广泛使用理校法判断是非,校改错谬。具体表现为:
(1)利用小学知识进行理校。如:①从字形上校谬。如《孙子十家注》卷五“兵之所加如以碬”,孙氏指出“碬”当为“碫”,形近而讹。②从训诂上溯源。《抱朴子内篇》卷七“芝檽之产于木石”,孙氏认为:“檽当作檽,即《礼记》芝栭也。《广韵》檽,木耳别名。可证檽即栭字矣。”③ 据音韵校改。如《抱朴子内篇》卷七“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孙氏认为“利禄”当作“禄仕”,才能与上文“子”、下文“耳”“已”“喜”“耻”押韵。
(2)根据文例进行理校。如《孙子十家注》卷八“必生可虏也”,曹操注“见利畏怯,不进也”,孟氏注“见利不进,将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亲战,士卒不精,上下犹豫,可急击而取之。”原本孟氏注中无“见利不进”四字,孙星衍因孟注总是先引曹注后增释之,故据《太平御览》补入。
(3)运用天文、地理、史实、典制等方面的知识进行理校。如《抱朴子》卷十七“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孙按:‘戌’当作‘丑’),五月未(孙按:‘未’当‘作‘戌’),六月卯,七月甲(孙按:‘甲’字当衍) 子,八月申子(孙按:‘申子’当作‘巳’)九月寅,十月辰未(孙按:‘辰’字当衍),十一月己丑(孙按:‘己丑’当作‘辰’),十二月寅 (孙按:‘寅’当作‘酉’)。”这段文字,各本因不懂历法皆讹错不通,孙星衍凭借自己的天文知识一一为之订正。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做到言必有征、信实有据,孙星衍往往同时使用几种校法。如《抱朴子内篇》卷二“夫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鍼”,孙校“狄”字云:“《藏》本作‘秋’,非也,依《意林》引改。‘狄’‘翟’同字,又见后《辨问篇》。”这里,孙星衍就用了他校与本校两种方法。
关于校勘改不改原文,历来就有争议。如同为校勘名家,钱大昕主张以“定立说之是非”为依据校改原文;顾广圻则奉行“以不校校之”的原则,力求维持古书原貌。孙星衍在自己的校勘实践中,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宋元旧本,主张影写存旧;对其他版本,从便于实用的角度出发,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主张校改原文。这种校改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1)据他书改底本之误。如《孙子十家注》卷七“动如雷霆”,原本作“雷震”,孙氏据《鶡冠子》《通典》《御览》改为“雷霆”。
(2)据底本订他书之失,如《孙子十家注》卷一“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曹操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言以九地形势不同以时制利也。”孙星衍认为“制利”一词,《通典》《御览》作“制度”,非。
应该说明的是,校勘改不改原文只是处理校勘结果的方式不同,方式本身不能强分优劣。校勘水平的高下也不体现在处理方式上,而是取决于校勘者的学识及对待校勘结果的态度。孙星衍主张校勘原文,但最反对妄删臆改、率而为之的做法。他校勘古书,态度极为审慎。他所校改的文字,往往证据极为确凿。对证据不足者,只存异文而不妄下断语;对不能判断是非者,提出疑问,以俟后学。这就形成了孙星衍谨严的校勘体例。他主张随文出校,备列各本文字异同,如有校改,说明校改的理由和依据;他反对校勘不注出处的做法,曾因《四库》本《渚宫旧事》未注出处而遍拣群书为之补注。他的校语极为简练,反对因繁琐考据而割裂原文。尽管由于学识所限,任何人改讹补阙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孙星衍这种择善而从的做法无疑更有利于实用,他所提供的处理校勘结果的方法直到今天也仍有其借鉴意义。
3 孙星衍的校勘学成就
作为乾嘉著名校勘学家,孙氏所校诸书影响当时,享誉后世。早在陕西毕沅幕府期间,孙星衍便开始校勘《晏子春秋》,成为清代较早关注、校勘《晏子春秋》的学者。他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作《晏子春秋序》中说:“儒书莫先于《晏子》,今《荀子》有杨倞注,《孟子》有赵歧注,唯《晏子》古无注本”。[10]有鉴于此,孙星衍便用当时较为完善的明沈启南本为底本首先对是书进行了校勘,并撰成《音义》二卷。后来卢文弨将他的校勘成果吸收到《群书拾补》中并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了校补。嘉庆十九年(1814年),孙星衍把自己新得的影元抄本(孙星衍、顾广圻、王念孙皆称影抄元刻,潘景郑先生则以为当系明本[11])赠给吴鼒作六十寿礼,吴鼒嘱顾广圻校刻于扬州。是本远比孙星衍所用沈启南本精善,虽然孙氏也曾用其校改自己校刻的《晏子春秋》,但追改已非易事。吴本出,顾广圻以赠王念孙,王念孙极为高兴,不顾自己八十岁高龄,复合诸本,进一步订正了孙、卢二人的错误,使《晏子春秋》的校勘更为精善,其成果收入《读书杂志》。自此,对《晏子春秋》的校勘研究工作进入了繁盛阶段。孙星衍又曾校注《墨子》《管子》《文子》《孙子》等,因此,他在先秦子书的校注、整理方面功劳极大。子书之外,孙星衍还校勘了大量的本草、医方、星经、地记、字书等(如前所列),在当时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氏所校诸书不仅为时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成果,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他通过理校得出的结论多为后得古本所验证,如《抱朴子内篇》卷二“有似丧者之逐游女”,孙校云“丧”当作“桑”,事见《列子·说符》《说苑·权谋》。今核之敦煌本正作“桑”,亦正引《列子·说符》为证。诸如此类在《抱朴子》一书中不可胜数。他提出的一些说法经过后人的深入研究也被确认为真知灼见,如今本《晏子春秋·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能聚者晏子谏第五》中有“令柏巡泥”,孙云“柏”即“柏据”。俞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柏”亦官名,与“伯”通,并引《管子·轻重篇》《文选·籍田赋注》《说文》等书为证。后来苏舆进一步研究孙、俞二家之说,判孙说为是。有些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及个人学识的限制,孙氏一时不能解决,但他通过校语提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后人沿着他提供的线索,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如《抱朴子内篇》卷九“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罥以捕麞”,孙氏指出“此下有脱文”,但苦于无善本校补。后劳格据《太平广记》引《抱朴子》下有“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窥取麞”十六字,即将其补入自己所撰《读书杂识》,孙人和作《抱朴子校补》时吸收了劳格的成果,使此句终得完善。
孙星衍校勘古籍付出了大量心血,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所校《元和郡县图志》《急就章考异》《三辅黄图》《周书六韬》《燕丹子》《华氏中藏经》《千金宝要》《神农本草经》《渚宫旧事》《抱朴子》等都被张之洞《书目答问》著录为善本。因其雠校精审,其成果多为时人及后人借鉴、吸收。如王念孙的《读管子杂志》中吸收孙说25条,今本《孙子校释》《晏子春秋集释》《抱朴子内篇校释》等更是多处采用孙氏成果而后来居上。经他校过的本子有的被一再重刻,有的直到今天仍被作为底本或主校本。如《抱朴子》有光绪间朱记荣重刻本,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和1991年出版的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都是以孙氏平津馆刊本为底本、参校其他版本而形成的校注本。《孙子十家注》《晏子春秋》《燕丹子》等还被收入多种子书汇编。1991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子校释·前言》中说“清代以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最可称道,在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2]《燕丹子》能够流传至今更是平津馆校刊本的功劳。虽然孙星衍不很注意从理论上总结校勘经验,所校之处也偶有失误,但作为一代校勘大家,孙星衍为校勘学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1] (清) 钱仪吉.碑传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8:443.
[2] (清)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M]//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88.
[3] (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续修四库全书第4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8.
[4] (明) 梅鷟.尚书考异 [M]//丛书集成初编 第36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
[5] (唐)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丛书集成初编第308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6] (唐) 余知古撰;(清) 孙星衍校并辑补遗.渚宫旧事附补遗[M]//丛书集成初编第317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7] (清)孙星衍撰;焦桂美,沙莎标点.孙氏祠堂书目[K]//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6.
[8] (宋) 吉天保辑;(清) 孙星衍,吴人骥校.孙子十家注[M]//丛书集成初编第93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
[9] (清) 孙星衍.续古文苑[M]//丛书集成初编第169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4.
[10] (周)晏婴撰;(清) 孙星衍校并撰音义.晏子春秋附音义[M]//丛书集成初编第51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
[11]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M]//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6-78.
[12] 吴九龙.孙子校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