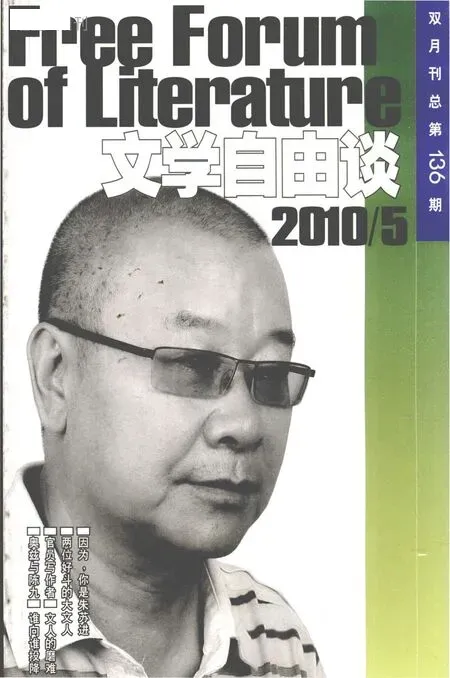劲直而明朗的批评
2010-03-21廖四平
●文 廖四平
面对复杂的文学现状,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和问题: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是否依然有效?传统的文学经验是否能成为当代文学生长的沃土?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坏优劣究竟应该以什么为标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如何改变文学评论的空泛虚浮之风?最近,我读了学者李建军的《文学因何而伟大》(华夏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一书,作者所提供的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和观点,对我认识那些长期困惑我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帮助。
《文学因何而伟大》收录了三十三篇论文,全书虽系单篇文章的合集,但是,在结构上却体现出一种逻辑上的递进感和完整性——全书大致可以分为“关于大师和经典的总论”、“文学与伦理学”、“俄罗斯文学论”、“现代主义文学论”、“中国文学论”、“文学批评论”等单元,而每个单元的论述“指向”大致相同或相似,那就是阐释“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文学的缘故》、《真正的大师》、《经典的律则》、《文学的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文学因何而伟大》、《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等文,主要阐释文学的意义和伟大之处以及文学经典、文学大师的特点等;《祝福感与小说的伦理境界》、《文学与政治的宽门》、《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识》、《文学主于正气说》、《托尔斯泰难题》等文主要阐释伟大作品与伦理学的相通的品质和共享的原则;《站在凯撒的对立面——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精神传统》、《俄罗斯经验: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契诃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全面理解契诃夫》、《高尔基为什么贬低果戈理》等文,则主要结合具体的作品论述俄罗斯文学大师和作品的“伟大”;《傲慢与黑暗的写作——评<尤利西斯>》、《为什么是库切》等文涉及现代主义作家,认为现代主义作家的过于强调写作技巧以及一味追求表达的标新立异等“偏好”,导致其作品不仅缺乏积极向上的道德指向,而且连表达的清晰性和阅读上的可理解性都成了问题,给读者带来的只是沉闷的阅读体验;《<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庸碌鄙俗的下山路——<色戒>及张爱玲批判》、《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自传与怀念的道理》等文主要论述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论及的作品既有古代的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又有鲁迅的小说、《色戒》、《百合花》等大量现当代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文学经验的重视和珍惜,对当代文坛上的消费主义、低俗化叙事等倾向盛行的关注和忧虑;《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伦理责任》、《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猪舌检查者与批评豁免权》、《小街上的面包店》、《水犹如此,人该如何?》则主要涉及文学批评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精神,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公正无私”,应该具有基于“事实感”的求真的精神,而不能一味地“与人为善”,丧失直面问题和说真话的勇气。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一切向钱看”在所难免,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不少人的共同追求,文学艺术也难以免“俗”——往往为了最大的读者群或观众群而不惜牺牲其应有的教化功能,文艺批评或研究也往往漠视文学艺术应有的教化功能。《文学因何而伟大》则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学应有的道德教化功能与伦理净化作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通过正确的道德伦理观念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应该像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那样始终保持着对苦难的超越、对理想的坚守,弘扬着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人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李建军也反复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教化功能和重要意义,并援引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因为,正是批评撼动了山岳,毫无思想的权力的山岳,死气沉沉的传统的山岳”来支持自己的这一观点。
一般来说,唯美主义和功利主义常常被看作是非此即彼、尖锐对立的两种观念或创作倾向,但《文学因何而伟大》却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关系:“文学因为‘美’而令人愉悦,从而显示出它的美学品质,但是它若想同时显得伟大,就不能放弃那些重要的‘功利主义’目标,具体地说,不能放弃它一个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因为,只有坚持执着地追求‘善’文学才能使自己在更高意义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永恒的价值。”(第32页)这种观点对于那种打着唯美主义的旗号而一味地标新立异,极端地追求所谓的形式美,放弃文学艺术应有的责任或功能,或者打着功利主义的旗号而忽略或放弃对形式美的追求,无疑是一种反拨,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也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倾向非常明显,即为了显示“博大精深”、“高深莫测”,批评家或学者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通俗的问题深奥化,因而其论著也往往晦涩难读难懂。而《文学因何而伟大》则一反此态——本来是很复杂的问题,却说得很简明;本来是很深奥的问题,却说得很通俗易懂,整个文本十分“平易近人”;在具体行文时,文章一般是先提出论点,然后引经据典或“实例”予以论述,而且所印证的材料繁多而又不累赘,如《经典的律则》一文,直接引用的中外学者的观点竟多达二十八处,引用的《静夜思》以及莎士比亚、坦尼森、松尾芭蕉等人的小诗等“实例”竟多达十几个;《猪舌检查者与批评豁免权》在论及文坛上拜权主义盛行和为尊者、权者讳等倾向时,援引历史上陈涉和现实生活中权贵作家的相关事例作为论据。此外,此书还注重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阐释问题——这在深化论述的同时,也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总之,《文学因何而伟大》观点纯正而不迂执,理论色彩强而又充满诗意,文字雅洁而又通俗易懂,从而,达到了“思辨性”和“诗性”的统一,形成了一种劲直而明朗的行文风格,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