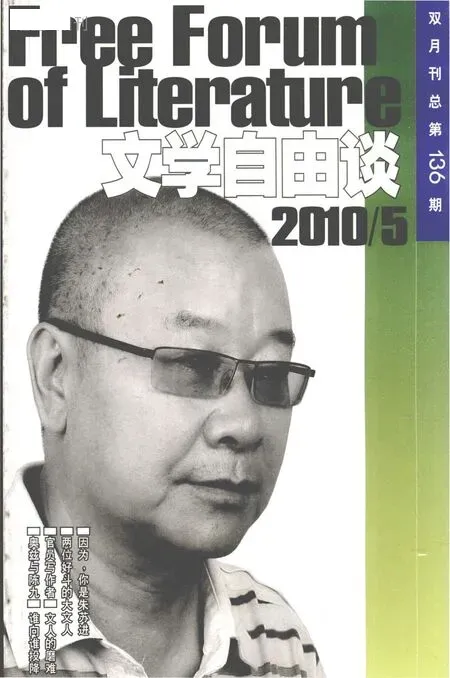杂文繁荣乃社会之福
2010-03-21罗青山
●文 罗青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论及杂文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杂文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社会黑暗的时代。因此希望杂文消亡,尽快告别杂文时代。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
据我观察,这种说法有两个“理论根据”。其一是基于杂文的批判性。认为杂文是匕首、投枪,是专门针砭时弊的。按鲁迅的说法,它是“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此,没有时弊,没有社会的阴暗面,就没有杂文的生存空间。而时弊越多,社会的阴暗面越大,杂文写作的素材就越丰富,杂文的繁荣发达也就可期。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成立,但深究起来却经不起推敲。首先,任何社会都有阴暗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所谓的“君子国”,所谓人人皆以奉献为乐事的“大同世界”,只存在于文人墨客的想象中,存在于乌托邦虚构的幻象中。其次,杂文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社会阴暗面的存在,而是杂文作者对社会阴暗面主动进击的结果。杂文作者不主动进击,即使阴暗面再大,也会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也不会产生杂文,更不会有杂文的繁荣。
上述说法的第二个“理论根据”是基于杂文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即杂文经常使用的皮里阳秋、曲折隐晦的“春秋笔法”。持此论者认为,杂文的这种表现手法是社会黑暗造成的,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种“理论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杂文虽然有其相对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但正因为它是文艺,其表达方式和风格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单一的、枯燥的,而应该是多样的、丰富的。它既可以是含蓄隐晦的,也可以是明白晓畅的;既可以旁敲侧击,也可以直抒胸臆;既可以迂回包抄,也可以正面进攻;既可以皮里阳秋、用“春秋笔法”,也可以实话实说、直奔主题。另外,杂文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也不完全是社会影响造成的。风格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东西。鲁迅风格的形成,固然有社会影响的因素,即他老人家说的“上了镣铐的跳舞”,但更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文学修养、艺术追求、审美意趣、个性特征等诸多因素的综合。
上述说法之荒谬,在于它背离了常识,背离了杂文的本质属性去谈问题。要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是要回归到常识的层面,即围绕杂文的本质属性去开展讨论。杂文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按《辞海》解释,杂文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直接而迅速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瞿秋白说得更直观,说它是“一种‘社会论文’”。可见,杂文兼具文艺和政论文的双重属性,它既是文学作品,又可归入言论的范畴。言论是关于政治或公共事务的议论。人有美丑,言有曲直。不能因为人家言说方式的委婉或曲折就把它排斥在言论之外。言论发达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即自由言说的环境,也就是通常说的言论自由。只有允许人家说话,才能把话说好。假如自由言说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被剥夺殆尽,谈何言论的繁荣发达?杂文是言论之一种,它的繁荣发达,同样需要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需要自由言说的充足的空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政治清明、舆论环境宽松的时代,杂文就繁荣昌盛;凡是政治黑暗、思想钳制严厉、舆论环境恶劣的时代,杂文就式微、凋敝,甚至消亡。远的不说,就以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杂文的兴衰为例。改革开放前30年,杂文创作除了有两年还差强人意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萧条的、乏善可陈的。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其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导致文化的大倒退、大毁灭,杂文首当其冲,不少作者因写杂文而获罪,杂文走向全面消亡。“文革”期间“硕果仅存”的“杂文”就是文痞姚文元的一组“小杂感”。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杂文创作才真正走上繁荣复兴的时期,正如朱铁志先生所说,其时“色彩斑斓的杂文创作像奔涌而出的潮水,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序言)这确实是持平之论。而新时期以来杂文创作之所以呈现繁荣局面,根本原因就是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舆论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舆论空间进一步拓宽。
杂文是社会的晴雨表。如果说杂文繁荣真有什么规律的话,那么,这种规律与上述说法恰恰相反,那就是:社会开明,杂文繁荣;社会黑暗,杂文凋敝。伟大的鲁迅的横空出世或许是个特例,但特例不特,坊间早就有一种说法:假如鲁迅活到现在,过得了“反右运动”,过不了文化大革命。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需要批评,容许多种声音并存的。“嘈嘈切切错杂弹”,才是社会的常态、和谐之真谛。杂文繁荣是社会之福,人民之福。我倒希望杂文能长盛不衰。我想,希望告别杂文时代的人,不是无知,就是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