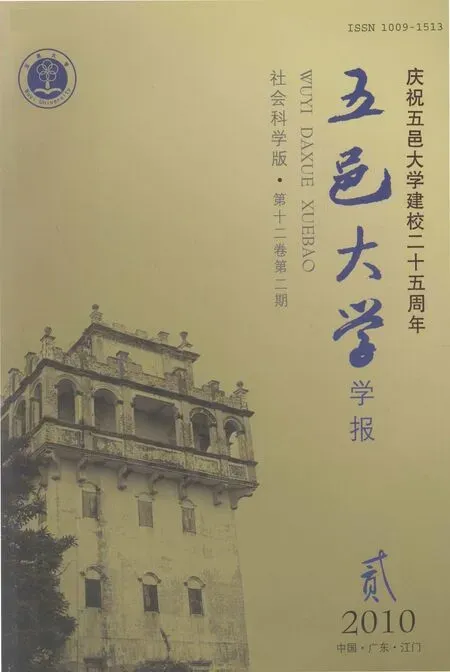李泽厚“积淀说”新论
2010-03-21韩小龙
韩小龙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李泽厚“积淀说”新论
韩小龙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李泽厚为了实现自己美学从历史主义到心理主义的转型,生造了“积淀”一词。积淀说的核心是“自然的人化”理论,它将美与美感、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李早期提出的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设定与积淀说存在着矛盾冲突。在转型过程中,李泽厚美学产生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
李泽厚;转型;张力;积淀
李泽厚为了实现自己美学从历史主义到心理主义的成功转型,生造了“积淀”一词。“积淀说”是联系历史与心理之间的桥梁。据李泽厚本人回忆,早在1956年他就提出了“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即美感是内在自然的人化,它有着两重性,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另一方面又是超感性的、理性的、具有功利性的。李泽厚早期从事的是认识论(或者反映论)美学研究,崇尚社会和理性而漠视感性直观,所以他认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但他这种把美与美感割裂开来的做法,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因为他把“美”当作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社会生产实践的再现,无形中便取消了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使其美学走进了形而上的怪圈。所以,有人批评他的美学是崇拜理性的黑格尔美学的翻版。为了让自己的美学走出形而上的困境,李泽厚找到了康德。康德哲学是一种先验论哲学,认为美的根源在于人类先天性的普遍必然性。李泽厚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认为“普遍必然性”看似先天,其实是后天的,是由于久远历史的烟尘遮蔽,现代人无从知道它的真正来历,此所谓“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李泽厚说,这个历史过程就是“积淀”的过程。“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认为,要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就是指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成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1]472构建“积淀说”不是李泽厚美学的真正目的,其真正用意是引出自己的“新感性”。于是,李泽厚不再满足于先前的认识论美学,而在康德哲学的帮助下建立了主体性美学,但主体性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又遭到刘晓波等人的挑战,于是,在海德格尔等人存在论哲学的鼓动下,他终于提出了对人的生存肯定的新美学,即“新理性”美学。
一、“积淀说”不合乎辩证法
李泽厚两个“自然的人化”理论值得商榷。他指出,自然的人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自然,即山河大地的“人化”,是指人类通过劳动直接、间接改造自然的历史成果;一是内在自然的人化,是指人本身的情感、需要、感知、欲望乃至器官的人化,使生理性的内在自然变成人,即人性的塑造。他认为,从美学角度讲,前者使客体世界成为美的现实,后者使主体心理获得审美情感;前者是美的本质,后者是美感的本质,它们都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这种论证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他将美与美感、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是不符合辩证法的。主观与客观应该是同一矛盾的统一体,成为美的现实的世界是从主观心理感受到的客体世界,没有独立于主观之外的纯粹客观;同样,主观也是相对于客观现实的美的主观。就是说,美的本质是基于美感的本质,离开美感是无法论证美的。朱光潜先生指出:“把‘社会性’单属客观事物,‘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就很难说通了,把人(主观方面)抛开而谈事物(客观方面)的社会性,那岂不是演哈姆莱脱悲剧而把哈姆莱脱抛开。”[2]
尽管李泽厚中期建立了主体性美学,但其美学体系并没有真正在实践基础上将主客观统一起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对李的影响根深蒂固。可以认为,李泽厚中期的主体性哲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美学也并非主体性实践美学。如果说从主体意义的建立到最终用客体意义偷换主体意义是康德哲学的悲剧,那么李泽厚“新感性”学说也具有同样的悲剧性。李人为地拔高了康德的美学思想,把康德的“先验论”说和人的主体性说结合起来,从而得出美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而忽视美的本质,即感性直观功能,把美看作是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心理积淀,看作一种结构存在。这反映了李泽厚中期仍然坚持主客二分的实体性思维方式,他将一切实体化,连同主客观不同的存在形式也被实体化。其实,美不是一种先验的既定的被动历史存在,而是有生命的、积极指向未来的现实存在;美与其说是“被历史化”了的“正果”,不如说始终是扬弃“成果”的实践过程;审美与其说是心理“积淀”,不如说是扬弃“积淀”的意识活动。所以,“积淀说”不过是主观二分实体化思维的变形,它将主观心理实体化的同时,也将客体的实践实体化了,实体化实际走向了僵化。李认为,美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历时性的概念,它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即美是历史的建构。高尔泰对此予以否定:“强调变化和发展,还是强调‘历史积淀’?强调开放的感性动力,还是强调封闭的理性结构?这个问题对于徘徊于保守和进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3]与李泽厚不同,高尔泰把美理解为一个动态结构、一个共时性概念,认为美更多的需要人的能动性去完成,美不是静态的存在,历史的积淀不可能产生美,只能从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中产生美。高尔泰反对把美看作既成事实,因为既成事实无需人的创造,那又怎么谈得上美?
二、“积淀说”与美感矛盾二重性
由早期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到中期的美是历史“积淀”的“心理本体”,李泽厚的学术思想确乎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由单纯的认识论美学转移到主体性美学,承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审美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仍然是他无法走出的困境。柏拉图曾希望找到一个美的共同理念,美就是理念被灌注,好东西就是美的东西。现在看来,这样一种美的共性追求似乎太简单了。那么,是否可以说李的“积淀”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理念呢?虽然它是历史的产物,但其面目究竟如何?谁又能说清楚美是何物?心理本体到底有怎么的规定性?李泽厚只是解释这心理结构(即人性结构)包括三部分:认知能力、道德伦理和审美直观。但这些依然是康德所说的三大部分人性的先验论结构,如果“积淀”的具体内容仍然是康德的先验论结构,那么,李的“积淀”与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理念”又有何区别?当指责别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学派时,李的“积淀”不也是一种类似于先天存在的客观规定性吗?李泽厚坚持将美的本质与审美对象做严格的区分,指出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他认为美的本质要贯彻到复杂众多的具体审美现象、审美对象上,得经历一系列中介环节。显然,他将美的本质与审美现象截然分开,带有强烈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他将美的本质看作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虽说是历史“积淀”而成,可毕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因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历史经验已成为人类大脑中的“先验”,他们依然不知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样的“历史积淀”不要它又有何妨?可见,纠缠于美的本质的本体论,和致力于审美心理研究的审美心理现象学比较起来,是一个大而空的具有形而上倾向的存在。李泽厚称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美学”。
荣格的“无意识集体原型”理论更受到李泽厚的推崇。荣格认为,人的大脑在历史中不断发展,长远的社会(主要是种族)经验在人脑结构中留下生理痕迹,形成了各种无意识原型,它们不断遗传下来,成为生而具有的、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艺术家就像炼金术士一样,要将人们头脑中潜藏的、强有力的原型唤醒,使人们感受到种族的原始经验。“人在这种艺术作品面前,不需要靠个人的经验、联想就会本能地获得对这些原型的深刻感受。荣格强调的是艺术——审美的超个人的无意识集体性质,这与我讲的‘积淀’有关。”[1]464李泽厚被这种十分神秘的形而上理论迷住了,他喜欢荣格是因为荣格将心理与历史联系起来,而历史又可以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相衔接,于是可以在“原型”理论基础上发展“积淀说”。其实,李泽厚的“积淀说”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真正的区别在于: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实现手段是遗传,是每个人大脑里都存在负责把这种“集体无意识”传给下一代的生物学机制;李泽厚抛弃了这种生物学机制,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并作以牵强附会的解释,生造出诸如“新感觉”、“心理本体”、“人化”之类充满神秘感的术语,来强调“积淀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气派的,与客观唯心主义有着天壤之别。其实,“积淀”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它超越个人感知经验的人类主体;集体原型、集体潜意识等都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其根本错误在于抹杀了个体在介入历史与生活中的作用。李泽厚曾举狼孩为例说明“人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这就等于从根本上摧毁了“积淀说”的基础。既然一切都必须经过后天学习,那么“积淀”的积极意义何在?“积淀说”必然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如果观念与想象真的能积淀成类似于遗传基因的社会共同心理结构,那么,这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必然会像生物进化一样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向更具有审美能力的方向发展。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柏拉图的后代若出现在现代社会,李泽厚必定会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弱智儿童,因为他身上缺少二千年文明积累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结论当然让人觉得荒谬可笑——按照庸俗遗传学的观点,柏拉图是伟大的哲学家,其子很可能出类拔萃。既然社会观念与想象的历史积淀没有必然联系,这便否认了“美感是主观直觉性与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相统一”这一美感矛盾二重性的先验设定。
三、“积淀说”的神秘感
李泽厚“积淀说”的论述充满着神秘感,让人迷惑不解而又肃然起敬。李泽厚认为“积淀”的动力是实践,但实践必以意识和理论为先决条件,这就意味着意识和理论先于审美能力,那么审美意识又如何产生呢?答案是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本身已经包含了意识,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李泽厚说:“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1]466这种“深层结构”到底指什么?人们该如何去寻找它的踪迹?这种“共同的人性”常驻哪里?是个体的心理吗?如果是,那它就可以通过遗传来传递,但李泽厚否认遗传的作用,认为那样会堕落到庸俗生物学的老路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将无从体现。那么,是文化艺术教育传递吗?如果这种“深层结构”是可以言传的东西,它就不可能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而会活在人类个体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是这样,那只好像牧师的传经布道一般,把人类的信仰引向那神秘莫测的世界。
李泽厚认为,内在自然的人化是他关于美感的总观点,它分为感官的人化与情欲的人化两个方面。人的感官虽然是个体的、受生理欲望的支配,但是经过长期“人化”逐渐失去了狭隘的维持生理生存的功利性质,再也不仅是个体的生理生存器官,而成为一种社会性感官,也就是感性的社会性。“感性的社会性”是李泽厚发明的又一新概念,是其为了打通认识论哲学与历史观哲学的障碍而设立的专门通道。有了它,李泽厚的认识论哲学便可以顺利地进入其主体性哲学;有了它,“积淀说”美学中的“学术瓶颈”问题就迎刃而解。为什么感性具有了社会性?李泽厚的论证敷衍而过,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李泽厚认为,审美就是超生物的需要和享受,如同认识领域内产生了超生物的肢体(工具)和语言、思维能力,伦理领域中产生了超生物的道德一样,人性也是这种生物性与超生物性的统一。认识领域和伦理领域中的超生物性经常表现为感性中的理性,而在审美领域中则表现为积淀的感性,超生物性完全溶解在感性中。“溶解”一词语义模糊,当李泽厚发现感性与理性无法会合时,经常使用这种粘合的方式实现二者的融合,它们是怎么相互“溶解”的?像水中之蜜那样浑然一体吗?它们融合后又会出现什么新质?李泽厚美学的“哲学加诗”,往往让人进入稀里糊涂的境界。
四、“积淀说”与宿命论
李泽厚说:“感性之中渗透了理性,个性之中具有了历史,自然之中充满了社会;在感性而不只是感性,在形式(自然)而不是形式,这就是自然的人化作美和美感的基础的深刻含义,即总体、社会、理性最终落实在个体、自然和感性之上。”[4]李泽厚秉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最先将“实践观”作为方法论用于美学矛盾的解决,因此美学被引入了人类学的思路而得出了“积淀说”。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观点与50年代的略有不同,他在80年代已经认识到认识论美学的局限性,开始倡导建立主体性美学了,他的哲学观点从原来单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观和实践观在他的学说中占有更重的份量,毋庸讳言,这是李泽厚个人学术研究的巨大进步。但是,50年代美感的矛盾二重性观点,制约着李泽厚的整个美学研究。李泽厚的美感矛盾二重性源于康德审美判断认识论中的知性分析。康德认为,美感是不涉及利害、欲念和概念的快感。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具有与知性相关的四项范畴——量、质、关系、模态,因此具有先验的性质。而李泽厚对美感矛盾二重性也采取了康德式的先验规定:“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简单说来,就是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质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即主观直觉性与客观功利性。”对比康德与李泽厚的表述,可以看出,李泽厚用“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质”取代了康德的“普遍”、“必然”概念,这样就将康德美感的二律背反降格为庸俗的主客观对立矛盾体。康德与李泽厚的美感矛盾二重性都具有先验规定的性质,而将康德归之于先验假设,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属于历史唯物主义,未免有失偏颇。
李泽厚对于美的起源、积淀作用等的论证也不是没有瑕疵的,他常用形式与内容这一矛盾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模棱两可的分析。“就整体看,从古至今,可说并没有纯粹的所谓艺术品,艺术总与一定时代社会的实用、功利紧密纠缠在一起,总与各种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内容相关联,即使是所谓纯供观赏的艺术品,如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也只是在其原有的实用功利逐渐消退之后的遗物,而就在这似乎是纯然审美的观赏中,过去实用的遗痕也仍在底层积淀着,如欣赏书法中对字形的某种辨认,古庙或神像观赏中的某种敬畏情绪,等等。”[1]503-504既然“过去实用的遗痕”在人类的无意识“底层沉淀着”,那么,人类又是如何发现它的存在的?如果人类能够发现它当下的存在,就证明历史积淀不可能发生过。没有原始社会生活消失后其内容仍然积淀在形式感之中,通过历史长时间的传递而在后代人心里重新复活的;即使复活也必需是在原始人当事者的心里才有可能发生。李泽厚的功利“积淀说”明显违反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因为他所谓的形式和内容,不是同一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积淀说”中,形式与内容经常处于割裂状态。内容与形式,应李泽厚的主观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原始人是内容变形式,在现代人是形式变内容。中间起传输作用的是万能的“历史的积淀”。“积淀说”果真有如此魔力?难道抽象形式感的背后存在着一种鬼使神差的宿命安排?
五、结 语
在回答“究竟艺术在先还是美感在先”这个问题时,李泽厚给出的答案是美感(审美)在先。他在谈到美的根源时强调指出,原始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秩序、形式规律有了某种感受,如节奏、次序、韵律等等的掌握、熟悉、运用,使外界的合规律性和主观的合目的性得到统一,从而才产生了最早的美的形式和审美感受。李泽厚谈美的本质历来与人的本质相互关联。其倾向应该是:先有外物及其规律,然后才有人对外物的驾驭,从而产生美感。可是李泽厚却认为“外界的合规律性和主观的合目的性得到统一”,这不就等于承认主观目的性在先?何为目的性?符合人的意志安排,满足人的本能及其他要求的意志诉求即为目的性。李泽厚的论证不就等于说人产生美感之前美感就已经存在了?既然原始人的“主观目的性”存在,就等于说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拥有了美的标准,有了美的标准不就证明了原始人的美感已经存在了吗?可见李泽厚在美感起源问题上用的是循环论证方法。李泽厚并没有走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循环论证的怪圈。
[1]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朱光潜.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J].哲学研究.1961(2):32.
[3]高尔泰.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J].当代文艺思潮. 1983(5):3.
[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34-435.
[责任编辑朱 涛]
I01
A
1009-1513(2010)02-0021-04
2009-11-02
2009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项目(批准号:09JC100008)。
韩小龙(1969-),男,安徽怀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