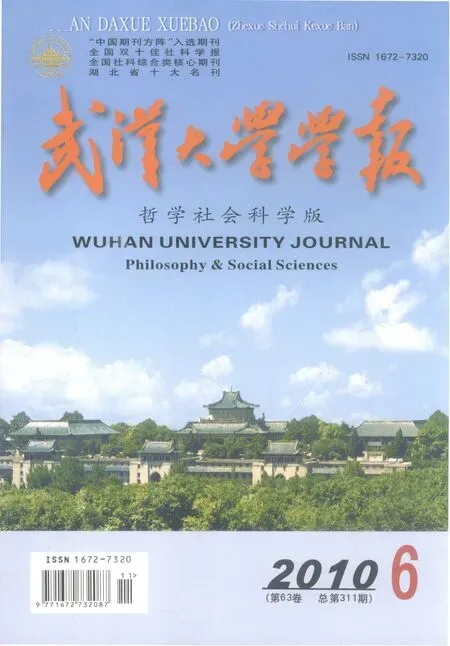政治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关联:历史与现实的审视
2010-03-21蒋英州
蒋 英 州
自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小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①概念以来,人们开始重视除了经济军事等以物质为载体的硬实力之外的以精神为载体的软实力。奈给软实力规范的内涵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前言)。或者说,软实力主要来自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对外政策等资源所产生的效力。在奈看来,一个国家文化的普适性及其建立有力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性的实力之源,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这些软实力之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②。对于软实力的表现方式,奈认为,“软实力不仅仅是影响,也不仅仅是说服,它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而吸引经常导致默许或模仿。”[2](第10页)由此看来,软实力是一种力量的要素集,包括一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资源所产生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这就说明,软实力的资源要素里蕴涵着一个重要的因子——政治文化。这不仅因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性质的文化”,既属于政治领域,也属于文化领域,是以文化学与政治学的“灵魂”的面目出现,具有指导作用与高屋建瓴的总体把握的价值[3](第9页),而且因为“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是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4](第15页)。既然政治文化在一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那么它自然会极大地影响着一国的软实力。
尽管奈在其论著中很少直接使用“政治文化”一词,但他一方面极其重视政治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政府效能必须用政治文化来衡量,而政治文化则比重视效率更重视自由。就意识形态力量资源,给予美国以政治远见并使它对其他社会有吸引力的自由和人权可能远比它们所带来的低效率有价值得多。”[5](第186-187页)另一方面,他把美国政治文化的对外传播作为美国软实力扩张的主要内容。他说:“美国还必须在有助于提供同化行为能力和软实力资源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这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内改革方面的投资,以增强美国政治文化的公开性和吸引力。”[5](第165页)由此看来,政治文化在奈的软实力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一方面,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综观中国对概念的运用与讨论,显示出在软实力概念上的多种解释,其中一些不符合奈的定义。”[6](第427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学界在软实力的定义上尚未取得完全一致,一些定义有过于简化的倾向,而另一些定义则显得措辞含糊[7](第40页)。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对软实力作了中国语境式的理解。正如有学者所说:“应该看到,无论就理论依据而言,还是就价值取向而言,我们所说的‘软实力’与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都有很大不同。”[8](第12页)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或许导致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政治文化对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价值。虽然我们不必唯奈马首是瞻,但理解软实力的核心内涵——政治文化对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却是必要的。于是,本文从历史与现实这两个维度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审视政治文化对国家软实力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从侧面揭示在增强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政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政治文化与国家软实力内在关联的历史溯及
“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的著作中,但它可能不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③。《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关于一种旧观念的相当新的术语”[9](第595页)。这句话所传达的信息是,虽然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它不是突如其来的全新领域,而是源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术传统[10](第246页)。对于政治文化,派伊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系统中的人们对政治形成的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政治心理,以及隐含在民族气质、民族精神、个人价值观、公共舆论、国民性格等中有关政治取向的因素④。这说明政治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许多资源,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政治文化对国家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全面而深刻的。正如一学者所言:“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又是强大有力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政治生活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社会的政治文化。”[11](第55页)因此,尽管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一方面政治文化的研究发轫于古代政治思想家们对国家政治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历史发展都比较清晰地凸显了政治文化对一国软实力的强大影响。
(一)古代
在西方世界,雅典向来被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雅典之所以能创造出西方文明的辉煌,在于民主与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激发了公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雅典公民看来,“城邦耸立于一切小集团之上,耸立于各种次要的团体之上,它赋予一切集团和团体以意义与价值。最高的幸福在于参与城邦本身的生活和活动,而家庭以及朋友和财产,只有作为这种最高幸福的组成部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使人享有乐趣。”[12](第32页)因而,孟德斯鸠十分仰慕雅典式的古典城邦,极为推崇投身于政治共同体生活的积极公民的理想和深切的公民责任感。正是这种理想和责任感,给古代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13](第106页)。这种生机源于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风尚为雅典公民的个体发展创造了条件。英国有学者曾专门探讨雅典城邦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促进了雅典哲学、科学、艺术等的发展⑤。一方面,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了雅典文化与制度的繁荣;另一方面,雅典的繁荣昌盛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使大批杰出人士移居雅典。那些为雅典繁盛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并不全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却都在这个文化与政治的小温床中受到无形的激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是这些人铺设了政治、艺术、文化、教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石,以至于随后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14](第3页)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随着民主政治的鼎盛,雅典城邦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以至于“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15](第206页)。伯里克利在为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举行的国葬典礼上的演讲,揭示了雅典的政治文化与其软实力之间的逻辑关联。他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生活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说的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获得它现有的势力。”⑥雅典能从诸多希腊城邦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影响力与吸引力的城邦,靠的是政治制度与民主思想的力量。例如,伯里克利“取得优势的手段是说话的艺术。他的统治靠劝服。一切决定经过公开细致的辩论,一切影响都服从思想的优势。”[16](第10页)思想上的优势是雅典软实力强盛的主要根源与重要表现。正如奈说的那样:“软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5](第25页)。
从东方中国的古代史来看,凡是对外具有强大影响力与吸引力的朝代,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国家实现了从动乱走向稳定的开明专制的治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唐朝政治上的相对清明、宽容与重民,造就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繁荣,由此形成的国家软实力也就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巅峰。“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均作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7](第128页)对于唐朝的邻国而言,“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汉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18](第8页)。唐朝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强大的软实力,唐太宗的这段话颇能解释个中缘由。他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城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19](第1616-1617页)由此看出,唐朝走向兴盛并成为世界上有强大吸引力与影响力的国家,根植于统治者的文德教化、重民安心的治国政治价值取向,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昌盛自然会吸引邻国的崇拜与归附。
对此,钱穆曾说:“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20](第73页)的确,唐以后的历代王朝未能重现唐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象。尽管宋朝在很多人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朝代,但就软实力而言远不如唐朝。宋代虽然在政治观念上有“不杀士”的传统,但由于过分坚持“祖宗家法”而失去了思想上的创新活力。明清(1840年前)时期尽管社会稳定,但这是严酷专制下的稳定,与唐朝的开明专制是有区别的。这种稳定下的文化心态其积极向上的与建设性的成分居少,而保守消极的与批判颠覆性的成分居多。虽然明朝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强大的,但这种强盛不再像唐朝那样充满对外界的吸引力,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已经不是先进的而是落后的了。“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展和贸易的更辉煌的未来。”“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21](第7-8页)国家活力与民族进取精神的衰退也就标志着明清以后的中国国家软实力逐渐衰退。
(二)近代
英国作为一个在北海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有限,如何会率先闯进现代化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人?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应该到英国历史发展的文化模式中去寻找[22](卷首语)。这里的文化模式主要是指英国的政治文化模式。诺思等人在探究英国16世纪悄然兴起的原因时同样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23](第170页)因而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为它首先爆发工业革命和率先进入现代化准备了条件。之后,英国的现代化模式为其他国家仿效。这些国家不仅学习英国的科学技术,也学习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这是因为英国正是依靠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渐进改革实现了16世纪的兴起、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整体上说,在“日不落”帝国期间,英国对世界的强大影响力,既有政治和军事上的,也有经济和文化上的,还有社会制度上的。这些影响,有的是伴随英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而去,或多或少地带有强制性,更多的则是其他民族和国家对英国模式的效仿。或者说,英国强盛的国势,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得在它国内出现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魅力,吸引别人来学习[24](第391页)。由于英国的示范与带头作用,加之对殖民地的广泛占领,“在不同的程度上英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表现在政体、宗教信仰、教育模式、市镇布局、文化口味、体育和消遣娱乐等方面”[25](第2页)。对此,奈说道:“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2](第17页)
在殖民扩张过程中,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也随之传播到英属殖民地。对移民殖民地,英国允许其按宗主国的摹本建立某种程度的自治,并通过派遣总督等行政长官来实行控制,以保证这些殖民地同母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联系。由于长期受英国文化、制度的影响,这类殖民地在跃升为自治领之时,一般都沿袭了英国的政治体制[26](第363页)。对直属殖民地,英国主要采取自由主义政策来实现它的管理,使表面上的公平交易买卖取代了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从而钝化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感情绪,并且还激发了他们对欧洲文明的学习和移植[24](第277页)。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7](第8页)。这类殖民地独立建国后,基本上未抛弃英式的议会制度和英语的官方地位。“对它们来说,虽然产生于各前殖民地的成文宪法、联邦机构和一党专政的国家几乎不能算是英国议会的翻版,但只要是与英国议会有相似之处的议会,就是自由的化身。”[25](第165页)因而,尽管英属殖民地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但在政治方面,殖民地管理机构默认或鼓励殖民地按照母国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无论是在早期的代议制政府模式中,还是在后来的皇家殖民地政府模式或者责任制政府模式中,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子随处可见。这非常符合奈对软实力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规范——一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被自愿地接受与移植。
在英国衰落的同时,承袭了它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美国开始崛起。“1860年,美国是第二流工业国,落后于联合王国,也许还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可是到1890年,美国跃居首位,其制造品产值几乎等于以上三个主要工业国产值的总和。”[28](第31页)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崛起”的过程⑦。对于美国的迅速崛起,很难用一种理论来完美地解释。不过,托克维尔的解释也许最有说服力。他说:“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29](第356页)在自然条件、法制和民情三种因素中,托克维尔认为,它们对民主制度也就是对美国繁荣致富的贡献的分级是: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在很大程度上即为政治文化,它揭示了美国崛起的根源。
从文化的角度看,过去那种用“短篇小说”来形容美国的历史是一种误解。因为“美国的主流文化植根于西欧文明。从这种文明中,美国政治继承了对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犹太—基督教伦理和由男性主宰社会决策的偏好”[30](第13页)。尽管北美13州的建立有先有后,建立方式上也存在差异,英裔移民有多有少,但由于英国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而产生的凝聚力使它们逐渐联合起来。在对欧洲政治文化进行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美国从建立之初就与欧洲不同。恩格斯曾经说道:“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31](第147页)因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是由一群挣脱了欧洲封建统治和神权枷锁的移民,在没有任何传统负担的前提下,选择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在欧洲文化财富中,清教徒选择的主要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科学主义和社会思想意识[32](第34页)。其中,路德关于“个人权利平等”和“国家教会”的思想以及加尔文关于“预定论”和“山巅之城”的观念、自然理性思想,以及来自英国的法治思想与自治精神,一起构成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源,经过殖民地时期至今的长期灌输,已经成为主导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正是在先进政治文化的凝聚力与感召力的作用下,分散来自西北欧等许多地方的移民逐渐形成美利坚民族,独立后建成合众国,并且爆发出巨大的活力,使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
美国在崛起之后,又约花了20年的时间在人均 GDP上超过英国⑧。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的迅速崛起与16世纪英国的兴起一样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主要借助于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创造性表现出来,而它们的政治文化则提供了最有效的动力机制。因为,在由邦联向联邦转变的过程中,“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相信,他们创立的架构将提供民主和稳定的政治体制。他们还相信,这个国家将以它的政治文化——一个定义为一套成形的理念、价值观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思维方式的概念——为依托。”[30](第13页)1904年马克斯·韦伯受邀考察美国后写就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试图解释美国迅猛发展的动力机制。他认为,在清教精神的指引下,竞争、奋斗、创新、职业平等、禁欲与关爱等精神,既造就了一批在上帝的许可内追求金钱利益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又“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33](第170页)。这种源于欧洲的新教精神在美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里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其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开始显示出对世界的影响力与吸引力。阿克顿勋爵曾说道:“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他们进展神速,胜过那些古老的国家,发展出我们因自然障碍而无所作为的一些原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我们梦寐以求的远景,实现了这里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16](第192页)因而在国内有些学者看来,美国的政治模式是一种根据理想和原则塑造现实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怀着同样理想、信奉同样原则的人来说是可以追求的、开放的,因而是充满了吸引力的。这是美国软实力的真实所在[34](第38页)。
(三)现代
具有政治意义的“政治文化”一词出现在1920年11月。当时,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列宁提到了“政治文化”,指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35](第368页)。在列宁看来,有关政治方面的文化知识、思想教育与培养公民对国家的政治感情、提高公民的科学道德素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可能需要重视两点,一是列宁对民主的高度肯定。1916年列宁在批驳一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就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36](第168页)的政治观念。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种新式的民主吸引了无数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正如汤因比所说:“俄国没有‘天然疆界’,而且,从克里姆林宫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从中国到秘鲁、从墨西哥到热带非洲的世界的农民阶级是一个有力的号召。”[37](第413页)二是列宁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虽然名义上作为协约国成员属“战胜国”,但在实际交战中,明显暴露出其在经济、军事上的落后性,特别是当时苏维埃政府为了退出战争而被迫与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给予列宁深刻而直接的刺激,使他对于通过发展俄国文化,切实提升国力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感与渴求[38](第96页)。所以,列宁在晚年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文化教育为苏联的崛起准备了智力条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巩固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联能够在卫国战争与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取得胜利,与这种政治文化方面的教育所凝聚的民族精神与力量是分不开的。
正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了另一种性质的政治文化,直接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美国认为它们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受到了威胁。因而在苏美硬实力竞争的背后,又直接演变为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的竞争——软实力领域里的竞争。这种竞争在二战刚结束时就已登场。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揭开了这个序幕。凯南声称,美国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进行遏制,将迫使苏联的行为变得较为温和与明智,从而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⑨。他希望通过对苏联的接触,即谈判与改善关系,来影响或促使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最终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按西方的意愿发生变化。在凯南看来,促使苏联和平变革的手段和方法主要依靠美国树立的榜样的作用,即为苏联树立一个真实的、令人羡慕和值得效仿的榜样。尽管凯南认为他的思想被美国的决策者们所误解而导致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结果,但是美国在加紧以军事经济为核心的硬实力竞争的同时,仍然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无非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思想观念的渗透与诱变。一种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较量的思想开始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现代政治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政治文化”一词来源于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人的研究。政治文化研究在此时兴起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宪政的垮台再次强烈地提醒人们注意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很显然,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主要依赖于制度与社会经济因素的观点是不全面的。”[9](第595页)1963年,阿尔蒙德等人出版了《公民文化》一书。他们研究的目的在于,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一种政治态度的模式和一套隐含的社会态度以维护稳定的民主程序。他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们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39](第545-546页)从现实政治来看,他们的这个判断无疑是比较准确的。
但在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此时的兴起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战后新兴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这些国家以及如何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是美国政府的重要外交内容。能用政治文化上的传播使这些国家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是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文化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因而“很明显,《公民文化》一书的创作驱动力是赢得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国家’中人们的心,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40](第211页),以便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西方的民主战胜苏联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美国政府组织学者研究政治文化,主要在于“向国会建议如何使美国的宣传有效地穿透共产主义的铁幕”[40](第227页)。美国学者研究政治文化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理论与策略,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政治文化对民主制度运转和社会稳定影响的比较分析,使人们对美英式的民主政治产生向往,即对非美英国家产生吸引力、影响力与说服力。从这一角度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政治文化研究一兴起的时候就与软实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软性力量潜移默化地使他国自愿服从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的思想就比较清晰了,加之凯南和平演变的思想,“软实力”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
作为一个新概念,“软实力”出现的时代背景就在于长期的美苏竞争,以及美国需要新的理论来归纳与阐释以前不占主流而现在却是急需的思想与策略。以前占主流的思想即为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述的经济与军事为核心的硬实力竞争。为反驳这种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衰败论”,1990年奈发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明确提出了“软实力”概念。随后,奈发表《软实力》一文指出:“美国比其它任何国家拥有更多的传统的硬实力资源。它还拥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软实力资源,这些资源使它保持在国际相互依存这一新领域中的领导地位。”[41](第171页)奈的目的主要是基于后冷战时代国家间竞争的需要,即在国家间的以军事、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硬实力竞争之外,寻找比硬实力更高层次的、更有效力的分析工具。在他看来,美国需要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传播与渗透,使其他国家潜移默化地接受美国的政治价值观,从而使它们愿意追随美国,最终在全世界培育起美国的软实力——以美国为仰慕的对象并视其为权威。
二、政治文化与国家软实力内在关联的现实考察
从整体上说,政治文化对一国软实力表现出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政治文化是国家用来凝聚和团结本国人们的一种强大的、无形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精神力量,它既可以用来抵御外来的思想渗透与诱变,又可用于对他国的政治思想侵蚀。二是政治文化作为国家宣扬本国政策、主张的一种工具,它既可为本国外交政策辩护,获得民众的支持;又可充当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本国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产生影响[42](第165页)。具体而言:
(一)政治文化构成软实力生发的社会前提
奈认为,“力量就是在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方面占优势。”[2](第5页)在他看来,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是考察国家软实力大小强弱的一个主要维度。纵观现代社会,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及其软实力的生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方面,“稳定在分析任何政治体制当中都是一个中心维度”[43](第9页);另一方面,“政府的稳定,对于国家的声望和与它分不开的利益,以及对于作为文明社会中主要幸福的人民思想上的安定和信任,都是必不可少的。”[44](第180页)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社会稳定根源于政治上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小觑合法性问题。“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当合法性受到侵蚀时,政府的麻烦事就来了。”[45](第5-6页)如果政府与法律、制度成为人们经常嘲笑与蔑视的主要对象时,那么人们也就不再信任政府,与政府对抗或违背政策与法律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政府的权威性就会被削弱,会直接导致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与资源调控能力的下降,致使国家软实力受到削弱。相反,“如果大多数公民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再者,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46](第35-36页)这样,具有较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在危机或困境中就能获得社会的支持,而在危机面前,社会内部能够自动激发民族凝聚力与爱国精神的高涨。对任何国家来说,民族凝聚力与爱国精神对其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而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由于与其民主制度相匹配的政治文化的缺失或供需严重的不对称,合法性常常受到反对党与社会的挑战,政治不稳定几乎成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然的政治伴生物。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47](第38页)因而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需要一种相应的政治文化来维系。而对稳定构成威胁的莫过于社会暴力,这就需要民主来发挥协调的功能。因为,只有民主政治在国家长期的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绵延功能,才足以适应化解社会暴力郁积以及建立张弛有度的秩序的需要[48](第56页)。对于现代开放社会而言,社会稳定需要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来维系与凝聚国民的共识精神。从软实力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稳定性程度高,则其软实力的生成和增长相对就要快,一个凝聚力强、国际形象好的国家,其软实力也相对要强[49](第 172-173页)。
(二)政治文化是软实力形成的基础与传播的核心
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虽然政治文化研究存在着不同范式间的争论,不同学者也秉持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总体而言,政治文化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民主制度的稳定问题。也就是说,学者们关心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来配套;怎样的政治文化类型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反,哪些类型阻碍甚至破坏了民主制度的稳定等问题[10](第247页)。因此,民主及其价值观在构成社会稳定相关要素的主要因子时,又成为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政策等的基础和核心之一。而对民主及其价值观的追求可以为软实力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不竭的动力。
美国正是依靠民主思想的全球传播形成了强大的软实力。1988年尼克松在总结苏美竞争的经验时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50](第114页)由此看出,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文化观念的传播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从整体上说,美国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传播手段日益成熟,途径日益多样。美国将这些价值观念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因而人们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拒绝仿效美国民主中的两党制与三权分立的模式,却无法在社会层面上消解美国民主的潜移默化——因为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公民个体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可以一种生活方式的面貌来打动他们所接触的人们。这种方式产生的软实力效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吸引力,尤其是以民主为核心的权利保护与权力制衡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广泛影响;二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在这方面,奈就认为,“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很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2](第11页)因此,他提出要增强美国文化同化力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从而使美国不仅在硬实力方面拥有优势,在软实力方面也拥有优势。同时,在奈看来,美国软实力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世界向美国看齐并接受美国民主的传播。他说:“软实力对促进民主、人权和开放市场等至关重要。吸引别人接受民主比强迫别人搞民主更容易。”[1](第16页)因此,“只要官方的内政外交遵从于民主、人权、开放和尊重他人意见等价值观,美国就能从全球信息化时代的趋势中受益。”[1](第30-31页)对他国知识分子而言,很容易引起对美国民主与民主制度的兴趣与追求,从而成为西化民主思想积极分子;对普通民众尤其是大中学学生而言,也很容易在接受西化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煽动或动员下掀起追求民主的浪潮。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的可怕之处。
布热津斯基曾这样说道:“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51](第23页)许多优秀人才被吸引到美国,他们既是美国软实力强大的体现,又在为美国软实力的强大作贡献。因为,“在美留学生通常怀着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颇为欣赏的态度回国。正如一个国际教育团体的报告所言,‘在过去的岁月里,数百万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构成了我们国家了不起的善意储备。’许多留学生后来身居要职,并能对美国所着重的政策发挥影响。”[1](第47页)对此,奈毫不隐讳地认为,除了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政治价值观进行渗透之外,还需要政府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对政治价值观的自觉推销。在这方面,“美国公司和广告业的经营者、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就在不仅向世界其他国家销售它们的产品,而且也推销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2](第73页)因此,在一般人看来纯属娱乐性质的美国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主题公园等,也在极力传播、确认、强化着人们共同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奈曾这样评价柏林墙的倒塌:“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前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压路机也不会管用。”[1](第51页)尽管从今天德国解密的档案来看,柏林墙倒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德意志民族内在的统一渴求,然而西方文化的渗透的的确确加速了它的倒塌。但这不是流行文化本身的威力,而是它们背后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关于民主、人权、自由、权利等的思想,因为这些才能在性质上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因而亨廷顿针对这一时期的民主化浪潮,说道:“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43](序,第5页)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文化观念的全球传播也就成为美国软实力扩张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奈的软实力思想的核心,因为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文化观念比其他软实力资源更有吸引力与说服力。因此,奈说:“我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有助于促进民主价值观,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人权和民主的信念又帮助增强了我们的软实力。”[2](第165页)
正因如此,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通过各种文化传播渠道在所到之处极力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力图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博爱”的国家形象。这种自觉行为的根源在于美国民众对本国主流政治文化的一种高度认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承担起作为“上帝选民”要把基督教文明推向全世界的使命;同时,通过这种行为使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能够持续不断地深入到公民的灵魂深处,从而凝聚民族的精神。美国主流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统摄力以及濡化与涵化的能力,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使大量外来移民所保留的亚政治文化服从美国的主流政治文化,移民基本上需要接受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才能融入美国社会。因而对主流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有效地凝聚了美利坚民族的团结并激发出了强大的社会活力,从而生成了美国内部的强大软实力。我们可以看到,“9·11”事件后,美国民众迅速站在政府一边,而由此引发的阿富汗战争,还包括此前的伊拉克战争,在整体上说美国民众是支持政府的。这里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不仅仅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深层次上说还出于美国政治文化推广的需要。因为在美国民众看来,人最重要的莫过于自身权利的保护,这种保护不仅依靠法律、政府,更要依靠自身。他们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多数人强烈地要求运用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就会得到保护并得以运用,于是制度就能够发挥功能。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要求和决心,无论是法院,国会还是议会都爱莫能助”[52](第216页)。他们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也希望他国民众的基本人权得到像他们一样的保护。当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不能保护甚至是侵犯该国民众的人权时,美国社会便对该国政府生发出一种道德上的强烈谴责,并产生一种“为实现这些价值观做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1](第7页)。这种道德法律的原则重新解释了“侵略”的含义,为美国政府在实现外交政策过程中进行渗透和颠覆提供了合理与合法的依据,并对战争的作用作了新的解释,并且提供了一条鉴别战争正义与否的新依据[32](第73-74页)。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为美国内外软实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因此,一方面美国可以不顾盟国的反对而一意孤行,并不在意外部软实力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战争对美国内部的社会凝聚与政府动员能力的消极影响。尽管战争使美国处在一种受谴责的境地,但是并没有妨碍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人才涌入美国,也没有妨碍美国社会内部的团结。这就是美国仍然拥有超级软实力的表现。所以,奈才认为,在所有的大国当中,只有美国在所有关键的实力领域里拥有丰富而广泛的实力资源,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即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的广泛吸引力⑩。
(三)政治文化是软实力资源产生效应的关键
布热津斯基曾说:“美国的全球号召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是它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53](第253页)这说明,政治制度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但是,政治制度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演变为一种政治观念与理论的形态。同时,政治制度要在国内发挥出相应的制度效力,必然要借助于政治文化的支撑。正如钱穆所言:“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20](第60-61页)英格尔斯通过多国的调查与比较,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54](第4-5页)这都说明了政治文化对社会制度甚至整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因此,政治文化成为社会制度产生软实力效应的关键变量。
同时,对于硬实力资源要产生软实力效应的话,也需要上升到制度与文化的层面上,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才可能完成这种转变。奈认为,虽然物质财富“也可以产生软实力”,但“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免费信息资源,加上可信度的重要性,软实力很可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物质资源的产物”[55](第280页)。因此,物质财富产生的软实力并不是指物质本身,而是由生产物质所产生的对信息与思想的制造与控制。因此,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要转化为软实力,就需要将促进经济军事科技发展的制度与文化因素提炼成理论与思想,以证明和展示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凝聚力与创造力,由此才能形成与展示一国的软实力。正如亨廷顿说:“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56](第89页)
三、结 论
从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内涵和外延仍有不同的认识,但并不妨碍战略界对中国软实力做出基本的评估。战略界普遍性的观点是,中国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均令人忧虑[57](第20页)。这种对中国软实力的忧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内部缺乏软实力所致。因为国内的诸如政治腐败、社会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信仰缺失等严重问题,以及社会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与提升。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与水平冲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文化在实践体系上还未发挥出主导性作用从而使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有关⑪。同时,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实际的’软实力很可能在继续增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为争夺世界影响力而战。”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的一系列因素最终会限制它的软实力,包括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环境的挑战。”[58](第126页)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软实力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它的国内政治。”[59](第2页)
对中国而言,中外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是看有没有一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政治文化能否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对世界各国的感召力[60](前言,第18-19页)。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政治文化的建设对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在另一面,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与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忌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倡导软实力。1998年,奈与基欧汉就明确地指出“,在更多情况下,软实力是一种无心插柳的结果”[61](第87页)。也就是说,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副产品或产生的溢出效应。在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的今天,政治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了。因而,国家软实力建设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应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政治文化的建设置于其首位。切实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以保障和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对中国形成真实长远的国家软实力具有深远的意义⑫。
注 释:
① “soft power”有多种中文译名,大陆有三种较通行的译法: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其中又以“软实力”最普遍。庞中英认为“,soft power”译成“软力量”可能更贴切“,软实力”的译法则是一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提法,因为“软”字后面跟着“实”字,实际上不仅不符合“软力量”的观念和思维,而且急功近利地把“软力量”变得硬化,把“软力量”也叫做“软实力”是典型的中国式误解(参见庞中英《:重新定义国家软力量》,载白岩《:新世纪的思考》第6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在本文看来,尽管“实力”、“权力”与“力量”在中文语境里的涵义各不相同,但“soft power”无论是哪种译法,它的涵义应该是相同的。因此,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一律采用“软实力”,而在注释与参考文献中保留其他译法。
② 参见 Nye,Jr.,Joseph S.1990.“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 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2):177-192.
③ 参见Barnard,F.M.1969.“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Herder’s Suggestive Insigh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2,Jun.):379-397.
④ 参见Pye,Lucian.1986.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 n.
⑤ 参见[英]G.E.R.劳埃德《:古希腊的民主、哲学和科学》,载[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公元前508年到1993年》,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2页。
⑥ 参见西方文明在线《:伯里克利演讲》,http://www.zfwmw.com/article.asp?id=2027。
⑦ 黄安年在《美国的崛起与发展》(上)(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对“崛起”和“崛起后”作了较为详细的区分,对我们认识“崛起”一词大有裨益。1894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是美国崛起的标志,此后美国属于“崛起后”的大国。不过,这个年份时间还值得探讨。美国学者布卢姆等人以1890年为标志。
⑧ 参见[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⑨ 参见 Kennan,George Frost.1947.“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25(4):566-582.
⑩ 参见 Nye,Jr.,Joseph S.1995.“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 ton Quarterly 19(1):5-24.
⑪《人民论坛》2009年11月26日至12月8日进行了“盛世危言:未来10年最严峻的10个挑战”的专题调查,共有8128人参与了投票。排在前十位的问题依次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基层干群冲突;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诚信危机,道德失范;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载《人民论坛》2009年第24期)。
⑫本文首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9年第4期。此次发表时作了修改。
[1][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2][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3]孙正甲:《政治文化》,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罗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5][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6]Wang,Hongying&Yeh-Chung Lu.2008.“The Conception of Soft Power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aiwa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56(17,August).
[7]刘 庆、王利涛:《近来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载《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
[8]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9][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编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载《复旦学报》1988年第3期。
[1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4][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1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6][英]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7][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18][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后晋]刘 昫:《旧唐书》卷七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钱 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21][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22]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4]刘景华、丁笃本:《“日不落”的落日——大英帝国的兴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25][英]P.J.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26]计秋枫、冯 梁:《英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8][美]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戴瑞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0][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2]汪 波:《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3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6]《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张 文:《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探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39][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0][美]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1]Nye,Jr.,Joseph S.1990.“Soft Power,”Foreign Policy Number 80(Fall).
[42]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43][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44][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5][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4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47][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48]任剑涛:《社会疲态下的暴力危害与民主救治》,载《探索》2009年第2期。
[49]孟 亮:《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50][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谭朝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52][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53][美]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54][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5][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5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7]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第2期。
[58]McGiffert,Carola.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A Report of the CSIS Smart Power Initiative,March,2009.
[59]Lee,Sook-Jong.China’s Soft Power:Its Limits and Potentials,EA I Issue Briefing No.MASI 2009-07,October 20,2009.
[60]刘建飞:《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61]Keohane,Robert O.&Joseph S.Nye,Jr.1998.“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 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