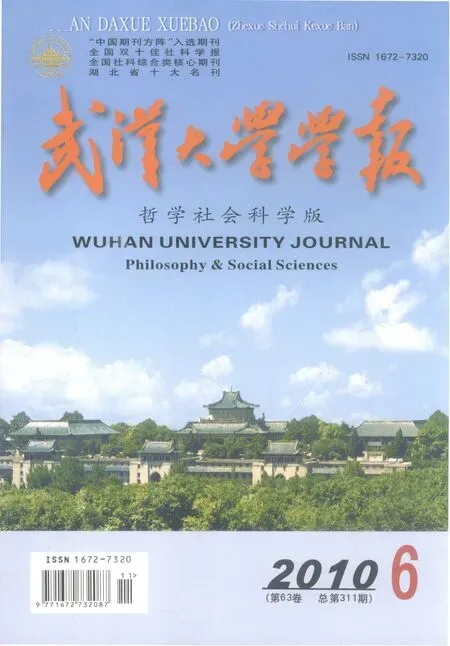国际化背景下驰名商标刑法保护探析
2010-03-21雷山漫
雷 山 漫
一、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及价值取向
驰名商标凝聚了权利人巨大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取胜的法宝。因此,设立驰名商标此概念的法律意义在于:“驰名”可以成为商标得到特殊保护的理由[1](第72页)。国际和各国立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正体现了这一点。
对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的模式包括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两种,1925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首次提出驰名商标的概念。根据该公约规定,凡被成员国认定的驰名商标,可以对抗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或使用与之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巴黎公约》还将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纳入了保护范围,但对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保护限于同类商品的范围内,这属于典型的相对保护主义模式。以《巴黎公约》为代表的此阶段驰名商标的保护使驰名商标得到了有别于普通商标的特别保护,但其所保护商标不包括服务商标,对驰名商标的侵权行为仅限于使用民事和行政救济而未启动刑事程序。1994年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即 TRIPS协定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是绝对保护主义的典型,它在肯定了《巴黎公约》对驰名商标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是将适用范围扩展到服务商标。二是对驰名商标实行跨类保护,即将保护的范围扩大到不相类似商品或服务,打破了《巴黎公约》仅限于“同类商品”上的保护界限。三是 TRIPS协定还规定了驰名商标侵权的刑事救济手段。协定第61条规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正是因为商标假冒侵权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私权,还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及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刑法介入商标侵权等领域逐步得到认可。现今,运用刑事手段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随着对驰名商标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驰名商标绝对保护主义已成为国际发展趋势,以刑法手段规制侵犯驰名商标的行为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运用。就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而言,世界各国普遍对假冒驰名商标的混淆侵权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假冒驰名商标的混淆行为在实践中可分为四种:(1)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2)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3)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4)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都将上述四种混淆行为规定为犯罪。不可忽视的是:各国出于本国国情和利益的考虑,对驰名商标混淆行为的刑法保护范围存在差异,不同主要表现在保护对象是否包括未注册驰名商标,是否包括上述混淆行为的所有类型,是否存在混淆行为刑法规制中普通商标和驰名商标的区别保护等等[2](第4页)。当前,对驰名商标刑法保护另一需要关注的问题即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问题。“跨类保护”是指将在不同或不相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驰名商标的行为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行为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根据“淡化”理论,由于驰名商标基于其“驰名”的特性而具有一种超越商品或服务类别的相对独立的价值,他人在非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他人的驰名商标也会对这种价值造成减损,所以当前国际和各国立法对驰名商标加以特别保护的主要形式就是“跨类保护”,并呈现出将其犯罪化并给予刑事救济的趋势[3](第379页)。如英国商标法规定:对于在英国已享有声誉的“驰名商标”,未经该商标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同意而在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也构成犯罪[4](第129页)。
以上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的发展进程体现了对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价值取向。鉴于驰名商标的特性及特殊价值,有必要给予驰名商标不同于一般商标之保护,这对打击屡禁不止侵害驰名商标的行为,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及消费者的利益,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意义重大。
二、我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的现状
我国刑法典就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在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简称《追诉标准》)第61条第3项规定:“假冒他人驰名商标或者人用药品商标的,应予追诉。”第63条第2项规定:“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驰名商标标识的,应予追诉。”据此规定,上述两种针对驰名商标的行为不管情节如何,都可以进行刑事追诉,这体现了对驰名商标区别于普通商标的特别保护,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刑事立法有关驰名商标的唯一特别规定。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解释(一)》)大幅降低了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犯罪行为的追诉标准,但对驰名商标未作专门规定,驰名商标和普通商标受到同等保护。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简称《追诉标准(二)》),其中侵犯商标权犯罪的追诉标准与《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解释(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定罪标准基本完全相同,没有关于驰名商标的特殊规定。此最新的追诉标准发布之时《追诉标准》同时废止,这也使体现了对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唯一规定不复存在。
以上立法体现出我国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有以下特点:第一,刑法保护的驰名商标范围小,对驰名商标实施弱保护[5](第105页)。这表现为:(1)我国刑法保护的假冒驰名商标的种类只包括商品商标,没有把驰名服务商标纳入保护范围,非注册驰名商标也不在刑法保护之列。(2)我国刑法规制的侵害驰名商标的行为类型限于“两同”的混淆行为,即“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和他人注册驰名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另外三种混淆行为被排除在外。驰名商标的淡化行为也不属于刑法调整范围。第二,我国刑法对驰名商标和普通商标同等保护。依照我国刑法规定,驰名商标和普通商标所受保护并无区别,若说2001年的《追诉标准》还体现了对驰名商标特别保护的精神,但《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解释(一)》及新近颁布的《追诉标准(二)》则消除了这种特殊性,使对驰名商标和普通商标的刑事保护归于同一。所以,在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驰名商标能获得刑事救济,但却是与一般注册商标同等的救济。
我国政府于2008年6月推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纲要》中指出形成一批拥有知名品牌和核心知识产权,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优势企业是近五年的目标之一,并将提高商标知名度,形成驰名商标,鼓励企业进行国际商标注册,维护商标权益,参与国际竞争作为一项专项任务。这表明了国家努力打造驰名商标的决心。在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日益加强的国际背景下,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需要,加大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力度,确实有在立法上给予驰名商标刑事特别救济的必要。
三、我国驰名商标刑事特别救济之探讨
(一)完善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
在完善刑法第213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讨论上,关注焦点一是扩大保护范围,将注册服务商标也作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二是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方式,将商标法第52条第一款规定的对商标造成混淆的四种行为都列为假冒商标罪的行为方式。对焦点一学界已无大的争议,但对焦点二的问题一些学者从TRIPS协定的要求及刑法的谦抑性、效益性角度出发,认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维持刑法规定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相同的商标”的情况即可,不必扩大到另三种混淆行为[6](第45页)。笔者认为实践中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的商标,是最原始、最低级的假冒形式,现在造假的花样翻新,此种低劣的手法已被造假者“淘汰”,更多情况是侵权人钻法律的空子,或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商标近似的商标,或将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用于类似商品,却只构成民事侵权,只能以商标违法行为处理。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将另三种假冒商标的行为犯罪化必将加大假冒商标行为的法律成本,《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战略重点中也提出“修订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法规,提高侵权代价”,这对于遏制此类由理性的市场主体经过利弊权衡的违法行为具有显著的效果。所以针对现实中的商标假冒大多是对驰名商标的假冒情况,将我国刑法规制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扩大到另三种混淆行为对加强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是很有助益的。
由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上述两方面的完善是对所有注册商标而言,不论注册的商标驰名与否都享受同等保护,且未注册的驰名商标得不到刑法保护,因而体现不出对驰名商标的特别法律救济,所以有学者提出增设侵犯驰名商标权罪、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驰名商标标识罪等[7](第25页),笔者认为这值得商榷。首先,驰名商标的“驰名”使其得到特殊保护,但特殊保护并非使驰名商标能够产生一种“驰名商标权”。对驰名商标而言,在商标制度内它和普通商标是相同的,其禁止力限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特殊”体现在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存在超出商标权范围的保护即“跨类保护”,这种保护是以反不正当竞争为基础的,而非依据什么“驰名商标权”,所以从增设罪名的设计来看显得有失考虑。再者,侵犯驰名商标权罪的提法也是为了将未注册驰名商标纳入刑法保护,但我国商标法律制度采用“注册原则”,未注册商标一般不能获得商标法的保护,通过商标法等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加以保护,已体现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因而不宜将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上升到刑法层面。
为震慑现实多发的侵犯驰名商标的犯罪行为,在对刑法规定的商标犯罪法条加以完善的前提下,体现特殊保护,无需增设针对驰名商标的新罪名,而可采取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方式。影响我国刑法中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和第215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这两罪的刑法要素是“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解释(一)》中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了相应标准,如“情节严重”有三种标准:第一,以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或注册商标标识数量为标准加以确定;第二,以侵犯注册商标种类数并辅以一定数量标准加以确定;第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在商标犯罪中依标准三将行为人假冒、制造的商标属驰名商标与否作为认定其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参考标准之一,从而给予特殊的刑事司法保护是有制度空间的。如果被侵害的是驰名商标,虽然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没达到定罪标准,但可以在司法解释中“其他情节严重”、“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兜底条款规定中找到依据,以此体现出对驰名商标予以特别保护的精神[8](第12页)。不过,对侵害驰名商标构成犯罪还是应在体现对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的思想指导下确定相应的起刑数额,若只要是侵犯驰名商标即属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而没有相应起刑点,则侵犯驰名商标的犯罪就由“结果犯”改为了“行为犯”,不仅模糊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间的界限,还可能将驰名商标侵权行为的犯罪化过于扩大,有违刑法谦抑原则。
(二)淡化行为刑法规制之否定
淡化是指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虽然不会引起混淆,但冲淡了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导致驰名商标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的能力被削弱的行为。淡化仅针对驰名商标而言。因为驰名商标的高度显著性使构成该商标的符号超越了商品和服务类别的限制,如果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仍局限于类似商品或服务,便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对驰名商标采用更为隐蔽的侵权方式,即“搭便车”,将驰名商标用于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借驰名商标良好的商誉推销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时间一长,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必然被削弱。在此情况下,禁止将注册商标用于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之上的传统商标保护制度显得力不从心,商标淡化理论应运而生。
由于当前国际及各国立法对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的主要形式就是“反淡化保护”,并呈现出将其犯罪化并给予刑事救济的趋势。于是有学者提出为与 TRIPS协定相协调,并趋向世界立法趋势,我国有必要使用刑法手段规制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9](第95页),即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引入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笔者对此观点难以认同。一是因为 TRIPS协定虽然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跨类保护,但它是从“禁止性”保护的角度对驰名商标淡化问题做出回应,限于行政救济手段。依 TRIPS协定的最低保护标准规定的义务对商标侵权的刑法规制只针对假冒商标行为,淡化行为不在此列。因此,从我国承担协定最低标准义务出发,对驰名商标淡化的刑法规制我国没有与该协定“相协调”的必要。再者,立法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随着驰名商标淡化问题讨论的日益增多,有观点提出是不是该把欧美国家已经出现的反淡化规定加进来或仿效美国制定反淡化法。这些观点与当前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强化,国际、国内主张高标准保护知识产权的声音越来越大不无关系。在驰名商标的保护上,同样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发展状况。虽然我国实践中也存在淡化现象,但情况并非很突出,而且在商标反淡化方面,目前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司法机关都没有太多经验,所以对淡化问题,根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予以民事、行政处罚即可,用刑法加以规制没有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何况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反淡化行为的根据都仅停留在民事或行政领域。
(三)反向假冒驰名商标行为的犯罪化
反向假冒是指未经商标权人同意,更换其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不仅损害了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商品声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均规定了反向假冒是要受到法律禁止、制裁的行为。将该行为作为犯罪进行处罚的也不在少数,如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等,都将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为犯罪。
我国对反向假冒商标问题的关注,大致发端于1994年的“枫叶”诉“鳄鱼”案。当时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此类行为的明文规定,直到2001年《商标法》修订时,第52条第4款才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但由于1997年刑法在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不可能将反向假冒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体系之中,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对情节严重的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刑法无法规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大幅度上升,由于驰名商标特别是世界级驰名商标的多寡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体现,所以我国政府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表明了国家努力打造驰名商标的决心。企业实施创品牌的“名牌战略”也正是其在国际市场寻求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近几年我国出现的反向假冒案件,许多都是国外大公司反向假冒我国的质优价廉的商品,用我们价廉物美的商品,换掉商标后去创他们的牌子,这无疑对我国起步较晚的民族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参与国际竞争非常不利。反向假冒若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将成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一大障碍。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看,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比现行刑法已规定的三种商标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要大,因为它具有对社会、团体及个人利益的多重侵害,且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综合其客观危害和预防难度,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益侵害更为严重,因此对其犯罪化的依据更为充分[10](第15页)。所以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角度出发,为保护我国的驰名商标,将反向假冒注册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发挥刑法作为利益保护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完善我国商标保护制度的可取做法。
在针对规制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完善上,有观点提出因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与假冒商标行为极其相似,可通过扩充刑法第213条的保护范围,即在该条后增加一条关于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规定(作为第213之一)。严格分析,难以认定反向假冒行为侵犯了被反向假冒人的商标权,或与假冒商标行为极其相似,因为侵害商标权的行为特指非法使用他人商标、借用他人商誉的行为,反向假冒是撤换他人商标,并没有使用商标权人的商标,不可能侵害商标权。另从国外立法例来看,一些国家将反向假冒行为规定于商标法中,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将其定性为商标侵权行为,如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反向假冒商标行为,通常是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适用商标法第43条a款,而不是作为商标侵权行为处理的,所以前述完善模式存在不妥。从我国现实需要出发,需要对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但应将这种行为直接规定为商标犯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专门设立反向假冒商标罪。
[1]李 琛:《知识产权法关键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肖中华、涂龙科:《论我国驰名商标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载《犯罪研究》2006年第1期。
[3]张延新:《我国驰名商标法律救济中的若干问题评析》,载陶鑫良:《上海知识产权论坛》第3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赵秉志:《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5]薛莉萍、杜小丽:《商标类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新探讨》,载顾肖荣:《经济刑法》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贺志军:《论TRIPS协定下我国商标权刑事保护两个问题》,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3期。
[7]孟丽君、于巍巍:《论驰名商标的刑法保护》,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8]高铭暄、张 杰:《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
[9]罗开卷:《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3期。
[10]傅跃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 车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