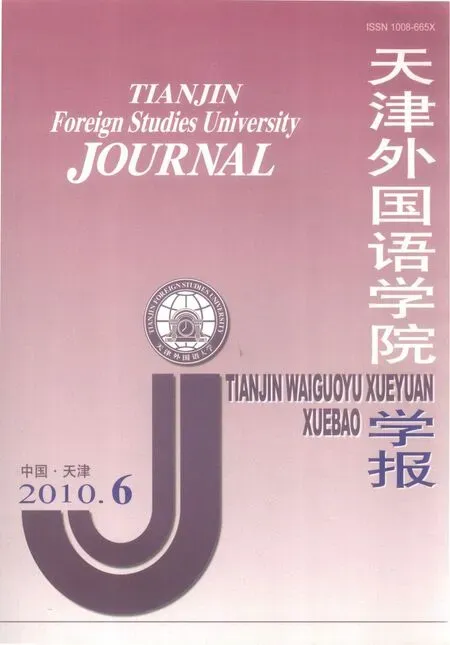颠覆侦探小说——论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
2010-03-20刘启君
刘启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颠覆侦探小说
——论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
刘启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代表作《纽约三部曲》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叙事语言三个方面对传统侦探小说进行颠覆,充分彰显了反侦探小说这一新文类的叙事魅力。同时,在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和拆解中也浸透着作者对当下文学创作以及都市人生存困境的哲学思考。
《纽约三部曲》;反侦探小说叙事;颠覆
一、引言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纽约三部曲》成功地反映了纽约的城市生活和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肯尼斯·米拉德(M illard,2000:180-185)将这部作品收入《当代美国小说》,并给出了十分精当的评价:“用元小说这个词来形容它是最贴切不过的,作者通过对逻辑理性的亵渎和对语言的解拆,给业已写就的文学传统进行重新编码,展现了后现代都市人在消解传统以后的匮乏和以不确定性对抗确定性后的迷茫。”
《纽约三部曲》里第一部问世的是《玻璃之城 》(C ity ofG lass,1985),之后 ,《幽灵 》(Ghosts,1986)和《锁着的房间》(The Locked Room,1986)陆续发表。在小说接近尾声时,作者点出“这三个故事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故事”(Auster,1900:346),都以带有侦探色彩的情节为主线,讲述了主人公对他者的跟踪和追寻,揭露了当代人难以言喻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隙。
奥斯特对于人生的思考是严肃的,表达的主题也是凝重的,但他却借用了侦探小说这一通俗体裁来完成其创作意愿,他这样做是有其独特用意的:披上通俗小说的外衣,待故事收获了众多的读者之后,再一步步地挫败读者的阅读期待,逼着他们去思考为什么侦探小说的根基——逻辑分析和因果推理——在这里会完全失灵。表面上似乎对侦探小说的传统奉行不违,可骨子里却对其彻底颠覆。这样的颠覆主要体现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叙事语言三个方面。
二、难以破解的内心之谜
《玻璃之城》中午夜的电话铃声、貌美女子的深夜求助以及具有科学狂人色彩的老斯缇尔曼,《幽灵》里两个男人怀特 (W hite,白)与布莱克 (B lack,黑)之间可能因情而起的冲突,《锁着的房间》中范肖的人间蒸发,凡此种种都是侦探小说里经常上演的戏码。它们以最快的速度攫住读者的眼球,可是故事发展到后来,并没有出现任何因为钱或性而导致的犯罪事件:刚刑满释放的老斯缇尔曼没有害人之心,依然醉心于他的语言实验;雇佣布鲁 (B lue,蓝)跟踪的怀特 (白)与被布鲁跟踪的布莱克 (黑)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并非如布鲁所臆想的情敌关系;范肖也没遇到任何意外,而是心甘情愿地走上了自我放逐的道路。
拨开叙述的云雾,剔除侦探小说中常用的噱头,《纽约三部曲》里剩下的不是赤裸裸的犯罪事件,而是一个个被隐而不去的悬浮感所攫持的裸露灵魂。奥斯特用三个没有终结也终结不了的追寻故事想要彰显的决非是他编织情节、制造悬念的精湛技巧,而是他对人性的思考和对当代人生命意义的叩问。
三个故事的主人公虚浮于多元混杂、人情冷漠的纽约大都会中,深陷在不可言说的生命困惑和意义缺失中难以自拔:昆汀,一个以写侦探小说为生的作家,关于他的家庭,小说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只是寥寥数笔提及他父母双亡,曾有过妻儿,亦离开人世;布鲁,一位年轻的侦探,他的老师和女友先后弃他而去,留下他一人苦苦地叩问自我为何,他者为何,以致在不断地怀疑和发问中无所适从;“我”对童年玩伴范肖的崇拜由来已久,一心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可纵使“我”攫取了范肖的写作成果,娶了他的妻子,认了他的儿子,还是发现范肖这个身份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彼岸,随着自我的丧失以及生存意义的丧失,“我”也只能在无底的深渊里沉沦。
疏离和隔绝,偏执和绝望以及对话的艰难成了奥斯特艺术世界里不断演绎着的关键词汇,飘泊的无根性成为了奥斯特笔下人物的本质特征。作者的思想触角伸向的不是社会暴力、钱权交易以及爱恨情仇这些侦探小说中常见的犯罪要素,而是更晦涩难懂、更复杂多元的后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作者关注的是后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以及在这个困境里苦苦煎熬的都市人的灵魂。
奥斯特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的作品与侦探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侦探小说是给答案的,而《纽约三部曲》是提问题的 (M cCaffery&Gregory,1993:269-312)。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体裁,侦探小说所关注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人们为了理清头绪、接近真相并最终获得新知而付出的努力 (M cHale,1987:9)。收集线索、检查证据、揣度证人的可信度,这些侦探小说中的常见元素,《纽约三部曲》里都有所体现,可奥斯特故意剥除的恰是侦探小说最关键的部分——柳暗花明、水落石出的那一刻。取而代之的是疑问被永久性地悬置,问题无从找出答案。
昆汀日夜监守着老斯缇尔曼,在红色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了他的所有行动以及自己的分析,可老斯缇尔曼是人如其名 (Still-m an),他的生活是静止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昆汀怎么努力,对他的生活也还是理不出丝毫头绪;布鲁在监视布莱克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生活乏善可陈,以致于麻木到把监视这一动作本身当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当他发现布莱克和怀特本是一人时,他之前笃信的认识体系完全崩溃,在狂怒中他找布莱克对质,可他原有的疑问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他不仅开始怀疑整个世界,整个价值体系,更开始怀疑自我;“我”越紧跟范肖的脚步,越发现自己不理解他,彼此的距离也就越远,苦苦地追踪了那么久,最后满以为见到范肖时,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可他连片刻明白洞悉的机会都没有给“我”,横在“我”和范肖之间的那扇门是永远也无法穿越的,“我”也只能和无休止的疑问继续纠缠下去。
对于这样一类小说,西方学者早就有所关注和论述。威廉·斯帕诺斯 (W illiam Spanos)在 1972年首先提出了反侦探小说这一概念,他认为,其核心是反亚里士多德主义,即拒绝满足因果期待,摒弃有始有终还有详尽发展过程的故事。之后的两位学者斯特芬诺·塔尼 (Stefa-no Tani)和汉斯·伯顿斯 (Hans Bertens)结合后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了这类小说的发展。中国学者也同样意识到了反侦探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胡全生和林玉珍 (2006:53)详尽地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如何借用侦探小说这类通俗体裁,并“釜底抽薪”,从而达到其颠覆传统、颠覆秩序的目的。《纽约三部曲》就是对传统侦探小说的一次解构,读者曾经习惯的阖卷时的释然感已然不复存在,传统的认识论被拉下了神龛,这里氤氲不散的是后现代世界的不可知性和不确定性。
三、多元杂糅的空间结构
在传统侦探小说里,高潮是在故事的结尾,所有的谜团被逐个解开,侦探们精湛绝伦的分析推理能力得到一次性的展示。这种剧情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侦探小说往往以时间倒回的方式和线性的叙述手法作为其主要的叙事框架,从发现尸体那一刻逆溯到谋杀动机产生时 (Russell,1990:71-84)。而《纽约三部曲》则明确地指出:“地点是纽约,时间是现在,并且地点和时间永远不会改变。”(Auster,1990:161)这与贝克特 (Beckett,1970:41)的《等待戈多》里主人公埃斯特拉贡的那句名言“什么事也没发生,什么人也没来过,什么人也没离开,感觉遭透了”遥相呼应,都在指射后现代人的生存环境,没有了终极意义,历史的车轮不再朝前,生活静态、盲目而空虚。
三位主人公就这样迷失在了一个充满偶然性、随意性和未知性的世界。追踪伊始,他们也曾信心满满,相信只要通过对被追踪者言行的周密分析,就一定可以理出一条思路,并最终查出他们的行为动机。在昆汀看来,人的一举一动,嬉笑怒骂背后都有其缘由,并且这些内在推动力是可以被他分析出来的 (Auster,1990:9);布鲁也天真地认为世界是如此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只要留心每个细节,找出最合适的语言记下它们,文字会为他打开一扇窗,走进事情的真相(ibid.:174);“我”自发现好友范肖没有失踪后,开始疯狂地整理范肖的书稿,追寻范肖曾走过的足迹,哈佛校园,远洋海轮,法国乡村……认为总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发现范肖的所在,敲开范肖一直紧锁的心扉。然而,随着三位主人公对他者跟踪的进一步深入,整个情节没有任何向前发展的迹象,侦探小说的时间框架和线性的叙述方式被完全打破,理性思考和既定原则在这里丝毫派不上用场。
当时间停滞,发展停滞,故事中不再有一环套一环,逐步深入地扣人心弦时,当环境迫使人踯躅不前,永远活在当下时,当泛滥的感官经验湮没掉历史的积淀,冲碎对未来的希望时,三位主人公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焦虑中。侦破没有任何向前进展的迹象,心中的焦灼与彷徨与日俱增。
侦探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安排都是围绕侦破案情这条主线展开的。有时主线也会伸出旁枝,例如,穿插着讲述主人公以往的生活经历、人性悲剧的形成原因以及侦探们曾经遇到的类似的案件等,但这些“节外生枝”仍囿于主线发展范围之内,是为完善故事情节、丰富人物形象服务的。《纽约三部曲》里也同样嵌着许多小故事,只是这些旁生出来的文字与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丝毫无关。如果把每部小说比作一篇乐章,那么,这些小故事就是其中最不和谐的音符,突兀地断裂在一边,可正是这样的一种不连续的断裂道出了其特有的含义。
《玻璃之城》中反复出现了爱伦·坡笔下的侦探故事情节,《玻璃之城》中还引用了爱伦·坡笔下的名侦探杜平 (Dup in)的话来分析案情,“既然侦探和他的对手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和能力,通过理性分析,案情总能得到解决”(ibid.:48)。这正是奥斯特要攻击的靶子。那些曾经被视为永恒自明的真理遭到了质疑,现代精神所追求的明晰性让位于后现代的模糊性。随着理性大厦和传统认识论的颓然委地,三位主人公颓败为在彻底怀疑否定中自我放逐的孤独灵魂。爱伦·坡笔下适用的真理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完全失灵,奥斯特将坡的侦探故事穿插其中,与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示了这个社会的暗晦和人们放弃追问任自我迷失的全部悲剧性。
《幽灵》中布莱克给布鲁讲述过霍桑写的一个小故事:一名叫威克菲尔德 (W akefield)的男子对妻子谎称要外出数日,却在城市里躲了起来。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么做。三四天过去了,他依然没有回家的念头,直到有一天路过家门见到亲人在为其举办葬礼,他仍然没有出面澄清,在外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一天雨夜,他散步至家门口看到室内暖暖的壁炉,想象着他要是在炉旁烤火取暖而不是在雨中受冻该有多好。这样想着,他就进去了,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这是一个有关出走后回归的故事。《纽约三部曲》正是对这个故事所要表达主题的彻底颠覆,三位主人公因为追踪他人的需要,也都离开了原来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都没能像威克菲尔德那样找到回去的路,只能沦落为无家可归的魂灵,在思想的废墟上飘荡,孤独地舔噬着身上的百孔千疮。
《瓦尔登》这部超验主义的名作在《锁着的房间》中屡次出现,梭罗的超验思想——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亦在小说中找到了一位践行者。范肖似在不折不扣地追随梭罗的步伐。他渴望静谧隔离的生活,远离喧嚣的人群,可他走向了极端,完全失去了控制自我的能力,远离尘世不为获得身心的宁静而仅是为了自我的放逐。奥斯特借助《瓦尔登》的血肉骨架,孕育出了这样一个变形的灵魂。马克思曾经作出一个有趣的断言:许多著名的历史故事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往往就成为喜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观点有助于阐述奥斯特对于经典的戏仿,即僵硬地或漫画似地再现以往的情节。穿插梭罗的超验思想是为了对其进行不伦不类的模仿,让原先一本正经的形象在笑声中被颠覆,让意义在打破的定式和反差的意象中逐渐显现出来。
穿插的这三个小故事给读者带来的决非是豁然开朗的阅读感受,也丝毫无益于读者对之后的情节发展的推测。相反,它们打破了原来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造成了阅读的断裂,重新设定了故事的走向,逼着读者去思考为什么原有的文学形象在新的上下文中改变了其原来的含义,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异化。这样的小说放弃时间、空间上的传承,“放弃传统的线性情节和人物发展……它们的故事是非线性的,往往不着边际,故事的指涉是不确定的,往往多元杂糅”(虞建华,2005:14)。
四、自我指涉的文字游戏
传统侦探小说的语言是达意的,意义是清晰的。飘忽不定、模糊混杂、似是而非的状态是侦探们决不能容忍的。他们用最精确的语言描述案发现场的环境以求在头脑里形成清醒的认识;他们迅速地分析处理证人的证词,找出他们话语中的漏洞以求案情的突破;他们善用语言,故意走漏风声,设置陷阱,逼凶手就范……总的来说,侦探小说是笃信语言能够表达客观现实,展现内心情态的。可是在《纽约三部曲》里语言所表示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多重的,可以作出不同阐释的。奥斯特甚至把用语言反映现实的困难作为了作品的一个讨论主题。小说作为语言游戏的场所,语言本身而不是事件成了小说的内容。
语言业已无法再现现实世界。在范肖的作品一举成名后,“我”答应出版社为范肖作传记,详述这位天才作家的一生。其实“我”心里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对范肖的描述有多细致,他的一生是道不明的,这样的传记无异于小说。哪怕是写自传,也不可能做到对本人生活的真实反映,仍然会有小说的印迹。这里奥斯特显然是继承了索绪尔的衣钵,认为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划不上等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永远无法统一。这样一来,矛头直指文学创作,因为语言是文学表达的直接载体。当文学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说不清时,当文学想表明一种意图,却又不可避免地使其含混时,当文学的语言不断地拆毁、破坏自身的意义,甚至破坏了所有语词所指的对象时,作家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困境,无法反映稳定的现实,无力揭示社会问题。语言已经成了写作的障碍,它再也无法传达人内在的心声和感觉。
语言表意功能的缺失给人物带来巨大的痛苦。《纽约三部曲》的人物群里有一位语言学家 (老斯缇尔曼),四位作家 (昆汀、布莱克、“我”、范肖),除了范肖缔造了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创作神话 (Neverland)之外,另外四位骨子里深受语言表意功能不完善的痛苦,只是这痛苦失却了本身性,奥斯特用荒唐的话语嘲弄式地把它们表现了出来。
老斯缇尔曼认为,伴随着人类堕落的还有人类的语言,为了领着人类重返伊甸园,他必须找到《圣经》中提到的和概念完全对等的原始语言,于是他开始了疯狂的语言实验,不惜把自己的儿子在暗房里一关九年,只为听到未经社会化的人所发出的原始声音;昆汀似已抛却了所有俗念,可是见到手捧他作品的读者时,忍不住还想听到溢美之词,一旦发现自己的作品只是被用来消磨时间,一个内心空空的隐士脸上竟也飘过了些许怅然若失,两种极不和谐的元素在同一个客体身上激撞出了最强的戏剧效果;布莱克也许是最执著于写作的人,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伏案疾书,可讽刺的是他什么也没写出来,只是麻木地记录他与布鲁互相凝望互相追踪的这些日子;“我”的创作同样也没有任何突破,最后不得不自欺欺人,沉浸在他人成就的辉煌里,幻想着已然逃出梦魇般的创作困境。
《纽约三部曲》对语言表意功能的颠覆,还体现在对文学经典的戏仿中。作品里除了这些苦闷的现代语言学家、作家之外还游浮着很多已载入文学史册的大家的幽灵 (霍桑、梅尔维尔、梭罗、爱伦·坡、约翰·弥尔顿、笛福、惠特曼、雷蒙德·钱德勒、路易斯·卡罗尔等)。可是经典中曾有的象征、寓言、微言大义以及种种说教式的庄重主题恰恰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奥斯特极尽戏谑、颠覆之能事,强烈地震荡了经典的地位、阐释权和文化等级,扰乱了经典对于思想的控制力。
众多大师均从高高的艺术祭坛上跌下来,与尘世中可笑的俗夫并无两异。《幽灵》中讲述了两位伟大作家梭罗和惠特曼的一次历史性会晤。来到惠特曼家的阁楼上,两位先人侃侃而谈各自的人生观,可就在这间充满着智慧火花碰撞的房子里摆放着满满一桶粪便,绅士梭罗瞥见之后兴致全无,看到这里,人们的阅读期待完全落空,一哄而笑随即填补了巨大的空白。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当把观察者的注意力引向一种普通人的弱点上面时,客体的尊严必在其心目中降低,“被奉若神明的圣人结果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弗洛伊德,1989:182)。
福柯已经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奥斯特笔下的世界是个神圣崩溃、权威过时的时代。所有的大词都如同空洞无物的符号躯壳丧失了真正的感召力。人物或是故事表象背后不再隐藏深层的含义,不再需要神话分析、原型分析或是象征体系的介入。
种种戏谑、颠覆层出不穷,每每收获了不少喜剧性效果。然而,这些喜剧性效果仅仅是文本内部的区域性游戏,片光零羽,语言在此中欢愉自适——这些临时性的喜剧成分不存在抵抗整体性压抑的悲剧力量。它制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旋生旋灭的笑声。因为从小说中人物的角度出发,他们被剥夺了作者和读者所享有的特权,没有全知全能的视野。他们既无辜也无知,看不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侦探们是幸运的,他们有语言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然而,《纽约三部曲》的主人公们体验到的不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他们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最后迷失在了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的后现代语言世界里。
五、结语
三个故事都用最典型的侦探小说中的场景拉开序幕,然后再一步步地挫败读者的阅读期待。会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吗?不,黑白不再分明,大家都活在中间的灰化地带,混沌一片。会有伤害与被伤害吗?不,故事压根与犯罪无关,每个人物都很可怜,灵魂裸露成为他们耗尽之后的共同写照。会有豁然开朗、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吗?不,故事不再向前进展,原有的认识体系和时空观念业已崩塌,理性分析已不能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无力把人们从悲剧性的深渊和存在的恐怖处境中解放出来。会从文字中找到突破重围的办法吗?不,语言和传统的文学经典不再提供任何的启迪和精神关照,从文字中再也找不到某种形而上的真谛,再也感受不到任何升华净化的浪漫色彩。
通过对传统侦探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语言上的颠覆,奥斯特想要给读者展现的是当代人虚浮、表层、零碎、绝望、非我的生存状态。蚌病成珠般深藏的是主人公隐而不去的伤痛。其实,一直在苦苦追寻的又何止故事里的主人公,作者奥斯特本人借助这三个有关追寻与迷失的故事,也在为后现代人叩问个体的有限生命要如何寻得自身生存意义的语境?人类要如何才能走出思想荒原的平面,获得救赎?一味守在固有的等级秩序中亦无可能,新的意义又将在何时以何种面目出现呢?
[1]Auster,P.The N ew York Trilogy[M].New York:Penguin,1990.
[2]Beckett,S.W aiting forGodot[M].London:Faber and Faber,1970.
[3]M cCaffery,L.&L.Gregory.Interview[A].In P.Auster(ed.)The Art of Hunger:Essays,Prefaces,In terview s&The Red N otebook[C].New York:Penguin,1993.269-312.
[4]M cHale,B.Postm odernist Fiction[M].London:M ethuen,1987.
[5]M illard,K.Con tem porary Am erican Fi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Russell,A.DeconstructingThe N ew York Trilogy:Pau lAuster’sAnti-detective Fiction[J].Critique:Stud ies in Con tem porary Fiction,1990,(2):71-84.
[7]Tani,S.The Doom ed D etective[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University Press,1984.
[8]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林玉珍,胡全生.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通俗性[J].当代外国文学,2006,(3):51-58.
[10]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张增武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1]虞建华.后现代环境与巴塞尔姆的小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PaulAuster is a rising star in contemporary Am erican literaryworld.This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anti-detective narrative in his postmodern fictionN ew York Trilogy.It exam ines the fiction’s subversion of c lassicaldetective stories in itsnarrative focus,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language.By m eansof subversion,Auster exp resseshis deep concern abouthum an nature,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living p redicam entsofmodernm en.
N ew York Trilogy;anti-detective narrative;subversion
I106.4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665x(2010)06-0056-06
2010-05-21
刘启君 (1983-),女,博士生,研究方向:当代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