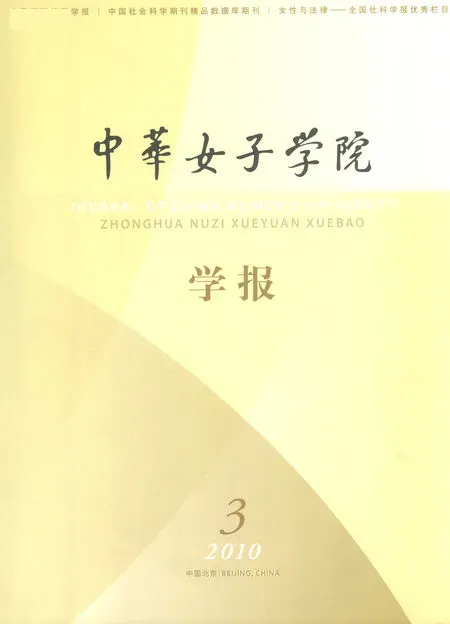《耻》:一种关于“性别困惑”的伦理叙事
2010-02-17王进
王 进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作为当代英语世界之中颇具争议的散居作家,现居澳大利亚的南非白人小说家库切(J.M.Coetzee)广受赞誉并获得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南非大陆却受到后殖民批评界的猛烈批判。在二度蝉联英国布克文学奖的代表小说《耻》(Disgrace)中,库切通过男主人公卢里教授的叙述视角,逐步展现出南非大陆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各种历史图景。国内外批评界对库切小说的评论过分集中于非洲形象的正义性问题,将研究视角过多聚焦在对诸如种族、历史与文化政治等社会问题上,遮蔽了该小说本身的性别批评空间。某些国内批评家(比如王安忆等人)虽然敏感地捕捉到库切小说在性别方面的立场问题,但是却没有关注到在性别书写之后的后殖民批评空间。诚如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困惑》中指出,“对种族之间性别规范的性别化过程需要透过多重棱镜来同时阅读”。[1](P33)因此,针对不同文化立场的阐释盲点,本文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从性别困惑与身份焦虑两个叙述层次,以性别批评的伦理视角重新解读作为“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的《耻》,分析作品中历史书写与男性权力的各种伦理悖论,进而在总结库切文学经验的同时批判其作品中的父权意识与性别政治。
一、性别困惑:男权意识的主体建构
《耻》的叙事结构包括三个部分的情节内容:卢里教授在开普技术大学的种种风流韵事乃至性丑闻,女儿露茜在边缘乡村遭受当地黑人抢劫和强奸的不幸遭遇,他和女儿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和结果。就小说本身的隐喻结构来说,《耻》的多层次含义既包括卢里作为大学教授引诱学生梅拉尼的“道德之耻”,也背负有女儿露茜被黑人强奸的“个人之耻”,同时暗含着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在非洲解放独立之后遭受欺辱的“历史之耻”。[2]在这部小说的叙事线索中,有关性的任何话题都是与种族问题紧密相连且相互渗透,因此种族化的性别问题大致构成了种族身份的主体维度,而性别化的种族问题则基本成为性别困惑的社会维度。在此之中,卢里这位男权主体的性别困惑作为重要的叙事线条之一,不但横向串联起种族问题的多线索叙事结构,而且纵向横亘着性别问题的多层次隐喻机制。
按照卢里本人的叙述,他的童年生活是在一个尽是女性角色的白人富裕家庭中度过,随着母亲、姑妈、姐妹从他的生活中淡出,她们相继被情人、妻子、一个女儿所代替。在女人堆里长大的特殊经历,使他一直以来清楚地意识到自身作为男性主体的各种性别权力,甚至使他成为善于玩弄女人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时常陶醉于自身的男性特征,为自己高挑的身材、匀称的骨架、橄榄色的皮肤以及飘垂的长发而洋洋得意;他甚至异常满足于自身的男性气质,对自己总能对女人产生吸引力而沾沾自喜。然而,当他逐渐步入老年,他才明显感觉到日渐衰老的同时吸引力也逐渐褪去,而他却无法接受前后的明显落差,实际上,卢里的男性能力与他的社会政治地位同时形成某种特殊的隐喻关系。经过所谓的院系专业的合理化调整过程,他的教学和学术工作累累遭遇挫折,因此他总是自我感觉“就像后宗教时代中的一群教士”。[2](P5)对于卢里来说,男性性征的日渐衰老让他深刻体会到性别欲望的难以启齿,而社会地位的逐渐没落则让他深切感受到男性主体的权力焦虑。
英国学者费鲁贝曾指出,“男性气质应该被解读为某种特殊效果,即符号意指的各种权力关系,特别是叙事的组织方式”,因此男性气质由此成为协调自我和主体身份的重要场地。[3](P8-12)就男性气质的叙事期待而言,卢里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形象,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继续享受男性身体的生理优势,而在学术事业中他也未能满足事业成功的性别期待。然而,就是在对男性主体的各种性别困惑中,也是在对所谓男性气质的各种阉割焦虑中,他偏执的转向对父权文化的性别意识来重新建构起自身男性气质的既定效果,也就自然选择了通过对女性他者的身体欲望来不断验证自身作为男性主体的性别权力。于是,“他开始急匆匆地同一个又一个女人乱搞。他和同事的妻子有染,去河边酒店或意大利俱乐部与游客交欢,他同妓女睡觉。”[2](P8)诚如巴特勒挑明,“性别是对身体的持续形式化过程,是在高度僵化的调节框架中的一整套行为动作,长久凝结的它能够产生某种自然种类的外形”。[1]由此看来,卢里本人真正在意的或许并不是男性能力的意指实质,而是它作为父权符号的意义延异链,也正是通过对女性身体的不断占有过程,他才能最终完成自身男性气质的权力验证,从而暂时消解自身作为男性主体的性别困惑。因此,在这些或许是“猎奇交欢”也或许是“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卢里陶醉于这种畸形的男性权力和父权意识,他甚至有些许沾沾自喜,“对自己这样年纪五十二岁、结过婚又离了婚的男人来说,性需求的问题可算是解决的相当不错了。”[2](P1)
然而,诚如福柯强调,“哪里有欲望,权力关系早已存在”。[4]或许正是源自卢里自己承认的这种“欲望的权力问题”,他不再满足与妓女索拉娅在每周四下午的短暂交欢,而企图越界进入她的整个私人生活;同样是出于这样的权力欲望,他在失去索拉娅之后继而转向作为弱势群体的女学生梅拉尼,不断引诱其与自己行苟且之事,借助她的弱势身体来找寻昔日雄风,从而延续对男性气质的建构和对男性权力的验证过程。换句话说,他对学生梅拉尼的这种占有过程,与其说是在生理上不断释放他过于旺盛的性别欲望,还不如说是在心理上暂时缓解他自身阉割情节的权力焦虑。正是出于这种对男性权力的验证目的,尽管卢里已经深陷性丑闻的现实困境,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有违正常、有违自然。或许是信服拜伦的性别观念,或者是崇拜劳伦斯的男性意识,曾经作为文学教授的卢里欣然接受上帝为人类安排的原罪惩罚,他拒绝学校方面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与此同时,既是出于对男性主体的性别困惑,也是源自权力欲望的阉割焦虑,他迫切地踏上前往边远乡村女儿那里的自我放逐之行,同时开启自身对男性气质和性别权力的意识恢复之旅。
二、身份焦虑:父权文化的另类表述
为了逃避由性丑闻对他将会造成的各种权力焦虑,卢里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女儿露茜的安全港湾,以图延续和巩固父亲角色的男性权力。以父权文化作为最后的权力屏障,不良的情欲冲动却仍然充斥着他对自身放逐之旅的整个叙述过程。对于索拉娅、系秘书、学生梅拉尼的那些尴尬记忆虽然尚未消失殆尽,卢里又继续不断地寻找新的欲望目标。对于乡间放学的小学生、甚至是面对自己的女儿,他也总是怦然心动而春心荡漾,就连“脑袋似乎就垛在肩膀上”的贝芙·肖也不能妨碍这种性别欲望的生成过程和男性气质的施行过程。卢里甚至自我解嘲地认为,是她们不断造就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然而露茜的各种嘲弄和反驳话语则让他体会到“做父亲是件相当抽象的事”。[2](P78)如果说我们的阅读只是停留在卢里的性别经验和父权意识,那么我们则无疑轻视了库切小说的社会介入意识。随着露茜的强奸事件发生,传统的性别问题经过种族意识的色彩渲染变得更加复杂却越显深刻:卢里作为欲望主体的性别困惑逐渐过渡到对各种文化权力的身份焦虑,而露茜作为女性他者的主体意识直接通向南非大陆在后殖民时代的各种现实问题。种族问题的中途入场,使得卢里不再满足于身体情欲的恢复过程而积极转向自身作为父权主体的权力建构,但是随着斯皮瓦克所谓的露茜的各种“反聚焦叙述”,他在这种由身体向身份的权力转向过程不断遭遇挫折而最终幻灭在种族问题的文化沟壑之中。
对于身体与身份的权力边界,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指出“身体存在于社会世界之内,而社会世界同样也存在于身体之中。”[5](P152)因此,作为主体实质的身体意义指涉到文化形式的身份机制,而作为权力隐喻的身份意识同样存在于形而下的身体空间。然而,库切并没有简单复制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关于欧洲优势文化单向征服非洲被动文化的种族志观念。恰恰相反的是,在库切小说的后殖民世界中,曾经作为黑人奴隶的佩特鲁斯俨然成为“自由帮佣工”和“农场合伙人”;曾经作为白人老爷的卢里却不得不“给佩特鲁斯搭帮手”,甚至于女儿露茜竟然被三个黑人强奸和抢劫。虽然卢里当初还自我解嘲地声称自己“喜欢带点历史味的刺激”,但是黑人的暴力事件不仅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男性身体的社会意义,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文化身份的权力焦虑。卢里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弱势,然而他对自己的白人身份却是明显充满尴尬和无奈,“他会说意大利语,他会说西班牙语,可无论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到了非洲的这个地方,哪一个也救不了他”;[2](P107)卢里也从未检讨自身过剩的身份欲望,他无疑对自己的父亲地位寄托了太多的权力想象,但是当女儿露茜再三拒绝他的关心和保护,他则不无焦虑地感叹,“这不再是父亲的小女儿,再也不是了。”
经过与露茜的多次争执,卢里发现女儿这里已经不再是自身性别困惑和男性权力的避难天堂,而似乎业已成为身体欲望和种族身份的人间炼狱。针对女儿露茜被黑人强暴的暴力事件,卢里认为这是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机缘,因此他要么积极地报警追拿涉案人员,要么就是被动地选择逃避而回到故乡欧洲。露茜本人则不断提醒他要面对当下社会的现实状况,“这是在乡下,这是在非洲”。最终卢里才颇为意外地发现,当地的黑人警察对此类事件是无可奈何,而自己作为已经失势的白人阶层确是无能为力,因此他不无伤心地断定,这次的黑人强暴事件是露茜的秘密,也是他的耻辱。或许正如范农指出,对于曾经是被殖民者的当地黑人来说,对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的那种象征性的暴力征服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是“某种清洗的力量”,“它将当地人从弱势焦虑、绝望和无助之中解脱出来;它让其变得无畏而恢复自尊”,因此,“他们疯狂杀戮的冲动是当地人集体无意识的特殊表达”。正是出于这样的民族焦虑心理,当作为强奸犯之一的小黑人男孩偷窥露茜洗澡被发现之后,他不断威胁要杀掉卢里和露茜,甚至在后者宽容地帮他擦洗伤口的时候也仍然不停诅咒“我们要把你们全杀掉”。卢里就此已经明白黑人暴力事件的这种象征性意义,他不停地质疑女儿露茜的缄默态度,“你以为忍受现在的苦难就能偿清过去的罪恶?”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复仇是一团烈火,吞噬得越多,欲望越强烈”。[2](P126)
如果说当地黑人对露茜和白人妇女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是对前殖民者象征性的征服方式,最终意味着对民族信心和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过程,那么对于卢里这类白人男性来说,对露茜她们的保护义务则意味着男性权力的现实建构和父权意识的历史回复,无疑也是象征着种族意识和文化身份的男权书写过程。然而,当女儿露茜决定生下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混血孩子,甚至答应给佩特鲁斯做第三任小老婆以求保留自己的容身之处,作为父亲的卢里充满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失落感:他既无法接受自己男性气质和父权意识的双重失落,同时也无奈地感叹于种族权力的历史落差和白人文化的身份焦虑。甚至于当女儿露茜直截了当地宣称“在我的生活中,做决定的人只能是我”,卢里这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种男性身体和父权身份同时被“阉割”的历史痛楚,他才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犹如狗一样的卑贱生活:“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卢里这时才真正明白过来,自己作为后殖民非洲“历史边缘的孤独身影”,“历史在这里起着更大的作用”。[2](P68)出于这种“历史边缘”的切身体验,他才最终决定为性丑闻事件向学生梅拉尼的父母登门道歉,同时也正是源自这种对“孤独身影”的身份焦虑,他直至万念俱灰也始终无法接受女儿露茜本人所接受的那种父权意识和种族文化的双重历史耻辱。
三、伦理叙事:文学经验的性别边界
无论是卢里的关于性别困惑的主导叙事,还是露茜坚持的种族身份的“反聚焦叙述”,库切在此之中均为读者预留下很大的伦理空间来深入思考文学经验的性别边界。比如说在梅拉尼的种族身份问题上,如果她是白人学生,卢里对她的引诱是否就只是某种纯粹的性别丑闻,如果她是黑人学生,那么卢里对她的侵犯是否就象征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征服和权力验证过程;另一方面,露茜被黑人强暴而怀有的混血儿是否就意味着非洲黑人对白人殖民者的历史性报复,抑或是后者对前者的某种文化补偿过程而似乎是象征着欧洲殖民文化与非洲本土文化的最终融合?由此看来,卢里本人的性别困惑或许只是权力焦虑的假导火索,而种族身份的历史问题才是伦理叙事的真正悖论。从文学经验的性别视角来看,在后殖民非洲的历史语境中,卢里这种关于“性别困惑”的伦理叙事显然是包括男性权力的阉割焦虑、父权意识的主体危机以及种族身份的历史耻辱,但是它最终指向的却是种族与性别的伦理悖论。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曾指出,“话语层面的殖民主体的构建,以及殖民权力通过话语的行使,要求以种族与性别差异的形式得以表达。”[6]身体既是欲望和主体的建构基点,也是性别和种族的差异形式;而身份则既是作为权力意识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性别和种族的话语平台。因此,身体的各种性别困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指向权力意识的话语形式,而身份的种族意识在同等程度上也激化了身体的各种焦虑。在身体困惑和身份焦虑的相互交叉之中,始终无法回避的则是性别与身份的权力合谋与仇恨和宽容的伦理悖论。卢里只有在经历了女儿露茜的暴力事件之后,才幡然悔悟地去学生梅拉尼家里登门致歉并接受上帝的惩罚;而又有谁该为自己女儿的悲惨命运来负责任呢?难道嫁给黑人帮佣佩特鲁斯做小老婆就意味着仇恨的最终消解?有论者指出露茜决定生下混血儿是她主动选择与非洲大地融为一体,但是库切本人则激烈批判这种关于种族融合的廉价的乌托邦神话。对于库切来说,这样的伦理悖论在权力失衡的后殖民非洲只能最终通向身份意识的对立和融合理想的幻灭。或许在他眼中,卢里和女儿露茜就好比佩特鲁斯用来庆典的两头羊,虽然曾经似乎意识到“它们的命运对他来说成了十分重要的事情”,虽然也曾有过将它们买回来放生的感性冲动,但是理性的绝望仍然导致他们对动物生命的根本漠视和对人性尊严的彻底放弃。
正如诺贝尔获奖词所说明,库切作为“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的文学叙述中,性别或者说是身体总是陷落“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过程”,而种族或者说是身份也就自然成为“一种主动干预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有关身体与身份的伦理悖论在库切的小说世界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南非大陆在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历史困境。如果诚如非洲批评家阿契贝所言,“无法设想非洲人能够回避灵魂之中的痛楚,也不能就此遗忘那些毁誉和自我毁誉的时代焦虑而重新获得自我信念”,那么库切对此提出的问题就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后殖民时代的非洲黑人就要以同样暴力的手段才能够恢复或者重新建构相对于白人殖民者的种族身份和民族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感性立场的伦理叙事,库切在文学批评界似乎经常是“陷落于一个艰难的境地,在旧帝国眼中,他是穿着诗人外袍的政府公敌;而对于众多黑人读者来说,他的写作又过于‘白色’”。[7]然而,库切本人却坚信“肉身也许是我们彼此归属于对方的基本存在方式,但是它也是我们彼此归属于独特自己的存在方式”。[8]因此,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白人小说家,他不相信那些具体而又僵化的道德界限,他宁愿亲力追随那种感性身体的历史意识,而不去随便盲从抽象身份的任何理性信念。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对感性身体与理性身份的性别书写,或者说是关于性别与种族的这种伦理叙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库切小说的专属品牌。
[1]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London:Routledge,1990.
[2]J·M·库切.耻[M].张冲 ,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3]Alice Ferrebe.Masculinity in Male-Authored Fiction 1950-2000[M].New Y ork:Palgrave,2005.
[4]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One:An Introduction[M].Robert Hurley(tran.).Harmondsworth:Penguin,1981.
[5]Pierre Bourdieu.Pascalian Meditations[M].Richard Nice(trans.).Cambridge:Polity,2000.
[6]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C].London&New Y ork:Routledge,1994.
[7]Harald Leusmann.J.M.Coetzee’s Cultural Critique[J].World Literature T oday,2004,(03).
[8]特里·伊格尔顿.批评的道德之维[A].立场[C].余虹,等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