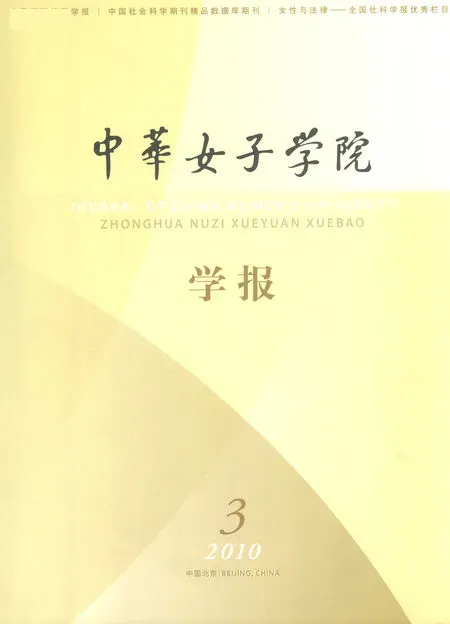文化镜像中女性人格的差异:以儒家文化与游民文化为例
2010-02-17于光君
于光君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与法学院 女性学系,北京 100101)
文化镜像中女性人格的差异:以儒家文化与游民文化为例
于光君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与法学院 女性学系,北京 100101)
在儒家文化中,尽管是男性本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女性仍然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的“人”。在作为对儒家文化反动的游民文化中,女性的人格、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沉沦为游民们仇视的对象,甚至物化为牛羊一类可以食用的动物,可以随便杀戮而不承担任何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儒家文化;游民文化;女性人格
女性是社会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作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是轻视女性的,强调“男主女从”、“男尊女卑”。但在与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完全相悖的游民文化中,女性的人格、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沦落为男性仇视的对象。游民文化具有强烈的仇女情节,把女性当作可以随便杀戮的对象,甚至把女性物化为像牛羊一样可以食用的动物。从显性的主流社会的儒家文化到隐性社会的游民文化,昭示的是女性人格和地位的沉沦。
一、儒家文化中的女性观
(一)儒家文化中“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女性观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说,自从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以后,女性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家庭生活中,都处于从属性的地位。因此,马克思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1](P520)
儒家文化从思想源头来讲,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的文王、武王和周公。西周初期,建立了以男性为本位的宗法制、分封制等一系列的等级制度,明确了性别分工,在国与家之间谈“公”“私”,在家的范围谈“内”“外”,公与外是男性的领域,内与私是妇女的空间。周礼的制定标志着父权制度的正式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国一进入父权制社会时就牢牢地扎下了根,它与宗法制紧密结合。儒家文化恰恰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映。“宗法”,就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是指“父家长利用其宗子地位,集父(夫)权、族权、神权、政权于一身,对本族成员乃至其他民众进行剥削和统治。”[2](P8)因此,与宗法制有着紧密联系的儒家文化其实质是男性本位文化,是为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男性服务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认为儒家文化属于男性化的,倾向于操纵和管理的文化。[3](P35)男性本位文化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逐渐沉淀为一种心理定势,使女性不自觉地被纳入“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男性价值体系中。儒家文化把男尊女卑视为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P154)儒家文化规定了女子的“三从之道”,“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於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5](P36)这里所讲的“三从之道”是封建道德“三从四德”的发端。儒家极力宣扬女性的从属地位,“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6](P39)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道德意识。
孔子把女子和小人并列,表现了对妇女的歧视和鄙视,在《论语》中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样的论述。[7](P35)当然此处的“小人”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朱熹《四书集注》即云:“此小人,亦谓仆吏下人也。”[8](P58)所谓“仆吏下人”,往往指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卑贱之人。尽管有学者认为孔子这句话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心理特征,对他们亲密,他们有时就过分随便,稍一疏远,就埋怨不已,这句话并不含褒贬含义。但这种貌似公允的说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男子也有同样的心理特征。这种对女性的轻视可以说对人们的认识影响深远。古代社会,在止雨的祈祷仪式上,即使贵为千石官吏的妻子也要回避。汉代儒学在理论上吸收了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把男女两性贴上阴阳的标签。男子为阳,女子为阴,女子被认为是不吉祥的象征,女性会影响人们实现好的结果。《春秋繁露》卷十六中有这样的记述:“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止雨之礼,废阴起阳,书十七县、八十离乡,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女子不得至市,市无诣井,盖之,勿令泄,鼓 ,用牲于社。”[9](P141)
儒家文化对女性既轻视、贬抑,又严格约束和禁锢。儒家历来宣扬克制私欲,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10](P56),荀子说:“君子守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11](《乐论·第二十》)及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更是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对女性的禁锢程度加深,由具体层面的规范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理”的高度,将禁欲主义发展到极致。性欲,尤其是女性的性欲被理学家们视为罪恶的化身,性禁忌观念渗透到宗法制社会人们的头脑中。为了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和对女性的绝对占有,儒家文化一直强调女性的贞操意识,即婚前贞洁、婚后忠诚。为此,儒家还制定了一整套礼教纲常对女性进行思想控制,如,“士无邪行,女无淫事”[12](P8),“女德有常,不谕贞信。”[13](P11)宗法制大家庭为了防止女性“失贞”,将他们幽禁在闺阁中,并教导他们“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内庭。”[14](P1)
(二)儒家文化中女性人格的独立性
儒家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好像下对上只能绝对地服从,其实从它的本意上来讲不是这样的。上下、长幼、尊卑完全是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单向的。《礼记》里曾经讲到,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四个方面:人情、人义、利、患。关于人义的解释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15](P43)如果君不仁怎么办呀?臣是可以不忠的。有人问孟子,周文王和武王作为臣子,怎么能够去杀商纣王呢?孟子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臣杀君这个事情,而只听说过诛一独夫而已。商纣王已经是一名独夫民贼了。到了荀子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的原则,不应该盲目地从君,应该按照道来做事情,所以,才有汤把夏桀推翻了。按照孟子和荀子对君臣关系理解的逻辑,可以说,作为人义内容之一的夫妇关系也不是绝对地、无条件地妇从夫。我们可以仿照上面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夫不义怎么办?答案应该是妇可以不听了。妇也应该是从道不从夫的。“妇听”的前提是“夫义”。
所以,在儒家文化中,尽管是男性本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女性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女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人格独立性,女性仍然是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的“人”。在家庭中,妻子是与丈夫对等的人,妻子和丈夫的对等性特别体现在对祖先的祭祀之中,宗子、宗妇共同承担着延续香火,以及祭祀祖先的责任。丈夫和妻子分别给予庄严的受尊敬的角色,无法摆脱地连在一起,并期待彼此在合作与和谐的基础上相互作用和影响。男女有着各自不同的互补功能,女性的位置和角色并非不体面。
那么,作为对儒家文化的反动,与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相悖的游民文化是否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呢?
二、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及女性观
本文旨在通过主流社会儒家文化中的家庭观和女性观来反观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和女性观。在讨论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和妇女观之前,必须对游民文化有一个基本的界定。
(一)游民及游民文化
中国自古是组织类型的社会,统治者力图通过宗法家族把社会成员控制在有序的网络之中。然而由于不可控制的自然灾害、官僚体制的腐败以及“经济发展的迟滞和社会结构的僵化及其相应的文化不能适应人口的激增”[16](P28)等因素,会引起大的社会变动,产生大量的脱离主流社会秩序——宗法家族秩序的人口,这就是游民。游民不同于流民,流民未必“脱序”,但是流民容易“脱序”而成为游民。据完延绍元的预测,汤武革命、平王东迁就可能造成了不少游民。真正有文字记载的“游民”最早出现在《礼记》中,《管子》中也有“游食者”的记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了游民就会有反映他们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游民意识。相对而言,游民文化出现得较晚。
宋代以后,由于游民群体和游民知识分子的结合,游民文化形成。游民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游民生活的作品。“游民文化集中表现在游民们独特的思想意识之中,这种意识主要从游民知识分子所参与创作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特别是江湖艺人所创作的话本小说、讲史小说、某些通俗戏曲和曲艺作品成为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载体。如《水浒传》及其相关的戏曲、《三国志演义》、‘说唐’小说系列等等。这些作品虽然最后多是由文士写定,其中不免要有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的渗透,但是其主导意识是属于游民的。”[16](P19-20)“脱序”是被迫的,游民们为了生存,就要组织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隐性社会,同时,形成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游民意识和游民文化。
(二)游民文化中扭曲的家庭观念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宗法社会,形式上是以“己”为中心,实质上是无“己”,“己”消融在家庭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又依附于宗法共同体,而这种宗法共同体又是与专制国家同构的。作为社会个体的“己”,就生活在这种同心圆式的差等有序的宗法网络之中。儒家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世代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农民对于儒家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很重视家庭生活,把家庭看成是自己的“安乐窝”,对家族有着强烈的依赖性。统治者也极力培养农民对自己家庭的热爱之情,这既顺应了农民的要求,又便于对农民进行统治,符合统治者的实际利益。从封建统治者的实际利益来说,他们最重视的伦理道德是臣民对皇帝的“忠”。然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却强调要“以孝治天下”,把“孝”这种调整家庭内部尊幼关系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国家道德的层面,并且用法律的手段强化和保障这种伦理道德的践行,使得伦理道德法律化,因为在主流社会中臣民们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孝”能够被臣民们所普遍认同,并且“孝”的覆盖面比“忠”的覆盖面更大。按照正常的逻辑,对自己父母等长辈“孝”的人对皇帝一定“忠”,家齐则国治。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力宣扬孝道,重视发挥宗法家庭的作用。家庭是宗法社会束缚农民最直接、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一根绳索,从家庭中“脱序”出来才是真正彻底地脱离了宗法社会网络,成为一个彻底的、真正的游民。
在游民文化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中是排斥“忠”、“孝”观念的。作为一个伦理范畴,“忠”的本意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先秦时不完全是指臣民“事上”君王的观念,有时也用“忠”去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战国之后,它完全变成了臣民“事上”君王的道德观念。由于已经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失去了“上”,无“上”可“事”,所以是不能接受“忠”这种道德观念的。“脱序”的游民靠结拜这种形式组织起来以增强自身的力量来对抗主流社会,博取生存的空间。结拜是模仿家族组织的形式,彼此之间称兄道弟,但家族中藉以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孝悌”观念在游民群体中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游民由于脱离宗法网络而已经没有了家庭的观念,他们靠“义”或“义气”把这些有着相同命运的异姓兄弟团结起来。游民文化中的“义”不同于儒家文化所讲的“义”,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儒家把“义”看成一种做人的义务与原则,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说。与儒家相反,墨家则把“义”与“利”打成一片,墨子在《贵义》篇中明确地指出“义可以利人”。主流社会的士大夫们讲的“义”多属于儒家,指本着儒家观念应该尽的义务。而游民文化中的“义”则接近墨家的思想,把“义”看作“利”,是赤裸裸的个人利益,而且也是一种追求回报的投资。“义”的本质就是游民们求生存的道德,对于一无所有的游民来说,他们离不开实际利益。“义”作为联结游民群体的道德纽带也必然会产生出超越性的一面,表现出对有着共同命运者的关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
游民文化中“义”的道德观念的产生和发挥作用是以消解了主流社会中的家庭为前提的,“义”是没有家庭拖累的“没家没业”的一群“脱序”男性群体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的视野中没有家庭宗法共同体的位置,当然也就没有了女性的位置。因此相对于儒家文化而言,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念是扭曲的,游民们把家庭视为在对抗主流社会的隐性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累赘。只有摆脱家庭的束缚,他们才能彻底摆脱宗法社会束缚他们的最后一根绳索,才可以毫无顾忌地站在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无牵无挂地干他们的大事业。
1973年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这个唱本所讲述的故事残忍而古怪,大悖于主流社会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起事之初,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为了杜绝自己的“回心”,关羽和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少几十口。张飞手软放走了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胡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认父,但是关羽却不认。关索翻脸威胁父亲关羽,如果不认他,他就要投奔曹操,带兵捉拿父亲关羽等五虎上将。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以绝“回心”的想法和做法,反映了“脱序”后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心态。
《水浒传》中的宋江仗义葬了阎婆惜的父亲后,为了报答宋江,也为了有个依靠,阎婆将才貌俱佳的女儿给了宋江。宋江依允,讨了一所楼房,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俩个,自己和他们住在一起。起初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后来渐渐疏远了阎婆惜。阎婆惜与小张三勾搭上后,宋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却没有恼羞成怒地找小张三和阎婆惜算账,或者是设计捉奸,扭送官府羞辱二人,而是以“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你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17](P215)来解脱自己,心态很是平和。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为主流社会中有着正常家庭生活的男人所不能理解,从中折射出一种扭曲的家庭观和女性观。
宋江为人不但仗义疏财,而且驰名大孝,为自己在江湖上赢得了良好声誉。宋江真是孝道,上了梁山,即使被朝廷通缉,还敢不顾身家性命,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也把家庭视为自己做大事业的“累赘”,在法律上断绝了父子关系,堪称忤逆。当然,宋江并没有像关羽和张飞那样采用极端的手段割除“累赘”,而是通过官方认可的方式割断了自己与家庭的关系。《水浒传》中宋太公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宋江怒杀阎婆惜后,阎婆以给女儿婆惜买棺材为借口骗宋江到县衙门口,准备将宋江扭送官府,唐牛儿替宋江解了围,使得宋江得以逃脱。知县只得派差役去宋江的老家宋家村“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当官府的差役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宋太公告诉差役,“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说他不从。因此,老汉数年前,本县官长处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汉户内人数。他自在县里居住,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亩过活。他与老汉水米无交,并无干涉。老汉也怕他做出事来,连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里告了,执凭文帖,在此存照。”[17](P231)在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才不取的时代,为官容易,做吏最难。宋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做押司的风险,恐怕一旦不慎犯事后连累父母及家庭,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官府给了执凭公文存照。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预先开的门路。宋江不想连累家庭,更不想让家庭连累自己。
同样是梁山首领的晁盖,为了成就大事,不受家庭妻儿拖累,以至于终身未娶。根据《郓城县志》记载,晁盖死后,他的族人没有让他葬在家族的坟茔,家族的族谱上也没有他的位置。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晁盖与家族的反常关系,也反映了他的作为和“事业”不能被受主流文化深刻影响的家族所认可和接受。
男子气,作为游民所必具的资格,是某种超越和排斥日常生活的东西,是通过逃离家庭这个女性世界来取得的。
(三)游民文化中的“仇女情节”
总的来说,游民文化具有明显的“仇女情结”。“脱序”的游民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在隐性社会中生活的巨大风险使得他们泯灭了主流社会中惯有的通过女人传宗接代的想法,他们对于构成家庭另一半的女人的态度易于在艳羡与抵制之间震荡。由于游民文化中扭曲的家庭观念,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女人,在游民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游民的世界完全是个男性化的世界,游民文化是一种极度男性主义的文化,女性已经沉沦为男性对立面的地位,女性成为游民们仇视的对象,可以随便杀戮而不承担任何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就是那些落草为寇的游民,仍然是视家庭为累赘,极度蔑视女人,哪怕游民的首领是女性的也多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在社会性别上已经完全男性化,完全没有女人对家庭的眷恋。
《水浒传》《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等这些承载着游民文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明显的憎女倾向。《水浒传》以及传世的几出以“水浒”为题材的杂剧中的女性多是负面形象。《水浒传》中描写了三十几个女性,大多数被贴上道德的标签,对于那些具有鲜明的女人特征被主流社会追求的女性形象都被贬斥为水性杨花的淫妇,而且被梁山好汉们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
这些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年轻女性几乎都不满意他们的合法丈夫,追求婚外的男性。香港学者刘靖之在《元人水浒杂剧研究》中指出,传世的水浒题材的杂剧有十出,而其中就有五种写了“淫妇”。《双献功》《燕青博鱼》《还牢末》《三虎下山》和《闹铜台》等五剧里的不正经勾当故事十分相似,叙述大夫人或二夫人与“衙内”式的人物或与自己的管家私通,并商议如何置妇人的丈夫于死地,以便双双逍遥快乐。他们虽然成功地诬告了丈夫入狱,结果都被梁山好汉救上梁山,“奸夫淫妇”被残忍杀死。凡是有“不正经勾当”的女人被梁山好汉抓到手,下场都是极为悲惨的。杀死的“坏女人”越多,证明他们的社会正义感越强。但以如此残忍的方法来处死他们,反映出梁山好汉极端憎恨“坏女人”的态度。可是,正儿八经的潘巧云、李巧奴等人也被残酷地杀死。
李逵把与人私通的狄太公的唯一的女儿残酷地杀死,这种乱杀无辜的现象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是不能单纯用李逵缺少人性来解释的。海外学者夏志清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说,梁山好汉在潜意识上以女人为他们的死敌,因为女人令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禁欲主义受到了威胁。故此,他们惩罚女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女人。其实,游民并非天生的禁欲主义者,女人的柔情和诱惑往往是他们最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脱序”后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压制了他们的欲望,因此,他们敌视有诱惑力的女性。另外,游民的“尚武”精神和传统的养生观念也强化了他们的禁欲主义思想。习武是在与主流社会对抗中提高生存能力的一种手段,习武生活对女色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传统养生思想认为过多地接近女性是会损耗身体的,所以,他们对女性的恐惧较一般人更严重,对女性的抵制再加上恐惧便会发展到敌视。《水浒传》中的好汉都是习武的,对女性的恐惧使他们由于冷落了女性而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例如,卢俊义有年轻的妻子贾氏,但他“平昔只顾打杀气力,不亲女色”;宋江纳阎婆惜为“外室”,但并“不以这女色为念”;晁盖更加极端,“最好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有些女性的被杀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成为累赘。游民经常处于“游”的状态,而且经常身处险境。在生死攸关的场合,为了保存自己,他们要摆脱女人,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女人。例如,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实际上是游民首领)不许与之无关的女人进入他的营地,当遇到被包围或其他困难时,先杀掉老营妇幼以保存自己。有个游民首领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其妻子是小脚,跟不上队伍,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她一枪打死了。
以上所说的这些被诛杀的女性,不管是被贴上道德标签而被诛杀,或是作为累赘物而被诛杀,还是被无辜杀死,最起码都是作为人而被杀。游民文化中憎女情节的极端表现是把女性当牛羊一类的食品杀掉供人食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刘备兵败下邳后,逃难山中,路上绝粮,猎户刘安杀掉他的妻子,用妻子的肉款待刘备。在游民文化中,这个情节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故事。
游民群体在对女性的敌视中发展出禁欲主义的英雄主义。那些好色之徒,是要遭游民耻笑的,称之为“溜骨髓”。这一点在游民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舆论,有的甚至把女性视为不祥之物,要千方百计地避开。因此,“不好色”成为江湖游民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好不好色竟成为检验是否是江湖英雄好汉的试金石。例如,《水浒传》中的生铁佛崔道成武艺并不亚于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因为他好色,才不被认作为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被梁山所排斥。再例如,蒋门神的力气、武艺都是远胜于一般人的,可是他不被认为是好汉的原因也是好色,自他霸占快活林之后,娶了个小妾,“掏虚了身子”,便被不好色的好汉武松三拳两脚打翻在地。游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都是将女色拒于千里之外的。所以,涉及可能对男性产生诱惑力的女人,游民至少是疏远的,《水浒传》则采取敌视的态度。这里的“女色”是个模糊的概念,既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包括正当的男女关系。
游民的世界是个极度男性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没有女性的位置,但可以有女人的位置,女性只有消除了其性别特征,表现出“男女都一样”的时候,甚至比男人还男人的时候,才会有她的位置。所以,女人要想成为被游民所认可的“真正的人”,首先必须成为“男性”。女人人性的完善意味着“男性价值”的实现。例如,《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三个女性,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嫂是两个典型,他们是比男性还男性的女性,有胆量杀人放火,动不动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这样的已经男性化的女性才是游民所认同的。所以,他们才能被游民世界所接纳,成为梁山的首领。游民文化中对于具有女性特征的女人,即便是游民的头领,也是采取敌视的态度,把他们放在最尴尬的位置上去。即使让他们有一个家庭,也要让丑陋的丈夫来统驭出众的女子,突出男性对女性的驾驭能力。《水浒传》中的扈三娘这样一个杰出的好女子,却嫁给了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的无赖王英,这样的婚姻结局满足了游民敌视女性的心态。一般说来,郎才女貌的婚姻结局是游民文化所不能容忍的。
游民道德的核心是“义气”,游民群体很重视异姓结拜兄弟的关系,这是他们增强自身力量,在对抗主流社会中得以生存的重要组织方式。对女性的留恋会消解“义气”这种道德规范在凝聚游民群体中的力量。有的首领仅仅因为眷恋某个女人就会导致众叛亲离。比如,《说唐》中的瓦岗山首领李密,因为一个女人而导致众将叛离,自己也在这个游民世界中身败名裂。为了贬斥女性,他们惯常用的比喻就是把女性比作衣服,可以随时更换,把异姓兄弟比作手足。孰轻孰重,不言而知。例如,《三国演义》中的游民首领刘备常挂在口头上的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异姓结拜兄弟张飞失守徐州后,要自刎以谢刘备。刘备把他抱住,夺其剑时,就说了这句话,又说“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在续乎?”[18](P207)再比如,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帮会生活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黑帮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可见这是游民对待女性的基本态度。
虽然《三国演义》中有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的描写,也有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但通过对小说中的话语分析发现,关羽和赵云他们所“护”、所“救”的并不是两个普通的女性,并不代表游民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与关怀。在关羽和赵云的心目中,甘、糜二位夫人是他们的主人兼义兄刘备的化身和代表。两位夫人不是以贤淑女性的形象而是以主母的身份展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尽管处在危难之中,他们还是坚定地恪守已经包含了主从关系的“弟道”,此举反而更彰显了关羽和赵云“义薄云天”的品格。这种品格正是为游民文化和游民道德所褒扬的。
三、小结
儒家文化建构着有序的社会,却同时建构着为有序社会服务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和性别结构。作为消解有序社会的游民文化打破了由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性别刻板印象,不自觉地建构了自己的性别认同,男性化的女性在游民文化中得到褒奖和称道。游民文化具有浓厚的仇女情节,这种情结源于为儒家文化所称道的、有序的家庭生活的消解。如果说在儒家文化中,女性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那么在游民文化中女性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成为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的游民发泄情绪的对象,女性已经被“物化”。女性或者被异化为游民在险恶无序的社会环境中艰难生存的累赘物,而成为在危急时刻被随意杀戮的对象;或者被泯灭了性别的特征而消融于极度男性化的世界中。相对于男性本位的儒家文化而言,游民文化是一种突破了男性本位的底线而极度男性化的文化。从男性本位到极度的男性化意味着女性的沉沦,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生存的权利失去了应有的保障。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祝瑞开.中国婚姻家庭史[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戴德.大戴礼记(再造善本)[M].卢辩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6]班固.白虎通(再造善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7]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8]朱熹.四书集注[M].陈戍国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5.
[9]董仲舒.春秋繁露[M].叶平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0]万丽华.孟子[M].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荀况.荀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12]管子[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仁孝文皇后,等.皇后内训东宫备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14]宋若昭.女论语[M].上海:会文堂书局,民国 5年(1916).
[15]礼记[M].张文修编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16]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17]施耐庵.水浒全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18]罗贯中.三国演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2.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华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女性学系主任韩贺南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The Difference of Woman Personality in the Cultural Image:Taking Confucius Culture and Vagrant Culture as Example
YU Guangjun
(Department of Women Studies,China Women’s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In the Confucius culture,with men’s domination and women’s subordination,women were still human beings with certain social position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In the vagrant culture,which viewed the Confucius culture as reactionary,women’s status were not promoted.On the contrary,they were degenerated into the object that vagrant hated.Women were transformed into animals such as sheep and cow which can be used for food even can be killed at will without undertaking the duty of morality and law.
Confucius culture;vagrant culture;female personality
C913.68
A
1007-3698(2010)03-0033-07
责任编辑:张艳玲
2010-03-12
于光君,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女性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女性学与女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