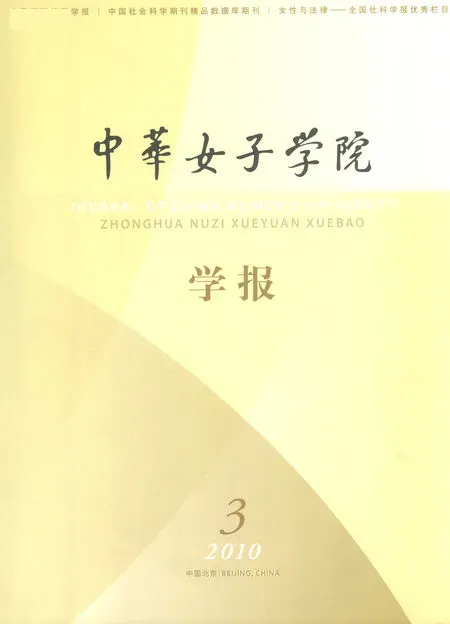婚内强行性行为的法律规制
——从同居权说起
2010-02-17刘廷华
刘廷华
(宜宾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婚内强行性行为的法律规制
——从同居权说起
刘廷华
(宜宾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7)
婚内强行性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严重危害了妇女的性自主权。同居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婚姻关系的身份权,而且是请求权。当同居权和性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法律应优先保护属于人格权的性自主权。结合当前国情,可规定婚内强行性行为在特定情况下构成强奸罪。
婚内强行性行为;性自主权;同居权;强奸罪
婚内强行性行为,是指男女双方正式确立夫妻关系后,丈夫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类似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规定:“各国政府应当承认并实施青年妇女不受性暴行、性骚扰和性剥削的权利。”这要求禁止婚内强行性行为,国外也有将婚内强行性行为定性为强奸罪加以禁止的立法例。反观我国,有众多学者认为它不构成强奸罪,其理由在于夫妻任何一方都有要求另一方与自己过性生活的权利,也有与另一方过性生活的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既然有一方义务和另一方权利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丈夫强奸妻子的问题。[1]然而,这是对同居权的误读。“尽管可以认为互相利用性官能的欢乐是婚姻的目的,但是,婚姻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一种专横意志的契约。”[2](P96)法律赋予婚姻关系内的性行为的合法性,但决不能因此推定婚姻关系内的所有性行为都是合法的。除了婚姻,合法的性生活还需要双方自愿这一实质要件,一纸结婚证书并不是丈夫可以实行性暴力的法律文书。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婚内强行性行为展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深入分析同居权的性质,说明同居权并不能构成婚内强行性行为合理化的依据;第二部分进一步分析婚内强行性行为的性质,结合犯罪构成理论,说明婚内强行性行为可能构成强奸罪;第三部分介绍国外关于婚内强行性行为问题的立法例,提出我国针对婚内强行性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同居权的本质
夫妻之同居,是指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等。婚姻乃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关系的基本表现,是夫妻共同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男女一旦决定结婚,理当意味着承诺与对方同居生活,没有同居,婚姻也就不称其为婚姻。[3](P33)正因如此,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对同居作了规定,例如,德国民法第1353条第1款规定:“婚姻双方相互之间有义务过共同的婚姻生活。”法国民法第215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义务。”日本民法第752条规定:“夫妻应同居,相互协力,相互扶助。”意大利民法第143条第2款规定:“依据婚姻的效力,夫妻间互负忠实的义务、相互给予精神和物质扶助的义务、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合作和同居的义务。”除了法律规定以外,学者对此也有关注。“同居义务,谓婚姻上之同居,非仅为场所上之意义,同在一屋如设障壁而分别生活,非为同居。场所虽有多少之间隔,亦得成立同居。同居所涵盖的内容包括:其一,夫妻同居为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要件,其义务为本质的义务,于婚姻成立同时发生,在婚姻解销前,继续存在;其二,同居义务为相互的;其三,性交当然为婚姻之内容,可解释包含于同居义务之内。”[4](P292)可见,同居权包括了请求对方履行性义务的权利。而且,由于婚姻法在其他地方单独规定了夫妻之间相互扶养、相互协助、精神安抚等义务,因此可以认为“同居权是由法律规定的,在婚姻关系成立之后,夫或妻享有与对方或要求对方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住所或居所,并进行以性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共同生活的权利。”[5]
同居权基于夫妻关系而生,理所当然属于身份权,是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享有的权利,离开了配偶身份,同居权便不复存在。[6]对于这种身份权的性质,有认为是支配权的,也有认为是请求权的。就权利的构造而言,支配权是权利人得直接使权利发生作用的权利,所谓直接使权利发生作用者,即直接取得为权利内容之利益之谓。[7](P26)故支配权的实质在于利益的直接实现性和对应义务的消极性。同居权绝非仅凭同居权人单方的意思就能实现,同居义务人所负担的也绝非只是消极义务。我国法律规定的身份权关系,其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是平等的,权利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我国的身份权并不是以对人的支配为内容的民事权利。[8](P32)而且现代社会,基于自由、平等、人权诸理念,法律更是不允许以他人人身作为权利之客体,支配权说逐渐失去支持。“不仅在财产关系部分如此,纵在身份关系部分,夫对妻之支配权人地位,亦有渐行消失趋向。”[9](P109)相对于支配权而言,请求权更符合配偶间的身份关系的本质,能更妥当地平衡相对人之间的利益。“请求权者,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也。”[10](P36)同居权是夫妻双方平等享有的一种请求权,当事人只能请求对方为同居之行为,而不能行支配之行为。例如,依外国立法例,配偶一方不履行同居义务,另一方得提起同居之诉。但同居之诉之判决,不得为强制执行。[11](P126)另一方面,同居权是请求权而不是支配权,关键在于该权利的特殊性。夫妻之间的同居权利义务是相互的,一方同居权的实现必须以对方愿意履行同居义务为前提。“所有人都有权利拥有他们自己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不属于父母、伙伴或社会。每个人有权以其选择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身体。每个人有权决定如何、何时被另一个人接触。每个人都有权拒绝任何的人类接触,也有权接受。”[12](P160)在实现同居权的过程中需要对方的身体,因此,同居权的实现依赖于对方当事人的配合,进而完全取决于对方进行性行为的意愿。性自主权决不容他人侵犯,这早已得到公认。正如《性权宣言》所提出的,“性自由排除生活中所有形式之性强迫、性剥削与性凌虐,无论何时,亦无论出于何种情况。”[13]
夫妻一方行使同居权时,可能遭到对方的拒绝。前已述及,同居为婚姻的根本义务之一,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必定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有时,这种拒绝是有正当理由的,也是允许的。“性交当然为婚姻之内容,可解释包含于同居义务之内,根本的性交之拒绝,为婚姻义务之违反,然于善良风俗及配偶之健康,亦有其界限,有正当理由不同居时,此义务亦停止。”[4](P297)有正当理由时,可以暂停同居义务的履行,这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都有所体现。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第2款规定:“夫妻的一方对他方在建立共同生活后所提出的请求,显然为滥用其权利或者婚姻已破裂时,无承诺的义务。”《墨西哥民法典》第163条规定:“如果一方并非出于公务需要或社团业务需要将自己的住所迁移至国外或是在不卫生或不恰当的地点定居,法院可以因此免除配偶他方的这种义务。”《瑞士民法典》第170条规定:“提起离婚或分居的诉讼后,配偶双方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归纳起来,正当理由大体上包括几种:因公事或职业需要长期外出、被判别居、依法被禁止同居(如入狱)、无婚姻住所、因身体健康的原因(如女性特殊的生理期)。
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同居的,可以向法院提起同居之诉,法院可以判令对方履行,但这种判决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01条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夫妻一方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同居时,他方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履行同居的义务。但基于人身关系的性质,此判决不可强制执行。”[14](P36)同居义务不得强制执行,主要在于执行该义务涉及对方的人身,依法理人身不得成为强制执行标的。即使是财产权利的行使,在涉及人身时也有例外规定。在一方违反基于人身依赖关系产生的合同和提供个人服务的合同的情况下,不适用强制实际履行方式,已成为惯例。因为这样做“涉及人身自由问题”。[15](P378)同时,违反同居义务也不能像一般债务不履行那样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民事责任是国家公权力得以介入私人民事生活的法律依据,而对何种民事关系予以公权力的保护是立法者的一个价值判断。同居义务不同于一般的债务,不以给付受领为目的,而以夫妻关系之和谐为最终目的。基于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策选择,对于夫妻生活,公权力选择了谦抑和审慎的态度,认为以损害赔偿的方式对同居权进行救济不具有充足的社会妥当性,因而在宣示其权利的同时并不科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民事责任的保障,依其性质不得强制执行,不能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因此,同居请求权实质上只是一种观念上的权利,一种“自然债务”,权利的实现上完全取决于义务人的自觉。必须注意,同居权虽然类似于自然债务,但违反同居义务却不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例如,在实行别居制度的国家,违反同居义务会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国家,违反同居义务是提起离婚之诉的法定事由。我国婚姻法第32条即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应准予离婚。夫妻双方互不履行同居义务,无疑是分居,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讲,违反同居义务可能引起夫妻身份关系的变动。
二、婚内强行性行为的定性
作为一种请求权,丈夫在行使同居权时需要妻子的配合。在有正当理由时,妻子可以拒绝履行同居的义务。即使无理拒绝,丈夫也无权要求强制履行,不只是因为这种义务涉及人身。事实上,妻子拥有能够和丈夫请求同居相对抗的性自主权。当“夫妻一体主义”渐被“夫妻别体主义”所代替,男女婚后各保有独立的人格,且相互间有权利义务关系,表现为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16](P196)“各国的婚姻立法一般都以夫妻别体主义为基础,即法律认为夫妻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各有其人格,夫妻双方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的人格都不能被对方所吸收。”[5]我国宪法第48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都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如果承认妇女也是公民社会中的法律主体,那么,妇女在性权利方面的主体地位就应当为法律所肯定。毕竟,妇女的身体是自己的,妇女必须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17](P299)
性自主权是妇女以其自由意志支配自己的身体进行性活动的权利,是身体权的派生权利,“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的完全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人格权。”[18](P82)如同其他人格权一样,身体权具有不可转让性。尽管结婚是男女双方对彼此共同生活包括共同进行性活动的承诺,但是并不意味着一方或者双方放弃其自由意志把自己的身体交由对方支配,只有在配偶自愿或者同意的情形下,另一方才得以利用其身体进行性活动。婚内强行性行为的重要原因在于同居权和性自主权的冲突。丈夫要求行使同居权,而妻子则以性自主权与之相抗衡,结果,丈夫在性欲的支配下利用暴力强制妻子履行性交的义务。那么,当性自主权和同居权相互冲突时,应该如何处理?“一旦冲突发生,为重建法律和平状态,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或有关的利益)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显然,这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方法,由所有的法益及法价值构成的确定阶层秩序决定。无疑应该可以说:相较于其他法益(尤其是财产性利益),人的生命或人性尊严有较高的位阶。”[19](P319)因此,对于性自主权和同居权的冲突,理应优先保护妻子的性自主权。
行文至此,可以肯定的是,同居权不能作为婚内强行性行为的合理依据。否则,一纸婚约无疑就演变成了丈夫肆意强奸妻子的“合法文书”。即,同居权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婚内强奸合法化,只要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交的行为,当然属于强奸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制裁。[20]至于其他否定婚内强行性行为的犯罪属性的几个说法,同样经不住推敲。例如,暴力伤害论否定说认为婚内强行性行为罪不应当针对性行为本身,而应当针对丈夫所施加的暴力和胁迫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身心伤害,应当作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来处理。“如果我们惩罚强奸,我们只是在惩罚暴力,而不是其他。这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一种:用拳头击打某人的脸和把阴茎插到他人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强奸)不是性,而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身体暴力,却不需要把性的问题考虑在内。”[21](P77-80)这种观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强奸的非法性并不在于对女性身体的侵犯而在于对女性性自由的侵犯,侵害了妻子的人格尊严中的性尊严,侵犯了妻子的婚姻平等权中性平等权。[22](P29)而且,如果将强奸只看作是对女性身体的侵犯,那么,当强奸并未对女性身体构成伤害时,女性的性自由就得不到应有保护,其建立在性自由之上的性权利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因为“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构成要件中,总可以找出其与某种法益的关系。换言之,即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因之,法益可谓所有客观之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之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准此,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23](P6)而且,“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所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24](P141)由此可见,合理解释强奸罪构成要件的前提是准确界定强奸罪的保护法益。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24]因此,强奸的本质特征在于违背妇女的意志,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性行为之决定自由或性自主权。[26](P509)正是基于此,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刑法的修订中,开始将强奸罪设定于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客体范围里。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将强奸罪放入第二章“伤害人之身体或精神罪”中;意大利1996年修改刑法典,将性暴力犯罪移至第十二章“侵犯人身罪”中。如上所述,由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妇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或性自主权,作为个人法益,妇女本人有权利处分之。因此,如果行为人明知妇女不同意,而强行与之性交的,则侵犯了被害妇女的性自主权,原则上便构成强奸罪。由此可见,妇女是否同意性交,或者说性交行为是否违背妇女的意志,成为是否侵犯妇女的性的自己决定权或性自主权的表征,从而成为认定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这与强行性行为的主体身份无涉。另一方面,承认婚内强行性行为属于犯罪也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运动,使广大妇女的性意识、性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性自由意识的产生,性主体观念的形成,对社会古老、封闭、传统的性关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冲击。妻子也不再是丈夫手下逆来顺受的性奴隶,而是平起平坐的性伙伴。在世界性人权公约中都写进了男女平等原则,自此以后所取得的人权成果,被法律规定为男人和女人共同享有。[27](P457)“人权保障是刑法的最基本的价值之一……依法治国的刑法文化就是要以人为本,具有人文关怀。”[28](P13)刑法的这种关怀,绝不仅仅是对婚姻家庭之外的妇女的性自主权的关怀,当然也包括婚姻家庭之内的已婚妇女的性自主权。
三、境外立法例及我国立法选择
英国早期的习惯法认为,强奸罪是指一个男人未经不是他的妻子的女人同意,使用暴力强行与她非法性交的行为。即,丈夫强奸妻子并不犯罪。因为在订立婚姻契约时,妻子就已经同意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满足丈夫的性需求,故丈夫不必每一次性交前都要征得妻子的同意。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马菲·黑尔爵士所言:“丈夫不会因强奸妻子而被定罪,因为根据契约,妻子已奉献其身给丈夫。此项承诺是不可撤销的。”[29](P199)这个观点在“皇室诉卡伦斯”案中得以落实。法官史密斯拒绝裁定丈夫强奸妻子。史密斯说:“在婚姻中,妻子同意丈夫行使婚姻权利……除非这种在婚姻时给予的同意被撤销,否则怎能说丈夫在运用婚姻权利时是侵犯他的妻子呢?”[30](P54-55)此案之后,英格兰法官大都同意这种观点,婚内强行性行为丈夫豁免的观点被视为金科玉律,除非妻子已经通过法律程序明确表示撤销“婚姻时给予的同意”。但是,英国的判例法是不断发展的,1994年英国《性罪行(修订)法例》中“非法性交”一词被划去,亦即间接删除了“婚内强行性行为豁免权”。自此以后,任何男人都不可以强奸女子,即使是丈夫与妻子之间亦不能豁免。[30](P54-55)
同英国法一样,进入20世纪中后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开始立法确认丈夫强奸妻子构成强奸罪。在美国,1980年《模范刑法典》开始认可在夫妻分居前提下的丈夫强奸罪。1981年新泽西州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或者性无能或者同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被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该规定肯定了丈夫作为强奸罪的主体的可能性。1984年纽约州上诉法院6名法官一致决议:“凡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的丈夫,可控告其犯强奸罪。”随后在美国的其他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也出现了类似的相关规定。到1993年,北卡罗来纳州成为美国最后一个废除丈夫除外的州。[29](P147-148)至此,婚内强行性行为入罪在美国得以全面确立。除了英美国家,其他国家也通过修订刑法的形式承认了婚内强行性行为属于犯罪。如德国1998年新刑法典第177条规定,“恐吓他人忍受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对其进行的性行为或者对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实施性行为的为强奸罪”。[31](P115)该条明确摒弃了丈夫除外原则。《法国刑法典》第222—223条中规定:“以暴力、强制或者威胁、趁人无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强奸罪。”[32](P64)1996年修订的《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90条之(2)规定:“行为人是被害人的丈夫的,且两人共同生活的,也构成强奸罪,只不过告诉乃论。”[33](P69)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118条规定任何男子强奸一名女子即为犯罪。因此,丈夫也可因强奸妻子构成犯罪。[34](P135)更准确地说,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婚内强行性行为实行的是部分排除,规定在三种情况下丈夫可成为强奸罪的主体:(1)在法律上已分居;(2)法庭已经令丈夫不能骚扰妻子;(3)丈夫对法庭承诺不骚扰妻子。[35](P104)
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法律规定看,没有排除丈夫的犯罪主体资格,即,婚内强行性行为是可以构成强奸罪的。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对婚内强行性行为问题的认识却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没有形成通说,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混乱。因此,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婚内强行性行为问题的认定依据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当前,既要否定婚内强奸无罪论,也不可将婚内强行性行为简单地一律认定为强奸罪。平野龙一指出:“即使一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治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或者其他社会统治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法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罚,这叫做刑法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35](P104)基于夫妻关系的特点,婚内强行性行为即便具有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也很难构成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也就是说,丈夫强迫妻子性交远远没有强奸其他妇女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为这两种不同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设定相同的法律责任,是和法律的正义性相违背的。[37]因此,有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丈夫奸淫妻子不构成强奸罪,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构成强奸罪:(1)男女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且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关系,而女方坚持要求离婚,男方进行强奸的;(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丈夫进行强奸的。[38](P87)这种折中的观点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1999年第三期《刑事审判参考》中第20号案例的“裁判理由”中写到:“如果是非法婚姻关系或者已经进入离婚诉讼程序,婚姻关系实际已经处于不确定中,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从刑法理论上讲是可以构成强奸罪的。但是,实践中认定此类强奸罪,与普通强奸案有很大不同,应当特别慎重。”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已经认定在婚姻的特殊存续期间可以成立强奸罪。如,男女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尚未按当地风俗习惯举行婚礼或同居,女方提出离婚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的;一审法院已判决离婚,判决尚未生效的。因为,在上述的特殊时期内,虽然在形式上双方是夫妻关系,但在实质上,夫妻双方的感情确已破裂,双方已不存在实质上的正常夫妻关系。
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我们认为,除了离婚诉讼期间、一审上诉期间和二审期间以及分居期间等婚姻的特殊存续期间可以构成强奸罪外,在女性的特殊生理期间,如果丈夫实施强行性行为,也应认定为强奸罪。女性承担着人类繁衍的社会责任,生理结构与男性截然不同。女性的特殊生理期间包括经期、孕期和产后(生产后和流产后的合理期间)。在此期间,女性身体十分脆弱,免疫力减弱,抵抗力低下。此时性交,会严重损害妇女健康,导致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丈夫在此期间置妻子的身心健康于不顾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应当认定为强奸罪,并予以严厉惩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最后,鉴于婚内强行性行为的特殊性,建议婚内强行性行为采取自诉的形式进行处理。这不仅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也是兼顾了婚姻关系的特殊需要。当然,“婚内强奸”行为之所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配偶和社会对性行为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所以通过司法机关特有的预防部门的宣传和教育,可以起到事前而非仅仅事后的预防效果[39],有助于减少婚内强行性行为的发生。
[1]邵世星.夫妻同居义务与忠实义务剖析[J].法学评论,2001,(1).
[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李莉.论夫妻间的同居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2).
[6]孟令志.同居制度之立法研究[J].法商研究,2001,(1).
[7]王伯琦.民法总则[Z].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79.
[8]王利明.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9]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80.
[10]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1]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Z].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6.
[12]J·P·蒂洛.伦理学 :理论与实践[M].孟庆时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3]赵合俊.性权与人权——从《性权宣言》说起[J].环球法律评论,2002,(春季号).
[14]李景禧.台湾亲属和继承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15]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6]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7]杰佛瑞·威克斯.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8]杨立新.公民身体权及其民法保护[A].民商法判解研究(第三辑)[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9]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20]马特.论配偶间同居义务的效力[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2).
[2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2]冀祥德.婚内强行性行为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23]林山田.刑法特论(上册)[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78.
[2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5]于跃江.强奸罪客体新论[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5).
[26]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M].李贵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7]孙萌.妇女人权实现障碍研究[A].徐显明.人权研究(第一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8]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21世纪刑法学研究展望[J].人民检察,1999,(11).
[29]哈里·D·格芬斯.家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0]周华山,赵文宗.整合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论述——重新阅读中国婚内强行性行为法[J].法学前沿,1999,(3).
[31]德国刑法典[M].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2]法国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M].罗结珍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33]瑞士联邦刑法典[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4]赵秉志.香港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5]高炳昭.香港刑法导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36]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7]杨德寿.婚内强迫性行为的法律责任论——由王卫明强迫妻子性交被判强奸罪说起[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5).
[38]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四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9]林占发,许艳明.“婚内强奸”行为定性的实证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1).
责任编辑:蔡 锋
D923.9
A
1007-3698(2010)03-0011-06
2010-03-11
刘廷华,男,宜宾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