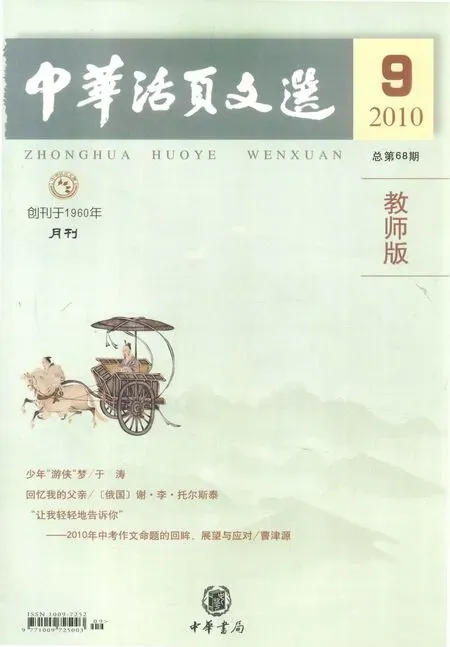拜金主义和封建家长制的双重典型:周朴园
2010-02-17仇恒榜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仇恒榜(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拜金主义和封建家长制的双重典型:周朴园
■仇恒榜(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曹禺先生 1933年创作的话剧《雷雨》,以其取材的精当和布局的精巧当之无愧被称为中国话剧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剧本采用“穿插”和“回顾”相结合的手法,把 30多年的人物恩怨情仇安排在某一个夏天,从早晨到午夜一天的时间。剧本围绕周朴园这个中心人物,展示了他与鲁侍萍、蘩漪、鲁大海等人物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重点塑造了一个拜金主义和封建家长制的双重典型周朴园的形象,作品问世 70多年来,对周朴园这一形象的认识可以说是众说纷纭,难成定论。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个不值得任何同情的伪君子形象,曹禺先生认为“这个人坏到连自己都不觉得坏的地步”。从 30多年的时间空间跨度来看,周朴园的发迹史涉及三个地方:无锡、哈尔滨和天津。周朴园这个人物也随之完成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他曾经反叛社会,继而顺从社会,最后是回归社会。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年轻时突破门户限制爱上了自己家的一个下人侍萍,并与之生了两个儿子,但他毕竟是封建家庭的阔少,为了娶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屈从于母亲的安排,不多久就赶走了侍萍,像世上所有的薄情人一样始乱之终弃之。当他后来娶了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蘩漪时,封建家长制的本性使得他处处采取压制的态度。作为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他过去和现在双手都沾满了工人的血汗:过去在哈尔滨修建江桥,故意使江堤决口,淹死了 2200个小工,从这些小工身上每人捞上 300元洋钱,还指使警察打死了 30个工人,现在他克扣工人工资引发工人罢工,这些事端充分显示出他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自私与冷酷。剧本写得最让人称道的是其中周朴园和鲁侍萍 30多年后再次相会的情形。此时的鲁侍萍早已不是 30多年前周朴园心目中的那个又贤惠又漂亮的梅小姐,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鲁妈了,此时她应蘩漪的要求来周公馆准备领走自己的女儿四凤。对周朴园来说,30多年的时间非但未能磨平他心目中的那段又美好又痛苦的记忆,反而使他越发的多情与感伤。他向面前的鲁侍萍打探起有关梅小姐的遭遇,声称要把梅小姐的墓修一修。鲁侍萍不动声色地告诉他梅小姐“复活”的情况,剧本刻画周朴园的神色是“汗涔涔”的,语言也不由得变得有些结巴,当他最后终于搞清楚站在他眼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口口声声声称自己难以忘怀的梅小姐时,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变得六神无主。半晌之后才回过神来,面对鲁侍萍的一句“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变得连你都不认识了”,此时的周朴园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喝问侍萍:“谁指使你来的?30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里来了?”侍萍愤怒地控诉“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周朴园凭借 30多年的老谋深算,不假思索地认定来者不善,这个女人一定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如果闹翻了,会直接影响他此刻的名声和社会地位,于是很快决定采用怀柔一手:他自我表白为了表达对侍萍的思念之情,多年来一直保存着侍萍当年用过的旧雨衣,旧家具,甚至保留了当年侍萍关窗的习惯,似乎一下子变得多情起来,当他由梦幻般的回忆转而回到眼面前的现实,并且弄清楚了眼面前的这个老年妇女并没有对他的地位、声誉造成威胁伤害的时候,伴随着一种情感的失落,他觉得自己确实做出了对不起鲁侍萍的事,他与鲁侍萍恢复了正常的交流与沟通,他要给侍萍 5000大洋,甚而后来再汇两万大洋,对鲁侍萍完全摆出一副你生我养,你死我葬的赎罪姿态。有人说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虚伪的,他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这样的解读实际上是把周朴园这个复杂的人性简单化格式化了。周朴园虽说是资本家,但他同常人一样有情感的诉求,年轻时的他对侍萍的感情也许没有掺杂更多的社会性因素,一见钟情也是人的常情常理,但为了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他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大年三十晚上赶走鲁侍萍,这种行为不能不让人鄙视他的人格,他娶了一位夫人,但不久这个女人就死了,当他遇上了年轻貌美的蘩漪并使出种种骗术终于将其骗到了手,受新思想影响的蘩漪与他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他不由得有意无意想起那个带给他无限美好回忆的“梅小姐”,算是对自己眼前不如意的婚姻生活的一个补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朴园的怀旧情感并非是装腔作势,也无需装腔作势。然而当 30年前的那个朝夕相处的旧情人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个年老色衰、阅尽人间沧桑的老年妇女与周朴园心目中的那个美好形象严重错位,要他在情感上认可对方恐怕是较困难的,30年后的周朴园已经缺乏年轻时的那种烈火喷油式的激情了,在他这样的年龄,已不大可能沉醉在昔日的感情中,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偶尔陶醉在过去虚幻的美好之中而已。
在整个剧作中,周朴园一直是个中心人物,因为他的存在,使得各种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头绪繁多。回归社会后的周朴园俨然是“社会上的好人物”,这种好人物的标准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倘若说明代小说《金瓶梅》塑造了一个原始积累时的资本家形象西门庆,此人纵情声色死于淫乱被人唾弃的话,那么《雷雨》中的周朴园则是自觉不自觉地——尽管这里也有不协调的成分——在维护封建正统秩序诸如三纲五常方面做了一个理性的回归。端坐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顶端,他在处理与外人、下人的关系方面绝对是丝毫没有商量余地的,他与人说话经常是用命令口吻,对不满意的人或事不会轻易放过。在家庭内部,他纪念侍萍之举很大程度上是刻意为之,为家人制造一个假象来维护自己好父亲好丈夫的形象,难怪周萍对他信服而且佩服。为维护他作为一家之长的最高权威,他在家里导演了一场要蘩漪喝药的闹剧。在蘩漪看来,她“什么都依着他,什么都不可商量”,她对周朴园习以为常,除了爱情,她一切都接受周朴园的权威,这本身也的确由不得她。剧中在表现周朴园和蘩漪的矛盾冲突时,精心安排了周朴园要蘩漪在孩子们面前喝药的场面。在他看来蘩漪的所作所为不可理喻,由此他断定蘩漪在精神上一定出了问题,于是他以关心她的病为名,要她喝下药做出服从的榜样,这样做可以一举数得,一是表明自己是个好丈夫,关心妻子疾苦,二是在孩子们面前是个好父亲,三是利用这个机会给蘩漪瞧瞧,他周朴园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他的绝对统治地位不可撼动。蘩漪终于在他软硬兼施之下喝了药,由此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家庭关系上,蘩漪觉得周朴园是压抑自己的丈夫,周冲觉得他是自己畏惧的父亲,在鲁贵看来他又是自己最怕的主子,三个人的叙述分别在夫与妻、父与子、主与奴三个层面上确认了周朴园的绝对权威,剧本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塑造了周朴园作为封建家长的成功典型,但光是这样的刻画还不足以表明周朴园的阶级定位,作为一个罪恶累累的资本家,他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榨是通过周的亲生儿子鲁大海与他的一番激烈较量来暴露的。作为罢工的工人代表,鲁大海历数周朴园过去的斑斑劣迹,周朴园恼羞成怒,当场宣布开除鲁大海,父子关系公开破裂,阶级地位使他撕毁了笼罩在这个大家庭身上的最后的面纱,狰狞的面目掩盖了脆弱的人伦天性。剧本的尾声向读者展示了周朴园一种天性的依稀回归,当他意识到他眼前的两个女人蘩漪和侍萍变疯,周冲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时,他身上再也看不出那种强硬固执的天性,他的眼睛平静而充满忧虑,呆呆地望着燃起的炉火,这样的安排似乎寄托了年轻的剧作家对这个复杂人物命运的无限悲哀。
一出《雷雨》塑造了一个双重的典型:既有拜金主义思想带来的金钱至上,又有封建家长制意识导致的蛮横专制。时有矫情作伪,时有冷酷自私,当然也有温情良知,尽管这种温情良知有时显得微不足道,但少了他就不再是“这一个”真实完整的周朴园了。客观全面,大气包容同时又不隐恶,这是我们分析这个复杂的艺术典型时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