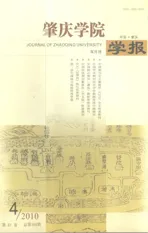《黑骏马》中被架空的“爱情”
2010-02-16陈慕雅
陈慕雅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黑骏马》中被架空的“爱情”
陈慕雅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张承志的代表作之一《黑骏马》描写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离去九年后重返草原,寻找往昔恋人的爱情故事。在对爱情的描写中,凸显了索米娅的两种角色以及白音宝力格对这两种角色的寻找,但这种爱情并没有落脚于具有个性的个体之上,因而是被架空的,不是真正的爱情。
《黑骏马》;男权;爱情;个性
《黑骏马》[1]是张承志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叙述了主人公“我”(白音宝力格)在离去九年后重返草原,寻找往昔恋人的故事。表面上看,“爱情”似乎是贯穿始终的主题,然而,若仔细分析,“爱情”只不过是一个被架空的美好字眼。
在小说中,“我”的爱情的对象索米娅虽然和“我”一样,依次经历了人生的不同阶段,然而,无论她的形象如何变化,在“我”的眼中却始终不外乎两种角色:要么是柔弱可怜,需要“我”保护或拯救的弱者;要么是纯洁美好,指引“我”向上的精神象征。而这两种角色是“我”站在大男子主义及由此演化来的理想主义的角度从外部强加给索米娅的,从而导致她的形象概念化、模糊化,沦为无个性的存在。爱永远是指向个性之路(别尔嘉耶夫语),但是,在《黑骏马》中,“我”所谓的“爱情”,并没有落脚在一个真实独特的个体之上,而成为飘渺的所指——一方面是“我”长成男子汉的陪衬和必需品;另一方面寄托着“我”的某种理想,某种“心绪”,某种“看不见的、独特的灵性”。
一、两种角色:交会与分离
一开始,由于“我”尚且年幼,索米娅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初次见面时,她给“我”的印象仅是“一个在一旁文静地喝茶的、黑眼睛的小姑娘”,“她的嗓音甜甜的,挺好听”。她的单纯和无性格正好衬托出“我”的强烈个性与自我意识。“我望望索米娅,她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大木缸上,信赖而折服地注视着我。我威风凛凛地挺直身子,顺手给了犍牛一鞭”。这时“我”虽然距离成熟还很遥远,却已经流露出了俨然以强者、被依赖者自居的心理端倪。
当“我”到达了“儿童和青年的分界”,智力和身体都已成人:“那时我寡言少语,喜欢思索……常常正在安静地读一本图文并茂的《怎样经营牧业》”,“我的汗水淋淋的两臂肌肉发达”。然而,这仅仅是成“人”,并不是成“男人”。要真正成为“男人”,成为“男子汉”,必须有相应的“女人”出场。小说主要通过两个场景来描写这一转变。
第一个场景是“我”突然间发现索米娅长成了一个“颀长、健壮、曲线分明、在阳光下向我射出异彩的姑娘”,其实就是发现她已经在身体上成为一个“女人”,“我”长成“男子汉”的必需品出场了。“她以完全陌生的东西敲击了一下我的心扉,并在一瞬间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启蒙”。这个“启蒙”便是性意识的觉醒。作者接着感慨道,“我从那么小就盼着长成一个男子汉。可是男子汉原来完全不仅仅是拥有一匹骏马”。这个场景是由纯洁的童年世界到情欲的成人世界的分水岭。然而,这时“我”只是有了“男子汉”的意识,“男子汉”的行动与真正的实现还有待下一个场景来完成。
这下一个场景便是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又一再被提到的,索米娅和朝霞相映生辉的景象。“我”不是在肉体上占有,而是通过心灵的契合真正得到了一个“女人”,完成了长成“男人”的仪式。一方面,索米娅的“可怜巴巴”激起了“我”的保护欲,激起了“我”心里“一股强烈的、怜爱的潮水”,“我”通过保护她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英勇的自豪感”。最终,这种感情上的冲动转化为理智,“我”意识到了自己“守护神般的、男人式的责任感”。这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就是“我”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心理感受,而这是和索米娅的柔弱可怜紧密相关的。“回忆中的索米娅弱小的形象可以说是白音宝力格为了配合诗意的想象和男性的征服欲望而制造的幻象”[2]57-59。另一方面,作者把索米娅定格在朝霞的背景下,定格在“感动”、“喜悦”的一瞬间,使得索米娅外表的美好和心灵的纯洁交相辉映。而描写“我”的爱人的纯洁美好,是为了将“我”原本充满情欲的爱情升华为“最纯洁、最优美的人间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离开草原后成为鼓舞“我”不断向上的精神动力。但究其实质,这种感情依旧是男性中心主义的隐喻,因为朝霞是初升太阳映照的云彩,男性就是“太阳”,女性就是被其映照的“云彩”(朝霞)。
在这个场景中,索米娅的两种角色交会在一起,“我”与她的爱情达到一个高峰。
小说第四节叙述了“我”那关键性的离去。这背后固然有文化的差异,也不妨看做是索米娅两种角色分离的结果。当“我”确认她已被黄毛希拉玷污,她的外表不再美好(挺着大肚子),她的肉体也不再纯洁,“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即继续扮演索米娅的保护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小说写道,“我等着她把满腹的委屈和痛苦向我诉说。我最终是会原谅她的,而且我坚信会有办法让恶魔希拉一直到死都不得安生”,“我一直在等着她来向我倾诉。每当我饮马回来,……我总以为,她会立即出现在我眼前并扑向我”。然而“我”发现,索米娅并“不回答我的呼唤”,并没有显示出往常的柔弱可怜,“我”连这个角色也无法扮演下去了,离开也是必然的选择。
正是在这一节里,我们看到了所谓“最纯洁、最优美”的爱情的虚伪、脆弱和不堪一击。首先,索米娅受到的玷污并非出于她自身意愿,丝毫无损于她心灵的纯洁,“我”的反应却十分激烈(或者说是过于激烈),可见“我”在心灵纯洁的幌子下,更为看重的是肉体的纯洁。其次,看到自己的爱人已经被“丑恶的力量”所伤害,明知她有“满腹的委屈和痛苦”,却自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地俯下身来安慰过她,而是“勃然大怒”,最终愤然离去,并且美其名曰是“去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真正的爱情吗?这种“勃然大怒”最终不过是“男人的愤怒”,甚至是居高临下的“主人的愤怒”,对被玷污的属己之物的厌弃。索米娅作为具体的爱情理想已然崩塌,并导致“我”转而追求抽象的人生理想,因此,她不过是被想之“象”,而非被爱之“人”。
二、寻找——“不是”
索米娅两种角色的分离导致了“我”的离去,而“我”的归来,同样是为了重新获得那两种角色。一是寻找那已经失去的纯洁美好,二是渴望再次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我”以拯救者自居的心理,从最初见到黑骏马钢嘎·哈拉,直到与索米娅相见,都有所流露。“我”问黑骏马,“你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你该明白我是多么惦念着她,因为我深知她前途的泥泞”。当“我”看过天葬的奶奶,决定去寻找索米娅的时候,又写道,“我不能再做迟到的悔恨者。也许,我的沙娜正在生活的旋流中呼喊着我,等着我向她伸出救援的手……”。如果说“她前途的泥泞”是“我”对索米娅的有待拯救的客观处境的想象,那么“我的沙娜正在生活的旋流中呼喊着我,等着我向她伸出救援的手”就是我对她亟待拯救的主观情怀的希望甚至渴望。但是事与愿违,当“我”见到索米娅时,“她并没有哇地哭出来,更没有一下子扑进我怀里,甚至也没有喊我巴帕。她丝毫没有流露出对往事的伤感和这劳苦生涯的委屈”。索米娅的坚忍和“我”的男权意识的失落与当初“我”离去时的情景何其相似!
“我”渴望再次寻找到那失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所以一开始,“我”对现实拒不承认。在“我”听了女教师对索米娅生活的叙述之后,在“我”亲眼目睹了索米娅工作的学校之后,“我仍然不能相信和接受它们,尽管它们是如此真实。我仍然只是看见她的那个形象:那是一个面对着朝霞的、眸子中闪跳着金红色的憧憬的美好姑娘”。后来,“我”与索米娅相见,亲身体验了她的生活,终于意识到,那个“披着红霞的、眸子黑黑的姑娘,我已经永远的失去了你”。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他的回忆中,索米娅弱小的形象可以说是白音宝力格为了满足自己诗意的想像和男性的征服欲望而制造的幻象。当现实中的索米娅以成熟的形象出现的时候,白音宝力格制造的索米娅的幻象失去了心理依据。回到草原之前,幻象蒙蔽了他对真实的索米娅的坚韧的本色的认识。现实中他看到‘草原上又成熟了一个新的女人’,成熟的索米娅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再需要他的保护了。”[3]
然而,张承志不同于一般作家之处正在于,他绝不允许自己在这无可挽回的伤感中戛然而止,不允许生命沦为虚无,沦为无意义的存在。他必须寻求新的出路、新的理想,必须赋予生活以新的意义。
于是,“我”看到了索米娅的蜕变,她的“目光里充满了使我感到新奇的怜爱和慈祥”,并在最后请求替“我”抚养孩子。“草原上又成熟了一个新的女人”。这种“成熟”是由“女人”到“母亲”的角色转变。“我”在最后差点说出来,“你将来一定会像奶奶一样慈祥”。这句没有说出的话向我们暗示了,“我”在索米娅身上找到了新的意义,这个意义已经通过之前女教师的话透露出来了,它便是从奶奶身上延续下来的伟大的母性。换言之,她的这种“成熟”反衬了“我”的不成熟,让“我”发出“快点成熟起来”的祈愿[2]57-59。她在无需被“我”拯救之后,再次成为指引“我”向上的精神象征。
在“我”眼里,索米娅青春时代的纯洁美好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慈祥的、伟大的母性光辉。这个认识过程便是古老民歌中所唱的“寻找——不是”的含义所在:虽然“不是”,却依然不懈的寻找。旧的理想不在了,但只要继续寻找,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发现新的信仰和支撑。或者说,这种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姿态,本身就是生命,就是信仰。这也就是小说开头反复提到的那“莫名的心绪”,那“独特的、看不见的灵性”的涵义所在。
在这种宏大的、超越的叙事背景下,“那此世难逢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倚托或框架”。小说中的这个描述,一开始就把爱情定位为次要的陪衬之物。当“我”在自己的爱情里,在爱人身上能够找到那“灵性”赖以倚托的东西时,“我”便歌颂它,仰仗它;而一旦“我”发现这种“纯洁”的东西被玷污,被“丑恶的力量”所破坏,“纯洁”或者“纯粹”难以为继时,“我”便不管不顾的愤然离去,寻找“更纯洁”的东西。即便“我”此后悔恨的回来,再度进行寻找,“我”所看到的依然是“我”想看到的,依然是可以为那“灵性”提供某种倚托的东西。这种爱情观,固然可以给“我”提供前进的动力,促使“我”一直去追求更纯洁、更美好、更光明的东西;但也阻碍着“我”,使“我”永远无法接近爱情本身,因为爱永远是指向个性之路(别尔嘉耶夫语),而非贯串小说的缺乏个性的青春幻象,也非小说结尾的精神还乡与“母亲”信仰。
[1]张承志.北方的河·黑骏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张一玮.往事重温与自我归罪─《黑骏马》及其它[J].甘肃社会科学,2001(4):58-59.
[3]刘俐俐.隐秘的历史河流─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考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77.
“Love”Hung in Black Beauty
CHEN Muy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The masterpiece of Zhang Chengzhi,Black Beauty,describes the hero Baiyinbaolige returning to the prairie after leaving for nine years,looking for his past love.In love description,two roles of Suomiya and the searching for them by Baiyinbaolige are outstandingly presented.The love is not to individual person, but hung empty.It is not real love.
Black Beauty;male power;love;individuality
I106.4
A
1009-8445(2010)04-0022-03
(责任编辑:禤展图)
2010-05-22
陈慕雅(1990-),女,河南漯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