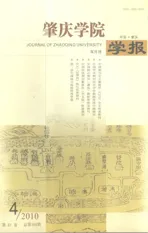前《天主实义》的思想嬗变
——利玛窦在粤书信阅读之管见
2010-02-16黎玉琴
黎玉琴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前《天主实义》的思想嬗变
——利玛窦在粤书信阅读之管见
黎玉琴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利玛窦在中国的所有活动都是以传教为宗旨的,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及其成果仅仅是围绕传教这个根本目标所达到的意外效果。因此,他的《天主实义》更应该成为研究利玛窦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活动时必须认真对待的文本。在利玛窦的思想历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即由对与罗明坚合作的《天主实录》的满意到失望,《天主实义》的产生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结果。
利玛窦;天主实义;天主实录
一、问题的提出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进入南昌之后,尽管他个人大出风头,而真正付洗成为天主教信徒的中国人却少之又少,因而逐渐形成了要“慢慢来”的缓进策略。如他于1596年10月12日在南昌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很少与他们交往,而且他们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百姓怕洋人,皇帝更畏惧洋人,这后者专制好似暴君,因为他们的祖先用武力从别人手中把皇位夺来,每天担心会被别人抢走。假如我们聚集许多教友一起祈祷开会,将会引起朝廷或官吏的猜忌。因此为安全计,应该慢慢来,逐渐同中国社会交往,消除他们对我们的疑心,以后再说大批归化之事。”[1]这其实可以说是利玛窦最真实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自然流露,当然也是对进入中国传教以来所经历过的、以传教为宗旨的活动进行的思想总结。这种思路上的变化使他更加注重在他所结交的中国士大夫中间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而把他本来所追求的传教这个根本目标做必要的退隐。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像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西方科技方面的文献的历史佳话,并且也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中华文明有机会接触到与自身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内涵与形态。
但是,如果紧扣其来华之目的,我们就有可能无法从整体上站在更准确的角度对他的各种文化活动进行理性的审视。何兆武先生曾经这样指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了解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一是传教士所传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而是当时的旧学,即不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思想与文化,而是与此相对立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神学和经院哲学;二是传教士的目的在于论证神学,他们的重要著述主要是有关神学和宗教的内容,而科学则仅仅是一种附带的手段[2]。虽然我们难以认同他的整个观点,不过何先生第二小点之所指,显然是任何具有历史意识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作为天主教耶稣会成员,利玛窦来华的宗旨是传教,“他更注重建设一个中国天主教文明”[3]。他进入中国后所做的一切也同样是服务于这个最根本的目的。可是,他和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所顺带的西方科学技术,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它确实包含了这个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最有价值的成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也总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在他的整个活动中仅仅是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传播活动。其实,从利玛窦挖空心思进入中国的终极目标来看,为传教目的服务而用汉语所写下的宗教文献《天主实义》,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利玛窦在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时必须认真对待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清理一下他在写作《天主实义》前发生在广东境内的汉语思想准备或者积累,对于理解利玛窦在华的文化交往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肇庆时期的汉语作品创作及其意义
按照利玛窦本人的说法,他登陆澳门,抵达中国,就立刻学习中文,也同时体会到学习中文的艰难:它远较希腊文和德语要困难得多。但是在自抵达中国差不多两年之后,利玛窦的汉语水平几乎可以说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这可以从他于1584年9月13日,即差不多是到达肇庆正好一年的时候,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的信中结尾处得到很好的说明,他这样写到:“由于忙着工作和学中文的关系,传教工作起初并不成功,感谢天主,到后来有了不少的进步,目前我们已经可以讲道和听告解了。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好,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觉得更有兴趣。我们已印刷了中文的《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中国人看后都觉得很好,也很高兴地接受了。”[4]14尤其是其中的《天主十诫》,成为了后来的《天主教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国著名学者张西平所说的那样:《天主教要》最初部分内容是由罗明坚完成,利玛窦协助,它在1585年的最初版本,应该是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共同完成的[5]。尽管对《天主教要》是否属于利玛窦的作品存在争议,但是从他在信笺中记录了用中文印刷了《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等作品这个事实,起码足以说明:虽然这个时期利玛窦的中文水平尚不能保证他能够直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即使《天主十诫》出自罗明坚之手,至少此时的利玛窦开始介入了以中文写作用于在中国传教所需要的作品。
参与罗明坚的《天主实录》的创作,应该是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在肇庆所做的传教准备过程中诸多事情中一件相当重要的工作,以个人之见,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逊色于制作自鸣钟和绘制世界上第一张中文地图,甚至与之相比,可能还要更加重要。他在1584年11月30日写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这样提到:“我的同伴罗明坚神父嘱咐我给您一本我们用中文编写的《天主实录》……。内容是一位中国教外学人询问种种问题,一位欧洲籍神父一一回答。条理分明,文词相当优美,对做教友应具有的知识无不网罗其中,当然是经过我们的至友(即肇庆知府王泮)润色过,我们设法适应中国主要宗派的思想而编译。”[4]59这也可以通过裴化行在《利玛窦传》以下说法得到说明:“自从6月或7月以来,他就在同一个秀才合作,审订罗明坚神父初步编写的教理问答:把它从口语改成文言文。”[6]在这里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即这本书是与罗明坚合作的结果,而且他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对《天主实录》应该说相当满意的。
在差不多一年后(1585年10月20日)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再次描述了对本书的满意程度:“在中国有一种习俗,凡出版一本新书,要请地方官吏或社会名流撰一序言,对作者恭维一下,对其内容也要褒奖一翻,这和欧洲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便请岭西道王泮撰写,他是我们这里的保卫者,去年自肇庆府升任岭西道。一切印妥,只缺首页,便是将印序言而保留的。他看了我们的《天主实录》后,非常高兴说:写得不错,理由也充足,但他称不需要写序言,似乎别人也不能撰写。”[4]64在这封信中他还特别指出,《天主实录》实际就是《要理问答》,同年11月10日他在给拿坡里马塞利神父以同样的语言和口吻,重申叙述了上述看法。而在这一年的11月24日给富利卡提神父的信中甚至说本书“给我们帮了大忙”,“很受重视,不少人要我们赠送”。[4]83-84
在后来具有回忆和总结性质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有这样的解释:他们来到肇庆后,通过交往发现,有教养的中国人肯定认为这些欧洲人是富有理论和学识的名望的,因此有高深学识的阶层中,有些人需要得到有关基督教教诫的更完整的解释,而不限于一部神父们惯于携带的《天主十诫》的内容。于是,神父们变得更大胆了一些,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他们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字,写了一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尽管神父们对于处理每个题目,写得还不是很内行,他们也不知道中国人是否赞同他们写中国字的形体,但是用这个方法使基督教的要义比通过口头更容易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新内容的书。[7]这就是《天主实录》。这些在事隔二十多年后的想法,毫无疑问地反映出利玛窦对刚刚进入中国传教,是与罗明坚所做的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上述这些材料表明:发现《天主实录》用于传播福音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实际上要大大晚于Doulas Lancashire和Peter Hu Kuo-chen, S.J.所说的1584—1591年。因为利玛窦在《天主实录》完成时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一般人都可能产生的初始成功的自我陶醉之中,远没有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生活历练之后,可能产生的对包括它本身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切身的体会。但我们认为,完全应该把利玛窦的这些工作看成是他一生用汉语传播天主教的重要准备,甚至可以将这看成是他后来完成《天主实义》的基础性工作,因为若没有这个阶段的在一定程度上即使还是比较粗糙的工作,他可能完全不会意识到有必要以更完善的内容出版以传教为宗旨的中文宗教作品,可能更不会对范礼安的文化适应传教思路产生深度的共鸣。
三、韶州时期思想的重要转变
但是,直到1593年12月10日再次给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我们才发现利玛窦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时他和他的同伴们在韶州已经好几年了,距离他到达肇庆的时间更是已经整整10年有余。他在这封信中这样写道:“今年我们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给目前已去世的石方西神父听,即四书,是一本良好的伦理集成,今天视察员神父要我把四书译为拉丁文,此外再编写一本新的要理问答(按即后来的著名天主实义)。这应当用中文撰写;我们原有一本(指罗明坚神父所编写的《天主实录》),但是成绩不如理想。”[4]135这表明利玛窦在尚未到达南昌之前,对此前甚为满意的《天主实录》已经没有了10年前的那种成功喜悦和自信了,而是已经意识到,它已经难以胜“为天主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赢得可接受的一席之地”的大任了,当然在这个时间之前,他肯定已经开始考虑配合在中国传教所需要的理论作品的更新问题了。
导致利玛窦在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因素中,他在肇庆六年尽管努力却并不成功的现实,无疑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他在肇庆期间并非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完全隐藏了他的传教使命,没有讨论过宗教问题。不仅《天主实录》本身是证据,而且由利玛窦在肇庆生活期间为帮助自己记忆用而编纂的《中葡词汇表》,正好概括了他与来访的中国学者所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中心就是宗教[8]277。尽管他在肇庆得到了当地官员的赏识,但一直到他不得不无奈地离开肇庆,真正成为天主教徒的中国人却是寥寥无几。由此所产生的内心冲击,与他刚进入中国不久所完成了《天主实录》所表露的心情无疑会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他在到达韶州时仍然很不顺利,传教工作也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观。这可以从他在1592年11月12日致罗马前初学院院长德·法比神父的信中得到明确反映,他回忆说:“神父,‘我们在中国传教区流徙的岁月无几而艰辛’。我所以长篇叙述这些事,是希望藉您和其他会友们的代祷,在将来的灾难中,感动天主再救助我们,以常能担起这吃力的工作。”[4]113作为一个无比聪明之人,如此心境促使他此时对曾经寄予厚望的《天主实录》产生一种“不如理想”的看法,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利玛窦的这种思想转变与他在韶州再次与瞿太素(名汝夔)交往也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利玛窦是在后者的劝戒之下放弃和尚装,改换儒士服的。这当然一方面是利玛窦在进入中国几年之后对和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地位深入了解有关,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和尚们“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意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愈况下。”另一方面也与瞿太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主流定位的清醒认识在利玛窦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关,传教士艾儒略曾经这样记载:“姑苏瞿太素……适过曹溪,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原从游,劝利子服儒服。”[8]277这些影响,对于利玛窦在思想上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使他认识到,如果天主教要深入中国的生活,它必须从儒家学说中寻找一些接触点,于是他采取与早年教会的神父们接受希腊思想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孔子:尽力保存它所包含的自然真理的全部基本观点,增加他所缺少的有关自然界的其他科学原理,介绍包含在天主教中的、由其教义所揭示的超自然真理的全部新秩序[3]19。而这恰恰是《天主实录》所缺乏的,不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将难以理解利玛窦在到达南昌之后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
虽然不能由此就如有的学者(比如韩国学者宋荣培)所断定的那样,《天主实义》就是《天主实录》的修订、补充、整理和重编,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利玛窦在经过十年之后,对《天主实录》的不足之处显然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理解,尤其是结合传教过程存在的问题,这种感受应该是很具体的。当然,这种变化应该说是与利玛窦对中国主流文化背景的深入而清楚的体会、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中国社会中佛教作为一个影响因子并没有当初所想象的那样重要,过多运用佛教用语而几乎没有引证有关儒家思想的内容而成的《天主实录》,显然难以胜任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重任了[8]277。而且他在肇庆期间,因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肤浅认知而导致的各种误解和碰撞,又大多是靠郭应聘、王泮、朱东光、蔡梦说、黄时雨、方应时等具有较深儒学素养的官员和文人学士的帮助,才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化解危机,走出困境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触动他自觉地以儒学思想而不是佛学理论为思考背景撰写《天主实义》,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利玛窦思想的升华,也是一个认识过程所达到的必然结果。
最后,利玛窦的思想转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德礼贤(P.Pascal M.d,Elia,S.J.)在其法文著作《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的观点:“16世纪以中文著述有关天主教教理的第一本著作为出版于1584年11月29日罗明坚神父所著的天主实录。此书随后即为利玛窦所著的教理杰作天学实义,即后来的天主实义所取代。”[9]这种替代关系表明的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依次递进、相互依存、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可以认为,《天主实义》基本就是《天主实录》的一种升级版。
[1]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0.
[2]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3]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M].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
[4]利玛窦全集.利玛窦书信集:上[M].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
[5]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62.
[6]裴化行.利玛窦传: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90. [7]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119.
[8]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张晓林.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M].上海:学苑出版社, 2005:17.
On the Ideological Change i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Reflection on Matteo Ricci’s Letters in Guangdong
LI Yuqi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 526061,China)
All what Matteo Ricci did in China was aimed at religious preaching.The fruits of promoting cultural ex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as unforeseen.So,his book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should be carefully studied when studying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China.In fact,there was a very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change in Matteo Ricci’s thinking,which was from satisfaction to disappointment at the book Veritable Records of Catholic Saints,a cooperative work between himself and Michele Ruggeri. The productio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was the result of such a change.
Matteo Ricci;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Veritable Records of Catholic Saints
B25
A
1009-8445(2010)04-0001-04
(责任编辑:杨杰)
2010-05-13;修改日期:2010-06-18
黎玉琴(1963-),男,贵州开阳人,肇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