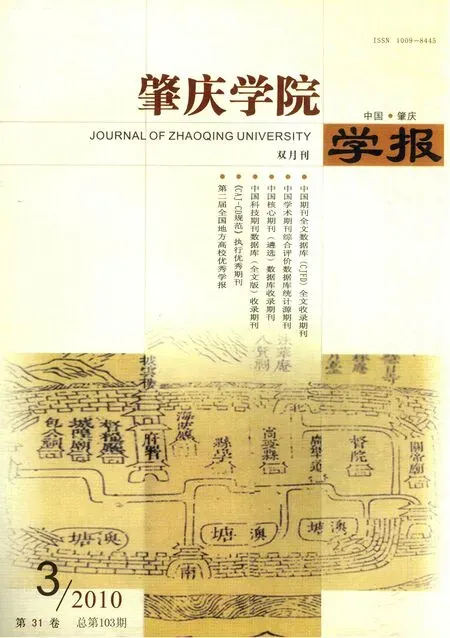唐代女性的书法教育
2010-02-16常春
常春
(西安美术学院书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5)
唐代女性的书法教育
常春
(西安美术学院书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5)
唐代女性的书法教育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无法与同时代的男性书法教育相媲美,但无论从哪个阶层看,唐代女性与以往相比都接受了更多的知识教育和文化熏陶,她们的书法教育或者来源于书馆、师长,或者来源于家庭、朋友,总之在她们非凡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下,唐代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工于书法的女性,这说明了唐代女性书法教育的发展。
唐代;女性;书法教育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延续了近三个世纪的李唐王朝一直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辉煌盛世。它上承秦汉之雄浑,下启宋明之繁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书法也继承汉魏六朝盛况而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书法文化极为兴盛,著名的书家也比比皆是。但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作为焦点的男性人物,而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来就不乏女性书家,从蔡文姬到卫夫人,从薛涛到李清照,从朱淑真到管夫人,从邢慈静到黄媛介等等。尤其在唐代涌现出一大批工于翰墨书法的女性,其中《新唐书》、《旧唐书》中,宋的《宣和书谱》、清人的《玉台书史》等书学著作中都有对唐代女性书家的书法事迹及笔墨风格等的大量记载,这种景象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
很明显,唐代女性书法的兴起不仅仅是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表现,而且也是唐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尤其是女性书法教育得到普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退和科举取士制度的兴起,教育也打破了以往严格的等级界限,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士敞开了大门。如唐人李华在写给外孙女的信中说:“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1]这一说法代表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女性教育的普遍认识,即通过对女性识字知书的教育,使女性知礼法,守妇道。然而,这在另一面也确实提高了广大女性的文化知识和书法水平。由此也可以看出,女性教育在唐代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也是唐代才女数量大大多于前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具体研究中,学者艾伯特·奥哈拉将中国女性分为四个阶层: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学者和官员之妻,贵族和统治者之妻。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2]而清代《玉台书史》一书则将女性分为:宫闱、女仙、名媛、姬侍、名妓、灵异、杂类等七个大类。[3]1基于以上两种分类方法,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将唐代女性分为宫廷女性、宦门女性、民间女性三个部分,分别对其书法教育情况进行研究。
一、宫廷女性的书法教育
宫廷女性是个统称,它具体指宫廷中的后妃、公主和宫女等人。中国古代宫廷的文化教育自先秦时代至清末一直延续并开展着,且有其相应的规章与体系。譬如专制时代都设有女官制度,担任各种职务的女官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样就促成了宫廷女性文化教育开展的可能。通过这一教育,在宫廷中聚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们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整体上远远高于名媛和民间女性等。唐代宫廷中的后妃、公主、宫女在历史上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中很多在诗、文、书、画等多个领域颇有造诣。就后妃而言,《新唐书》、《旧唐书》之“后妃传”中共记载后妃34人,其中有诗文、书法、绘画之长的就有11人。同时,当我们细读《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时,也不难发现唐代公主们总体上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她们中懂礼法、有才学者不乏其人。如太宗女襄城公主,“性孝睦,动循矩法,帝敕诸公主视为师式”。太宗女晋阳公主,善翰墨,“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4]。临川公主“工籀隶,能属文”,“雅好经书”,“犹善词笔”,所撰文笔及手写诸经,“并流行于代”[5]。至于一般后宫女子的文化教育,从《全唐诗》中所收录的众多宫女的诗作,特别是广为人们所熟悉的“红叶题诗”和“战袍题诗”的故事来看,唐代后宫女子的文化教育是比较普及的。
唐代宫廷女性的文化修养和习书风气与帝王的倡导和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分不开的。唐代帝王们的文化修养普遍很高,又都崇尚书法,尤其是唐太宗时期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编制和规模,除了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外,还增设了弘文馆、崇文馆和医学馆,置教习。而朝中高官贵族子弟多在弘文馆、崇文馆习书。皇室子弟另配有侍书一职,当时的书法大家柳公权等都曾任过翰林侍书,为太子、诸王等教授书法。唐代帝王对书学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除书学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生也必须学习训诂、书法,具体要求如《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云:‘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地方州县学生习业与国子类同。”[6]同时,统治阶级重视美术典藏的收集保存。唐高祖时期的弘文馆和崇文馆,广泛收集了书法和绘画的图书古籍,并命人抄写研摹。经过多年的努力,图书之盛近世无比。根据《唐会要》记载,至唐太宗贞观六年,御府所藏共1 510卷书画名迹。
在整个宫廷书学教育的基础上,唐代宫廷女性的书学教育也随之展开。譬如“唐代内侍省的掖庭局设宫教博士两人,掌管教习宫人书算众艺。在宫廷中亦有习艺馆,后改为学艺馆,选宫人中有文学才能的担任学士之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7]这就在制度上保证了宫廷女性的书学教育。在情感上,上之所好,下必行之。帝王们的雅趣必然带动他们身边众多的后妃、公主、宫女的追崇。相传杨贵妃也善书法,厉鹗《玉台书史》中记:“真定大历寺有藏殿,其殿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皆极可观。有涂金匣藏心经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云,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3]384究其原因,其中既有她们对书法文化本身的喜爱,又有对帝王趣味的迎合。而后一点从一些后妃、公主对帝王书迹的熟练摹写中可以看出。如高祖皇后竇氏,不仅“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又善书,与高祖书相杂,人不辨也。”[8]
二、宦门女性的书法教育
宦门女性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较之社会底层的劳动女性,她们属于衣食无忧的有闲阶层。宦门女性大多因其祖、其父、其夫等的原因,自幼秉承家训,读书习字。这其中既得他人的熏陶,也渐渐成为她们个人兴趣之所在。诚如有学者指出“在女性文化家庭教育中,一个主要的途径与方式是父母兄弟家人对其女性的文化教育,这恐怕是受中国古代家族性影响的结果,其教师的担当者一般为与女性较亲近的人,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堂伯叔父、自己兄弟等等。尤其是在秦汉以后,由于父母陪伴教育女性制度与形式的渐趋衰亡,在没有提倡女性教育的时代,父母兄弟或家族长者又不愿自己的女性在文化知识上有所委屈,就自己担当起教师的职责,来教授其家中的女性。”[9]
除了受父兄的熏陶外,有些官僚家的女子读书条件也很优越,“父兄不能执教者,往往出资延聘有才学的教师代为传授。如《太平广记》卷四四九《李元恭》条引《广异记》记载说:唐开元中,吏部侍郎李元恭有外孙女崔氏寄居家中,一日,有少年自称胡郎入见,与元恭子颇相结识,久之,少年“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崔氏)颇通诸家大义”。接着少年“又引一人教之书”,一年后,崔氏“以工书著称”。最后胡郎又引荐了一位胡博士教崔学弹琴。从文中记载的内容来看,贵族官僚家庭的女子学习条件是颇为优越的。为使家中女子教育得到全面发展,所聘教师往往不只一个;教育内容既有经史,也有书法和音乐。”[10]从这则笔记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代宦门女子受文化教育的真实状况。
也正因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唐代宦门名媛中的善书者据清代厉鹗《玉台书史》记载,其人数远远高于其他。如《书史会要》记崔简妻宗元姊柳夫人“为雅琴以自娱,善隶书”;“桓夫人,善书,评者谓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杨夫人,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11]《书苑菁华》记前人答柳柳州诗三首形容其工书善墨[12]。其一:日日临池弄小雏,远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牙敛手徒。其二:小儿弄笔不能嗔,浣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其三:昔日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衡。此外,还有刘秦妹、崔夫人、封绚、薛瑗、关氏、金銮等等一大批有文献记载的唐代宦门善书女性。
另外,唐代许多文化名人的教育就直接来自于他们的母亲。如颜真卿“少孤,母殷躬加训导。既长,博学,工辞章”[13]。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亦“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14]。试想如果颜真卿、欧阳通的母亲不通辞章,不精翰墨,如何能教育出这两位唐代的杰出人物。而这样的例子在唐代史籍中不胜枚举,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女子的文化程度。
无可否认,女性无论在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所受的教育程度都远远低于男性,而且对于她们来说,文化知识的教育只是伦理妇德教育的附庸。但在层层桎梏中,这些被压迫在宗法社会之下的女性,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着她们一切值得讴歌的天分和能力,在日常的伦理生活中苦心营造出她们的精神空间,这是一片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
三、民间女性的书法教育
民间女性主要指社会中平民阶层的普通女性。唐代世风开放,对女性的礼教约束也相对比较宽松。尤其是武则天做女皇,用女官的行为,虽不能改变整个封建制度和社会习俗,但至少对男尊女卑的礼教传统有所冲击,一些普通女性也因此增加了社交的自由,获得了广泛学习的机会。
另外,唐代州、县、乡学以及私塾家教讲学之风盛行。“依唐制,地方州县诸生习业与国子同,以合子弟进科举的要求,经学、文学、书法成为天下书生受业的主要内容。唐代明经、进士中好书、善书者不计其数。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基本体系,亦藉唐代科举制的完备而进入正轨。此后,以钟王尤其是唐楷为范本的书法教学,成为中国从太学到州、县、乡学以及私塾家教诸生都须修习的日课”[15]。同时设置书学馆,开“书学”科,设书学博士,教授文武官八品以下和庶人子弟书学。而唐代民间女性也在这次文化大普及中获益匪浅。在正史之外的地方志和文人学士的文字里,有无数对女性才华的颂歌,就是在唐代女性自己的大量诗文歌赋的写作中,也充分显示了当时女性文化水平的发展。
对平民女性的教育我们可以从最早一部表彰、记录女性的著作西汉刘向的《列女传》里获取信息。从中不难看出秦汉时人对女性道德品质、文化修养等诸多标准的认识。可以说从刘向的《列女传》开始,胆识才华和聪明智慧也曾被作为一项基本标准而长期存在。而后来贞顺节义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这直接影响了宋元以后妇女的命运。对于唐代女性教育的具体项目,李义山在《杂纂》中载有十则:“一、习女工;二、议论酒食;三、温良恭俭;四、修饰容仪;五、学书学算……”然唐代最为重要的一本女教书《女论语》中“并未提及‘学书学算’的事,可是也无反对学书的话。《女论语》很多针刺时病的话,所以常用‘算学……’的语句,既未主张或反对书学,足见书学一事在当时尚无问题。”[16]
另外,唐代宗教对普通民众的讲习教育,无疑大大提升了唐代普通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而抄写佛经箴言也是女信徒的普遍敬神行为。例如唐代的吴彩鸾工于书法,尤善楷书,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写经手。《宣和书谱》记载:吴彩鸾“自言西山吴真君之女。太和中,进士文萧客寓锺陵……萧拙于为生,彩鸾为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然不出一日间能了十数万字,非人力可为也。钱囊羞涩,复一日书之,且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得之。历十年,萧与彩鸾遂各乘一虎仙去。”[17]她书风丰满浑厚,结字遒丽,结体自然,出凡脱俗,人称仙品。
四、后记
在中国的传统史观中,尤其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女性普遍是受压迫的、受遮蔽的形象,在历史的天空下是“沉默”的一族。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压制下,多少有才华的女子被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佼佼者在历史中留存着她们的姓名和光辉的一笔。正如唐代诗人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中所称道的那样:“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唐代女性书家的兴起首先取决于有相当人数的受教育女性群体的存在。同男性书家一样,她们在这些受教育女性中出类拔萃。其中绝大多数不仅在书坛留名青史,而且在文学、绘画等方面也颇有建树。然而,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中毕竟属于从属地位,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也限制了她们在艺术中的自主性和合法性。
[1]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M]//全唐文:卷315.北京:中华书局,1983:3 195.
[2]高彦颐.闺塾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
[3]厉鹗.玉台书史[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卷44.
[4]诸帝公主[M]//新唐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5:3 645.
[5]颜真卿.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J].文物,1977(10):50.
[6]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61.
[7]蔡锋.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知识内容的考察[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4):55-60.
[8]后妃:上[M]//新唐书: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5:3 469.
[9]蔡锋.古代女性家庭文化教育的形式[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3):45-51.
[10]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7.
[11]陶宗仪.书史会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194,450-451.
[12]陈思.书苑菁华[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60.
[13]颜真卿[M]//新唐书:卷153.北京:中华书局,1975:4 854.
[14]欧阳询子通[M]//旧唐书:卷189.北京:中华书局,1975:4 947.
[15]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62.
[1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7-118.
[17]厉鹗.玉台书史:引宣和书谱[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卷44,390.
(责任编辑:杜云南)
G529;J292.24
A
1009-8445(2010)03-0087-04
2009-12-25;修改日期:2010-04-04
陕西省教育厅2009年度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7)
常春(1981-),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美术学院书法教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