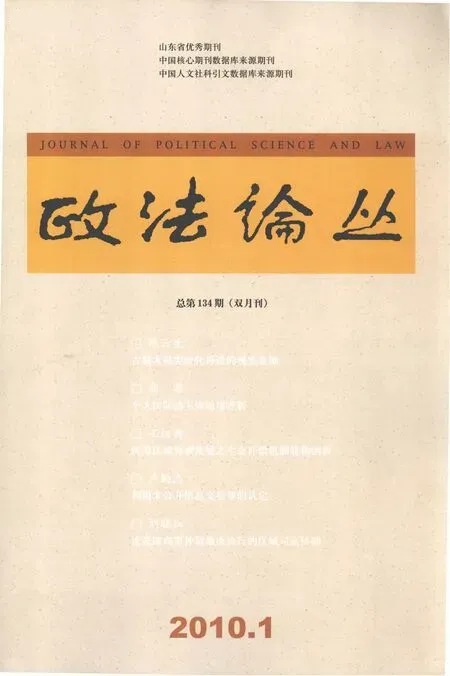略论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判断及其方法*
2010-02-15管伟
管 伟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对案件进行事实判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是司法裁判过程中必然的逻辑起点,作为法律适用逻辑起点的事实判断,其使命在于为构建法律推理所必须的小前提作准备。在将“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换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的小前提构建过程中,对“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是否可信和是否采纳的事实判断是这一构建过程的关键,其结果直接影响着法律适用的进行以及案件裁判结果的正义性。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对于法官的事实判断的正当性保障往往通过正当程序和严密的事实认定规则的设计来进行。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极为缺乏的。那么中国传统司法官是于何处寻找事实判断的资源呢?这种没有正当程序和严密的事实认定规则制约下的事实判断,又是如何保障它的正当性的。本文试图从情理、习惯以及司法官个体的经验与智识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司法官据以作出事实判断的资源,分析其事实判断正当性的保障。
一、情理判断
情理,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中国传统法律生活的全部。在传统司法官司法裁判过程中,情理更是扮演的一种全能的角色。当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则与传统伦理道德产生明显违背时,情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官确立裁判依据的法律渊源。而在审理案件事实过程中,情理又成为一种事实判断的基准。事实上,“最初对情的强调,也是从司法领域开始的。所谓情理,在其初,不过是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断狱必得先弄清案情、得到真情,并要据此案情、狱情判断,这在古人是明确的”[1]。作为一种司法技术,情理在事实判断过程中起到了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可以用以判断案件客观事实是否存在或行为是否真实,又能据以判断主观事实发生时的状态,以确立行为人行为过程中是否为故意或过失、是否合于伦理道德等。
在古代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官通过引入情理因素,以作为事实判断的基本方法,主要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的。
第一,以情理作为从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或当事人陈述及行为是否真实的基准,这是古代法官们在累积古代审判经验的基础之上所总结出来并进一步的制度化的结果。①其一,从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变化入手,利用人们在特定事件面前的基本情感体现,来作为判断案件事实或行为真伪的依据。人类所具有的这些基本情感往往是生而有之,也可谓之是一种本能。而在特定事件面前的情感流露,自然也就最能体现其行为时的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其行为的真实性往往也就最容易判断。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聪明的法官们往往从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变化入手,利用人们在特定事件面前的基本情感体现,来作为判断案件事实或行为真伪的依据。如后魏李崇在苟泰与奉伯的争子案中,[2]P349从生父对亲子的真实情感入手,阴使诈术,假谓所争之子已死,从而观察双方当事人闻此噩耗时的情感流露,从而判断出事实的真相。再如陈述古祠钟一案中[2]P432对于案件的查明,法官同样也是利用了真实盗贼在特定事件面前情感的流露而寻找到破案的线索。其二,根据行为或事实的存在是否符合人类行为的常态,即事实的发生或行为的可信度是否能够满足他人对此的合理的期待,亦即是所谓的人之常情以判断事实真伪。如程颢校年一案中,[2]P432对于老者所主张的是富民张氏子之父,并以相关文书为证的事实,法官程颢从其所提供的文书中所记载的“抱儿与张三翁为养子”中发现了破绽,因为从时间上推算,适时张氏仅二十几岁,而以二十几岁的青年以三翁之名称之,显不符人之常理,故由此判断该老者所言不实,实属冒认。其三,通过分析事物发展所应具备的逻辑属性,并进而从分析一般事理即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出发,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推理得出案件的真相。例如《名公书判清名集》中所载“吴肃吴鎔吴桧互争田产”一案则典型地体现了传统法官通过对事实发展逻辑属性的推理而做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从本案的争讼事实来看,原告吴肃所持证据是自吴鎔处典到所争田产,并持有合法有效的典契,但并未得到该田产之上手干照,只是于契约中“批破祖关去失”,而在事实上也已行权五年。而被告所持有对该田产所主张的依据是其祖卖于吴鎔之祖赤契,该契于空纸后批有“淳熙八年赎回,就行租赁元佃人耕作”。该案中事实判断的焦点就在于吴桧所持之卖契之后所批“淳熙八年赎回,就行租赁元佃人耕作”之语是否真实可信。法官范西堂认为:“元契既作永卖立文,其后岂容批回收赎?纵所赎果无伪冒,自淳熙八年至今,已历四十二年,胡为不曾交业?若曰就行佃赁,固或有之,然自吴四一至吴鎔凡更四世,未有赁田可如是之久者。”[3]P111其一,永卖之契后而附之以收赎之文,情理不通且逻辑矛盾。其二,即使所赎之文可信,但对所赎之田,田主四十二年不曾交还产业,这并不符合赎田收业的常理,其三,再假如认可其所言就行佃赁可信,但凡历四世、时间跨度如此之久的赁田显然又是情理上说不通。因此,范西堂也正是从这一系列不通情理,违背事物发展逻辑的疑点中,推断出该案争端原由实是“实以吴鎔不曾缴纳上手,寻将与元出产人吴桧通同昏赖”。
第二,作为据以判断案件事实发生时的相关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的基准。在此,情理一方面指的是案情,通过案情事实的分析来判断行为人是无心、有心还是故意,即是成为判断某项行为有无动机,是故意还是过失等等,清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曾明言:“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争险之状。衅由曲直,秋审时之为情实,为缓决,为可矜,区以别焉。争殴时所持之具,与所伤之处,可以定有心无心之分。有心者为故杀,一必干情实,无心者为错杀,可归缓决。且殴状不明,则狱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关键,审办时,必须令许作与凶手,照供比试,所叙详供,宛然有一争殴之状,历历在目,方无游移干驳之患。”[4]这里的“情”,主要指的是司法官必须从具体的案件事实出发,分析判断行为动机等“情理”要素。而在另一方面,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判断,除了分析案情事实等客观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则是与道德判断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依据来分析并判断行为主体的动机,并以动机作为判决其有罪与否及罪刑轻重的最后根据。这就是所谓的“原情定罪”,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也正如董仲舒所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5]P23当然,这种以伦理化的道德价值观作为评判行为主体动机的基准,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离了对案件的事实判断,成为一种伦理色彩极浓的价值判断了。
第三,以伦理化的道德价值观作为评判行为主体动机的基准的极端化表现有时还在于以行为主体的身份作为分析判断案件事实的真伪的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裁判中也许并非是常态,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并不乏实例。盖因中国传统社会不但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而且更是常常把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归结为道德是否净化,人心是否浇漓,同时也归之于统治者和士绅阶层能否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优秀的品质和模范行为去感化民众。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对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抱有一种理想性的追求。不但在立法中赋予其优厚的特权,而且在诉讼中,也处处维护,以维持其具有理想道德色彩的声誉。在涉及传统士大夫阶层道德声誉的场合,在无明确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裁判中,传统司法官有时宁愿相信其考虑处事的动机是合理,且有道德意识存在的。换言之,传统司法官有时也根据当事人的不同身份来判断认定案件事实。在《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不少有关于此类的案例。如在“从兄盗卖已死弟田业”一案,[3]P144-146从兄丘庄盗卖丘萱之田,自立两契,为牙卖与朱府(朱县尉及朱总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交易诸盗及重叠之类,钱主知情者,钱没官,自首及不知情者,理还。”因此,本案中的处理则必然涉及到该田的买主朱府,朱府在此项交易中动机是否为善意不知情。对此项事实的判断,法官的态度是:“朱府名贤之阀,举动悉循理法,此等交易,断不肯为,未必不为丘庄与干佃辈所误耳?”断言朱县尉、朱总领即使交易违法,以其身份“常识”不可能触法,若是有误,责任归咎于丘庄和干佃辈。而在“辨明是非”一案中,[3]P239-241再次反映出传统社会对于士大夫的道德理想的维护。本案起于韩知丞亡故后,桑百二、董三八持刀擅入韩家,但经被告之母辩称,董三八实为韩中丞之子,本欲认祖归宗而被拒,故有此争。因此,本案的焦点转入审查董三八是否为韩知丞之子的事实上。法官叶岩峰否认了被告所述之事实,其否定的理由之一就于韩知丞是一位“通经名士,晚登科第,可见洞明理义、饱阅世故,岂不知爱妾之子,犹龙生于蛇腹者也,何忍委弃于卖菜之家,经涉年岁,不复收养,乃自轻遗体如此,何也?”
中国古代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以情理作为事实判断的方法,尽管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因素,但同时也增加了案件裁判的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将其对于情理的认知凌驾于法律形式上的证据事实,比如前汉时的“何武断剑”一案中[2]P461,何武依靠情理所推断的事实并无任何可资证明的证据,而富家翁所留之遗嘱,无论从立约的形式还是约定的内容都在法律允可的范围,以现代法律思维来判断分析,它毫无疑问是法官应认定的事实。因此,法官只须依相应的证据事实,将富家翁所遺之剑断还于其子就可完成诉讼。但太守何武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官吏,从富家翁所遺之剑竟而推断出决断之意,从而推翻了法律形式上无所可疑的证据事实,但却“闻者叹服”,在使人啼笑皆非的同时,感受到在缺少了正当程序和严密的事实认定规则的制约下情理判断,实有因其主观性色彩过浓而走向任意的必然性。
二、习惯判断
习惯被引入司法领域,其意义有二,其一是在法律无明文时,习惯就成为法官寻找裁判依据的场所。其二是当案件事实或行为是否存在或真实性难以判断时,习惯也就成为法官进行事实判断的基准。事实上,在承认习惯法的国家或地区中,习惯被引入司法领域的这两种方式往往难以分开,作为一种规范形态的习惯法,它的适用,其实既是一种事实判断,又是一种法律判断,也就是,符合习惯法规范形态的行为,事实或行为的真实性往往会得到确定,同时释放出法律意义。即使是在不承认习惯法为正式法源的国家和地区,习惯仍能以法官作为事实判断的基准而进入司法领域。因为,作为具有群体意义上的习惯,是一种长时间持续并经多次反复而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群体性的行为方式,具有一种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在面对难以认定或真伪难断的案件事实时,它显然有助于法官从复杂的案件中理清头绪,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换言之,在面对即使有证据,有时也难以以对于当事人所述之事实或行为是否存在或真实的判断时,法官要作出合适的判断,往往就要分析理解当地存在的习惯或风俗,看其是否与当地的习惯与习俗相符合,并以之作为判断考量的基准,从而成为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因素之一。
那么,在中国传统司法领域,习惯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当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习惯法,学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不欲展开,暂且不论。但是习惯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被大量引入司法领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的案例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当然也是部分国内学者认可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习惯法的论证之一。但仔细分析相关案例,我们发现,习惯在中国传统司法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传统司法官事实判断的基准之一而出现的。
事实上,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群体性生活秩序的行为习惯,既存在于民众的经济及交易活动中,也广泛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存在,为传统司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提供了基准或参考。如浙江某地习惯,砌墙辄以较光滑的一面向外,较粗糙的一面向里,这种生活习惯则成为判断此墙垣所有权争议最有力的证据。再如江苏泰兴县习惯,买卖契上概写虚数,大都以七分五厘写作一亩,而钱粮仍照实田完纳,[6]P39-40这种交易习惯显然为传统司法官判断契约内容真伪提供了依据。因此,对于某些特定案件,传统司法官只有在充分了解当地通行的某些习惯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待决的案件事实进行正确的判断。正是出于上述考虑,称职的司法官员在其任上就比较重视对于当地风俗民情的理解,如汪辉祖认为:“人情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初到官时,不可师心判事,盖所判不协舆情,即滋议论,持之于后,用力较难。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傅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平。一日解一事,百日可解百事,为数月诸事了然。不惟理事中肯,亦令下如流水矣。”[7]P203当然,地方官员重视对于地方习俗民情的了解,首先是出于治理与“亲民”的需要,或可说成是如何使民众更好的守法,以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其所期望的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为其将来可能遭遇到的疑难案件的事实判断奠定基础。对于一个睿智的法官而言,要在复杂的案件审理中做到洞察秋毫,对当地的风俗习惯深加了解是其基本要求。因此,在传统司法裁判实践中,称职的司法官往往充分挖掘当地的生活及交易习惯,甚至是恶意规避法律的“恶习”、“锢弊”,从中寻找据以作出正确事实判断的资源。
如《樊山判牍》卷一“批周十四呈词”中所载原告周十四控卢孟丙欺骗钱财案中,原告所称之被欺骗之事实也并无其他有力证据以为旁证,但法官樊增祥从分析当地生活习惯入手,认为“出钱讨寡妇,乃陕西人惯技。尔此次媒定冯氏为妻,财礼追往,乃通例也。然亦何至二百五十六串之多。至外加羊酒离母钱十串,尤属闻所未闻,总由尔(想)老婆心急,人要多少,尔即给多少。谁知此意被人窥破。卢孟丙遂以事外之人,横杀一枪,使尔口越渴越不得喝水,肚越饥越不得吃肉。观呈中急喊速救四字,大有倒县求解之意,诚为可笑可怜。姑准唤案查讯。”②对于本案中原告所诉之事实,樊增祥以“出钱讨寡妇”,是陕西之习惯为根据,基本认可了原告的所诉的被卢孟丙欺骗钱财的事实,因此,尽管对原告的行为大加嘲讽,称之为“可笑可怜”,但也作出了“姑准唤案查讯”的裁定。显然,在其他相关证据不明的情况下,法官樊增祥所作出的事实判断的根据就在于当地的“出钱讨寡妇”这一生活习惯的存在。
而在《折狱龟鉴》“刘沆问邻”一案中,法官刘沆则是充分利用了民间交易习惯,对所争议的契约真实与否作出了正确的事实判断。[2]P334该案历二十年不得直而刘沆一审便判真伪,并不在于刘沆有多神奇,而是在于他对于当地“卖田问邻,成券会邻”交易习惯的了解上,尹氏之契为伪造的判断,就在于它的成立形式并未符合当地的田产买卖习惯,其真伪立判。而在《名公书判清明集》“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一案中,法官同样是通过对于交易习惯的考察,对契约内容的真伪作出了正确的事实判断。本案原告高七一通过提供相关干照证据,要求返还已归并于陈庆之田产,南宋法官范西堂在审查其所提供之干照效力时,发现干照内“无号数亩步,别具单账于前,且无缝印”,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显然有瑕疵,但这一瑕疵是否就是影响案件事实的关键因素呢?范西堂从分析当地的立约交易习惯入手,认为“乡原体例,凡立契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今只作空头契书,却以白纸写单账于前,”“显是欺诈”。[3]P103因此,本案中证据的判断和事实认定,正是以当地的立约交易习惯为基准。
而在《受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案中,法官用以判断事实真伪的基准则是恶意规避法律的“恶习”、“锢弊”。本案原告吕千五与被告詹德兴就某一田产的所有权发生争议,被告对该田持有合法的上手干照,而原告则持有被告亲立的将该田典于吕家的典契。孰是孰非,单凭双方证据则难以确定。针对出现的一田两契事实原因,法官翁浩堂分析道:“推原其故,皆是乡下奸民逃避赋役,作一伪而费百辞,故为之纠纷也。”[3]P131显然,翁浩堂对于当地民众为逃避赋役而规避法律,以假卖田产而另立户名,同时立典以为据的恶俗民风深有了解,从而使这一看来复杂的问题得以澄清,确认了该田产所有权的归属。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里,习惯由于是在一个地区内长时间形成的,它与风俗密切相关,因此习惯形成的地域性不可避免,且表现为一种散漫的,随机的经验方式。因此,要以习惯作为判断案件事实真伪的基准,不但需要梳理不同地域习惯的存在样式,更要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确立习惯认定的程序机制,才有可能使法官在纠纷解决中通过习惯掌握诉讼事实的真相,而不致于因掌握习惯“话语权”的个人因素而致案件事实被遮蔽和扭曲。显然,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诉讼制度,使习惯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事实判断资源,就颇令人怀疑。
三、经验与智识判断
中国传统司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以直觉性思维来裁断案件,判断案件事实真伪。而对此提供支持的则是他们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智识。中国古代历史中广为流传的“青天”角色,其为人所称颂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法不阿贵”的品格,而且还在于依靠他们的经验与智识,对难以决断的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中国传统社会缺乏相应的证据和程序规则的规制,不发达或落后的科技又难以为其司法实践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的情形下,依赖于司法官个体的经验与智识实现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事实判断,就成为传统司法中重要的因素。
当然,传统司法官的经验与智识对于事实判断的关键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司法体制的特性有关。中国传统司法不仅具有司法与行政不分的特性,而且其内部也缺少必要的职能分工。正如美国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司法机构或法学。县令集警察(他要拘捕罪犯)、起诉人、辩护律师、法医、法官、陪审团的职责于一身。”[8]P26事实大致如此。中国传统司法体制的特性,往往使传统司法官扮演着一种全能的角色,尽管机构内也有比如“仵作”(类似于现代法医)等专业人员,但传统社会和民众对于一个地方官是否称职的判断,往往是建立在其能否“事必躬亲”的基础之上。正如汪辉祖所言:“故遇勘案,总要亲到,转委佐杂,徒费民财,不惟不公,即公亦不足服人”。“验伤填单,例取何辜,何等慎重……,故仵作喝报后,印官犹必亲验,以定真伪。”[7]P209因此,“事必躬亲”的司法官,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社会及司法经验以及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如医学知识、勘验知识等,就难以判断案件事实,发现相应的线索,从而揭示案件事实真相,而且也不能令民众信服。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面对案情复杂多变,证据真伪难辨又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加以鉴别的情形下,称职的司法官往往利用其丰富的经验与智识,从细微处入手,从中寻找线索,进而发现事实真相,判断证据真伪。如《折狱龟鉴》“张咏勘僧”一案中,法官张咏就凭借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敏锐地观察到案件事实判断的相关线索,从而揭开了事实真相。在该案中,张咏通过观察到自述为已为僧七年的假僧额有系巾痕这一细节,从僧人不系头巾这一基本生活常识出发,推断出该犯所述不实,从而破获了一起杀人案件。显然,对该案事实的正确判断,完全是张咏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所致。难怪郑克对此评论道:“善察贼者,必有以识之,使不能欺也;善鞫情者,必有以证之,使不可讳也。实兼此二术矣,可不谓之明乎。”,[2]P441而在“江某伸纸”一案中,法官江某对该案事实的正确判断,是建立在其对“远年纸,里当白”这一鉴别纸张年代远近的基本知识的了解上。而在“章频验券”一案中,法官章频同样通过对于“券墨浮朱上”,系先用印而后书之这一常识,对一起伪券夺田案作出了正确的事实判断。[2]P310
同时,在传统司法实践中,利用物证和司法检验进行事实判断同样也离不开司法官的经验与智识的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根据司法物证和检验鉴定结论定案,仍然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只有有赖于有经验的司法官通过其经验与智识来审查判断,才有可能使事实判断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在“和琳图火”一案中,[2]P86程琳并未迷信所谓的现场所发现的物证,而是依靠其经验与智识敏锐地觉察出该物证并不可靠,在重新进行勘察实验的基础上,避免了一起可能因物证的不实而出现的冤案。在“张举烧猪”一案中,张举正是依靠其基本的法医学知识,以呼吸功能的存在与否,来鉴别生前烧死和死后焚尸之别。活人被烧死时,因有呼吸功能的存在,在火场中便可吸入烟灰炭末;死后焚尸,因人已死,呼吸运动停止,则不会吸进烟灰炭末。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了动物(猪)实验,然后进行尸体检验,获得了可靠的资料,作出了正确的事实判断。[2]P363
在“李南公捏痕”一案中,则更是综合典型体现了传统法官所具备的经验与智识,对于案件事实判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2]P380在本案中,法官李南公充分利用了其所具有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了解南方有榉柳,以叶涂肤,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置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棓伤者,水洗不落这一当地生活经验),相关的勘验知识(各有青赤痕),以及一定的法医知识(了解殴伤者血聚则硬的道理),并将其综合运用于案件事实的判断过程中,从而辨明了事实真相。
依赖于司法官个体直觉性思维下的经验与智识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的因素在内,将其正确性的保障完全维系在了传统司法官个人身上,就必然导致传统司法官在事实判断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于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却并非是建立在相关程序和严密的事实认定规则的基础之上,而是在于传统司法官品格的理想化的诉求,其实施的结果不难想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事实判断所持有的方法看,由于中国传统由儒家的圣贤教育、严格的科举制度所选拔的那些“体察民情,通晓风物”的士大夫们所充任的司法官群体,相关的法律知识储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司法行政混在一起的体制,更使法官在传统社会中所承担了多重角色,支持中国古代法官在事实判断过程中的思维趋向的背后,实质上是古代中国人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李泽厚对此评论道:“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9]P320古代中国法官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运用的各种事实判断的方法,则完全着眼于案件事实背后的客观真相,甚至不计成本、不顾形式与方法,甚至于借助于神鬼之说、卜筮、怪异之类,哪怕是对于事实的主观臆断,也要在判决中使民众认知到他的对客观事实追求的努力,并将法律事实的认定和司法裁判作为获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现今众多流传下来的所谓的名吏断案故事或判例中,为民众所称颂的往往是那些能用各种方法来获得案件事实真相的法官,至于其所用之方法和形式,则很少有人关注或提出质疑。如《折狱龟鉴》的作者对于前秦苻融通过占梦以决狱案的评论为:“古之察狱,亦多术矣。卜筮、怪异,皆尽心焉。至诚哀矜,必获冥助。是以冯昌之罪具服,而董丰之冤得释也。冯之马边非水,乃冰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曰也。苻融以意言,其事遂验。此周宣所谓“神灵动君使言”者也,岂非至诚哀矜而然欤!”[2]P6
过分重视个案事实的背后真相,却又缺乏相关证据的认定规则及法律程序的规制的情形下,将事实真相发现的责任寄托于司法官个人的品格和才智,不论是依情理判断还是依习惯判断,亦或是凭借个人的经验与智识来判断,所要求的都是司法官在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的前提下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全能角色,他既要熟读诗书,通晓风俗人情,又要具备丰富的社会生活及司法经验,并要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依赖于整个法官群体的道德自律或对其心目中的伦理目标的恪守,真可谓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但问题是,缺乏正当程序和严密的事实认定规则的制约的情况下,这个群体成员却存在着在巨大的自由裁量权面前失却了道德自律和伦理的追求的可能性,“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诱惑”,[10]P91因此,对于传统司法官的这种理想化的诉求与相关制度及程序设计的不足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事实上也是造就司法腐败的温床,这实在是中国传统司法一个无法根治的体制之病。
注释:
① 当然,以人之所情为事实判断的基准,是中国传统法官们在累积古代审判经验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判断当事人口供的真伪的方法,其典型的体现则是“五听”判断方法的制度化。根据《周礼·秋官·小司寇》所载:“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尽管“五听”断狱在形式上带有法官明显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但其中也不乏合理的因素,而且从其内在机理而言,也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心理学基础,也是传统司法官屡试不爽的判断法宝之一。
② 《樊山判牍》卷一“批周十四呈词”。何勤华教授在援引该案时将其视为古代法官以习惯为裁判依据的典型,此说当可存疑。事实上,法官在裁判中援引此习惯的目的只是为了证实案件的争议是否存在,并未涉及到处理。
[1] 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3.
[2] [宋]郑克.折狱龟鉴译注[M].刘俊文译注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Z].“命案察情形”.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 郭成伟主编.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8] [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1800年至今的历史回顾[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9]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10]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