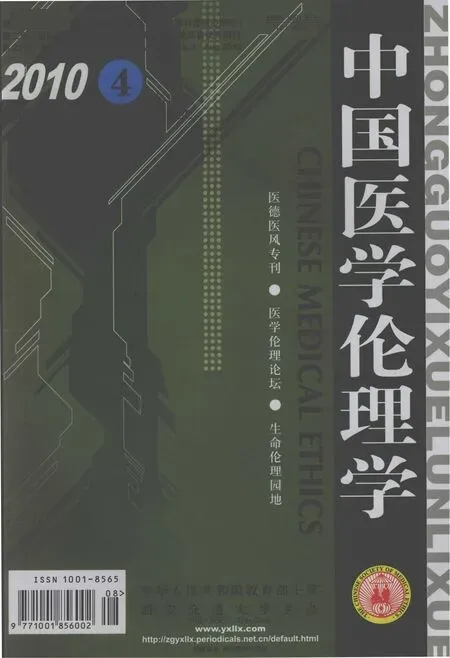器官尸捐之指定捐赠与伦理争议
2010-02-13李素贞
李素贞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 中坜)
1 前言
近年的一则新闻报道:“脑死弟肝捐兄遗恨,家属控诉——法律杀人”。案例为台中某 59岁市民,于 2008年 6月初经医师诊断为肝癌,医师建议进行肝脏移植。恰巧其弟于 6月 6日发生意外撞击后脑,医师认为可能脑死。由于其弟与兄血型与体型相符,家属认为刚好适合捐赠肝脏给哥哥。于是由其妻儿签下同意书,但医院认为于法不合,不能直接指定捐赠器官给哥哥,造成家属不满,认为法律不顾人情。因此家属在愤怒之余,认为既然不能捐给自己亲人,宁可谁都不捐。直觉上我们会同情家属,为何自己亲人不能相救?可能存在着的问题是弟弟不会说话,无法表达意愿,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器官买卖,因此,不能指定捐赠对象,也是为了保障亲属的健康安全。也就是说,脑死的器官捐赠,必须将器官送至捐赠中心登录,再从全社会等候移植名单中来进行配对。此案例突显出脑死器官指定捐赠的伦理困境。有关尸体器官指定捐赠伦理的探讨,中外学者探讨的文献并不多,在开放与禁止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本文先探讨脑死与器官移植之伦理问题,其次针对脑死器官指定捐赠的伦理性进行分析,希望从保障潜在捐赠者健康安全的立场尝试提出可行的方案,以作为拟定脑死器官捐赠分配政策的参考。
2 脑死判定的伦理问题
尸体捐赠主要依赖的是脑死者的器官,首先有关脑死的判定即存在着伦理的争议。反对脑死判定者认为脑死者犹如“有心跳的尸体”,所以摘除脑死者的器官事实上等于杀死一个濒死者,从其身上取走器官,并不是从“死者”身上摘除器官。脑死是死亡与生存的交界,借着人工呼吸器的协助,家属明明看到病人胸部仍有起伏,心脏仍在跳动,却要家属接受已经脑死的事实放弃治疗,若家属未接受详细的解说,常易造成无法认同的医疗争端。脑死的判定,主要是根据脑干死的观念制定的,由于目前医学认定若是脑干死亡,即使使用呼吸器取代呼吸功能,再加上医疗最新仪器监测,给予最积极治疗与努力,仍无法长期维持病人心跳,脑死病人会很快的死去。实际上病人已经“脑死”,并不是谋杀。
其次,脑死判定若不谨慎,可能导致病人“提前”死亡。如邱浩彰医师所言:“虽然制定了严谨的脑死判定标准,但执行层面若有偏差,或不熟悉判定的步骤程序,容易造成误判或被同仁质疑有放水之疑。”[1]换言之,若主持器官移植医师对器官需求心切,或加压于脑死判定医师,则可能导致其做出不客观的判断标准,造成病人潜在之伤害,如器官过早被摘除,或未达脑死程度而被判脑死,即违背不伤害的伦理原则。因此,为了客观,并取得家属之信任,脑死判定医师会希望为病人检察脑干功能时,家属最好在场,让家属了解病人实际上脑干已经死亡,以减少家属的心理压力并争取脑死判定的认同。
一般对脑死判定的另一疑虑是,脑死者是否不被当人看?当外伤病人宣称脑死要尸体捐赠时,是否受到放弃急救治疗的威胁,因而影响到应有的医疗质量?然而事实刚好相反,当有严重脑部受伤病人送到急诊时,医师通常需要当场决定病人是否有存活可能,以决定是否急救。若认为无存活可能,则放弃急救,以免面临为病人装上呼吸器后要拔除呼吸器之困境。如果家属表示脑死后要器捐,那么医师没有心理负担,脑部严重受伤的病人反而可以得到适当的急救。如器官移植权威史达策医师(Starzl)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移植手术的一个重大附加价值是,促进严重受伤病人的照顾品质和这些照顾措施的适当应用。”[2]显然,临床上若病人急救最后仍然脑死,为了维持此病人其他器官的有效机能,那么必然会维持良好的医疗照顾品质。
3 脑死器官指定捐赠的疑虑
脑死器官是否可以指定捐赠,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可以预立遗嘱或书面同意,指定某些人“受赠”我有用的器官。然而,指定捐赠对象可能涉及器官买卖之交易行为,除非遗嘱上清楚说明器官捐赠是无偿的,换言之,必须载明被指定的受赠者不需负担任何费用。第二种情况,若是病人处于脑死状态,由最近家属同意器官捐赠,家属可以指定吗?若是指定给朋友或陌生人,同样的很难排除有酬劳的器官交易,甚至器官买卖。第三种情况,若是刚好自己的近亲需要器官捐赠,那么可以先指定给自己的亲属吗?从亲情考量,指定器官捐赠是亲戚关系的相互关怀,较不涉及器官买卖问题,应该较为可行。毕竟器官属于稀有资源,若是死后器官能再利用,且能嘉惠自己的亲人,那么脑死后之尸体捐赠,不只是遗爱人间,而且是延续着自家人的生命,有如自己重生一般。可能的伦理问题是,须考量如何保护潜在捐赠者的健康安全,在维系亲情之际,确保尊重生命的权益。
4 潜在捐赠者健康安全之保障
对一般潜在捐赠者而言,最重要的伦理问题是可能受到伤害的风险,甚至是间接导致死亡。而对脑死器捐者方面,一般可能的伤害是担心从脑死判定滑向谋杀之可能性。如学者徐宗良等指出:“如果脑死亡没有明显的界线和标准,可能会成为谋杀的一种最有效的掩护。”[3]换言之,为了器官移植,救活了一个人,却牺牲了另一个人生存的权利。
若是脑死者指定器官捐赠给他人,那么难以避免发生器官买卖之情况,也因此,目前法令并未开放指定器官捐赠。若是将脑死者指定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亲属,那么器官买卖的疑虑可大部分排除,存在着主要的风险是其近亲可能为了获得器官而犯罪。设想若近亲可以被优先指定为脑死者器官受赠者,不用登录排队等候,那么若是居心不良的亲人认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才是最重要的,则周遭的亲人有可能变成潜在捐赠者,而将面临健康安全的威胁,随时有被陷害或谋杀等危险,或是脑死者家属可能受到居心不良的亲人要挟强迫同意捐赠器官。
如何让脑死者指定器官捐赠优先受惠于亲人而又没有上述之风险?
第一,脑死者的代理人不能是器官受赠者,就是配偶也是一样。设若亲人甲为了得到器官捐赠导致亲人乙意外脑死,则是否获得器官捐赠不是由亲人甲自己做决定,如此亲人甲就不一定可依其意愿得到器官。又如妻子意外脑死,其丈夫刚好是等待受赠器官者,那么妻子脑死后之器捐不能由其丈夫来决定,而必须由其父母或子女来决定,否则受赠者同时是代理同意者和受赠者,有球员兼裁判之嫌疑。
第二,造成脑死者意外直接或间接肇事者不能是器官受赠者。如此若亲人甲是造成亲人乙意外死亡之肇事者,那么虽是至亲,亦没有资格获得器官捐赠。
第三,确保脑死者之代理同意人没有受到不必要的要挟或恐吓,而应受到尊重。换言之,虽然一般认为脑死者的器捐是值得鼓励的利他行为,但这并不表示拒绝器官捐赠在道德上就是错的,也不表示没有捐赠器官给需要的亲属是不可谅解的。
第四,弱势者的保护。若是有亲人是靠人工机器维持生命,或是呈现植物人状态,他可能是潜在的捐赠者,但要确定的是他仍活着,所以其生命的维持应考量其最佳利益,生存权益不能被忽视。不能因为有其他亲人等待器官移植,而不考虑他有可能复原的机会。换言之,弱势者的积极治疗权利可能被漠视,而被期望尽早成为尸体器官的捐赠者;或预设他的死期以符合器官受赠者的器官取得时间上的方便。如有亲人病重,则可能被要求不要进一步治疗,选择提前死亡,类似自愿消极安乐死。而亲属中若有植物人,可能会被要求同样对待,以便其有用之器官可以贡献给需要之亲人,导致非自愿性安乐死。这种安乐死伦理上可以接受吗?显然不能,因此弱势者的保护,最好能尊重其自我意愿,若最亲家属作为其代理人,也应当以弱势者最佳利益为依据,以避免弱势者提早被判死。
第五,有人担心若是脑死者的器捐可以优先提供给亲属,那么可能发生家属急于救人,于是采取自杀手段,造成自杀人口增加。家属会做我们认为的“傻事”吗?最有可能的自杀者是父母,为了抢救其子女,使其得到有用器官改善其生活或延续其生命,于是“一命救一命”选择自杀,将器官捐给子女。另外,若选择自杀,则不论跳楼、服毒或烧炭自杀,其器官一定会受损,不只造成亲人之哀伤,大部分器官亦无法有效移植,达到捐赠目的。Gillon指出“此共识是不可怀疑的,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都没有人应该为了维持他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将器官捐赠给他人。”[4]换言之,从器官移植伦理上,自我牺牲的奉献在道德上是被反对的,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都不应该为了救助他人(甚至是自己的至亲)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脑死器官优先指定亲人方面,自杀不只是应被禁止,而且是要预防的。
5 利他与利己之伦理
在脑死器捐上优先指定捐赠给亲人并不违反人们对生命关爱的观念。从关怀伦理的观点,亲属之间的关怀,如父子、手足之情,是自然的关怀情感,如诺丁斯(Nel Noddings,1984)认为关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关系性,在关系建立中,自然的关怀是最原始的,有如母子关系,是自然而有感觉的。[5]同样的,Held认为关怀伦理学对于关怀的对象主张“由亲而殊”的道德等差性,反对“一视同仁”的道德规范。[6]换言之,其关怀的思维应该是先考虑自己亲属的需要,再考虑其他人。
从照顾自己人的立场出发,伦理学者 Singer(2005)亦认为我们的本能倾向于首先帮助与我们关系亲近的人,因为我们觉得对亲人的义务比对同胞公民的义务更强烈。其道德的基础在于优先帮助自己人,是形成关爱与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责任机制。[7]若我们认同首先照顾自己人之伦理,那么尸捐优先指定给亲友虽是一种类似利己的私人道德,但是却是符合道德观点的,因为若是与陌生人的利益相比较(捐器官给陌生人),则我们的本性应该是更愿意促进自我与我们近亲的利益。以此思维,对一个脑死者而言,虽然其器捐是由代理人书面同意,但从自然的关怀,其亲属是关系最密切者,应具有指定优先性,必要时其他器官再捐赠给需要的他人。
吾人期望脑死器捐亲人可以优先受惠之分配原则可以顺利推动,也希望因此带动器官尸捐之风气。但是在“亲人优先等候”的原则下,器官捐赠必须遵循不伤害等伦理原则。
[1] 邱浩彰.脑死判定:法律与医学伦理[J].台湾医学,2004,8(4):595.
[2] 史达策.拼图人—— 一个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的回忆录[M].林哲男,译.台北:望春风文化,2007:180.
[3] 徐宗良,刘学礼,瞿晓敏,等.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93.
[4] Gillon,Raanan.Transplantation and ethics From Thomasma D.C.and Kushner T.,Birth to Death-Science and Bioeth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11.
[5] 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方式[M].于天庆,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6.
[6] Held,Virginia.The Ethics of Care:Personal,Political,and the Global[M].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6:98.
[7] 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M].刘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27-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