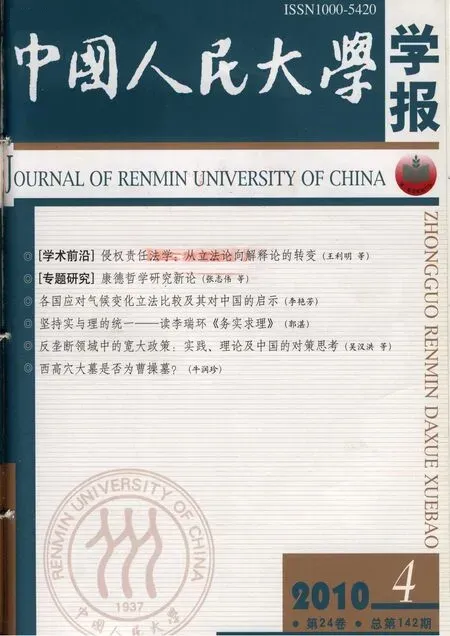“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
2010-02-10刁克利
刁克利
“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
刁克利
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作者是什么》是现代作者理论的两篇最著名的论文,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与作者建构的争论。澄清作者与作家概念的混淆,把文本阐释中的作者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进行分界有重大理论意义。作家在文学理论史中有不同的形象。作家重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作家理论、作家批评与作家生态,它们各有不同的研究资源、内容和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作家重建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就当代文学理论而言,回应巴特提出的“谁在说话重要吗”的质问仍然重要。
作者之死;作家重建;作者理论;作家研究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者是什么》是现代作者理论的两篇最著名的论文,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作者之死”的争论与作家重建的反思。澄清作者与作家概念的混淆,区分体现文本意图的“作者”和创作文本的“作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重建作者理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一、关于“作者之死”的争论
关于作者的研究,20 世纪最著名的文论莫过于巴特的《作者之死》和福柯的《作者是什么》。巴特的“作者之死”不是说作者不再写作戏剧、小说和诗歌,而是说这些文本的作者在阐释中已不再重要,甚至会压制读者,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其实,早在形式主义者那里,当他们用“文本”(text)这个概念取代传统文论中的“作品”(work)时,就切断了作者与文本的联系。后来,新批评理论提出所谓“意图的谬误”,明确指出阐释中重要的是文本而不是作者的思想。福柯回溯了作者概念的产生,认为作者在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才逐渐被看成是他们创作的文本的所有者,那时,所有权制度和版权观念才建立起来。[1]
巴特和福柯提出那么极端的说法,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学的观念,所改变的是文学批评的方向。他们把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看做是作者的发端,认为作者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和个人主义高涨的结果,即现代的作者是一种人为的构建和社会的产物。可以看出,巴特和福柯否认的不是作者创作文本这一事实,而是反对将作者看做历史人物的批评方法。他们反对试图精心重构作者作为人物的历史角色,理由是,这种角色是压抑性的,会限制读者的自由。为了读者的自由和阅读狂欢,作者必须死掉。此后,很多理论家都竭力从不同方面证实作者之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①相关的论文除了《作者之死》和《作者是什么》之外,还有:Merold Westphal.“Kierkegaard and the Anxiety of Authorship”(《克尔凯郭尔和作者的焦虑》),David Weberman.“Gadamer's Hermeneu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Authorial Intention”(《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作者意图追问》),Jason Holt.“The Marginal Life of the Author ”(《作者的边缘化生活》),Peter Lamarque.“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 Analytical Autopsy”(《作者之死:分析报告》)等。比如,皮特·拉马克(Peter Lamarque)在《作者之死:分析报告》中,从四个方面检查了“作者之死”和“作者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作者的诞生发生在现代时期,只是在中世纪以后的某个时间点文本才被视为像现在这样的作者。他仔细检查了“作者之死”的含义,指出一个文本的作者行使分类和限制的功能,而不是指一个写作了文本的人。[2](P319-331)这些论述,和解构主义 一道,使得“作者之死”和读者狂欢理论被普遍接受,作者从文学阐释以及文学理论构架中黯然失色,直至逐渐消失,成为被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的20世纪留下的诸多具有颠覆性和理论冒险的遗产。
当然,对作者之死的质疑和回击也时有所闻。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在《作家、文本、作品、作者》一文中,对福柯所阐述的“作者是什么”的理解和解释是,福柯难以把作者作为一种功能和作为一个实在的人区别开来。他对作家和作者的区分是:作家是一个牢固局限于具体境况之内的历史人物,这个具体境况即促使文本产生的原因;而作者则是为读者所理解的、产生了那个文本的任何人。作者的这种角色有更多的阐释自由,隐含于作者功能中。[3](P267-291)
尼古拉斯·帕帕斯(Nickolas Pappas)在《作者身份和权威》一文中指出,强调抗拒权威是福柯的一个主题。帕帕斯建议把对作者意图的注意转移到读者动机上。他以阅读普鲁斯特、尼采和柏拉图为例,认为对这些作者的尊重并不必然等于尊重他们权威。[4](P325-326)
罗伯特·斯坦克(Robert Stecker)在《表面的、隐含的和假定的作者们》一文中,讨论了表面作者、假定作者和隐含作者等概念。他认为,区分文化构建的作者和真正的历史中的作者没有实质意义,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如果关心作者意图,就没有必要建构作者。[5](P258-271)
琪瑞尔·沃尔克(Cheryl Walker)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作者》中指出,在阐释中建构的作者角色对女性主义批评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她们应该站在巴特和福柯一边来反抗作者权威和对读者的压抑,另一方面,也应该支持作者作为人的真实存在的观点,以此来推动和提升那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妇女作家的地位。沃尔克的结论是,虽然我也许不希望把文本当作那些作者的私有财产,但我也不愿意失去那种至关重要的联系。[6]
乔基·格雷西亚(Jorge J.E.Gracia)在《作者理论》一文中,进一步明确区分了创作文本的那个真实的“历史作者”和我们在阐释文本时创造出来的作为历史中介人的“假设历史作者”。他支持更细致区分二者。他认为,历史作者是生产文本的真实的人。假设历史作者是一个建构,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那个历史作者的复合体。因为我们关于那个历史作者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和近似的,我们的假设历史作者是那个历史作者的不完美的对应者。作者建构绝对不是武断的,而是尽可能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7](P161-189)
威廉姆·埃文(William Irwin)在《意图主义和作者建构》中认为,意图主义者可以从作者建构中受益,也需要作者建构。[8](P191-201)埃瑞克 · 布朗森(Eric Bronson)在《塞万提斯之死与唐·吉诃德的生命》一文中,检查了作者死后这部名著的生命,得出的结论是:对唐·吉诃德的完全不同的阐释实际上和塞万提斯广阔开放的意图相吻合。[9](P205-216)
从以上关于作者之死和作者建构的诸多争论中,可以得出两个启示:一是在已有的作者理论中,对作者的重建主要是在文本解读的层面上,立足点停留在巴特所框定的作者原意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关系上;二是区分体现文本意图的作者和创作文本的作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重建作者理论的必要前提。
二、作者还是作家
作者还是作家?在巴特提出“作者之死”以来,这种概念的混淆一直存在。那么,果真存在“两个作者”吗?答案是肯定的。
其一,具体文本中的作者。这个概念带出的相关问题是:作者与文本是否有关系,作者是否一定要死去才能带来读者的狂欢?他的意图是否真的重要,在何种程度上重要?对作者与文本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巴特的现代作者理论和传统的作者理论的根本分歧。否定作者与文本的联系,忽略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是巴特和福柯的作者理论的支点。注重作者意图在文本中的体现,强调作者与文本的必然联系是传统的作者理论的基本观点。这种分歧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和批评实践。
与此相连的一个事实是:必须是在文学文本发表之后,作者意图与文本阐释是否关联才能成为一个命题。没有读者阅读的文本不成其为作品的说法也是基于这个基本事实。所以,巴特的作者理论和意义阐释只能发生在文本发表之后,关注的只能是读者阅读中的具体文本。
其二,现实生活中以文学创作为诉求的作者。这个概念带出的相关问题是:作者如何创作文学作品?作者的素质特质构成为何?通俗地讲,这些问题就是:谁在写作,谁能够写作,如何写作,为什么写作?文学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文学有何期望,对文学与人生、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理解?他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生存状况、精神存在和情感诉求如何?
与此相连的一个事实是:在文学创作之前和创作过程中,这些问题就有研究的必要,并且可以进一步延伸:如果文学作者是一种职业,他和其他职业比如科学家、工程师、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文学是一种精神存在,它和其他的知识领域和作为精神存在的宗教、哲学和艺术的区分在哪里?这些问题远远超越了具体文本的阐释。
从像巴特和福柯一样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那里获取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有些冒险。要回答现实生活中以文学创作为诉求的作者所带出的上述问题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换一种思路来看,如果能从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那里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有益于文学理论的建构。这里包含着一个作家和哲学家不同的思考起点和思考方式,即作家从创作的源头和文本的产生思考文学的问题,哲学家和批评家惯于从文本本身和文学生产的结果开始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所以,对作家创作动机的探询包含了对文学产生意义的体验和追问,包含了对文学产生之前、创作过程之中的体验和了解。这种思路至少对哲学家和批评家的思考是一个反驳、矫正,至少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作者理论的重构首先要区分“作者”和“作家”,进而确立“作家”的概念。被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至解构主义所精心营造和构建的“作者”概念显然不适合回答上述相关问题和延伸问题,因为这种区分远远超出了作者与文本是否相关这个问题的范畴。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在一起的是“作家”,就是深谙文学魅力、为之折服、并下决心为之增添荣耀并倾心其中,尽力为之,以文学为精神寄托、职业追求和思想所依的那一类人的一个称号。这可以是一种职业,一种精神生活领域的从业者、追求者,一种在现实物质世界中从事以虚构和想象为主要事业的人。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不管这种追求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这种精神追求的本身具有的启发性应该得到重视。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和态度。他们应该被称为“作家”(而不是“作者”),他们的创造应该被称为“作品”(而不是“文本”)。
这种“作家”,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所有文学形式的创作者的一个合称,一个文学的书写者和创造者。他们的创造不仅是供批评家分析阐述的“文本”,而且是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对生活的深度观察与思考密切相连的“作品”。作品是他们的生命体验。如果能把这种体验和观察过程挖掘、还原,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会给我们更多更丰富的启示。这超出具体文本的启示,而与读者自己的状态相关。
根据以上的阐述,作品阐释中的“作者”和创作作品的“作家”是两个概念。“作者”是文本阐释的产物,是一种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是虚构的、阐释中的,因而是多变的;他产生和出现在文学作品完成出版流通并被阅读批评之后。“作家”是具体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存在;他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与文学作品的产生相伴相随,并在作品中体现和永生。虽然可以是同一个人,但一个是人的文本属性,一个是人的现实存在。
作者不等于作家,正如文本不等同于作品。文本是批评和阐释的素材,作品是有传统光辉和生命力的独立的存在。任何文本都是作为构成作家作品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作者到作家的认同,可以不但体会作者阐释的一切,包括文学技法、形式、素材和内容,还能体验作家的生命和思想,体验人类思维的高度、情感的强度和胸怀视野的广度。对于作家,我们遗忘了很久,我们忽略得太多。
三、作家的责难与辩护
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所谓作家,也可以称为诗人、艺术家和作者等。由于诗歌的历史最为悠久,由于诗歌在人类大多数时期都是现在意义上的文学的主要形式,也由于诗歌最能代表文学的品质,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诗人”这个称号被普遍用来指称文学的作者。
在西方文论中,诗人曾经被定义为很多不同的角色。在《伊安篇》中,柏拉图诱使可怜的伊安承认,“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10](P8)。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诗人描述成模仿者,诗人的模仿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他给诗人的罪名是:不真不善。因此,在他理想的城邦里,不准许有这样的人。柏拉图同时也为诗人重返理想国开出了必要的条件:“她不仅能让人愉快,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有益。”[11](P80)这样的诗人方可准许进入城邦。诗人的宿命从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站在理想国的城门外候审。亚里士多德从一个新的角度定义了诗人:诗人写诗乃是出于人喜爱模仿的天性。“诗,按照诗人的个性,分为两种:较庄重的诗人往往模仿高尚的行为,较轻浮的诗人则模仿卑劣人物的行为”[12](P6)。亚里士多德对诗人的看法简单的概括是,诗人应该回来,回到人间。
由于柏拉图的巨大影响,西方文论史后来对于诗人的定位,都是在把诗人请进来还是赶出去之间摇摆,或者都是对诗人合法性的辨与驳的延续。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赞成诗人的合法性和诗的功用。他觉得,诗之用大矣。好诗贵在“寓教于乐”,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诗人之用大到驯服蛮荒民族,甚至野兽,教化风俗,传播文明,指导人生,小用则能使书商赚钱,诗人扬名,作品畅销海外。朗吉努斯从诗歌风格与诗人心灵的密切联系的角度论述了诗人培养崇高风格的五种途径和重要性。他说,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养成伟大心灵的途径是:到大自然中观高山飞瀑,在古代经典中修养品性,同时既须挣脱奴性的枷锁,又要能够超越物质的引诱。
对诗人的责难一直不绝于耳。诗人们的辩护同样前赴后继。在神学统领一切的中世纪,奥古斯丁以上帝的名义斥责过诗人模仿的拙劣。文艺复兴时期,斯蒂芬·高森把诗人和吹笛手、演员、小丑等放在一起,把他们比作国家和社会的蝗虫,要求对之展开痛快的严惩。他反对诗的理由是:诗是谎话的母亲;诗是腐化的保姆,使人染上许多瘟疫性的欲念。针对斯蒂芬·高森锡的责难,德尼爵士为此写下著名的《为诗辩护》,对其所责难之要点逐一进行了反驳。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的世界原是铜的世界,诗人则为人类铸造一个黄金的世界。
另一次比较著名的论战在两个私下里关系不错的好朋友之间进行。英国作家托马斯·皮科克(Thomas Peacock)于1820 年发表了《诗的四个时代》,对现代诗人提出了批评:在科学突飞猛进、使人类生活舒适、给世界带来文明的现代社会里,诗歌只是一种不合时宜、毫无用处的东西。“今天的诗人,是文明社会里的半野蛮人。他生活在过往的岁月里。他的观念、思想、感情、联想,总是带有野蛮的风俗、已废弃的习惯和被破除的迷信。他的理智的发展宛如蟹行向后倒退……今日的社会情况下,一个作诗的人是一个虚抛自己岁月的浪子和一个夺取他人光阴的强盗。”[13](P69-70)次年,雪莱以《诗之辩护》为题,为“被侮辱的缪斯”进行了全面的辩护。他激情洋溢地宣称:“诗人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表现了连他们自己也不解是什么之文字;是唱着战歌而又不感到何所激发之号角;是能动而非被动之力量。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4](P177)
在为诗人正名的论述中,几乎所有文论家都对理想的诗人形象寄予深深的厚望。柏拉图希望诗人能成为安定城邦、教化青年的良师,贺拉斯认为诗人是寓教于乐的榜样,朗吉努斯的诗行回响着一颗伟大心灵的激荡,普罗提诺的诗人心灵映照着绝美的神光。对于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诗歌是对上帝荣光的赞扬。华兹华斯把诗人定义为“一个向全人类说话的人”[15](P655)。近代思想家叔本华寄予诗人解脱生之苦难,尼采祈盼诗人超越痛苦、超脱生死而精神飞扬,海德格尔更把看护人类诗意栖居的使命郑重托付于诗人。
作家消隐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久已有之。自然主义提倡作家在作品中主动隐退,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意识流创作中将作家定位为“漠然的上帝”,一边静观故事的发生,一边漠然修剪自己的指甲等等做法,则是作家一种主动求变的写作技巧和策略改变。
作者曾经被神化、被人化、被吁请召唤过、被放逐肢解过。他可以是神性的分有者,也可以是人性的集大成者;他可以与民族历史社会大义相提并论,也可以将他的私欲本能剖开来作精神分析;他可以被搁置在文本批评的边缘,也可以被看做阅读接受的一个对流源;他可以是文化生产活动中的一环,也可以在快乐的阅读游戏中被视而不见。在长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作家以不同的面目穿行了长长的历程。
四、作家重建的方向
从以上关于文论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作家”这个词的界定范畴:作家是历史现实中的作家,是创作作品的作家,是贴近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作家,而不仅仅是作为文本阐释的作家,不仅仅是作为心理分析的作家,不仅仅是存在于作品中的作家。作家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称谓,而且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也可以指称作品产生前和过程中的作家。关注作家包括关注他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存在,比如作家生成的外部文化语境、写作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还有作家自身的生成规律,如作家的教育背景与文学思想的形成等。
把作家缩减为作者,不是简单的名称的改变;从作者到作家,同样也不是称谓的不同。由“作者之死”到作家重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还原,不是对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至解构主义所精心营造和构建的作者概念的还原,以及对古典文论概念的简单的循环;而是一种对20 世纪至现在的文学批评遗产的反思。这种由作者到作家的研究重心的改变还意味着文学边缘化大背景下文学理论构架新的方向。
对“作者之死”的误读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文学的持续不断的被边缘化:一方面是文学批评自说自话,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后来的“小说死了”、“文学死了”、“理论死了”以及“理论之后”的理论、“后现代之后”等理论表述;另一方面是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理论家热衷于论述“作者死了”,作家仍然在写作,批评家仍然从文学创作中获取批评的养分。经常有人问:作者死了,作家还写什么?文学死了,为什么还有写作?理论死了,文学研究何以为继?这些都是由于概念的混淆而导致认识的不清。每每这时,我们总能看到作家和读者对理论家的冷笑。
现代文学批评的巨大缺憾是:对于文学的现象,我们一向阐释得过多;对于文学的生成,我们已经遗忘得太久。以至于当“作者之死”被提出之后,很长时间,我们无法回应,我们亦无所适从。其实,对上述问题,简单的回答是:作者死了,作家还活着;作者可以被肢解,作家必须精气神一体。文本可以被解构,好的作品却常读常新。一种理论会死亡,文学生生不息。因为作家和文学同在,固守在文学的源头,和文学的本原是一体。
所以,区分作者和作家、文本和作品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换言之,在新的文学理论的建构中,作家应该重新归位。在商业主义甚嚣尘上、所谓读图时代业已来临的当今,在新的文学理论的版图上,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渐行渐远的轨道上,从《作者之死》的思路上拉回来,重建作家研究,重视作家研究,不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的重建也许还是要从关于文学和作家的基本命题开始。文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文学是因人而产生的,因作家的书写而存在的。从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说,文学的状况与作家的境况密切相连。所以,重视作家研究,有回到源头的意思。从文学发生的源头开始,对于找回文学的意义,唤回人们对文学的热情是可能的。对于新的文学理论架构是必要的,至少是一个可以而且可能的途径。
目前的文学现状是:实际上投身写作的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博客、个人空间等数不胜数,写作者渴望表达自己,但水平良莠不齐,迫切需要文学创作指导和作家培育。什么人可以成为作家?即作家需要什么要的心理机能、素质特征,或先天禀赋等。如何成为作家?即作家必要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写作环境与指导,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等。成为作家意味着什么?还有,作家与读者、批评家及出版者的关系是什么?在很多职业都在进行职业咨询和就业指导时,对作家的这种研究不应该显得荒唐。还有为什么写作的问题,等等。对类似问题,其他的行业也许不需要回答得特别清楚,作家却要一直面对,永远不能回避。这些都应该被纳入文学理论和作家研究的范畴。
因而,作家研究要有新的方向。作家理论的建构要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重视作家研究,重建作家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进行拓展和深化。
(1)作家理论:以西方文艺理论史为资源,研究作家的产生、界定和职能,即以作家是什么、作家为什么写作、如何写作、作家的心理机制等为核心命题,研究作家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与文学、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家以及他创作的文学与其他知识领域的不同和联系,以及作家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这是文艺理论史的基本格局。
(2)作家批评:以国别文学史为资源,以作家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作家个人创作与文学潮流的关系为中心,研究作家作为个体的产生、生平与创作的关系、创作特点的形成和概括,以及对文学史的贡献。这是传统作家研究的内容,和国别文学史的目前状况。
(3)作家生态:以作家的当下存在为研究目标,考察作家与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研究作家产生和成长的禀赋特征、早期经历、教育背景、写作环境、职业身份、素质特征、作家角色特征与定义,以及写作目的、个人写作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作家与读者及批评家的联系等。这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研究领域。
重视作家研究,要回顾过往。文论史的资源中,实证主义的作家传记在各种文学选读中依然适用,精神分析对作家的潜意识的探讨、直觉主义的分析、象征主义的意义仍有启发。作家传记与作品产生的关系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重视作家研究,要重新发现、研究很多新问题。作家的角色需要重新界定,作家的教育背景、写作环境、成长历程值得关注,作家与读者、与批评家的关系应该密切,作家本人对文学的理解应该重视。
五、结语
“谁在说话真的重要吗?”[16](P16)巴特在《作者之死》的最后,借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这一句话提出问题。
我也想提出同样的问题。对于被任意阐释的作者来说,对于“狂欢”的读者而言,“谁在说话”的确没有太大的重要性,不过是多了一种说话的方式,多了一个恋人的“絮语”。而对于以作品为精神诉求的作家来说,这很重要,或者说,至关重要。中国当代作家莫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17]《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在说话,意味深长。能解开其中味,会收获很多。
文学是人类深沉的需要,一位美国诗人如此说。[18](P120)从对“作者”的种种理解和阐释中,我们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从“作家”那里,这种断言比比皆是。对同样的文学,会有如此不同的判断和结论,是我们思考和对话的方式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本身遇到了问题?这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命题。
[1]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 ?”.inJosuéV.Harari(ed.).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2]Peter Lamarque.“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 Analytical Autopsy”.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30 ,No.4 ,1990.
[3]Alexander Nehamas.“Writer ,Text ,Work,Author ”.inCascardiAnthony J.(ed.).Literature and the Question of Philosophy.The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Nickolas Pappas.“Authorship and Authority”.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47 :4 ,Fall ,1989.
[5]Stecker Robert.“Apparent ,Implied,and Postulated Authors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87(11).
[6]Cheryl Walker.“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uthor ”.Critical Inquiry,1990(16).
[7][8][9]William Irwin.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Author.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2.
[10]《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1][15]Vincent B.Leitch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York:W.W.Norton Company,2001.
[12]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13][14]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16]Samuel Beckett.Texts for Nothing.London:Carder and Boyars ,1974.
[17]莫言:《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载《文学报》,2000-03-23 。
[18]刁克利:《诗性的对话:美国作家访谈与写作环境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责任编辑 林 间)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riter
DIAO Ke-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d “What Is an Author ?”are two most influential essays in modern author theory,leading to fierce debate concerning the death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author ,among the debate there appears the ambiguity and even confusion of the author concept.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ve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author (s)”and clarify the difference of the author in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the writer in realistic life.There have been various images of th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critical theory,and the writer has been attacked and defended in different ways.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riter can be based on three aspects :the theory of the writer ,the criticism of the writ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writer ,each with relevant resources ,methodology and resolution.It matters to respond to “What matter who's speaking”,aquotation by Foucault at the end of his essay,as for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writer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death of the author ;resurrection of the writer ;author theory;writer study
刁克利: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