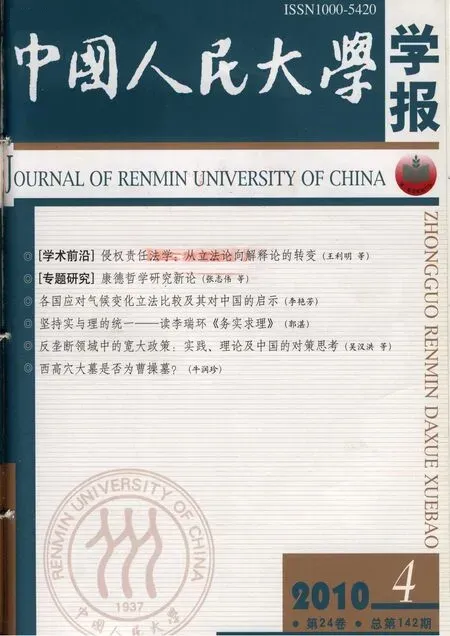儒学向经学转变的意蕴及超越*
2010-02-10王鸿生
王鸿生
晚清皮锡瑞言“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1](P19)。徐 复 观 认 为 此 说 “在 历 史 中 很 难 成立”[2](P6),称经学发端于周公及周室之史,由孔子及孔门奠定基础,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有发展。[3](P6-53)范文澜1941 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新哲学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所以经也托始于西周,周公是其代表人物。这三论各有所据,但均未虑及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若着眼于中国传统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演变,“儒学”与“经学”有不同含义,可言儒文化的根在西周,儒学乃发端于孔子,经学则始于汉。
历史地看,西周有儒文化但无儒宗,周公是权势者而非儒者,其言多是“诰”、“命”,而非“论”、“语”。言儒学发端于孔子,盖因孔子以鲁国布衣之身论仁说礼,当时并不被天下诸侯王公认同,却堪称一家之言。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始与皇权体制建立特殊关系,“孔孟之道”逐步转变成“纲常名教”,儒学完成“华丽的转身”。此后,经化的儒学从伦理层面为皇权的正当性提供文化解释,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也被皇权压缩了发展的空间。直到晚清科举被废,皇权体制倾覆,儒学才在死而复生中重新回归学术的本位。就此而论,“儒学”作为“经学”的这段历史涉及学术和政治的复杂关系,值得深入研讨。
一、从儒学到经学的“退化”
根据儒学史,汉武帝尊儒前,新一代儒家便开始改造儒学原典。可以说,儒学是在自身的调整和变通中走上了经学之旅。进入汉代,“儒学要真正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如何脱胎换骨地改变自己作为普通民间教师的世俗形象和身份,以重新获得王权的信任而成为其中政治决策的设计者”。为此,“两汉时期由儒生和方士合作制造的大量纬书,即是以孔子神话为特征开始了儒家在上层政治的‘象征建构’过程”[4](P17)。如果这种说法符合实际,那么,由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汉代的儒者调整了追求价值理想的方式,开始语“怪力乱神”,在精神层面也偏离了荀子“天人相分”的理性方向。
在这方面,对汉武帝“尊儒”有过影响的董仲舒的思想很能说明问题。具体来看,董仲舒在《公羊春秋》的基础上“观天人相与之际”,吸取了阴阳五行的思想,甚至法家的思想[5](P251-261),认为“圣人法天而立道……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以“君权天授”的观点论证君权来源的“正当性”。其实,对于君权的来源,周武王认为是在“民心”和“天意”变化基础上进行“革命”的结果。孔子和孟子只讨论“德治”、“仁政”问题,不讨论君权的来源问题。对汉朝开国者刘邦来说,君权是“马上得来的”,也无须讨论。但对继承祖上衣钵的汉武帝刘彻来说,“君权天授”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大一统”在西周是一个政治设计,在孔子那里是以“微言大义”表达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则用“大一统”论证武帝时代的皇权政治体制。此外,董仲舒还在阴阳家“五德终始”的基础上,用黑白赤“三统”周而复始的说法解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论证汉代皇权是“奉天承运”,巧妙地回避了改朝换代的具体原因。
从学术角度看,董仲舒的理论并未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认识,反而是对本来已经相当明白的事实做出了歪曲而复杂的解释,因而是一种退步。相比而言,周公作为权力的拥有者,直接把“民意”作为革命的口实,无须多余的解释。刘邦则直言“马上得天下”,对汉家政权的真正来源讲得非常明确,也符合实际。董仲舒讲“君权天授”,是没有权力的人言权力,他的理论无非是对皇权高雅的奉承。回头再看先秦儒家,他们不是权势者,但他们真诚追求“德治”和“仁政”的理想,因而能超越权势者的视野,在政治和伦理方面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探索,其理论不但相对理性,还蕴含理想。但董仲舒的理论主要表现了理性在皇权面前温柔的退却和自我贬损。比如,董仲舒承认“三统”、“四时”、“五行”都变化,但面对“皇权”时却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犯了“自我矛盾”的逻辑错误,是为了政治上的要求而牺牲了理论上的一致性。另外,董仲舒借“天人感应”苦心规劝皇帝,与周公对统治者“敬德保民”的直接要求相比,既“柔和”又“间接”,转了很大的弯子。在对“天”的态度方面,《尚书》中有“天不可信”和“天命靡常”的感叹,孔子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感叹,这些都是非常直率的表达。相比而言,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则有着虚饰的成分和神秘性,是理性在权力面前“狡黠的退步”。
当然,董仲舒以高雅的奉承向皇权献礼时,也借“天”的名义向统治者提出了温柔的劝诫:“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罚刑),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天有“五行”相生相克的次序,天子行政应该“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作为一种附带的警戒,董仲舒还提出了“异灾遣告”的观念,来限制“天子”任情使性的行为,在整体上形成了“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春秋繁露·玉杯》)的天人感应理论体系。比如,他在《对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这种说法用心良苦,但会助长谶纬迷信的风气。对皇权而言,这是和“高雅的奉承”捆绑在一起的“诅咒”。事实上,异灾的出现不一定和皇帝的行为有必然的联系,倒是儒者要借天灾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关切。皇帝也可以通过罪己和祭天的方式来试图解脱对天灾的责任。这样便构建了一种儒者和皇权互动的方式。但这种互动的基础是缺乏理性的,因为它混淆了“天灾”和“人祸”,给皇朝政治涂上了愚昧的色彩。在汉代,王莽和刘秀都曾用谶纬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制造舆论环境,但谶纬也同时充当过反对汉朝统治秩序的舆论工具。事实上,谶纬放大了皇权政治中的非理性因素。
总体上看,董仲舒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运用“温柔的智慧”把本来无关的东西编织在一起,完成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理论花环,作为给皇权的献礼,这彻底重建了儒学与皇权的关系。面对皇权,他尽力保持儒者的尊严,因而被后世称为“醇儒”。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他也不自觉地偏离了纯正的儒学轨道。相对而言,他的理论是借“天”的名义来断定人间秩序的合理性,而不是像孔、孟那样从人的各种具体关系中探讨这种合理性,因而相对孔孟之道是退了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董仲舒的理论相对于先秦的儒文化,在理性层面有一种退化,在价值和理想的层面则有一种淡化。这是“儒学”转变为“经学”的代价。
二、儒学和经学的区别
金耀基在讨论“仁孝”问题时注意到梁启超的一个观点:“后世动谓儒家言三纲五伦,非也,儒家只有五伦,并无三纲,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6](P91)金先生认为这“确是灼见”。因为孔孟时代儒家的“五伦”作为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角色系统,有一种“契约取向”。比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任何一个角色都处于权利和义务对称的关系中。“可是到了汉朝以后建立在‘大小’、‘上下’上的‘三纲’(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思想出现了。从此父亲对儿子,君主对臣子,丈夫对妻子变居于‘合法的’绝对性的地位,这么一来,五伦中原有的‘契约取向’的色彩全退色了,而真正形成了片面的、绝对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即为非对称性的关系。”[7](P26-27)
在金先生看来,这种“移宫换羽”的关键是《孝经》的“移孝做忠”,所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从此,君父的权力被扩展为绝对,义务则被隐去。徐复观也认为,儒家人伦思想由“五伦”向“三纲”的变化,“实亦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是儒家孝道被歪曲的大标志,是假借孝道以助长专制的总根源”[8](P27)。如果再注意熊十力的说法,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殊不知,纲常之教,本君主所利用以自护之具,与孔子《论语》言孝,纯就至性至情不容己处,以导人者,本迥乎不同。中国皇帝专制之悠长,实赖纲常教义,深入人心。此为论汉以后文化学术者,所万不可忽也。纲常为帝者利用,正是凿伤孝弟。”[9](P9)
应该说,上述思想是很深刻的,说明“儒学”和“经学”确有极大区别。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儒学史上曾由汉代的扬雄提出,被称为“真儒”与“时儒”的区别。[10](P122-123)具体来看,“三纲五常”是经学向皇权表示的“高雅的顺从”,汉武帝前后的儒家确实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拿传统社会的婚姻来打比方:皇权好比阳刚十足、脾气乖戾的丈夫;“真儒”是未嫁的怀春少女,还是自由之身;“时儒”便“已成人妇”,常常“身不由己”;科举时代的“儒”则更是“口称妾身”,即使面对横暴的丈夫,也要委曲求全,甚至在外人面前还要为夫君护短。总之,“真儒”和“时儒”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作为价值理想的“孔孟之道”与被皇权选中的“纲常名教”,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
比较而言,“真儒”之所以“真”,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霸道政治的角逐还没有落幕,士人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和孟子作为士人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一生真诚地“以学求道”,真诚地相信自己的“道”,也真诚地希望诸侯王公能以其道治国。不过,孔子在鲁未被重用,周游列国14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孟子曾见过梁(魏)惠王、齐宣王等,但国君们只把他看做一个老叟,未聘为国师。对孔、孟而言,国君是可以选择的,“道”则需要自己坚持和弘扬。因而,孔子和孟子都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诸侯王公对孔孟之道“敬而远之”,才成就了孔、孟的真儒地位。
但西汉时期皇权体制已经相对稳定,儒学随之被皇朝择为道统,“时儒”的历史文化使命便不再是“以学求道”或“以人弘道”,而成了“以道辅政”、“以道弘人”,“学”变成了辅政、弘人的工具。得到“独尊”的儒学,用内部的争论取代了诸子之学的争鸣①当然,在中国文化史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的地位也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在唐代,道教一度被宣布为国教。在元代和清代,藏传佛教被蒙古和满族统治者所信奉。,但无论是“时儒”对“真儒”的解读,还是各种“时儒”间的对话,都常把“学术”问题变成“道德”问题或“政治”问题,也往往只从儒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且是围绕皇权的文化需求进行思考的。因此,经学内部的争论,常需要皇权的介入。比如,今文经学中《公羊》与《榖梁》之争,最后由汉宣帝在公元前51 年主持《石渠阁》会议加以平衡。古文经学在西汉末对今文经学独占主流地位的挑战,有王莽支持的背景。东汉时今古文两派之间的争论,实质是要分享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因而,汉章帝在公元79 年召开白虎观会议,亲自出面来解决和调停。
从思维路向上看,儒学讲“内圣外王”。但面对君主,经学者一般是自修“内圣”,“外王”要依赖皇权。皇权犹如一条可以搭乘的“船”,儒者希望搭乘这条船达到理想的彼岸,但搭乘后才发现,它虽不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贼船”,却是由“任情使性”的船长驾驶的,作为乘客并无选定航向的权利,最多只能以劝导和建议的方式来影响船长,却往往不能奏效。这便是经学的尴尬。可见,儒学获得经学的地位是以弱化其学术品格为代价的。而且,对传统的皇权政治体制而言,经学实际上并非其遵循的“常经”和“常道”,而只是其常用的思想工具而已,在一定意义上是“儒术”。传统政治自身仍沿“霸道”的轨迹前行。在经学的理论框架中,儒者对儒学原典的不同理解成了思考的基本方向,许多学术的争论都成了池水中的波澜,甚至就是为了争得皇权的垂青。总之,经学很难摆脱皇权的影子。皇权虽不直接决定儒学对话的主题,却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理论的选择和裁判。政治权威往往能以独断的方式做出价值判定,或者说,“权力”可以超越“道理”。经学的道理往往采用“举例”和“劝诫”的方式,权力则可以树立“模范”,下达“诰命”和“圣旨”。在皇权的直接监控下,儒学基本失去了独立性和开放性,当然不可能发展成为学术意义上的政治学理论。
这种状况对儒者人格的影响也很深刻。经学为儒者进入官场打开了通路,但儒者在进入皇权体系后也往往变成了“卫道士”,而不再是孔、孟那样的“弘道者”。皇权体制为儒者“立功”开辟了通道,“立言、立德”的空间反而被压缩。经学、皇权之间有了荣宠爵禄的黏合,便构成了一种“文化势阱”,把“儒学”变成了“儒术”。在经学时代,士人作为皇朝官僚的后备军,最悲凉的遭遇是皓首穷经,却不再有孔子周游列国时那种“丧家之犬”的境遇,也不会有孔子那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悲壮。当然,他们中的一些才俊也曾经“疑经问道”,却很难“离经叛道”,传统文化中再也没有出现比孔、孟更有思想创造力的人物了。
李宪堂在研究先秦儒学时曾提出,儒学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践倾向,全面参与到了权力机制的建构之中,因而全息地带有专制主义的元素。[11](P2)这种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汉代以降儒学借助皇权获得意识形态的霸权,显然不好追诉到孔子、孟子那里,而只能由汉武帝之后的经学担当。因为经学依托皇权获得了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感,由此令经学在许多方面都背离了孔孟学说中的文化价值。这里蕴含着儒学文化命运中的一个悖论:要实现儒学的价值理想,就必须诉诸政治权力;而儒学一旦与政治权力结合,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真儒的价值理想。
三、儒学发展的新视野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儒学的发展,可以看出,经学时代的儒者也有创新思考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进展。比如,汉朝的桓谭①桓谭在王莽和刘秀崇信谶纬的时期,不迎合,对谶纬表示了理性的拒绝,差点被刘秀处死。参见《汉书·桓谭传》。、扬雄②扬雄著《法言》,认为“真儒”的精神是至简至易的,反对儒学的经学化和谶纬化。试图坚持“真儒”的气节和理念,王充③王充作《问孔》、《刺孟》,讽刺时儒曲解儒家精神。其《论衡》讨论了相当广泛的问题,有不少新知。、张衡④张衡是著名科学家,曾制造候风地动仪,可测出发生了的地震。则试图沿理性的方向拓展经学的知识视野,但都不过是“戴着脚镣跳舞”。魏晋玄学对儒学理想和皇权政治都感到失望,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勇气,但缺少建设性的思想建构。宋明理学和心学曾有“拓学弘道”的努力,但理学对道德理想的追寻和精神家园的建构也不能超越“纲常名教”的藩篱。明清“经世致用”的实学有面向实际的倾向,但在皇权最为专制的时代并未塑造出使传统文明再生的社会理想。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体西用”的经学思维更没能引领传统文明的现代化。20 世纪初,清廷废除科举,随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和儒学都成了历史文化的遗产。儒学的这一历史文化命运是值得感叹的。
一般而言,“学术思想革命”和“科学革命”类似,首先应从对原有理论的“怀疑”开始。事实上,经学史上并不缺少对经典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始终未能达到“离经叛道”的地步。比如朱熹对《古文尚书》、《孝经》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对《诗经》中的一些内容做出了与孔子“思无邪”截然相反的解释,但仍不放弃“卫道”的立场。[12](P234-239)而且,朱熹所卫之道在很大意义上已不是孔、孟追求之道,而是和皇权联系在一起的纲常之道了。根据列文森的见解,清代思想家戴震对宋明理学具有怀疑精神,但仍然确信儒家的传统,而且“一旦做出最后决定,他总是要从经典中求得确认”[13](P9),这是借助儒家经典来为自己提供某种保护。可见,戴震畏惧的并不是冒犯儒家的传统,而是皇权和文字狱。事实上,作为经学的儒学在一定意义上正如歌德小说中的“浮士德”一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不管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再次获得失去了的自由。
儒文化很早就有“革命”的理念,但儒学自身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却始终没能发生学术意义上的“革命”。这导致儒学在中国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之际被束之高阁。究其文化原因,还在于儒学曾转变为经学。这一方面疏通了儒者实现理想的权力之路,但儒学本身也因此失去了自由的文化生命力和发生学术革命的可能性。因为经学受到了皇权的“绑架”,其学术发展的文化空间被挤压和限定,“离经叛道”的思想不仅要冒学术风险,而且要冒政治风险。所以,经学发展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历史道路被皇权封死了,秦汉以降的儒者在孔孟之道基础上进行“思想革命”的文化阈值太高了,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几乎不可能发生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比如,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已入木三分,但“民主”的观念“呼之欲出”而未出。清代儒者曾静在《知新录》中曾提出“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大义觉迷录》卷二),这对雍正皇帝而言是“大逆不道”的,但曾静心里仍是有个“皇帝”的,只不过是“儒者”做而已。直到晚清废科举,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经学被废弃,儒学才重新回归了学术本位。
从文化发展逻辑的角度看,儒学有可能通过发展,在政治理念方面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这一假设的基础是存在的:儒家崇尚的尧舜时代的政治有原始民主;孔子、孟子、荀子的理论有丰富的德治、仁政、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和“民本论”只需一次“哥白尼革命”就可以转变为“民主”和“民权”的思想。再如,秦代陈胜、吴广起兵反秦时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儒家一贯提倡“内圣外王”。这里的问题已聚焦到了一点:谁都有做王的理想,如果把所有人的理想同时都实现不就可以了吗?或者说,中国古代并不缺“王”的理想,缺的只是在“王”和“普通人”之间画等号的“想象力”!其实,现代民主最核心的政治文化理念就是“主权在民”,每个公民都是“王”了!“民主”和“民本”不过一字之差,转化也就在一念之间。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是可能发生革命的,只不过是没有发生而已。
当然,文化的逻辑总是假设,历史的过程才是事实。辛亥革命以来,儒学的学术生命在摆脱政治权威的束缚之后逐步得到了恢复。20 世纪的“新儒家”事实上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儒家,其根本就在于人们试图再次回归“真儒”那种“以学求道”和“以人弘道”的精神,而且政治思维领域已经发生了从“民本”到“民主”的理念革命,这就为儒学回归学术本位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平台。如果说作为经学的儒学是由于君主专制制度而窒息了学术革命的可能性,那么,20 世纪初期发生的辛亥革命所蕴含的“民主”政治文化理念,恰恰又代替儒学完成了一次超越“民本”的理念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儒家牟宗三才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出了透彻的剖析,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是“有治道而无政道”[14](P48-49);徐复观则对儒学几千年政治思想的缺憾做出了精彩的揭示:始终没有超越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考虑政治问题的局限性。[15](P54-55)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国学”研究再次引起社会关注。儒学在国学中居于重要位置。可以肯定,儒学在开放的现代文明环境中具有吸收多元文化要素的文化生命和发展潜力。今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归儒学原典,但要超越经学把儒学当成实用工具的功利心态,也要摒弃那种把孔、孟当做“圣人”的崇古心理,在尊重和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21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明。这种态度的认识论基础有三个可靠的判断:任何一代的贤哲或思想家都不可能窥知和洞悉“人道”和“人性”的全部秘密;人类的价值理想和伦理道德也随社会的演化而演化;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往往超过人的想象。历史地看,孔、孟在缺乏行为准则和思想规范的时代依靠自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勇气独立地探究了“为人”和“从政”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同样,我们也应像他们那样担当起21 世纪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文化使命,可谓任重而道远。
[1]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3]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4]杨念群:《儒学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及其终结——兼论“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载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3 :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5]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中国儒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
[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7][8]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9]熊十力:《原儒》,“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0]参见庞朴主编:《中国儒学》(一),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
[11]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2]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13]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4]牟宗三:《政道与治道》(修订本初版),台北,广文书局,1974 。
[15]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新版),台北,学生书局,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