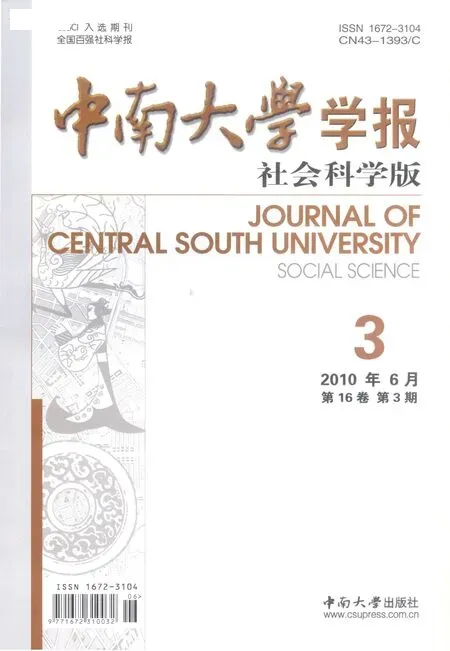合同约束力的判断标准
——以“法内” “法外”之间的允诺为分析对象
2010-02-09郭翔峰
郭翔峰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0031)
合同约束力的判断标准
——以“法内” “法外”之间的允诺为分析对象
郭翔峰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0031)
合同经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由于当事人内心意思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由自由主义衍生出来的主观合意理论,在众多游离于“法内” “法外”之间的允诺的效力判断上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坚持大陆法传统主观合意理论的基础之上,应当充分发挥客观合意理论作用,并吸收英美法上对价制度、允诺禁反言制度中的合理成分,以解决上述允诺的效力问题。
合同约束力;主观合意;客观合意;对价;允诺禁反言
合同是交易的法律形式,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工具。通过缔结合同,民事主体可以重新分配资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允诺或约定是否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具有法律上的合同的属性。德国比较法学者海因·克茨对这一问题做了否定性回答:“具有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每一次订立的、没有被错误、欺诈或胁迫玷污的协议,是否都应产生或引起可履行的合同义务?没有一个法律制度会这样认为。”[1](8)美国合同法巨擘科宾亦认为:“一个允诺必须伴随某种其他要素,才能够被强制执行。”[1](9)可见,不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都承认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不受合同法调整的允诺。之所以有此结论,是对人类有限理性和法律局限性的正确解读:法律并非万能,在法律之外尚存在大量的法外空间,我们不应也无法用法律的手段加以干涉。然而,对于那些游离于“法内”“法外”之间的允诺,能否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干预,长久以来困扰着法官和学者们:一方好意搭载朋友,途中发生了车祸,搭乘人能否请求违约损害赔偿;一方允诺,若另一方能帮助其完成某项工作,他将赠送一份厚礼,事后其未履行承诺,另一方能否请求履行;夫妻之间达成的忠诚协议,约定若一方违反将负担财产上之不利益,另一方能否以违约为由请求赔偿。诸如此类的各种事例,皆涉及一核心问题,即民事主体之间的允诺或约定是否具有约束力,或者说如何判断民事主体之间已形成一个法律上的合同。本文拟对此加以阐述,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些确定性的标准和方法。
一、意思合致——合同约束力的基础
“合同”一词源于罗马法上的contractus,由con和tractus二字组成,意为“共相交易”[2](256)。合同的涵义有如下内容:一方面合同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则表明合同是交易的法律形式①。罗马法上的这一概念为大陆法所继受,《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是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概念主义法学的集大成者《德国民法典》则通过法律行为制度明确合同是产生债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萨维尼更是明确指出:“契约之本质在于意思合致。”[3](5)我国《合同法》虽未明确规定合同即合意,但从该法第2条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的规定可以看出,合同亦是当事人双方共同合意的产物,只不过该条文是从合同内容的角度对合同所下的定义。可见,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合同的本质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有存在合意,合同才能对双方产生约束力。这一观念与18、19世纪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哲学密不可分。依自由主义哲学,私法的基础在于意思自治,民事主体有权自主安排其行为,并受该行为的约束,于是便有了《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庄严宣告:“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如同法律。”合同本质乃合意的理念也成为了大陆法系契约法的基石。与大陆法系相对的英美法则不同,在英美法学者看来,允诺才是合同法的核心概念,整个合同法体系都是围绕允诺能否强制执行而构建的。当然,英美法亦不排斥合同即合意的理念,合同即合意的理念在两大法系得到普遍承认,尽管英美法较少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合同一词。
因此,要判断一项允诺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合同,对当事人是否有约束力,关键在于探究当事人是否已就该事项达成了意思合致。所谓意思合致,是指一方意思表示为另一方所接受,即符合要约、承诺的规则。一旦意思合致形成,法律上的合同便告成立,任意一方违反皆应承担违约责任。须注意的是,此处所达成的合致应为“法律上的合致”。“法律上的合致”与“生活上的合致”相对,前者是指当事人通过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所达成的合致,它能产生一定私法上的法律后果,而后者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的合意,如两人约定共同前往某地,这一类合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法律上的合致”必须是当事人欲设立一定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所达成的共识。
德国法上有一著名的女方服用避孕药案,其主要案情为:一对男女为同居关系,双方约定,同居期间女方须按时服用避孕药。后女方私自停药且未告知男方,以致女方怀孕,双方关系亦告破裂。随后,女方向法院起诉要求男方支付抚养费,法院支持了女方的诉讼请求。男方遂提起另外一个诉讼,主张女方违反双方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法律行为通过相应的意思表示而形成,表意人具有发出一项有拘束力的、法律行为上的意思表示的意识时,即存在一项意思表示。女方为防止怀孕而承诺服用避孕药,根据交易习俗,此项承诺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项她愿意接受法律上拘束的意思表示……双方既然有意识地放弃用婚姻制度来规范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表明他们不愿意将自由的伙伴关系置于法律规定的约束之下……因此,双方当事人并不愿将其人身的、隐秘的关系作为合同拘束的标的。”[4](7−8)最终,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在德国民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它表明了德国在判断合同成立问题上所奉行的主观合意论,主张必须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出发,探求当事人是否有受合同约束的意思,否则,该行为仅仅是纯粹的“情谊行为”。[5](148)德国法的这一做法具有代表性,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继受,即使在英美法上,法院往往也会做出类似的判决。②
就我国合同法而言,在面对前述游离于“法内”“法外”之间的疑难案件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应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因为我国整个合同法体系是按照合意理论构建而成的。《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系“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30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否则将构成新要约;合同分则也将赠与合同由原来的实践合同变更为诺成合同,受赠人表示接受合同即告成立。甚至《物权法》中都将合同的成立生效与物权变动区分开来,“为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可见,主观合意理论仍然是贯穿我国合同法的一条主线。以前述好意搭乘为例,即使途中遭遇车祸,搭乘人亦不能请求开车人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开车人同意搭载前者,乃是出于朋友之间的一种情谊,并非要与搭乘人订立一法律上的合同,愿意受合同的约束。相反,如果开车人先前认为双方将成立一合同,从一个合理人的角度看,他甚至会拒绝搭乘人的请求,因为其所承受的风险与所享有回报根本不成比例。因此,探求当事人真意仍然是判断合同效力是否成立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保护”。[6]
二、客观合意——合同约束力的外部化
客观合意,是指对合意的考察并不局限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或实际意思,而是从意思的外在表现或客观表象来判断。显然,客观合意理论与主观合意理论是截然对立的,在契约自由滥觞的19世纪,客观合意理论基本上无存在的余地,因此,有学者主张的客观合意理论于普通法中早已存在的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7],至多只能称之为萌芽。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合意理论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法官之一霍姆斯在其著作《普通法》一书中对Raffles v. Wichelhaus的评述谈道:“人们通常说这种合同是由于对标的物的共同错误而无效,因为双方没有就同样的东西达成共识。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解释是误导性的,法律不管当事人心里状态。在合同中,与在别的地方一样,都表现为外部的因素,需要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判断。假设只有一艘皮尔斯号,被告由于出错,说Pierce时指的却是Peri,那他仍有法律上的义务。”[8](272)霍姆斯由此被认为是英美法上客观合意理论的奠基人。在其之后,《合同法重述》(第一版)的起草人威灵斯顿举起了该理论的大旗,他认为:“毫无疑问,法律通常通过主观的意向性术语来加以表述的,而远远不是客观的表述,但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证据。但是,当法律被确立时,我们见到的只是实质的法律规则而非任何证据规则。此时,整个主观理论便宣告失败。”[9](58)在霍姆斯和威灵斯顿的极力主张下,客观合意理论成为了英美合同法上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合意的通说,法官们也将注意力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转向了合意的外在表象。客观合意论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与其内在的科学性和主观合意论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主观合意论是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类绝对理性的思想,但其唯意志论的本质使得法官在探究当事人主观意思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意思属于意识范畴,外人无法知晓和重现当事人订立合同的主观状态,法官在裁判时仅能借助于当事人所举示的证据,但基于举证能力的不同,通过证据所展示的与真实的状态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而客观合意论的出现,却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当事人主观意思与外在表象发生冲突时,法官往往选择依后者进行裁判,这与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的机理是一致的。美国法上的Lucy v. Zehmer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③
须注意的是,客观合意论并非英美法所特有,即使在奉行主观合意论的大陆法系国家,也不乏其身影。早在上世纪40年代,德国法学家豪普特就任莱比锡大学教授时,发表了专题演说“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这篇文章震动了整个德国法学界,造成的影响可谓史无前例。豪普特教授认为,由于强制缔约的存在,很多情况下契约的创设根本无须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仅依事实过程即可成立契约。他还归纳了三种此类型的契约:基于社会接触、基于团体关系和基于社会给付义务而产生的事实契约。[10](127−131)豪氏的这一观点一经抛出,褒贬不一,赞成者虽多,反对者亦不少。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拉伦茨持赞成意见,并对豪氏观点加以完善,提出了“社会典型行为理论”:基于现代社会大量交易而产生的特殊现象,在很多情形下,当事人无须为真正意思表示,依交易观念或事实行为,即能创设契约关系。[10](135)不久之后,德国联邦法院在著名的停车费一案④中,采纳了“事实契约关系”理论,判决被告即使无缔约之意图,甚至是不愿缔约之意思,其行为已成立一事实上契约,应支付停车费。随后,在电力服务案、公共汽车案中,该理论得以继续适用。然而,联邦法院的这一做法受到了民法学界的强烈批评,最终“事实契约关系”理论也遭到废弃。[11](84)事实契约理论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其与大陆法系所奉行的主观合意理论格格不入,它极大地冲击了现有的合同观念,甚至威胁到传统的法律体系,在该学说本身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未被学界和实务界采纳亦不足为奇。
如前所述,我国合同法是以主观合意论为架构,但英美法上的客观合意和德国法上的事实合同理论,对我国法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尽管主观合意论在判断一项承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诸多表意不明的场合,该理论将面临诸多难题。如在一货物买卖合同中,双方之所以发生纠纷,在于对合同标的物存在严重分歧:买方认为合同指向的标的物是适合于烧烤和油炸的嫩鸡;而卖方则认为只要是鸡肉就可以,即使是较大的炖鸡。依主观合意理论,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物尚未达成一致,应认为不具有合意,合同不成立。显然,这样的认定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不符合现代社会所追求的交易迅捷和效率。相反,根据客观合意理论,并结合合同解释的方法,我们则可以确定最终责任的承担方。⑤又如,在某些情况下,沉默(并非以行为作承诺)同样可以构成有效的承诺[12](60−61),因为双方已达成客观上的合意。事实上,我国法并不绝对排斥客观合意论,因为制定于1999年的《合同法》可谓兼容并蓄,吸收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有关国际公约中的各项制度,客观合意论的身影在该法中亦有体现:合同法第62条的缺省规则和第125条合同解释方法便是佐证。因此,在我国法上,利用客观合意理论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并不会像德国法那样产生严重的“水火不相容”的现象,只不过是法官将现有用于合同补漏和解释的方法扩大适用于疑问案件的合同约束力判断上而已,这也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新近颁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条被认为是从司法层面上对“事实合同”的承认。[13](23−24)因此,适用客观合意理论在我国并不存在障碍。
三、对价制度——实质正义的英美法解读
对价(Consideration)是英美法上特有的概念,其源于英国早期的违诺赔偿之诉(assumpt)。在普通法发展的早期,并未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对价制度,直到古典合同法正式建立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对价制度方才形成。[1](136−139)对价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其理论基础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起初是获益受损理论,由英国法院发展起来,该理论认为对价是一方所获得利益或另一方所遭受的损害,这是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出发而构建的,被英国普通法奉为经典。但是,获益受损理论本身存在的逻辑矛盾:如利益-损害的对立假设的解释力不足、其与以允诺为中心的交换现实不符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损害是侵权法范畴[1](152−155),导致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对价制度的存在基础。由此,美国法上的交易对价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由霍姆斯率先提出,他认为对价的本质在于它是允诺的诱因,也就是所允诺人为了获得对价而作出允诺,受诺人为了得到允诺而提供对价。科宾也称赞道:交易对价理论开创了美国对价理论和合同理论的新局面,提告了对价制度的清晰度和简洁性。[14](170)于是,交易对价理论成为美国法上的通说,并为两次《合同法重述》采纳。对价制度能够成为英美法合同法上一道“靓丽的风景”,与其特有的判例法传统密不可分。在英美法上,法律体系主要是通过法官创制和发展而来的,他们关心的不是合同法理论的逻辑演进和严密,而是如何为当事人提供救济,从而,对价便成为了其中最主要的判断工具,“合同法首要的重大问题,便是何种允诺应当被执行——这一问题通常包容在对价的标题之下”。[15]
纵观整个大陆法系,恐怕也无法找到一个与英美法上对价类似的制度。基于此,不少大陆法学者可能会认为对价制度是法律上的一个畸形儿,是对私法自治的粗暴干涉——因为它要求当事人在达成合意之外必须存在相应的对价。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这一制度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恐怕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英美合同法是以允诺为核心构建的法律体系,但仅仅是一方的允诺尚不足以产生法律上的义务,法官在裁判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受诺人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对价。之所以把对价作为允诺能否强制执行的判断标准,与英美法官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观念密不可分⑥,这一结论从对价制度的源起可以得出。普通法上的对价源于清偿债务之诉中的“相等补偿原则”(quid pro quo),依科宾的观点,相等补偿是“与不付代价的收益相对立的,它表达了一种关于协商成交——以此物与彼物交换的思想”,[16](226)可见,相等补偿展现的是传统法律制度对等价有偿、交换正义的追求,霍姆斯甚至将其看作是对价制度的实质源泉——尽管他认为对价是一个类似于盖印的形式,但学者们从不否认通过对价背后的实质目标来作出允诺能否执行的判断。[1](89−94,238,261)而在美国合同法大师埃森博格看来,交易对价理论的正当性亦有两个:公平(fairness)和效率(efficiency),即使对价并不要求价值的对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放弃了对公平的追求。[17]
与英美法以对价来判断允诺是否具有强制力的做法不同,大陆法上的主观合意论认为,合同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的意思合致,但主观合意的不确定性和难以再现使得在大陆法上对合意存在与否的判断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处于“法内” “法外”中间地带的允诺更是让法官无所适从。而在英美法上,这一问题却不存在:因为对价独立于当事人合意之外,法官不需要考虑诸如缔约意图之类的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因素,而只须看受诺人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对价——对价是一个客观的要素,只要在价值上满足充分(sufficient)这一条件即可。因此,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对价“纯粹是一个技术性问题”[18](80)。对价的技术性和客观性使得英美法官在判断合同效力成立问题上变得简单而明确,具有主观合意论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由于我国并不具备类似英美法“允诺—对价”的制度基础,因此机械地移植对价制度并不可取,但是该制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维途径。如前所述,对价制度蕴含着公平正义的理念,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民事活动应遵循公平原则”、《合同法》第5条则明确了“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义务”。依通说,民法基本原则具有补充法律漏洞的功能。[19](43)因此,在涉及合同效力成立与否的疑难案件中,如果缺失具体规则,应当允许法官依据公平原则来衡量双方利益,以确定合同是否具有约束力。事实上,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早已有了类似的判例:三原告与被告组成一摸彩共同体,每周拿出50马克按确定数列进行投注,被告为负责人,由其填写彩票。一日,被告耽误按约定数列填写彩票,导致他们错失万元马克奖金。现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关键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约束力的合同。依主观合意理论,很难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此种合意,而州高等法院在判决中如此写道:考虑到被告所承担事务的无偿性,在认定存在法律义务与否时,应考察对受托人而言是否属于合理期待。对本案而言,这一利益衡量得出的结论是,在一般情况下,应否认受托人负有按照约定填写彩票予以交付的法律义务。[4](20−24)因此,在无法认定当事人是否存在合意——包括主观合意和客观合意的情况下,适用公平原则对双方利益进行衡量便不失为一种认定合同效力的方法。
我国某地区法院曾审理过一有关夫妻忠诚协议的案件:两夫妻结婚后感情出现问题,丈夫开始彻夜不归,妻子由此大吵大闹,丈夫为息事宁人,与妻子约定,若其晚上12点至凌晨7点不归,则以每小时100元支付妻子“空床费”。后双方终于闹至离婚,妻子的诉讼请求之一便是要求丈夫支付 4 000余元的“空床费”。该案件诉至法院后,令法官左右为难。笔者以为,法官应支持妻子一方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之间有相互照顾、扶助的义务,丈夫日夜不归,让妻子在家中承受家庭的负担,忍受孤独寂寞,给妻子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因此,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丈夫彻夜不归所要负担的不利益,实际上是对妻子的一种补偿,从公平原则角度看,法院应当认定该协议的效力。事实上,本案主审法官便是遵循这一思路来裁判的。⑦因此,以公平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应成为客观合意论之外判断合同效力的又一客观标准。
四、允诺禁反言——从信赖到合同
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又称不得自食其言、允诺禁反悔,是指一方为允诺后,另一方基于对该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自身的处境,则允诺人不得背弃自己的允诺。允诺禁反言是现代英美法的产物,在早期的英美法判例中,无对价即无合同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是诸如霍姆斯之类的法学大师对信赖保护也持怀疑态度,“如果受诺人由于信赖允诺就可以使一个无偿具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对价原则就会从根本上失去意义”⑧。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人们发现墨守传统对价制度将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于是允诺禁反言规则率先在美国得以确立。一开始,该规则仅适用于无偿转让土地、无偿保管、慈善认捐和家庭成员间的无偿允诺,但到了1933年,美国法律协会制定的《合同法重述》将其扩大到了所有的允诺。[20](91−93)而英国,一般认为,直到 1947年著名的丹宁勋爵在 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v. High Tress一案中才正式确立该规则。
根据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允诺禁反言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① 允诺人有理由预见受诺人会产生信赖;② 受诺人实际上信赖了该允诺并对其处境进行了改变。可以看出,允诺禁反言规则的理论基础在于信赖,它体现了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在英美法上,首次对信赖利益进行系统论述的当数L.L.富勒教授,他在《论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将合同法上的利益分为期待利益、信赖利益和返还利益三种,并对信赖利益保护的正当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打破了美国合同法上“要么赔偿期待利益,要么没有责任”的损害赔偿规则,为合同当事人提供了另一种救济方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富勒的这篇文章是现代信赖理论的起点,它拉开了讨论对价原则与合同上各种类型可判给赔偿之间关系的大幕。[21](60)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允诺禁反言规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原先的非交易性扩展到商业领域,为信赖利益提供了充分的救济,成为英美法上允诺得以执行的又一依据。⑨
不同于对价制度,允诺禁反言并非英美法所特有,大陆法上已被各国广泛确认的缔约过失制度与其有众多相似之处。缔约过失制度由德国学者耶林于 1861年提出,他指出:“从事契约缔结之人,是从契约外消极义务的范畴进入了契约;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展中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内……所谓契约不成立、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的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因此项信赖所生之损害。”[22](230)耶林这一学说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在契约成立之前的缔约阶段亦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一义务将承担法律责任的观点,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缔约过失理论为德国法所采,并对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瑞士、土耳其、希腊、台湾地区纷纷引进该制度,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亦对该制度加以确认。允诺禁反言和缔约过失都体现了对信赖利益的保护,两者在功能上有诸多重合之处——《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的起草人范斯沃斯便认为,在美国法不需要引入类似大陆法的缔约过失制度⑩,因为依照这种方法给予的救济完全可以纳入到允诺禁反言、侵权和返还法中。[23]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制度,允诺禁反言还承载着某些缔约过失制度并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发掘和借鉴这些功能对于完善我国合同法不无裨益。
缔约过失制度所要解决的是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的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请求权问题,合同成立与否与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并无必然的联系。允诺禁反言则恰恰相反,它是允诺能否得以强制执行的判断工具,一旦法院认定允诺符合该规则的构成要件,则判定允诺人须履行允诺,当事人之间成立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允诺人承担的也是合同义务或责任。因此,对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游离于“法内” “法外”之间的允诺的效力,缔约过失制度无法回答,我们只能借助于允诺禁反言规则。以美国法上著名的菲因博格诉费弗尔公司案为例,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雇员,她于17岁开始便在该公司工作,因此,董事会在讨论她退休问题时承诺,鉴于她对公司的贡献,将在她退休后每月支付她200美元。由于相信了被告公司的允诺,原告决定退休,但事后公司拒绝支付她退休金。根据允诺禁反言规则,由于原告是信赖被告所作出的给予退休金的允诺才决定退休的,因此她有权请求法院执行被告的允诺,按月支付退休金,当事人之间成立一个有效的合同。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缔约过失制度与允诺禁反言是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径,缔约过失对于合同约束力的判断无能为力,相反,在很多情形下,它是以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为前提的。
由于我国已经确立了缔约过失制度,两者在功能和作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因此并无全盘移植允诺禁反言规则的必要。但是,鉴于缔约过失在合同效力认定上存在着上述缺陷,修正和完善现有的制度却是当务之急。缔约过失在我国法上遵循以下思路:诚实信用原则——先合同义务——缔约过失责任,而在英美法上则是信赖利益——允诺禁反言。尽管两大法系存在不同的思维模式,但其保护信赖利益的立法精神则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后一种模式中的合理成分。具体而言,在不改变现有立法的前提下,笔者以为应当充分发挥缔约过失的上位概念——《合同法》第6条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通过解释的方法,对介于“法内” “法外”之间的允诺,以信赖保护的名义,明确当事人之间可以成立一个法律上的合同。之所以赋予其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缔约过失责任无法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缔约过失赔偿范围一般限于订约费用、履约费用以及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害[24](251−255),很明显,在前述退休金案中,原告并不存在这三项损失。因此,承认诚实信用具有衍生出信赖保护的功能,能够扩大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救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公正。
五、结语
对于特殊情形下允诺的约束力问题,在大陆法上,长久以来并未引起学者和实务界人士的足够重视,因为他们多秉持合意即合同的理念,认为该问题不过是纯粹的理论探讨,并不具有实践意义。相反,在英美法上,由于合同法体系是以允诺为中心建立的,允诺的执行是合同法最为基本的问题,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因此,笔者选取了较多英美法上的制度作为比较对象,并结合大陆法的一些制度,对该问题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建构,以期为判断此类允诺的约束力提供一些有益参照。
注释:
① 这一点在英美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英美法大多数学者认为交易是自由经济的主要动力,而交易的实现则是通过当事人的自愿磋商形成,合同便是这一磋商的最终结果。并且通说认为,英美法上的对价制度的理论基础便是交易——对价与允诺互为交易的对象,即对价的交易理论(bargain theory of consideration)。
② 参见Balfour v. Balfour, 2 KB 571(1919),其主要事实为:有一对夫妇,丈夫于斯里兰卡工作,但妻子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留在英国,不能随同前往。双方遂达成一口头协议,丈夫将每月给妻子30英镑直至妻子能够前去斯里兰卡与丈夫一起生活。但其后双方感情出现问题,丈夫拒绝再支付这笔生活费。妻子遂提起诉讼要求强制执行允诺。法院判决后认为,这类允诺不构成法律上合同,因为双方在约定时并无创设法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图。
③ 该案案情如下: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农场转让合同,并提出一书面合同。被告主张该合同是自己与原告开的玩笑,并且当时双方都已喝醉了酒,因此并未达成真正的合意。法官则在判决中认为:“当事人双方意志上的契合并不是一个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一方的语言或举动确切无疑地表达出了一个合理的意图,他那未曾吐露的内心想法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除非对方当事人清楚了解他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不合情理的。”从而认定双方在客观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合同,被告应受合同约束。
④ 汉堡市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将马路两旁的道路开辟为停车场,交由私人企业经营,并收取一定费用。被告认为该地属于公用地,不应收费,因此拒付停车费用,经营企业遂提起诉讼。
⑤ 参见 Frigaliment Importing Co. v. B·N·S·Intl. Sale Corp., 190 F.Supp.116.
⑥ 在英美法上,公平和正义仍然是法官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即使在当代英美法国家已经不存在衡平法院,但其精神仍然传承至今,所谓的“良心法庭”依然是法官判决中常见的词汇。公平正义观念是法官解决疑难案件的重要工具,甚至在制定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官认为用该条文适用个案将导致不公平结果的出现,他亦会拒绝适用制定法。例如,合同即使符合制定法规则,但违反公共政策,仍然无效。
⑦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暴力行为,以精神损害赔偿金为由,支持了原告方4000元的诉讼请求。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实际上回避了对该协议效力认为的问题。而二审法院则认为“该笔费用是指原告与被告在婚姻关系期间,一方不尽陪伴义务,另一方给予一定补偿的费用,名为空床费,实为补偿费,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约定,依法应予主张”。二审法院虽然在说理时认为合同真实有效,故被告应履行合同约定,但须注意的是,法官将空床费定性为一方不尽陪伴义务的补偿费,实际上就是从公平原则出发,对双方利益进行衡量所得出的结果。
⑧ 参见Commonwealth v. Scituate Sav.Bank(1884).
⑨ 由于允诺禁反言规则的成为允诺得以执行的依据,它势必与传统对价制度产生冲突,有人认为允诺禁反言正在不断侵蚀对价制度的领地;亦有人认为相对于对价制度,允诺禁反言仍然处于从属地位。详见刘承韪《英美法对价原则研究》一书第五章,287页以下。
⑩ 英美法较少直接使用缔约过失(culpa in contrahendo),更多的是采用先合同义务或先合同责任(precongtractual liability)。先合同义务是前提,违反先合同义务将产生先合同责任,而缔约过失则是先合同责任的一种,另外一种责任形态为效力过失责任。缔约过失制度起源于对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责任承担的探讨,但在之后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早已超出了这个范围,如我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以及第43条违反保密义务,皆可以成立于合同有效的情形之下。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参见王泽鉴先生对台湾地区“民法”第 245条将缔约过失限定于合同不成立情形的检讨,详见王泽鉴著,《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32页以下。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90条规定:违反这个允诺(禁反言)的救济应当限制在实现公平所需要的范围之内。因此,英美法官在实践中往往根据自由裁量,给予受诺人以期待利益的救济。可见,英美法上的信赖利益与大陆法并不完全等同。
[1] 刘承韪. 英美法对价原则研究: 解读英美合同法王国中的理论与规则之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 王家福.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1.
[3]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一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 邵建东. 德国民法总则编17则案例评析[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6] Wayne Barnes. The French subjective theory of contract: spearking rhetoric from reality [J]. Tulane Law Review, 2008, (12): 359.
[7] Joseph M.Perillo. The origins of the objective theory of contract 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J]. Fordham Law Review, 1995, (2): 69.
[8] 霍姆斯. 普通法[M]. 冉昊, 姚中秋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9] 格兰特·吉尔默. 契约的死亡[M]. 曹士兵, 等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10]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1] 罗伯特·霍恩, 海因·科茨, 汉斯·G·莱塞. 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12] 王军. 美国合同法[M].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4.
[13] 沈德泳, 奚晓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14] Daniel J. Klau. What price certainty? Corbin, Williston and the restatement of contract [J].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0, (5): 534.
[15] 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responsive model of contract law [J]. Stanford Law Review, 1984, (5): 1107.
[16] A.L.科宾. 科宾论合同[M]. 王卫国, 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17] 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bargain principle and its limits [J]. Harvard Law Review, 1982, (2): 741.
[18] Claude D. Rohwer, Gordon D. Schaber. Contracts (Fourth Edition)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2003.
[19] 梁慧星. 民法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0] 艾伦·范斯沃思. 美国合同法[M]. 葛云松, 丁春艳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1] 朱广新. 信赖责任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22] 王泽鉴. 债法原理(第一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23] E. Alan Farnsworth. Precongtractual liability and preliminary agreements: Fair dealing and failed negotiations [J]. Columbia Law Review, 1987, (3): 217.
[24]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The determination to the binding of contract——An analysis of promises between the law and virtue
GUO Xiangfeng
(Civil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The contract forms with mutual assent and both parties are bound. But, owing to the indistinct and uncertainty of will, the Subjective Theory in civil law can not distinguish the promises between law and virtue.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ubsequent theory, judge should adopt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Objective Theory,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sory Estoppel to solve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
the binding of contract; subjective theory; objective theory; consideration; promissory estoppel
book=16,ebook=5
D923
A
1672-3104(2010)03−0057−07
[编辑:苏慧]
2009−11−04
郭翔峰(1986−),男,浙江金华人,西南政法大学2008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合同法,物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