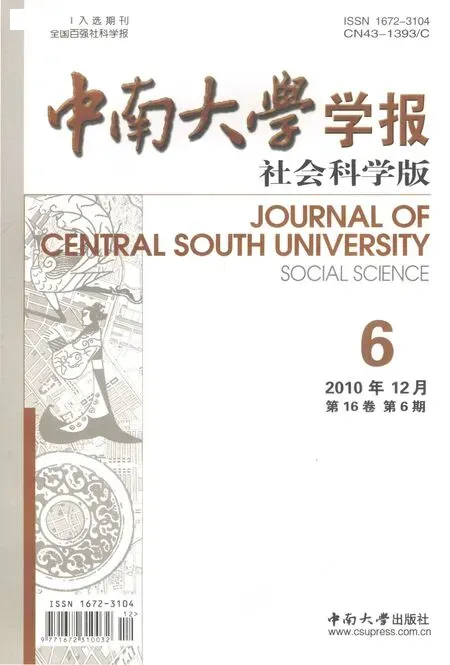旅行文学三题
2010-02-09杨保林
杨保林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旅行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重要实践活动。旅行的动因很多,或为受人驱逐的无奈之举,或为躲避战乱的主动行为,或为追求特定目标而进行的自我放逐,此种意义上的旅行大多是痛苦的体验,经历的不是愉悦而是创伤;旅行也与异域探险、体验异质文化紧密关联,此种意义上的旅行大多与娱乐休闲、实现自我价值有关。旅行具有文化传播与消费的功能,旅行文学作为行旅体验的文化书写,对旅行这一实践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前现代时期的旅行者即有车马舟楫之便,现代旅行者更是借助飞机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纵横四海。旅行的普及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发展,而旅行文学反过来激起了更多人旅行的欲望,但在批评家眼里,旅行及旅行文学不是休闲娱乐的衍生物,而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有着更深层次的指涉。旅行文学的大量涌现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的殖民主义扩张关系密切,旅行文学通常被视为“巩固殖民统治的殖民主义话语”。[1](76)西方旅行者借助现代技术工具深入异域或殖民地,与现代性“他者”近距离接触,他们因害怕殖民地的瓦解而产生极大的心理焦虑,罗伯特·迪克森教授称之为“殖民主义精神紊乱”(colonial psychosis)。[2](17)本文拟从旅行文学的发生与批评,旅行文学对异域的想象性建构,以及旅行文学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是于贤达。
一
中西方的文学传统大相径庭,但在旅行与文学的发生关系这一层面存在诸多共通之处。荷马史诗描写的英雄历程、《圣经·旧约》中关于摩西引导犹太人逃离埃及的记载、中世纪的圣杯传说与骑士冒险传奇都与旅行相关,而中国文学经典《论语》《离骚》与《西游记》等无不与旅行密切相关。但是,要将旅行文学作为一种特定文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话,以上说法由于指涉面太广而显得空洞繁杂。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可以是诗歌、小说、旅行见闻札记、日志、书信、传记、回忆录等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但并非所有的旅行写作都是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如“苏州园林导游词”、“天水麦积山石窟旅行攻略”等就不属于旅行文学的范畴。游记(travel book)或旅行见闻(travelogue)是一种特殊文类,属于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s),简·波尔姆认为旅行写作或旅行文学“不是一个文类,而是一个集合术语,指那些以旅行为主题的虚构或非虚构文本”。[3](13)本文则认为旅行文学比旅行写作更加具体,旅行文学是具有文学价值的旅行写作,从文类范畴上讲,旅行文学是亚类文学,属于旅行写作的范畴;从主题层面上讲,旅行文学指以旅行(包括空间旅行与时间旅行等)为核心主题的虚构作品。为研究方便,本文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类别的旅行写作,但以旅行文学(即关于旅行的虚构作品)为中心话题展开。
旅行文学源远流长,但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旅行文学发展缓慢。西方现代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但旅行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亚类文学,被主流批评话语所忽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旅行写作(旅行文学)的研究逐渐吸引了批评家的注意,丹尼斯·珀尔特的《困扰的旅行:欧洲旅行作品中的欲望及越界》(1991)、玛丽·露易丝·普拉特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与文化转变》(1992)等著作预告了旅行写作批评时代的到来。1997年,唐纳德·罗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组织了第一届国际旅行写作大会并成立了“国际旅行及旅行写作协会”,由蒂姆·杨格斯(Tim Youngs)主编的《旅行写作研究》也于同年发行。受福柯和萨义德等人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旅行文学批评广泛关注旅行文本中的知识权力、性别政治、东方主义话语等因素,迄今已有相当数量的旅行文学研究成果得到出版和发表,引起了众多文学批评家的关注。
旅行文学批评主要以后殖民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等为研究范式,这是因为殖民主义扩张与旅游业的兴起使得旅行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旅行写作尤其是旅行文学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元素,显示出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如《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财富的觊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具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话语特征。玛丽·露易丝·普拉特指出,旅行作品在帝国读者当中广受欢迎,因为旅行作品给阅读公众“创造了好奇、激动、冒险的感觉,甚至激起了对欧洲扩张主义伦理的狂热心态”。[4](3)正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旅行文学的双重作用下,无数的帝国主体开始了探索之旅,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但对亚、非、拉等地区造成的影响尤甚。牙买加·金采德在其著作《小地方》中如此写道:
你们来了。你们拿走了本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你们杀了人。你们把别人关押起来。你们抢劫别人。你们开了银行,却把我们的钱存在里面。账户上写着你们的名字。银行也在你们名下。你们当中肯定也有好人,但是他们在家里呆着。[5](35)
贾斯丁·爱德华兹认为金采德的《小地方》表明:“旅行者并不是坐在那里欣赏风景的消极主体,而是文化消费与剥削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过程建立并延续了欧洲的殖民统治。”[1](74)旅行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了殖民主义进程和现代意识形态,而旅行者在关于殖民地或异域知识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
无论是对异域的“白描”讲述,还是关于异域的想象性虚构,旅行文学普遍强调异域知识的“真实性”(authenticity)问题,但是,旅行文学的真实性受作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反映的不一定就是真理(truth),相反,旅行文学中关于异域的知识往往基于作者对异域的想象性构建。著名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许多著名作家(如雨果、歌德、福楼拜等人)的旅行文学作品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构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对东方的定型写作,即“神化了的东方”,这种东方神话源于西方对东方的当代看法与偏见,也源于维克所说的民族想象与学术幻想。[6](53)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进一步指出,小说等文化载体“在帝国主义的态度、指涉和经验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7]可以说,在旅行文学中,不仅东方被神化了,其它殖民地或异域领土也被神化了。
萨义德认为西方知识范畴内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幻想产物,东方主义话语没能描述真正的东方(the actual Orient),但反映了西方想象的显著神话。[8]东方本来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描述下逐渐演变成一个文化概念,继而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东方由于历史及社会原因而落后于西方,因此东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贫穷落后、愚昧低劣的代名词。旅行作家笔下的东方几乎千篇一律:或千疮百孔、民生凋敝,或放纵奢靡、成为西方旅行者的猎奇场所。由于旅行作家亲历东方社会的缘故,他们笔下的东方被赋予了“真实性”的色彩,这使得那些未曾有过东方经历的西方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以为获得了关于东方的知识。这种建构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神话在西方旅行作家的笔下不断被强化,并得到了西方读者的普遍认同。因此,无论是旅行作家还是其读者,他们在这种旅行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关注的是异域情调,东方究竟为何物,他们并不在意。正如澳大利亚作家阿历克斯·米勒在其小说《祖先游戏》中所写的那样:“我对旅行毫无兴趣……如果我去了中国,那叫我怎么想象它? 我关心的不是亲历它,我感兴趣的也不是中国,而是对它的想象。”[9]
米勒的说辞并非毫无道理,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旅行文学作为虚构性作品,如果离开了想象,恐怕就变成旅行见闻札记而显得缺乏创意和深度了。不过,尽管旅行文学是虚构的,但其毕竟离不开现实的参照,尤其对于具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澳大利亚作家而言,现实与虚构在小说中交相映衬则更为明显。克里斯托弗·考什在其小说《危险年代》]中就强调,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纯属虚构,只有公众人物除外。[10]考什的小说背景设在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故事讲述了印度尼西亚政变前后一些西方记者在雅加达的生活与经历。《危险年代》首次出版于1978年,距当年印尼政变已有13年,而考什曾于1968年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委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成员的身份去过雅加达。在当时的印尼,“空气中到处都充满着猜疑”,[11]P20考什在雅加达的工作生活经历无疑给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同时也给其小说赋予了一种真实性色彩。地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虽然位于澳大利亚的北部,但长期以来被继承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澳大利亚人视为“东方”,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澳大利亚所忽视,考什属于最早将创作眼光转向亚洲的澳大利亚白人主流作家之一。《危险年代》由于其曲折新颖的故事情节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赢得了澳大利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考什的文学创作声誉。而根据该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彼德·威尔执导、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同名影片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赞誉。考什的创作受东方主义话语思维的影响,他笔下的印尼充满着异域情调,战乱、贫穷、猎艳、肮脏等都是小说情节中常有的片段。
事实上,考什出版于1965年的小说《穿越海墙》就提到过印度尼西亚,而该小说的主要背景则是印度。作为最早将创作目光转向亚洲近邻的澳大利亚主流作家之一,考什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与深度,他对异域的想象一方面是出于情节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澳大利亚文化身份的考虑。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一样,曾经属于欧洲的殖民地,类似的出身使得澳大利亚和这些亚洲国家具有微妙的共同点。考什认为现代澳大利亚与这些亚洲国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殖民地,是精神的殖民地而非政治意义上的。”[13](71)如同美国人喜欢游历澳大利亚一样,澳大利亚人也乐于游历亚洲,两者的共性在于对前殖民地的怀旧情结,美国人在澳大利亚看到了自己处于殖民地时期的影子,而澳大利亚人在亚洲得到了同样的体验。考什对亚洲尤其是印尼的态度恰恰传递了这一信息,他对异域的想象性构建与其说是表现他者,还不如说是出于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身份的考虑和关怀。考什认为这是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具有的典型性特征,也是“澳大利亚文学的奇特性质”。[13](71)旅行文学对异域的想象在这一点上并无二处:猎奇仅仅是表象,怀旧才是深层心理。换句话说,异域想象是为了心理满足,表现他者是为了建构自我。
三
旅行既有时间的跨度,又有空间的位移,旅行文学作为行旅体验的文化书写,对自我文化和异质文化必将做出一番比较,因此,旅行文学“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14](115−120)旅行文学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关注异域情调与自我认知的关联性。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历史久远,但彼此之间的认识仿佛是铁板一块,大多数的情况下对彼此只进行集体想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对西方的描述即有“妖魔化”嫌疑(如《山海经》《西游记》等),而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想象则是“坚船利炮”等。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也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古代东方文明的赞誉与对现代东方社会的鄙夷,这正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论述过的。这种集体想象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方想象是服从欧洲中心意识的,西方想象是服从中华(东方)中心意识的”。[15](21)
东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陆地文明,而西方文明则属于海洋文明。当“丝绸之路”成为往事,海洋交通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海洋文明的发达无疑促进了西方的殖民主义进程,西方旅行者也受益匪浅。帝国主体借助海洋交通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殖民活动与旅行探险。罗伯特·迪克森在考察了旅行文学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之后指出,旅行文学与殖民扩张及统治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谋关系。[2](22)当然,殖民主义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不可否认,新殖民主义又以各种形式凸现出来并影响着当今世界格局与人文观念,正如考什所说的那样,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文化及思想意识方面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痕迹,而曾经是殖民主体的西方国家,在现代社会依然延续着其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只是换了另外的表现形式而已。旅行文学对促进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功不可没,但其隐含的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往往被忽视乃至遗忘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世界霸主,当时的旅行作家对东方或其它殖民地的描写并非“好奇”这么简单,在意识深处,这些旅行作家将殖民地作为参照来考量自己的文化身份:异域的奇特及落后正好印证了帝国的正统及强大。西方的殖民扩张及统治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解殖活动中土崩瓦解,但这只是政治意义上和军事意义上的,在文化领域并非如此。旅行活动替代了原来的殖民扩张,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延续着帝国思维。旅行作家以“注视”、“观看”前殖民地的方式,通过“记录”并“描写”前殖民地社会及人民,继续行使着帝国权力,这种“注视”与“描写”不只强调异域情调,同时具有自我认知意义。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作家“借助东方来改变当时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东方兴趣的兴起与英国社会上层日益增强的精英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责任感密切相关。”[16](233−235)同样,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作家对异域风情的描写也与构建自我文化身份有关。
哈根指出:“观光者之注视”(tourist gaze)不仅为观光者所见提供媒介,而且引导观光者该如何观看。”[17](83−89)这种观光者的注视受东方主义思维的影响,渗透着话语与权力的因素。当然,把所有旅行文学都看作是东方主义话语思维的写作将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毕竟东方旅行者对西方的描写,以及殖民主义之前的旅行写作不属于这个范畴。但是,“观光者”或旅行者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通过对异域的“注视”与“描写”,行使着话语权力,而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由于东西方之间力量悬殊,大量西方游客深入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由此产生的旅行作品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烙印。在与东方社会的“他者”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西方旅行者一方面审视着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则调整着自我认知,在这种意义上,旅行文学表现出的不只是对异域的好奇,更是对自我文化身份定位的深入关怀。
[1]Edwards,Justin.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 [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2]Dixon Robert.Prosthetic Gods: Travel,Representation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M].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2001.
[3]Borm Jan.Defining Travel: On the Travel Book,Travel Writing and Terminology [C]// Perspectives on Travel Writing,ed.by Glenn Hooper and Tim Youngs.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4.
[4]Pratt Mary Louise.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2nd edition)[M],New York: Routledge,2008.
[5]Kincaid Jamaica.A Small Place [M].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8.
[6]Said Edward.Orientalism [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8.
[7]Said 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M].London: Chatto &Windous,1993.
[8]Levin Stephen M.The Contemporary Anglophone Travel Novel:The Aesthetics of Self-Fashioning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M],NY: Routledge,2008.
[9]Miller,Alex.The Ancestor Game [M].Ringwood: Penguin Books,1992.
[10]Koch,Christopher John.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M].Melbourne: TNA Pty Ltd,1978.
[11]Koch,Christopher John.Crossing the Gap: A Novelist’s Essays[M].Sydney: Angus & Robertson,1993.
[12]Koch,Christopher John.“An Australian Writer Speaks” [J].Westerly,1980,(3): 98−99.
[13]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J].社会科学战线,2006,(6):115−120.
[14]李岚.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2007,(5): 43−44.
[15]空草.维多利亚女性旅行家笔下的东方[J].外国文学评论,2009,(4):233−235.
[16]Broinowski,Alison.The Yellow Lady: Australian Impressions of Asia [M].Oxford: Oxford UP,1992.
[17]Huggan,Graham.“Transformations of the Tourist Gaze: India in Recent Australian Fiction” [J].Westerly,1993,(4): 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