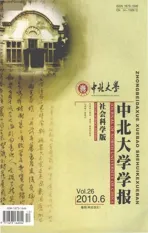“百家讲坛”栏目生存空间的深层挖掘*
2010-02-09郭文君宁竹青
郭文君,宁竹青
(1.黄河电视台,山西太原030001;2.中北大学出版部,山西太原 030051)
“百家讲坛”栏目生存空间的深层挖掘*
郭文君1,宁竹青2
(1.黄河电视台,山西太原030001;2.中北大学出版部,山西太原 030051)
”百家讲坛”栏目要想保持延续性并开拓长久的生存空间,必须放弃对收视率的刻意追求,通过正确的方式诠释精英文化、实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作共生,在循序渐进地提高普通大众文化水准的同时向大众介绍和推广精英文化;在制造学术明星的同时,要严格把关,认真筛选,加强管理,使得这些”学术明星”真正成为大众了解精英文化,熟识传统经典的领路人;不能单纯追求收视率,并像纯娱乐节目那样靠观众的捧场来生存,而要肩负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引导观众深层思考并树立高尚境界的责任。
百家讲坛;生存空间;娱乐化
近几年,电视讲坛类节目在电视屏幕上大放光彩。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推出的“百家讲坛”栏目,为普通百姓构筑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国学电视讲堂,获得了较好的收视率,但也引发了许多质疑。我们在品评“百家讲坛”栏目异军突起,推陈出新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该栏目备受追捧的表面繁华之下,一直涌动的争议浪潮。“争议化传播”在将主讲人推到火爆境地的同时,折射出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栏目中沟通与融汇的表象之下本质的隔阂与争议;电视栏目包装下造就的“学术明星”,在获取了高知名度、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存在为迎合大众趣味而违背严谨治学、曲解传统经典的倾向;电视栏目在推行媒介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所带有的诸种“娱乐化”因素,已经对文化知识的传播造成了妨碍,传播知识的目的大有让位于“娱乐化”效果的趋势;而栏目形式的单一化与栏目内容的固定化终将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这些潜藏的危机正成为导致该栏目收视率下降、品牌受损以至生存受到威胁的诱因。
1 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百家讲坛”栏目在历经三次改版之后,传播的内容窄化为中国历史文化经典。而“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之域,寄托和承载着人生‘何所来、何所去’的终极之问,人们要借此追求人生的超越,以赴人生的彼岸”[1]。这些经典作品富于创造性、纯粹性、自律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对这种积淀民族文化底蕴、蕴涵民族社会性格的文化经典进行学术探讨和挖掘属于精英文化研究的内容。然而在“百家讲坛”中,却以大众文化的解读方式来诠释这些代表精英文化的传统经典。这种解读方式一直被学术界所争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百家讲坛”栏目中完美结盟的表象背后,二者的本质差别不断凸显。然而,表面融合与内质隔阂的不断冲撞是否会歪曲经典、误导大众,破坏精英文化的严肃性和学术性呢?这种冲突的激化正是“百家讲坛”栏目发展过程中潜藏的隐忧。因而,栏目在传播过程中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挖掘栏目潜藏的生存空间,更有助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解读与发扬光大。
精英文化是指体现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和美学探索旨趣的、具有独特的审美特质和内蕴的文化形态。而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的、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够满足受众获得感性愉悦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2]。由此可知,在知识精英眼中,“精英文化是不可复制的,是大众传媒无力承载的、独一无二的、激发人主动思考而非被动享受的文化,它强调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有个性的张扬,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毫无个性的平面化接受。[3]”
当大众文化借助传媒的力量被广泛传播与流行之初,精英文化已经开始逐步被大众文化边缘化了,“担心精英文化将来有一天只能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研究和鉴赏的古董,会沦为大众文化用以进行参照比较的‘他者’文化,也并非危言耸听”[1]。比如以麦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学者曾经对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冲击下的生存状况以及由大众文化的勃兴而导致的“文化上的野蛮状态”表现出极度的忧虑,并对大众文化作出以下批判:其一,大众文化是同质性文化,它把所有的人整合得千篇一律,成为所谓的“单面人”。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只在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框架里去思考,只是顺应着大众文化的逻辑和价值方向去获得精神享受,不会产生任何逆大众文化的想法,更不要说什么批判的观念。其二,大众文化过于浅薄,它消解了经营文化的内涵,从而使人们变得浅薄。
中国传统经典——“国学”,正是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在古代,是否知晓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不仅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划分依据,更是确立封建社会社会阶层的准绳。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现代文明逐渐取代了传统国学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当今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又使得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即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普通大众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种种方面的原因,“总是宁可取流行小说的娱乐,舍弃那些更为认真而严肃的高雅文化。[4]”都市中的普通民众需要的是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获得轻松地娱乐和消遣的大众文化,而不是追求那种具有深度的“精英文化”。但是,从大众文化在中国蓬勃发展以来,人文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精英文化生存境况的关注。一些学者以精英文化守护者的姿态痛斥大众文化的泛滥,指责传统审美文化在通俗文化围攻下被支离破碎地曲解和断章取义的分割,以精英文化的预设立场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并试图通过对经典学术的重新解读来恢复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主流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5]。因而,更多的人文知识分子看到了大众文化的不可阻挡之势,明显感受到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所以,他们的文化主张是要以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契机,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明确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力图创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现实共生机制。其实,提倡审美化传播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可能动摇严肃知识分子守护的高端价值,而不过是扩大了大众的娱乐权限。这一扩大只是在表面上似乎对精英文化提出了挑战。
但是如果“百家讲坛”以消遣、娱乐的方式解读精英文化,就会使得大众关注“百家讲坛”,只是出于该栏目所呈现的精英文化中的某些碎片对大脑皮层的感官刺激而激发的好奇心。主讲人的解说迎合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一旦观众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其关注的对象势必转移,对“百家讲坛”的狂热也就不再继续。虽然某些学者批评“百家讲坛”栏目“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有些偏激,但是,该栏目在以“大众文化”的视角解读“精英文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制约该栏目长久发展的隐忧。“百家讲坛”要搞学术大众化,就必须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用精英文化来引导大众、熏陶大众,而非通过对精英文化的世俗化去迎合大众、麻醉大众。“百家讲坛”栏目只有放弃对收视率的刻意追求,通过正确的方式诠释精英文化、实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作共生,在循序渐进地提高普通大众文化水准的同时向大众介绍和推广精英文化,才能保持栏目的延续性并开拓长久的生存空间。
2 认清“学术明星”与专家学者的距离
一个社会中,精英文化掌握在知识精英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手里,尤其是他们掌握着精英文化的阐释权和评论权。普通大众远离高雅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而是因为接受起来就有难度。精英文化的文本不是刺激人们的感官享乐,而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因此,人们在电视中欣赏精英文化是需要与有一定文化底蕴和知识积累的知识分子相结合,需要由知识分子来引导的。但是目前这种结合并不尽如人意,走向了两个极端。
其一,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和电视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格格不入,甚至蔑视这种低俗的文化;而电视工作者却认为所谓的高雅文化曲高和寡,甚至是故弄玄虚。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就曾经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加强的,交流的环境是预设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6]”而中国的电视人崔永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的名为“电视的庸俗化”的演讲中指出:“电视工作者对知识分子不够尊重,导致知识分子在面对电视表达方式的时候,其知识化程度受到很大的损耗,使他们在知识界或者学术圈的名誉收到影响,口碑降低;电视节目的操作有着特有的方式和技巧,知识分子由于对这些不够理解,很难达到与电视人的契合,这一点很难与知识分子沟通。[7]”由此也可以了解,在当下中国的文化界,精英文化圈与大众文化圈之间有很大的隔膜,各自遵循的规则和逻辑也不一样。知识分子没有找到进入电视的最佳通道,而电视人也不太清楚该如何利用精英文化来为自己服务。
专家学者参与“百家讲坛”节目同样要经受这种审查与限制。比如“百家讲坛”就一再强调其不是学术论坛,而是给普通大众做的,所以栏目组要求主讲人所讲述的内容必须是大众能听得懂并乐于接受的。“所谓大众,其实就是以初中文化水平来衡量。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让一个15岁的孩子感兴趣?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得改;如果你改不了,就上不了“百家讲坛”。[8]”而这种如同“超女”海选一般的对专家学者的选取方式,在保证了栏目收视率和娱乐性的同时,也把一些正真有学术水平的大家拒之门外,其所传达的精英文化理念也就有可能不纯粹、不全面、不完整。
其二,部分知识分子被电视媒体“招安”,变成了所谓的“学术明星”,他们的思想观点脱离了精英文化的逻辑和轨迹,完全为既有的电视体系所利用,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电视和知识分子虽然可能分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层,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的,有时反而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电视等媒体为知识分子提升其文化资本,获取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提供了场所和平台;另一方面,媒体有时可以利用知识分子的权威和学术观点来提高收视率。但是这些与电视相结合,被电视包装造就的“学术明星”出于利用电视的考虑,有时反被电视利用。他们为了能够上电视,放弃了自身的立场,转而迎合电视的需要。这就导致这些“学术明星”在电视上演讲的依据并不是自身的专业认知,而是电视收视率的需求。专家们在电视上出现的意义本来是该给观众正确的引导和解释,结果却变成了迎合观众口味,把严肃的学术话题断章取义或片面化,通过调侃和娱乐的形式传达给了大众。文化精英这样参与电视显然无助于精英文化在电视中的传播。理想的精英文化在电视中应该是以独立的系统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黏附在大众文化之上的碎片而存在。
在今天的社会中成为“学术明星”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已使得诸多学者过分推崇大众传媒的作用,这一点从“百家讲坛”一时的火爆程度足以证明。但是学术明星毕竟不同于专家学者。如果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了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徕观众的符号。在这个意义上,专家、学者一走上电视就不再是专家、学者了……他们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6]。
“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曾把栏目主讲人的挑选标准解释为“三维”,即“学术+电视化语言+个人人格魅力”。相比其他专业领域的尖端人物,具有教师职业背景的主讲人更擅长将学术内容以通俗、浅近的语言讲述出来,从而有效地拉近了节目与受众的距离。但是,学术性节目除了要符合观众需求、提高栏目收视率外,还应对在该栏目中演讲的学者负责,而不能通过商业化途径为造“星”而炒作。因为这些“明星”的主要身份仍然是学者,其主要任务是做学问,炒作的结果很可能使得这些“学术明星”疏于治学,成为栏目的商业筹码。在这种环境中,“学术明星”们很难再有时间和精力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最终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代言人,距离精英文化的专家学者越来越远,“更让人担忧的是,拥有明星地位的学者无法保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甚至会成为新的‘学霸’‘学匪’”[7]。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明星学者”,在学术界可能是某方面的专家,一旦与电视结合,登上“电视讲坛”,无论是学术界、电视媒介还是普通受众都不应该再以专家学者的学术水准来要求他们。他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对精英文化的研究与探求,而是一种文化普及与推广的工作。而对于一个文化普及者的要求应该是:其一,讲述的内容是精英文化的精粹,导向正确,受众需要了解;其二,讲述的内容能充分激发受众的兴趣,受众乐于接受;其三,讲述的方式应是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受众易于接受;其四,讲述者应该在受众中树立一定得威信,取得大众的信任与喜爱。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家讲坛”栏目所培养的“学术明星”在文化传承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而,从文化多元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既需要代表精英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以大众文化传播模式培养而成的“学术明星”,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都可以为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但是作为“学术明星”,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牢记自己的学者身份,遵守学术道德,勇于承担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丧失学术的严谨性,歪曲经典、曲解文化。而作为电视栏目,“百家讲坛”在制造学术明星的同时,要严格把关,认真筛选,加强管理,使得这些“学术明星”真正成为大众了解精英文化,熟识传统经典的领路人。这样做不仅体现了栏目对观众负责、对精英文化的尊重的态度,更是为栏目建立品牌效应、获得长久发展提供了保障与路径。
3 拒绝娱乐化
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兴起,大众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倾向得以凸显,找乐成为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8]。一档电视节目存在和发展的支柱都是收视率,而“娱乐”恰是收视率的保障。为了获得更高的收视率,电视媒介往往会刻意遮蔽现实生活中枯燥、呆板,难以理解的文化经典,而将经典仔娱乐性的元素不断夸张放大,最后形成了让观众开心但与真实的社会生活脱节的电视景观。各类电视栏目为了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尽力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把追求“娱乐”“通俗”当做首要选择。因而,娱乐性成为电视媒介最主要的特性。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由此对照“百家讲坛”栏目完全符合波兹曼提出的娱乐三原则:其一,“百家讲坛”栏目的观众定位是“只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大众”,主讲人的讲述通俗易懂,大多观众不需要也不可能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其二,“百家讲坛”栏目采取解说员提出问题、设置悬念,主讲人解决问题、回应悬念的“自问自答”的讲述方式,观众无须费神思考;其三,“百家讲坛”栏目所讲述的内容回避传统演说方法,注重“故事”的发展脉络,而不涉及理性的逻辑思维。而观众喜欢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觉得听起来很轻松。电视开在那里,不用盯着看,你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聆听,有种类似于小时候听说书的感觉,只是现在说书的人学究气更重一些,江湖味更少一些。我相信这个节目的大多数观众,跟我一样,并非出于全听全信的心态来看这档节目,七分娱乐,三分借鉴”[9]。在观众眼中,“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明星”的性质与娱乐明星相近。从某种程度而言,“百家讲坛”已经被当作由电视媒介、“学术明星”与受众共同参演的极具娱乐特征的“学术秀”。
但是电视媒介的娱乐化有其负面效应。虽然,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不快、所有的负面因素在电视中都有可能因此被化解掉,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消遣的需要。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电视所带来的娱乐性消遣对于成人来说是一种逃避,等到白天重新面对真实生活得时候,他们内心的反差会油然而生,这将更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电视不仅仅是在传播特定的信息,而且它还在传递电视创作者对社会的理解。电视媒介用一种逼真的画面营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电视世界,这个世界用自己的美好遮蔽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如意,给人以快乐的幻觉。这是电视普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诉求。读书、思考可能给人带来批判和反思的精神,但看电视更多地让人们认同这个社会,产生一种顺从心理。
波兹曼面对美国电视的娱乐化大潮忧心忡忡地警告:“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比如电视,作者注),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如果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关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0]”
同样,“百家讲坛”中表现的“娱乐化”倾向也已经对精英文化在大众中的有效传播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解读精英文化、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大有让位于“娱乐化”效果的趋势。主题设置上,侧重于故事性强、关注度高、符合观众猎奇心理的内容,而不注重这些内容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的大小;主讲人选择上,对专家学者讲解风格个性化、讲述方式通俗化的要求重于对其专业素质的考量;传播效果上,注重产品包装、竭力提高收视率而忽视观众的收视心态以及栏目的长远发展。的确,对于一个电视栏目而言,收视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节目要体现传播的价值,必须通过收视率来考量。但是我们不能唯收视率,更不能以牺牲知识的严肃性为代价来追求节目的娱乐效果,换取最大收视率。
“百家讲坛”栏目传播的内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这些国学经典具有严肃性、连贯性、纯洁性的特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与文本体现。如果以娱乐的方式传播这些文化知识与理念,就会使其陷入快餐文化的漩涡,使人们在轻松娱乐中削弱了批判地吸收和理性地思考的能力,消解国学经典所负载的价值,同时会对观众形成误导,进而对整个中华文化的知识传承体系造成伤害。更近一步说,“百家讲坛”栏目以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解读精英文化,肩负着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引导观众深层思考并树立高尚境界的责任,更不能单纯追求收视率,并像纯娱乐节目那样靠观众的捧场来生存。
[1]陈力丹.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J].现代传播,2007(3):36.
[2]赵猛.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流变与整合[D].长春:吉林大学,2006.
[3]祁林.电视文化的观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39.
[5]王俊棋.超越精英与大众的紧张[J].当代文坛,2007(5):29-31.
[6]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电视的庸俗化——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EB/OL].[2009-03-10].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97013.htm.
[8]万卫·解密“百家讲坛”:主讲人是核心竞争力[EB/OL].(2007-08-01)[2009-02-16]http://www.zjol.com.cn/05cjr/system/2007/07/31/008657204.shtml.
[9]李倩倩.对学术性节目与“学术明星”的思考[J].新闻窗,2007(1):38-40.
[10]尼尔·波兹曼.娱乐致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On the Living Space of Lecture Room
GUO Wenjun1,NING Zhuqing2
(1.China Yello River TV,Taiyuan030001,China;2.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030051,China)
Lecture Roommust give up pursuing audience rating if it wants to continue and last.It should interpret elite culture in a proper way so as to realize a combination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and to improve cultural level of general public while simultaneously introducing and promoting elite culture.In manufacturing academic stars,it should strictly screen and strengthen management,so as to make these“academic stars"become guides in spreading elite culture.Finally it should give up pursuing audience rating as its only aim and living by the number of audience like entertainment programs,and shoulder a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lassic culture and giving the audience much food for thought and cultivating a noble personality.
Lecture Room;living space;infotainment
G220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0.06.014
1673-1646(2010)06-0054-05
2010-04-22
郭文君(1965-),女,主任编辑,从事专业:新闻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