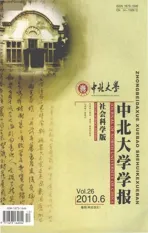《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主义解构视角*
2010-02-09张小彩刘陈艳
张小彩,刘陈艳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 030051)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主义解构视角*
张小彩,刘陈艳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太原 030051)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理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颠覆了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主张打破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不再是全知全能的的作者,而是邀请读者涉入到虚构的故事中来,打破了作者与读者的二元对立。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萨拉的主体性解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话语权,她在寻求自我解脱和自由的过程中也帮助查尔斯得到了心灵的自由。
《法国中尉的女人》;后现代主义;解构;二元对立
后现代主义是指发生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并于其后70,80年代流行于西方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从总体来看,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放弃现代性的根基,对现代文明发展和传统的各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1]。20世纪后期,西方的哲学观将逻各斯(logos)看作是万物背后的根本原则,一个潜在的上帝或神,所有的人和物都要遵循逻各斯的运转原则。西方哲学体系中全面设置了如主人/奴隶、真理/谬误、同一/差异、主体/他者、本质/现象、必然/偶然等二元对立[2]。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正是相对于逻各斯中心论和结构主义的哲学观念而缘起的[3],是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理念。解构主义主张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秩序,包括社会秩序、道德秩序、思维习惯和个人意识等。文化的转型也呼吁一种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模式。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在1969年发表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正是对这种社会文化及文学转型的一个敏感而迅速的回应。
1 “作者已死”,叙述者是开放的、自由的
后现代主义小说观认为作者不再是单纯的作者,而是明确告诉读者小说纯属虚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并邀请读者涉入其中的虚构世界[4]。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场的消失和死亡,同时又存在于阅读的新的在场中,而文学作品在场的消失和重建活动也摆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5]。从结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福尔斯对小说的成规、法则和作者的权威均提出了质疑。叙述中作者对自己的叙述权威进行了公开坦承的嘲弄,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提出了置疑。前十二章中作者用生动的笔法向读者描绘了一个追求自由独立的“谜一样”的女性,但在十二章结尾的时候,作者突然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令读者猝不及防的问题:“萨拉是谁?她是从哪个隐蔽的角落里冒出来的?[6]”在第十三章开头,作者开始了与读者直接的交流,自问自答地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完全是想象。我创造的这些人物只是在我头脑里……也许我正住在我虚构的小说中的一栋房子里,也许查尔斯就是伪装的我,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4]”在第五十五章,作者索性放弃了传统意义上作者的权威,而是扮作故事中“一位四十多岁满脸胡须的男子”[6],与查尔斯坐同一节车厢前往伦敦,并声称“我不能再装下去了,那个男子是我约翰·福尔斯。[6]”作者一会以作家的身份出现,一会以虚构人物的形象出现,一会又是一位故事的旁观者,“从叙事内部颠覆了传统经典叙事的叙事规约。它的叙述者具有穿梭故事内外的滑稽身份,将故事统筹于全知叙事中,又用自省评述暴露故事的虚构性和游戏性。[7]”这样,叙述者、读者和故事人物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游戏,三者之间互为依存又各自独立,作家与读者似乎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现实主义小说在叙述上维持线性的结构,故事严格按照开端、发展和结局的顺序安排,而故事的结局往往是闭合的、唯一的。福尔斯对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批判尤其体现在开放式的小说结尾。他在结尾近乎放弃了对小说中人物、情节和读者的控制权,而是给了读者充分的自由,设计了四种可能的人物结局。这四种(也许是无数种)可能的结局使文学的虚构性完全暴露在读者的面前,因为“真实只能是一个,而虚构则有无数的可能。[8]”福尔斯通过开放性的结局“打破了传统小说固定的线性模式,在给读者提供了发散性的思维空间的同时也使读者不知不觉参与到叙事活动中来,进而也解构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9]”
2 男性话语权的解构
西方哲学体系为求压倒多数,强力推行等级制度,在主体/他者的二元对立中,前者统治支配,后者从属派生[2]。受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查尔斯一直将女性视为受保护的对象。与萨拉初次见面时,他曾警告正在欣赏海景的萨拉远离防波堤;在他了解了萨拉的处境后,劝她离开莱姆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萨拉自己的选择,“正是这种耻辱使她活了下来”[6]。当查尔斯要到伦敦去时,他要萨拉等他,并提出给她经济帮助,但是萨拉说她不会再见他了。萨拉离开后,他还幻想着她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着他。所有这些都是查尔斯罗曼蒂克骑士精神的体现,但他还是没能超越男人强大的古老而虚幻的神话。当他千里迢迢找到萨拉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啜泣和求援的双手[8],而是萨拉的拒绝。格罗根医生可以说是莱姆镇权力的化身,也是小说中男性话语权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萨拉得了忧郁症,建议将萨拉送进疯人院,并列举了女性由于追求爱情和安全感而变态的故事。在男权话语的经典叙事中,萨拉将是这一叙事的女主人公。而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颠覆了这一叙事传统,萨拉的“自我放逐”和对自由的渴望使其得到了解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
对比而言,蒂娜更像是传统叙事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代表。蒂娜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她出身高贵,并且用维多利亚传统将自己建构成了一个正统的天使般的人物。蒂娜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查尔斯身上,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当查尔斯坦白不再爱她的时候,她说:“你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行,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让你满意,只要你不离开我。[6]”尽管这样,小说的第一和第三种结局中她还是被查尔斯抛弃了。
萨拉具有一种抵抗男性话语权的叛逆,她希望从男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因而对既定的社会道德秩序构成了威胁。在第三种结局中,萨拉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她意识到只要她们结婚就意味着她要承担妻子的义务,而这与她渴望自由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拒绝查尔斯求婚的同时,她也拒绝了“妻子”这一父权社会为女性指定的传统角色,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传统的维多利亚社会价值观里,男性是主体的拯救者,女性是客体的等待救赎者,萨拉拒绝了查尔斯,也就拒绝了其等待救赎的被动客体身份,而是坚持了捍卫自己主体性的决心。当查尔斯离开萨拉的房间走向街头的时候,读者也许会感到他终于摆脱了时代的束缚,获得了解脱和自由。因此,萨拉是促使查尔斯思想转化的关键人物,对萨拉的爱使他有勇气解除了与蒂娜的婚约,但也因此受到了舆论的羞辱[4]。
3 “上帝已死”,自我诞生
在西方精神文化中,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万物的中心,是宇宙意义的神圣化象征,人生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一声断喝——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10]。以尼采哲学观为主要思想渊源,解构主义反对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法国上尉的女人》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的顶点时期和大英帝国经济文化的全胜时期。反映在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上,当时的人们大都妄自尊大,又因循守旧。男主人公查尔斯风流倜傥,大学时学古生物学,酷爱化石。在未认识萨拉之前,“上帝”深深植根于他的道德观念里。感情上偶有越轨,他便会在教堂里忏悔[10]。在第四十七和四十八章,当他发现萨拉并没有失身于那个法国佬的时候,他冒着大雨离开萨拉,走进一个教堂祈祷,“他看见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而是他自己,那十字架也化成了萨拉。[6]”“被钉上了十字架”的查尔斯正经历着从传统束缚向自由转变过程中的煎熬与痛苦。关于查尔斯的忏悔,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独白:“查尔斯突然领悟到了基督教的教义……他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整个时代骚动不安的生命和它那硬如钢铁的戒律成规,压抑的情感和滑稽的幽默,它严谨的科学和不严谨的宗教,它腐败的政治和一成不变的阶级观念……这个时代完全没有爱和自由,没有思想,因为欺骗就是它的本质。它没有人性,只有一台机器。[6]”查尔斯的道德观念带有明显维多利亚时代的烙印,他与蒂娜订婚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婚姻形式。当时上流社会通行的婚姻依然是以财产和门第为基础,所以从门第上来说,查尔斯与蒂娜是门当户对的配偶。但与萨拉的邂逅与相识使他觉得自己之前的生活与化石相去无几,他被萨拉的神秘深深吸引。萨拉的神秘、萨拉的自我放逐、萨拉的与众不同使查尔斯意识到自己所恪守的维多利亚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他所牺牲的自由。
萨拉是一棵生长在人群中间带刺的树,她用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方式寻求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在莱姆镇,她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是“堕落的女人”,她时常披着黑色的外套来到防护堤上,久久凝望。有人猜测她是在等待曾经抛弃她的法国中尉的到来,所以送给她一个“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称号。她冷漠、寡言、孤独,从一开始就与周围的世界处于敌对的状态。作为一个被世俗者唾弃的离经叛道的女性,萨拉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使她一直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并成为被世俗者嘲弄的对象。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上尉的女人》中文译本的前言中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描写“在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6]”
4 结 论
福尔斯在《法》中曾坦言:“如果这是一部小说,它不可能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11]”那个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作者已死”,他可以是故事的叙述者、参与者或旁观者。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萨拉是神秘的,也是叛逆的,查尔斯似乎被她牵进了一座黑暗的迷宫,渴望光亮的出口。萨拉的主体性也解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话语权,争取了一个有意义的自己存在。福尔斯的《法国上尉的女人》无论从作者身份、叙事规约还是人物描写上都折射出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
[1]克里斯·加勒特,扎奥丁·萨德尔.介绍丛书·后现代主义视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77.
[2]赵一凡.从胡赛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7:351.
[3]云红.论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J].南昌大学学报,2010(5):124-127.
[4]张中载.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176.
[5]杜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探析[J].社科纵横,2010(6):114-116.
[6]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M].陈安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邓帮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策略再研究[J].四川外国语学院报,2006(11):34-37.
[8]林萍.超越现实主义——析《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人物塑造[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9):49-53.
[9]孟佳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主义特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4):47-48.
[10]王玉洁.《法国中尉的女人》: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图解[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6):46-48.
[11]陈静.从“新小说”的角度看约翰·福尔斯的真实观——兼论《法国中尉的女人》[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1):62-65.
The French Lieut enant’s Womanat Deconstruction Philosophy Lens
ZHANG Xiaocai,LIU Chen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030051,China)
As the typical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Derrida’s deconstruction philosophy subverts the logos-centered ideology and claims to break the metaphysics thinking mode of binary opposition.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John Fowles is no longer the omniscient writer.Rather,he invites the readers to be involved in the story an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writer and reader is broken.Sarah is one of the typical characters in post-modern novels,and her existence deconstructs the male discourse rights.She helps Charles to find spiritual freedom when she is freeing hersel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post-modernism;deconstruction;binary opposition
I106.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0.06.011
1673-1646(2010)06-0044-03
2010-03-09
张小彩(1977-),女,讲师,硕士,从事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