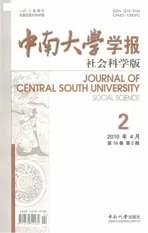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刑法意义研究
2010-02-09黄瑛琦张洪成
黄瑛琦,张洪成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中国刑警学院刑侦三系,辽宁沈阳,110854)
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刑法意义研究
黄瑛琦,张洪成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中国刑警学院刑侦三系,辽宁沈阳,110854)
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是刑法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其承诺在刑法学上可能就难以成立,这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互动关系的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而言,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如果被害人不具备认识能力,那么,在我国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一系列罪名就因为不符合构成要件,而无法展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而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判断,必须结合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被害人;被害人的认识能力;被害人的承诺;刑法意义;西方刑法理论
被害人的承诺是刑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在探究该问题的时候却很少追问被害人的承诺以什么为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必须归结于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承诺的可能,被害人的承诺也就没有探究的必要。当前,我国及国外的相关刑法理论对该问题的研究均局限于诈骗罪这一具体罪名上,而对于其他类似的牵涉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却没有展开应有的研究,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供操作的标准。笔者拟从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的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群出发①,对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以期归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被害人认识能力之刑法意义概述
(一) 被害人认识能力刑法意义的滥觞
肇始于西方的近现代刑法学,深受罗马法中私法主导地位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即在于个体权利的保护、意思自治思想的贯彻等。这样,在法律上(包括传统的私法,如民法等;也包括公法,如刑法、行政法等)就非常注重对被害人的个体意思的保障。其根源,通过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的法律格言“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就能得到全面的体现,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1]对于出于被害人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场合,就不会产生权利侵害问题,也就无由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现代的法是建立在国家对各种群体和个人的充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之上的,建立在国家对‘强制的垄断’之上的法。”[2]对于个体权利,国家更加注重对公民个体意思的保障,对于其在正常意思表示下所作出的行为,国家承认其为最高的权利,有凌驾于国家刑罚权之上的效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在对西方刑法理论充分借鉴的同时,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传统刑法中的“重刑轻民”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软化,人们从法律的客体逐渐变成了法律的主体,个体权利得到彰显。当前,我国《刑法》也充分赋予了国民以自我处置权,即对于公民出于其个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自损或者他人在一定范围内的损害行为,刑法一般均不将其纳入打击范围,除非这种损害行为超越个人承诺权限的范围,而侵害了国家、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国民的利益,否则,刑法不会主动介入。但对于行为人欠缺认识能力、并进而影响其辨认能力的情形而言,我们就应当全面分析,因为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欠缺可能直接导致行为人的损害行为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与被害人承诺的损害表象无关的其他犯罪。这样的情况在刑法中并非罕见,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对之展开讨论。
(二) 被害人认识能力刑法意义的研究现状
国外及我国刑法学界针对被害人认识能力对行为定性之影响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被害人承诺的范围内,即被害人承诺的有效要件是什么,这中间就涉及到被害人的承诺能力问题。而要正确地判断被害人的承诺能力,就必然要探究被害人对承诺事项的认识能力,因为被害人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是其作出有效承诺的前提。目前学界探讨最多的就是诈骗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问题。②在该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多数学者均认为,诈骗罪中被害人必须具备认识能力,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对行为的定性。③该定性直接牵涉到的争议就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问题,即对于没有认识能力的被害人,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学界基本上将之认定为盗窃罪。其原因是千篇一律的“从无行为能力人如幼儿、高度精神病患者手中骗取财物或者从限制行为能力人处骗取该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权处分的财产时,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因此,仅有处分事实而无处分意思的,不能认定为诈骗罪”。[3]笔者认为,这样的论断基本符合我国的司法现状,但论者却没有从根本上对该问题展开讨论。笔者以为,在该罪中,如果行为人确实明知被害人为没有认识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那么对行为人认定为盗窃罪是没有疑问的。其原因在于,该行为可以直接认定为是侵害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其财产的实际占有人的财产权,在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时候,于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其财产的实际占有人而言,该行为属于“秘密”手段,即未成年人或者高度精神病患者的代理人或者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根本不知道行为人所实施的侵害其财产权利的行为。这样,该行为就完全满足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从而阻却了诈骗罪的成立。
在英美刑法中,犯罪构成的双层结构赋予了行为人可以将被害人的同意作为正当的辩护理由的权利,但这种同意以被害人出于自愿为必要,即被害人出于自由意志所承诺的行为才能成为正当的免责事由,“自由意志是达到一定年龄,心理成熟,精神正常的人的一种心理能力。因此,精神病患者和未达法定年龄的人是不能表示法律‘同意’的”[4](93)。而被害人因为欠缺认识能力,在行为人的欺骗下实施了一定的承诺行为,并不能成为行为人免责的理由,“‘欺骗’虽常常影响人的真实意志,所以一般认为,‘同意’应当排除‘受欺骗’。但是,‘欺骗’情况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从犯罪构成角度看,欺骗可分为‘事实欺骗’和‘动机欺骗’两类。前者导致被害人对被告人‘行为事实’的误解,后者仅仅涉及对‘引起行为发生的有关情况’的误解。例如,医生同女患者性交,而她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她以为这就是医生对她说的进行特殊检查与治疗。这是事实欺骗,该妇女不能被认为是‘表示同意’,因为她没有表示同意性交,同意的是接受治疗,所以被告人医生不能免除强奸罪的责任。”[4](94)这样,在被害人没有认识能力的情况下,其承诺行为并不影响对行为人侵害行为的定性。
以上研究表明,目前学界的研究视角仅限于个别罪名中,而对刑法中大量的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即涉及到行为人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从而引起被害人认识错误,并作出一定处置行为的罪名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并没有被展开专门的研究,也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本文拟从刑事犯罪的相对方,即被害人的角度出发,并以其认识能力为立足点,来探讨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亦即从其认识能力具备与否这个角度来探究其意思表示对权利侵害人的行为的法律性质的意义。
二、我国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之概况
从最广义的角度讲,被害人的范围非常宽泛,既包括狭义的自然人,也包括非国有单位、国家,甚至社会。[5]但笔者倾向于将被害人限定在狭义的层面上,即被害人专指其财产权利或者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自然人。
从我国现行刑法体例的设置来看,涉及上述狭义被害人认识错误的罪名主要集中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章节中,其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强奸罪,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强迫他人吸毒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引诱他人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等。此外,其他章节中涉及该研究问题的罪名还有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这些罪名均无一例外地涉及到被害人的认识错误问题,即只有被害人具备正常认识能力,且在其认识范围内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才能满足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
从目前的研究实践来看,刑法学者是从积极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的,即认定这些罪名的时候均假定了被害人是具有正常认识能力的‘人’,而对于欠缺构成要件要求的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则完全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导致在实际的司法操作中,人们往往很容易认为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根本就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导致罪名适用上的不当。因此,这些罪名当中涉及的被害人的承诺,无疑均要求以被害人对于行为人欺骗的事情或者事由存在正确的理解、认识为前提。如果这个基本性的前提不具备,那么就可以说,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根本就不齐备,因此,无由在这些罪名范围内认定行为的性质。故要求被害人应当具备与这些罪名要求的基本的认识能力,否则,其作出的所谓承诺完全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从而可能从根本上影响行为的定性。
三、对刑法中行为的“认识能力”的理解
从现行的刑法规定来看,在刑法中涉及“他人认识错误”等的罪名,主要集中于侵犯公民个人法益的罪名中,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因为只有这些罪名才涉及“他人”(即被害人)对自身权利如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处分行为,也才存在被侵害的危险。
纵观现代法制社会的发展进程,笔者认为,一方面,现代社会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复苏,一定程度上给个人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或者其他权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另一方面也给刑法在判断行为人意思的表示真实与否时设置了障碍。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人”的是否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的判断成为问题。
从法理的角度,明确将刑法中所要求的“他人陷入错误”等罪状中规定的“他人”限定为具有一定的认识、控制能力的人,不具有这一能力的人不能理解为刑法意义上的具有正常承诺能力的被害人,也就不存在“陷入认识错误”的问题,就更不存在构成以这些认识错误为基本构成要件的罪名。
笔者认为,凡刑法中规定的行为的客观方面要求被害人对具体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从而作出错误意思决定的时候,其前提就必须存在被害人对具体事实存在认识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本身由于智力障碍或者其他心理、生理原因,导致其不能认识虚假的“事实”本身,质言之,行为人没有认识能力,则毫无疑问应当将之排除出该罪名的领域,至少不能成为认定特定罪名中的客观方面的依据。如,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基于犯罪人的欺诈而陷入认识错误,就必须以被害人本身存在认识可能性为前提,否则,就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而只能以盗窃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典型的情形为:犯罪人诈骗脱离监护人监护的精神病人或者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从而获得其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对此情形,目前理论界、司法界的一致观点均认为,此行为应该构成盗窃罪。其原因即在于犯罪人实施的所谓欺诈行为,在这些特定人的面前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从而阻却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成立,故不能盲目地将其界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
同样,可以列举的典型情形是:行为人多次教唆、引诱、欺骗不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吸毒,或者教唆、引诱、欺骗多名精神病人或者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从事吸毒活动。在此,我们从刑法的用语和立法本意也可以看出,这类行为本身没有成立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毒罪的余地。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刑法设立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毒罪,本身就暗示了被害人本身对于教唆、引诱、欺骗行为应该有概括的认识,即基于犯罪人的教唆、引诱、欺骗行为陷入错误,如果行为人本身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对这类行为如果还是僵硬地套用这个条文,无疑是不正确的。笔者更倾向于将这一行为归类为强迫他人吸毒罪。因为行为人在主观恶性的指导下,实施了上述行为,于被害人而言,实则相当于强迫行为,只不过其行为的方式为与暴力、胁迫相并列的其他方法,而且事实也表明,对行为人科以这一罪名,完全与其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不会导致罪行适用上的不均衡问题。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强奸罪的罪状进行考察。在我国刑法中,强奸罪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即与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即使事先已经得到了被害妇女、儿童的同意,也不影响强奸罪的成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该罪所涉及的这几种情形中,其实都存在被害人的承诺问题,但因为被害人欠缺认识能力,即缺乏对性行为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从而陷入错误,导致自己的承诺行为无效。否则,具有正常认识能力的成年妇女,其作出的同样承诺行为,就直接排除了行为人行为的犯罪性。这可以说是被害人承诺行为无效的典型表现。即立法者预设的情形就是这些人没有认识能力,其本身不存在承诺的可能性,故对之必须与无承诺甚至反对相等同。
四、对被害人缺乏认识能力的处理
(一) 被害人认识能力之判断基准
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但又必须给予正确认定的概念,否则,就无法正确判断被害人是否存在认识能力。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不能单纯地依靠固定的模式来判断,而要采用客观的标准,即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从被害人所处的地位及其智力的程度来判断其对于行为人所实施的欺诈行为有无认识的可能性。如果其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可能,对于处分自己的权利没有了解能力,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陷入认识错误、处分自己财物的问题。正如有学者在论述诈欺罪(即中国刑法中的诈骗罪)时所指出的那样:“完全缺乏处分财产的意思的幼儿和高度的精神病人等,不能说会作出财产性处分行为,所以,欺骗这种人、夺取其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为了能够说存在处分财产的意思,需要处分行为人自己了解其处分行为的意义。”[6]
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所涉及的对象,即被害人对什么内容具有认识才是本文所讨论的认识能力。笔者认为,认识的内容应该限定在被害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具有认识的基础上,换言之,被害人能了解行为人所编造的虚假事实,并且对于自己的处分行为具有认识,而且对虚假事实与处分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认识,但在自己的错误认识下,处分自己的权利。如果欠缺上述内容的认识能力,那么被害人就属于典型的欠缺认识能力,其所作出的行为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个人作为被害人的场合,只要被害人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并在该认识下作出正确的承诺即可。对于被害人的承诺行为的有效年龄,我国的澳门地区刑法典对之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37条第3款:“同意之人必须满十四岁,且在表示同意时具有评价同意之意义及可及范围之必要辨别能力者,同意方生效力。”[7]如果行为人要具备基本的承诺能力,那么其必须首先具备认识能力,即正确认识自己行为性质的能力。
我国在“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中对相关被害人的承诺能力或者认识能力并没有涉及。这样,关于被害人认识能力的问题,从刑法角度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规范标准。但根据法规范的统一性原理,可以从民法的角度找到其规范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第13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由这些相关规定可以知道,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应当参照其基本的民事行为能力。因为在涉及到的诈骗罪、欺骗他人吸毒罪等犯罪中,被害人所承诺的均是行为人对其基本的财产权、健康权等的侵害行为,这些承诺行为均建立在被害人对这些基本的民事行为的错误认识基础上。因此,参照这一民事法上规定的认识能力标准是完全合理的,即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一概否认其具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对于10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及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的认识能力则存有疑问。笔者认为,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能力,可以参照正常的社会观念上的普通人对相应的行为的认识能力来认定其有无认识能力。但对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对于损害其较大利益的侵害行为,笔者更加倾向于认定其为无认识能力。④这也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上的考虑。
(二) 被害人缺乏认识能力的处理
关于诈骗罪中被害人的认识错误问题,我国已经有学者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如张明楷教授曾指出:“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或者说,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但有成立诈骗未遂的可能性)。”[8](776)该论点就直接指出,在诈骗罪中,必须存在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并且也只有存在行为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情形下,才有诈骗罪(一般指既遂状态)存在的余地,否则,诈骗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就无法满足。在此存在明显的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的就是对机器、没有处分能力的幼儿、高度精神病人实施的所谓“诈骗”行为。如张明楷教授指出:“机器不可能被骗,因此,向自动售货机中投入类似硬币的金属片,从而取得售货机内商品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再如,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幼儿、高度精神病患者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谈不上行为人的欺诈与被害人的处分,故不成立诈骗罪,只成立盗窃罪。”[8](779−780)
关于信用卡诈骗罪,我国理论及实践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而且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为我们立足于被害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如《刑法修正案》(五)的第2条就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基本形式就是:“(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恶意透支的。”同时该条的第3款对于盗窃未废弃的信用卡并进行使用的行为,明确定性为盗窃罪:“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立法例的基本立场与上述列举的从机器中骗钱的行为完全一样。有学者立足于行为人无视使用信用卡的场合上的差异而主张对该行为进行统一认定的观念:“如果行为人没有取得信用卡相关的证明,则行为人必须采取一定手段才能够实际对信用卡上的财产取得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区分行为人行为的对象。如果是 ATM之类的机器,应当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如果是特约商户或者银行,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定罪更具有合理性。”[9]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分存在问题的,因为既然盗窃的信用卡仍然需要具备其他条件才能使用,那么我们不如将之作为修正案(二)第一款中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从而排除对《修正案》(五)第2条第3款的适用。从立法本意来看,第3款所指之信用卡,应该是有效且不需要任何伪造的信用卡,对盗窃这样的信用卡并且利用的,才可能属于其文字的应有含义。
以上我们列举的两个典型的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目前在理论及实践界已经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对于其他涉及被害人认识错误的罪名,却并未展开深入的探究。笔者认为,对于涉及被害人为个人、并且其系处分个人财产的场合,可以视为无承诺,即可以将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视为刑法意义上的“秘密”等。如在诈骗罪等犯罪中,如果被害人欠缺相应的认识能力,则宜定性为盗窃罪,行为人所实施的诈骗等行为,可以视为是以未经财物所有人或者法律意义上的占有人的承诺,且这里直接实施交付的主体本身没有诈骗罪等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被害人资格,欠缺相应的承诺能力。
对于针对没有认识能力的被害人实施的侵害其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笔者认为,这完全可以参照我国刑法对行为人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或者严重精神病患者发生性关系的认定方法,即将这样的承诺行为认定为无效,而视之为无承诺行为,以“强制”的概念取代之。因此,对于涉及侵害个人权利的罪名,如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引诱他人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等,宜将之分别定性为:强迫他人吸毒罪、强迫他人卖淫罪、强奸罪等。⑤因为这些罪名中虽然并未涉及到强迫的手段问题,但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的这些行为对于无认识能力,并且不能正确认定行为的社会意义的人来讲,其危害性类似于刑法中的“强制”。而且,该欺骗、教唆、引诱等行为本身也完全等同于刑法中在该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所要求的“以其他方法”,故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刑事政策角度考察,我们也应当以后果更为严重的处罚方法取代相对温和的处置措施,从而达到遏制此类犯罪的目的。
五、结语
总之,刑法中涉及到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罪名还是相当多的。在这些罪名中,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承诺的行为均是此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如果被害人因为欠缺相关的认识能力而不具备认识的可能性,那就可能使行为人的行为无法满足特定的犯罪构成,从而导致犯罪性质上的直接转变。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不能盲目地把所有的行为通过原来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而要对欠缺认识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行为人欠缺认识能力的前提下,所有涉及被害人认识错误的罪名均被阻却。这实质上是说,该行为中并不存在实际的被害人承诺,类似于直接违背了被害人的真实意思,且被害人对该行为欠缺相应的认识。因此,我们在对该类罪名进行认定时,必须具体分析案情,根据刑法规定的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具体的分析,确认其具备什么样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做到准确定性。当然,本文研究的视角仅仅局限在被害人为自然人的角度,对于被害人为单位、国家或者社会等的问题,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 所谓罪名群,是一个没有严格刑法界定的词语。笔者为了方便概括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所有罪名而临时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其正确性值得探讨,但这样便于称呼。
② 关于诈骗罪等犯罪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相关内容的研究,主要见诸于张明楷教授著的《刑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在赵秉志教授主编的《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没有涉及到被害人认识错误的内容。可见,该问题的突破性研究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这也说明该问题的研究处于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中。
③ 有关被害人承诺的内容,现在各国的刑法均将之纳入违法性排除事由。而在我国的刑法中,则将之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具体可以参见刑法学相关教科书。如张明楷:《刑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关于诈骗罪中被害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等,也有大量的论文、著作对之展开了讨论,具体可以参见张明楷《机器不可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载刘宪权主编:《刑法学研究》2006年第2卷。
④ 有关被害人承诺的年龄,有学者从刑法关于特殊犯罪的形式责任年龄出发,并结合民法的相关规定认为,作为被害人,对于自身的重要人身权利的认识年龄为14周岁。因为对于重要的人身权利,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了完全的认识,而且这种权利仅限于生命权、身体健康权等一些重要的人身权利,而其他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还应当以刑法中的16周岁为准。参见徐岱、凌萍萍:《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但笔者认为,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了,因为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才应该将被害人的认识能力的标准定为对生命权、健康权的认识能力的年龄等于或者高于对财产权的认识年龄。
⑤ 如有人在论述被害人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时,就对引诱幼女卖淫罪作了专门的研究,并指出,刑法第301条第2款规定,在聚众淫乱行为中,如果被引诱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该行为成立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而不成立一般的聚众淫乱罪。参见杜杰灵:《刑事被害人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将未成年人理解为年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论断是正确的,但如果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就应该认定为强奸罪。
[1] 张明楷. 刑法格言的展开[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253.
[2] H·科殷. 法哲学[M]. 林荣远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114−115.
[3] 王作富.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1275.
[4] 储槐植. 美国刑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 刘生荣. 犯罪构成原理[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119.
[6] [日]大冢仁. 刑法概说(各论)[M]. 冯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247.
[7] 肖敏. 被害人承诺基本问题探析[J]. 政法学刊, 2007, (3): 15−19.
[8] 张明楷. 刑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9] 黄京平, 左袖阳.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6, (4): 36−40.
Crim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HUANG Yingqi, ZHANG Hongcheng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The Third Department of Crime Investigation, China Crime Police College, Shenyang 110854, China)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riminal law. The crimes related to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are not minor. If the victim does not ha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then it is impossible to explore the victim’s promise, whi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victims. On the whole,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belongs to the element of criminal constitute. If the victim does not ha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a series of charges relating to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may not be handled, nor can they be carried out on the perpetrato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do not meet the elements of constitute. We should combinate the civil law and other laws to judge the victim’s cognitive ability.
victim; cognitive ability of victims; promise of victims; criminal significance; western theories relating to criminal laws
book=16,ebook=158
D924
A
1672-3104(2010)02−0015−06
[编辑:苏慧]
2009−06−23;
2009−12−15
黄瑛琦(1980−),女,安徽泾县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学;张洪成(1978−),男,江苏新沂人,中国刑警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