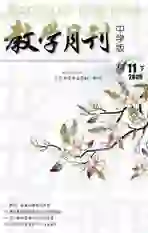教师:权威向智慧的转型
2009-12-31范远波
范远波
编者按:2009年第7期的“视点”栏目,我们曾探讨过“今天我们怎样当教师”的话题,本期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话题。在本期所选的两篇文章中,《教师:权威向智慧的转型》一文论述了当前学界较为关注的“教育智慧”问题;《国内教师隐性暴力行为研究综述》一文综述了当前国内教师隐性暴力行为的研究现状,旨在从另一个角度引起广大教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教师,一般理解为传播人类知识经验和思想意识,并促进个体发展的专业人员。这种认识赋予教师一定的责任与权力,即认为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是国家教育方针的实施者,是学校规章制度的维护者,是家长管教权力在学校的委托者。因此,在许多教师的观念中,教师权威与教育活动相伴随,是一种能改变学生思想行为方式并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量。有些教师错误地认为,既然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拥有这种职业赋予的责任和权力,就应该充分依靠或利用教师权威给学生施加影响,甚至可以凭借权力压制、威吓和体罚学生。
一
教师权威观念源于教师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它与传统的教师形象定位有关。传统教师往往被赋予在某一领域掌握丰富知识、具有某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角色形象,在一些学生的心目中甚至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能形象。因此,教师成了知识的源泉、智慧的象征,是学生必须遵从和敬重的对象。其次, 它与传统的育人观念相伴随。传统的教育目的在于让学生服从管理,遵守秩序。教师有义务让学生的心智得到服从,以约束其超出常规的活动,有责任阻止或扑灭学生正在形成的倾向于邪恶的意志。正如赫尔巴特所说,教育要做的事情就是遏制儿童恶的意志,“给予这种恶的意志以深刻的否定,使它受到挫伤”,而这种挫伤恰恰需要权威,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最活跃天性的人来说,权威是最不可缺少的”。[1]我国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说教。这些育人观念无形中在孕育和强化着教师的权威形象。最后,当前教育中的纪律和评价导向构建了以教师权威为核心的师生关系。教师权威本质上是一种教育交往的心理状态,对学生来说,是严肃、敬畏和恐惧,对教师来说,是驾驭、控制、管理的教育力量。教师凭借自身“闻道在先”和社会赋予其“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 在教学和管理中有意无意地树立起自身独断的权威,强化师道尊严的普遍认同。涂尔干在其《教育与社会学》中就认为,“教育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威”,“教师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伟大的道德观念的阐释者”。在现实中,这种权威往往依靠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学校规章制度和纪律、社会和家长的督促期望等形成。比如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三好”学生评定,“听老师的话”“尊敬师长”等教育中的习惯用语所体现的种种要求本身就在营造着维护和服从教师权威的社会氛围。
然而,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广泛普及,教师权威观念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在逐渐发生变化。那种忽视教育对象复杂多样的情感和追求,单纯靠强调威胁、限制、发号施令、使用压力等来教育学生和管理班级的做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尤其是班主任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艰巨。在对待学困生的问题上,教师权威形象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无论在学校情景还是在社会其他情景中,它都难以让学生产生敬畏和服从感。学生追求的是多元、多样和自主,不愿停留在统一标准的规范和要求中。如果教师不明白这一点,仍然站在教师的权威观念上指导和教育学生,迫使他们顺从自己的意志,就可能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甚至遭到抵制和对抗。去年发生的“杨不管”事件,其实并非不管,而是管不了,学生无视教师在课堂上的权威形象,或者说教师已经没有了控制课堂正常秩序的权威形象。面对学生打架,杨老师虽然很生气,但也只能说一句气话:“要有劲下课到操场上打去。”可以想象,假如教师或班主任失去了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权威影响力,类似杨老师的无奈和压力恐怕就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难言煎熬,随之而来的也就是职业挫败感和职业倦怠症。就学生而言,在长期的权威影响力压制下,也容易形成默认、顺从的氛围和守成观念,不利于学生质疑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养成。
二
在学校教育情景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成员,其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辅助者、管理者、咨询者、激发者的角色离不开其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不应该来自社会各方面赋予教师的权威形象,而应该来自教师教育教学行为中的机智、幽默、公平、公正、诚实、谦虚等体现教育智慧的能力、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教师权威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的体现往往以教育内容的唯一性和标准化代替学生认识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以教育方式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代替解释、说服和理解。而智慧型教师则恰恰相反,当教师面对课堂上一些无心学习的同学在小声聊天,影响正常教学时,不是怒气冲天地对那些学生大动干戈,或给予体罚,而是采用教育智慧,比如突然停下来问学生:“乌鸦和喜鹊都是喜欢叽叽喳喳的鸟,为什么我们喜欢喜鹊叫,而不喜欢乌鸦叫呢?”在学生的注意力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吸引之后,教师才慢慢地说:“因为喜鹊是在大家希望它叫的时候叫,而乌鸦却是在大家不希望它叫的时候老是不停地聒噪,吵得人无法忍受。现在我们有些同学就跟乌鸦一样,在大家不希望他说话的时候却老是说话。”老师的话刚说完,教室里就出奇地静,因为每个学生都怕被同伴扣上“乌鸦嘴”的帽子。当教师面对学生无理取闹时,与其拉下脸严肃地批评学生,倒不如幽默地化解。特级教师钱梦龙就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在检查了解学生自读课文的情况时,要求同学们尽量不看书回答,并顺口说:“如果实在忘了怎么办?”下面就有学生接口说:“偷看一下。”引得全班哄笑,钱老师没有痛斥和批评那个学生,而是马上说:“偷看一下,说得好呀!别笑,偷看也是一种能力呀,很快地在书上一眼扫过,就马上找到自己所要的那个词、那个句子,不也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吗?不过,请注意,考试的时候可不要培养这种能力。”[3]当教师面对众多个性鲜明的学生时,难免会有自己的爱好和取舍,即所谓的偏心,钱钟书说:“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也就是说,偏心客观存在,无可厚非,有谚语云:“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而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喜欢漂亮的孩子,乃人之常情,关键在于教师的偏心如何体现为公平的爱心,既不至于让学生有被歧视或被冷落感,也不至于让学生产生心理阴影或负面影响。如果教师尊重、爱护每一位学生,依靠集体力量和自己的人格魅力来组织、管理、教育和促进学生发展,而不是借助自己的教师权威或管理者权威来压服学生,那么,学生就会在群体的认同和压力下服从教师提出的各种要求,并自觉地接受有利于班级和自身发展的秩序。事实上,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在心理上、行动上、言语上的冲突时常存在,将冲突防患于未然或有效地化解,并将学生的需求和愿望纳入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并得到学生认可的秩序中,确实需要无穷的教育智慧。
三
教育智慧是一种实践智慧,具有动态生成、独一无二的特点。陶行知曾对“智慧”与“知识”作出这样的区分,他说,智慧是生成的,知识是学来的,“说话能力是生成的,属于智慧,说中国话、日本话、柏林话、拉萨话,便是学成的,属于知识”。[4]陶行知把智慧看成个体与生俱来并伴随人的学习成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自然这种能力不属于某一方面的能力,它体现在个体所有的思维活动和言行活动中。教育智慧就是体现在教育教学情景中的智慧。对教育智慧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的一种创新性品质;有人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感受的敏感性、教学机智、与学生沟通等能力的综合;也有人认为,教育智慧是教师具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意识、教学能力和教学艺术等能达到的一种教育境界。[5]尽管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但教育智慧无疑是指教师在教育情景中所展现出来的合乎目的、合乎规律的言行表现。它来源于教育者的各种经验、知识和理论,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经验、知识和理论。它通过对具体教学情境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经验提升并内化为教师自身理性的实践能力。
首先,教育智慧借助教学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和规律,在教育情景中不断生成多种可能,并在这些可能中寻求因时、因地、因人的最佳处理和最优解决方案。所谓最佳,是指学生能从教师的教育言行中体会到教师的爱和良苦用心。许多时候,教师虽然尽心尽责、苦口婆心,但是却得不到学生的理解,以致导致师生冲突、误解和不满。所谓最优,是指以最小的代价(资源、时间、空间、精力的投入)得到最令人满意的效益(产量、质量、预期等),因此,教师的教育活动要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不仅要考虑到眼前的短期效益,同时要兼顾长远的效益;不仅要注重设计的简单、方便、易行,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其发展价值。简言之,要善于选择那些节省教育资源、运用范围广、适应性强、派生作用大的最优化方案或模式。同时,教育智慧还表现为教师善于与学生打成一片。只有让学生亲近教师、理解教师,教师的设想、计划才能得到顺利实施。但是,许多教师,特别是科任教师,多数时候是一上完课便离开学生,学生只知道该科任课教师所担任的科目,平时只好称呼他们为“物理老师”,“英语老师”或“语文老师”等,压根不知道这位老师姓啥名什。有些教师不管上课抑或课后,总是摆出一副不苟言笑、高高在上的样子,学生对他敬而远之,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淡漠,甚至连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少讨论。如此一来,与其说学生不重视、亲近教师,倒不如说教师让学生感到陌生。
其次,教育智慧突出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地位,承认学生是复杂的人,是自主发展的人。教师把学生当做有多种需求的、自尊而又情感丰富、活生生的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教育智慧便无从谈起。自主发展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强调个体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熟练的技能,更需要有积极向上的情怀、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但在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以单向的控制关系为主,教师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学生成为知识和说教的“接收器”,独立思考、主动参与的权利被剥夺。教育过程中感受不到学生的灵气、活力与复杂细腻的情感,师生间缺乏思想与灵魂的碰撞与交融。有些教师甚至以扼杀学生的情感来强化自身的权威。如下面这个案例:
在我上初一的时候,我的同桌上课经常迟到,班主任对她印象不怎么好。一天早上,早读课铃声刚响完,班主任就出现在教室门口。班主任发现她还没有来,就站在门口那里等着她来。过了不久,同桌来了,班主任就叫她拿着书本站在教室门口读书,以此作为惩罚。第二天早上,不料我的同桌又迟到了,班主任还是站在门口等她来。才一会儿,只见我的同桌急急忙忙地跑进来,在门口处停下,衣服上沾有血迹,双手也流着血,而且手上还沾有一些油污。只听她说:“对不起,老师,我又迟到了,因为我的自行车的链子突然坏了,我就不小心摔了一跤。”只见她一边说一边伸出流着血的手给老师看。此时我看见她的手就觉得她应该好痛啊,但此时发怒的班主任就冲她一句:“明天你的自行车肯定爆胎的,你肯定又要迟到的。”班主任刚说完,同桌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哭起来。班主任非常生气地走了,同桌就站在门口一直到下课。此后有些淘气的同学就经常笑着问我的同桌——今天你的自行车有没有坏啊?同桌听到他们的嘲笑不敢抬头。班主任的那句话不但缺乏理解和同情,而且伤了同桌的自尊,让她经常被同学嘲笑。
这位班主任一味强化教师权威,极容易伤害学生,或引起教师与学生的直接冲突。
再次,教育智慧追求和谐、乐学环境的营造。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面对的是一切生物中最复杂最神秘的人,善教的教师,会充分考虑这复杂性,不断改变教学方式。《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善教就是一种教育智慧。正因为善教,教师的要求和期望才不会与学生的追求和愿望产生冲突,才能内化为学生自觉的认识和行动。杜威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其终点必在训练之中,但是,它的过程却在于使心智为其自身的目的而从事的有价值的活动之中。”[6]让学生从自身目的角度去充分认识活动的价值,而不是从社会、家长、教师的目的角度去看待教育活动,自然,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直接冲突就能得到避免和化解。善教不但融洽了师生关系,而且体现了教师雍容大度、谦谦君子的形象。学生也亲近他,尊敬他,容易接受他的教导。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把教学当作艺术有利于学生接受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学生获得快乐的情感体验。夸美纽斯认为,学校不应该成为儿童恐怖的场所,不应该成为他们才智的屠宰场。“学校本身应当是一个快意的场所,校内外看去都应当富有吸引力。”[3]这个吸引力需要全体教师去营造,需要教育智慧去创造。然而,在现实中,学校缺乏这种吸引力,难以成为学生向往的场所。一首改编的灰色童谣就反映了学生对学校、教师的“敌意”:“太阳当空照,骷髅对我笑。 小鸟说, 早早早, 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 我去炸学校, 老师不知道。 一拉弦,赶快跑, 轰隆一声, 学校炸没了。” 童谣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儿童对这个世界最直观最朴素的认知。一般而言,儿童还不具备对善恶的理性分析能力,其情感反应往往是直观、直率的,儿童对学校有如此“深仇大恨”,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学校生活的排斥,同时也反映了学校带给他们的压抑和痛苦,反映了学校教育智慧的缺失。■
参考文献:
[1] [德]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M]. 李其龙,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9.
[2] [法]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M]. 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22.
[3] 李如密. 教学艺术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86.
[5] 李巧林,梁保国. 论教师的教育智慧[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6] [美]约翰·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