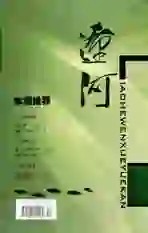惊艳一枪
2009-12-25惊艳一枪
惊艳一枪
想起艾比湖的日出,那个每年大面积干枯的湖泊。退水的湖床皲裂,多盐碱的细沙板结,像大片倒置的瓦片,光脚踩上去酥酥地塌了。环湖疯长的芦苇荡里,野鸭子的梦将醒未醒。万古的晨曦之光,轻摇芦花和苇叶,踏着波光静静飞翔。十几个少年男女,一只黑狗的剪影被记忆封存。
——《音乐之光》
高中毕业那年去艾比湖玩,七个人住在一个同学家里。同学的父母和小妹住一间,我们七个住一间。三男四女横躺在同学家唯一一张大床上。尽管入睡前的姿势有些拘谨和兴奋,但是大床的铺板还是轰然倒塌了。
——《睡姿乱谈》
我跟她们说是因为艾比湖的水好,一年消退几里,原来都被你们吸收去了。那时候我还有赞美女孩子的心计,如今面对类似的青春美丽,只剩下哀叹的份。
——《毁誉》
多次在文中提到 “艾比湖”,言犹未尽。我想,要是不把那件事情说出来,艾比湖的波涛将会萦绕一生的梦境。那面巨大的湖泊水汽迷漫芦花漫天,暗夜里泛着冷冷的波光。
从引用的前两段话看得出,自己的记忆明显出了偏差。刚才给新疆的同学胡芳打了电话,问当时到底是七个人还是十二个人?她说也记不全了,中午正好同学聚会,问一下其他几个人,下午再打电话告诉我。她说,你现在可以先回忆一些别的场景,时间,地点,事件,把开头和结尾先想好。
时间是1986年夏天,高考刚刚结束。
地点是90团。阿拉山口常年大风,白杨树胡杨梧桐只有半边的枝条和叶子,一律背风向南生长。海娃从90团转学博乐,最后一年插班成为我们的高中同学,一下子成为好朋友。他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说那里看到的艾比湖日出,和书里写的海上日出一样美。
50几公里,我们骑自行车去的。康忠背了把吉他,彭健还带了高压汽枪,买了6盒子弹。海娃说湖边有许多野鸭子,湖边的河道草长水深,结网垂钓都能捕到大鱼。我和海娃最后一个走进家门,海娃用手一指暮色苍茫的东方,说那边就是艾比湖,明天太阳升起的地方。
下午胡芳来电话,确认是十一个人加一只黑狗。五男五女,还有一个男的是海娃的小弟弟,狗就是他养的。想起小弟弟的象棋水平很高,刚到那天夜里在煤油灯下对弈。开始一直输给海娃,以为弟弟好欺负,没想到他两门黑炮使得出神入化,杀得我只剩下个光老头子。
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听康忠弹吉他胡芳唱歌,还一起放录音机跳迪斯科,几个人一堆聊天,我和二哥还偷空溜出去走了一段夜路。她那时候比我高半个头,第一次两个人走这样的夜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外面满天都是星星,晚风里仿佛能听见远处艾比湖的波涛声音。
就像《睡姿乱谈》里那样,海娃弟弟妈妈一起睡,我们九个一张大床横着睡,确实发生床铺塌陷的事故,折腾到半夜才睡稳。天蒙蒙亮,我用铁锹头刮水泥地吵他们,玉新骂骂咧咧地第一个跳起来,二哥、师傅、胡芳、文玲、洪江、康忠、朋健他们都躺着大笑。阿姨早煮好大锅的苞谷面糊糊,烙了一大盆饼子。
一共八辆自行车,我带着师傅,康忠带着二哥,海娃带着弟弟,其他一人一辆车,带着鱼网、锅碗瓢盆等用具和食物,浩浩荡荡出发。现在的我要屏住呼吸静心追忆,才能听见一路上饭碗在铝锅里磕碰的声音,听见小黑狗兴奋的叫喊声,听见那帮年轻人的欢歌笑语。狗自己跟着车队跑的,它一会儿在我们前面,一会儿在我们后面,一会儿跑进路边深深的芨芨草丛和芦苇荡,惊起野鸟贴着芦花飞走。
车轮在大脑皮层翻滚,一场大风刮低芦苇,旭日不等我们就要出来了,没到湖边就看见红透了半边的天。在岸上摔倒自行车,拎着鞋子拨开芦苇,穿过一片湿地和草甸。 “退水的湖床皲裂,多盐碱的细沙板结,像大片倒置的瓦片,光脚踩上去酥酥地塌了。”光脚踩在那片沙地上的时候,太阳刚刚要脱离水面。要是你相信我说的,一群野鸭子正飞过朝霞升腾的湖面。
迎着朝阳并排站着,阿娃告诉我们,“艾比湖”在蒙古语里就是“向阳湖”的意思。婆罗科努山的间歇河流,奎屯河博乐河的水汇聚来此,以前有上千平方公里的浩瀚。农田灌溉大量截水,湖面下降,30多年缩小了一半,如今只能面对那些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痴心疯长的芦苇和芨芨草,想象鹳、雁、天鹅,野鸭、鸥鸟、白鹭、野鸡出没的盛景。
牵网渡河,刚刚会水不久的我被鱼网缠了脚,眼看要沉了,吐出一串泡泡来。亏了一路上逗小黑狗玩,他们都没办法救,小黑狗像电影上演的那样从坝上纵身下水,借背我扶。它如此轻小,而我只要借一点点浮力上岸。惊魂未定,欢呼,被小黑狗又抖一身水。它瞪我一眼,怪我不小心。鱼一条没网上,倒是交了个狗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那天午饭前他们都去哪里了?都遇见了什么好玩的事?想不起当时怎么散开玩的了,谁又和谁在一起?这些小城里待了十几年的少年男女们,猛然来到那么大一面湖泊前,举止行为和这里野生的飞禽走兽没什么两样。
几个女孩子踩倒了一片芦苇,把周围的芦苇尖绑起来搭了间棚子。掘土为坑叠石成灶,拣来干木棒红柳枯枝梭梭草,书包有米军壶带水,她们架起铝锅熬粥。那道炊烟起初是青的,后来变白变淡了。几个女孩子隔着河滩呼喊,回来吃饭回来吃饭——她们双手圈成筒子罩在嘴上。我一直跟拿枪的在一起,分苇拂草地在草甸某处现身。虽然什么鸟也没打上,多像涉猎归来的一家之主们。
棚子太小了却更有隐秘感,已近正午的烈日照不进来。铺了块塑料布,人挤人脚碰脚蹲着坐着,吃的东西都快没地方摆了。罐头苹果梨子水蜜桃,咸菜馒头粥,汽水博乐白,勺子筷子手,稀里哗啦风卷残云。嘻嘻哈哈聊天,叮叮咚咚弹琴,避着发白的毒日头。没这么开胃过,没这么开心过。大家都说了,有机会还要来河滩野餐。
本来是多么愉快的一天。炭火浇灭踩熄了,陆续走出“帐篷”收拾行囊。我最后一个出来,看见师傅和康忠站在不远处,一丛红柳边,正往自行车后架上绑东西。我背着高压汽枪,口袋里还有两枚子弹。压一发上膛,环视一圈,朝着康忠的脑袋瞄了一会儿。我近视,康忠的脑袋在准星上那个圈里,看起来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说过一天什么都没打上的,不知怎么就扣了扳机。枪声没风声大,也没打着。康忠有所察觉,直起身笑骂,你那臭把子,能打中什么啊?枪管折下来,最后一发压上去,“啪”一声合上,我的手有点抖了。再瞄,两点一线,三点一线,感觉清楚了很多。手指又扣下去,我看到那颗子弹了。它在瞄准镜里越远越大像个愤怒的黑拳头。它离开枪管到达康忠的头颅时候,那些沙丘红柳迅速向我倒伏。“砰”,是这样的一声巨响,伴着师傅的尖叫,康忠捂着耳朵仰天倒在沙堆上。
都跑过去围着。血从耳朵鼻子嘴角流下来。师傅和玉新吓得哭起来。朋健一把把枪抢过去,他们都开始骂我。从耳朵打进去了,会不会打到大脑里?谁说的,快点回去送医院啊,会死人的。康忠在被掺上车架前撂了一句狠话,他说,死了就算了。没死,你等着。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从艾比湖到团部八公里,我带着康忠用最快的速度冲在最前面。一路上没人说话,谁也没心思再看两旁深深的芦苇荡了。只有车轮滚动链条脚蹬摩擦链盒的声音,还有我喘息的声音,汗水源源不断地流下来。记得康忠坐在后面用手给我扇风,康忠说慢点我知道你尽力了。
那天的女孩子体力惊人,没有一个人掉队。一排车到了海娃家门口,我看见海娃妈妈迎出来。我跳下车就跪倒了,原来腿上早已没了力气。送医院,急症,X光,看见左脑门一点暗黑的子弹影子。医生说还好,软骨组织挡住缓冲了子弹,要手术,打不打麻药?康忠是数学天才,摇摇头说不打。一刀割开口子,止血钳进去夹,子弹到处跑。口子太小,再割开些,又进去掏。康忠汗水湿透,腿蜷紧,浑身颤抖没吭一声。夹住了,连筋带血拖出来,一刀剪断,粗手指把肉塞回去。“当”一声,落在白盘子里,弹头都变形了。缝针,白药,包扎,医生连连说团里医疗条件不好。
团长和政委来海娃家看望的时候,我正和弟弟在外间下象棋,等着阿姨开饭。团长站着,政委蹲着看。政委斜着眼问我,就是你开的枪?阿姨笑呵呵迎出来,说进里屋坐,都在里面弹琴唱歌,他是不好意思进去呢。
留了团长政委一起吃晚饭,十几个人围坐成一圈。阿姨煮了大盆手抓肉,那天都喝白酒。康忠头上缠满白纱布,也喝白酒。团长政委端着杯子,不知说什么好,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大家都笑起来。康忠还问,如果路上就死了,你们会怎么办?他们愣了一下,推推搡搡的。朋健说,我们核计过了,一个好朋友都去了,不能再去一个,反正那里芦苇荡很深,我们回来就说你失踪了。康忠眼睛圆瞪,“哇”一声大吼。大家又笑。那天有两个女孩子盲目崇拜,喜欢上了勇敢的男子汉康忠。
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对当时的动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也没人再追问我,只是我不再玩枪了。大家还是好朋友,他们打电话来,今年8月同学会,让我一定要回去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