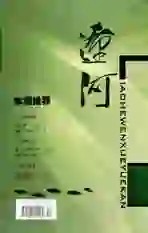楼顶三国(外二篇)
2009-12-25大英
大 英
点式楼,我家住在顶楼,顺搂梯向上,拐个弯直通楼顶。开发商许诺,买顶楼可赠送空中花园,圆你一个庄园主的梦。到楼顶去视察地形,只见一个规模不小的鸽子笼早已存在,不知是被哪个楼层的邻居捷足先登了,鸽子养了几十只,白的,灰的、花的,见到人嘴还挺甜,全都是杨过对小龙女的称谓,不住声地乱叫姑姑。每天能够观赏鸽群在天空飞翔盘旋,而且不必劳神费力,挺好挺和谐。
从南窗望去,也是两座点式楼,结构一样,东侧的那座,楼顶盖了一座简易活动房,旁边是一个更小的建筑,一只狗经常出没往返,才知道那是个狗窝,德国黑背,是条半大的少年狗,城里养狗是要办证的,价格比狗还贵,估计这是只没有户口的黑狗,每天在楼顶跑来跑去,不用主人陪伴,完全是自己溜自己,简易活动房只给它留下一米左右的过道,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摔下去,证明重力加速度定律的存在,我常常担心那只狗,却不担心头顶的那群鸽子,鸽子会飞,而狗连降落伞都没有预备一个。
由于不存在遮光的问题,西侧的那座楼离东侧的很近,楼上保持着原始状态,既没有花园,也没有鸽子窝或狗窝,不久前,突然发现最高点站着一只鹞鹰,俗称老鹞子,传说专门抓小鸡。园区里同样是不许养小鸡的,于是,又多了一份担心,它每天用什么活物来果腹?鹞鹰用敏捷的动作打消了我的疑虑,箭一般地扑向我家楼顶,惊起那群鸽子争相逃命,由于隔着楼板,看不到楼顶兵荒马乱的情景,不过看过《动物世界》,鹞鹰和鸽子体形相差无几,完成空中捕猎的过程却瞬间即可结束,真正的惊心动魄。
鹞鹰没有出现之前,鸽子们常常会去骚扰那只狗,可能是喜欢那份狗粮,偷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纷争,那条狗自然要保卫家园,左突右冲,由于数量上相差悬殊,往往顾此失彼,累得狗耷拉着舌头直喘粗气。
鹞鹰把那条狗当成竞争对手,只要见到狗在顶楼出现,就是一个闪电般的俯冲,狗就绕着圈子弃窝而逃,钻进通往楼梯的房门。狗往往很不甘心,不过也多了一份小心,再次出现时先探头探脑,观察一下周围情况,空中黑影一闪,乱吠两声立刻缩了回去。鹞鹰会雕像似的站在西侧的楼顶,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注视着东方,吃饱了没事干,它唯一的乐趣好像就是驱逐那条狗。
三座点式楼,呈三足鼎立之势,虽然有些牵强,还是让我不禁联想起三国演义,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博望赤壁战火连天。那只鹞鹰应该是曹操的化身,曹操世称枭雄,枭,也是老鹰的一种,爪尖喙利野心勃勃并且占据天时。那只狗,只能委屈孙权了,珍惜传国玉玺般地看护那个狗食盆子,没有翅膀,四脚落地,却也占有地利的优势。那群鸽子懦弱胆怯,与其说像刘备,不如说更像一群阿斗,数量不少,算是人和吧。
在三分天下的布局中,那群鸽子属于弱势群体,常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好能出现一个诸葛亮似的人物,巧设锦囊调配人马,最好能联合那条狗,让狗事先埋伏在隐蔽处,派几只漂亮的鸽子在附近漫步充当诱饵,待鹞鹰捕食时突然攻其项背,即便不能一举成擒,也能挫挫它的霸气。
楼顶的鸽子最先退出这场纷争,可能是主人察觉损失了鸽子和鹞鹰的威胁,将其安全转移,那只鹞鹰也随之转战别处,只有那条狗仍在,低着头在楼顶遛弯,一副斗士落寞的神情,偶尔凝望西北,像是在留恋刚刚逝去的那段热闹时光。
东方佛都
一尊出名的大佛后面,一定跟着许多大佛,甚至更大。游览东方佛都,这是我的观后感。
东方佛都位于乐山大佛的后山,一公里左右的山路,在乐山旅游的路线之内,但不在旅游公司承诺的价格之内,想游览需另外收费,每人门票80元。女导游舌绽莲花,说佛都有170米的卧佛,有媚态观音,有蛊惑三魔女……冲着卧佛的大,观音的媚,魔女的妖,都是头一次听说,很新鲜,于是,麻溜掏钱。
佛都依山取势,洞窟穿山,大小佛像上千尊,千姿百态琳琅满目。这里的山石适合开凿洞窟和佛像,所以,才有了闻名遐迩的乐山大佛,现代人的精明不逊古人,所以,才有了集各地佛像于大成的东方佛都。冷丁看到一尊佛像标明建于晋代,刚想感叹一下年代久远保存却如此完好,接着看到括号里还写着敦煌洞窟几号的字样,方才明白原来只是一尊赝品,都是从别处仿来的。佛都里都是现代作品,建于90年代,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五百年后再来观光,才能算是文物。
游览乐山大佛,敬仰之心会油然而生,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氛围包容着每个人的身心,虔诚向佛的,还能感知信仰的神秘力量。得知佛都出自现代艺术家之手,游人一下放松了许多,敢于对着佛像指点品评,这种立场的转换自然而然,艺术欣赏本来就是一种享受,不必过于拘谨也极少忌讳。终于看到了媚态观音,不记得观音的变化身里有媚态这一款造型,如果说这个女人是杨贵妃许多人会有同感,观音本该是圣洁和庄严的,这个媚的姿态是否有媚俗的成分?可观音本人都不介意,别人也没必要去充当护法。
聚财造佛和造佛聚财,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海通禅师不惜剜目保佛财,是为了把资金用于大佛的修建。现代人修建佛都,为的是佛像搭台经济唱戏,和宗教信仰关系不大,这种佛是不能轻易参拜的,艺术品和真正的佛像内在的区别很大。一路走马观花,发现路边的石壁上支着许多木棍,不解,问当地人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叫撑腰棍,是求佛给自己撑腰的。我笑了,满山的石像没有一尊真佛,还是自己保护自己吧,走山路小心脚下,不要闪了腰。
终于看到那座卧佛,刻在一面石壁之上,立体感不是太强,更像是一幅壁画,佛头朝东,佛脚朝西,而中间部位,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头脚加上原生态的中间地带总长170米,卧佛只能远观不能抵近观赏,没有望远镜只能看出一个大概轮廓,隐约能看到雕琢的痕迹,和乐山大佛不可同日而语。总体的感觉,好比逛完故宫博物院,再逛一下潘家园,随便逛逛,别怕上当。
看场院
我看场院的搭档是大才,他三十出头,是个外来 户。大才受伤之后,日夜陪伴我的是大黄,大黄是一条狗,不挣工分,陪我看场院是友情客串。
我插队的地方山清水秀,可是风景不能当饭吃,吃粮要十几年如一日地靠国家返销,庄稼年年种,可是收到场院的却少得可怜。所以看场院的人选就要比挑姑老爷还要精心,知青是当然的人选,而选中大才是社员们公认他“生性”,猪马牛羊都敢杀,六亲不认,也无亲可认,不会把集体财产送人情。
失火失盗的大事不曾发生,每天忙于应付的是猪拱鸡刨牲口扯。大才脾气火暴,镰刀不离身,对那些哑巴畜生出手过重,每当他把镰刀当成飞镖甩,我都忍不住要闭上眼,生怕目击到血溅当场的惨相。我处理这类事情有自己的一套高招;场院上的大喇叭正在播放大队支书的通告:“秋收期间,各家各户的猪都要圈起来,否则打死勿论!”话音未落,一头老母猪踱着方步,在十来个小猪羔子前呼后拥中驾临场院。我给这头猪起个外号叫“太后”,在整个堡子这一亩三分地里没有它不能去的地方,就因为它的主人是支书他妈。大才又要出手,被我夺过镰刀。我在场院里挖了一个凹槽,把“太后”引到那儿,请它仰面朝天地躺在沟里安歇,这样任凭它蹬破天也休想翻过身来。天黑前我俩把“太后”扶正后,它已经像邯郸学步一样腿脚直劲“拌蒜”。
每次去场院,大黄把我送到栅栏口就绝不肯在向前迈步,它对大才的成见太深。都是朋友,我试图消除大才和大黄之间的芥蒂,大才不屑地哼了一声:“一条狗,配吗?”
我几乎是同时认识大才和大黄的,刚下乡时,大队派大才给青年点当炊事员,第一次开饭,大黄就在不远处一脸馋相地看我吃大饼子,我掰了半块扔过去,它跃起接住。大才瞪了我一眼说:“我们这儿,有的人家过年才能敞开量吃上一顿大饼子。”蒙谁呢?又不是旧社会,我心里不服。每天开饭时大黄必到,我也照喂不误,大才劝过也吵过,可这是我自己的饭份,谁也管不着,我乐意拎着瘪肚子去战天斗地。大才对我无奈才迁怒于大黄,抽冷子一炉钩子刨在大黄的头上,大黄躲进柴禾堆,昏迷了十来天才睁开满是眵目糊的眼睛,在我的照料下它竟然奇迹般地高大威猛起来,并且没有留下痴呆、偏瘫、 抽羊角风等后遗症。不久,大才因看不惯城里这些“少爷小姐”们的做派,猪八戒摔耙子——不侍候猴了,大黄再出入青年点连奔都不用打,上饭桌都行。
有人从村南头回来,说队里的白菜地里进猪了,大才叫我和他一起去赶,我们是专职看场院的,看菜地的是村支书的弟弟,他形象猥琐半精半傻,竟然也会狗仗人势,我打心眼里没瞧起他,所以我没有动窝,大才自己拿着镰刀走了。不巧的是,这猪和大黄是一家的,打狗欺主那口恶气还没有出,又想来伤猪?新仇加上旧恨,猪和狗的主人父子俩前后夹攻,一石头敲在了大才的头上,大才当即和大黄当初一样也是昏迷不醒,被送进省城医院抢救
从那天起,大黄便和我一起住进了场院的窝棚,并且马上显示出其看家护院的天分,场院里清静了许多,赖皮如“太后”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夜深人静,抚摸着大黄的颈毛我常常为大才担忧,一个好人,一条好狗,就为一口微不足道的大饼子何苦要这样冤冤相报?
打完场,拆窝棚那天,大才死了。悲痛之余,我发现大黄没到青年点来吃饭,顶着北风烟雪,喊遍周围的沟沟坎坎也不见踪影。兴许是回主人家了吧?大老远我就看见篱笆墙上晾着一张狗皮——这户人家把大黄当成了生离死别的最后晚餐。老乡们议论纷纷,都认为是大黄引发了这场塌天大祸,它不该贪吃那口金贵的大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