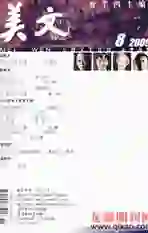傅庚生先生
2009-10-24阎琦
阎 琦

阎琦1943年10月25日生于陕西礼泉。1963年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68年毕业。在陕南作中学语文教员8年,1978年再入母校读研究生,81年毕业留校任教。94年被聘为教授。现已退休。
在考入西北大学以前,中文系老师的姓名已经为我所知者,惟傅庚生先生。这可能与傅先生经常有文章发表在省内文艺报刊上有关。傅先生几种主要的著作当时我都没有读过。及至后来,我才知道傅先生的名望远不至于此。前西大校长郭琦鼓励教师科研写作,有一句名言,就是“要打出潼关去”,要在全国知名。我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就发现国内所到之处,没有人不知道西大有个傅庚生。“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说,傅先生是中文系真正“打出潼关”并誉满天下的一人。
入学以后,偶尔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见过傅先生。五十岁多一点年纪,清癯,衣冠整洁,步履轻盈地走过。同学们向傅先生鞠躬致意,傅先生也微微点头示意,很“飘然”的样子。谁今天在系上见到傅先生了,回到宿舍不免有一番“兴奋”的张扬。二年级时,傅先生给我们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作品”(那时古代文学分两门课讲授,一位老师先讲作品,另一位老师随后讲文学史)。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仍能感受到傅先生讲课时我全身心的那种“享受”。呵,那不是在听课,那是生徒在听维摩诘大师讲授心源大法,而碧空祥云之中有飞天仙女在撒着香花。无论别人,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两节课很快就过去了,时间在傅先生话语的细流中似乎凝滞了,又似乎不着痕迹地流逝了。
傅先生讲课的声音并不响亮,纯正、又略带一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傅先生其实是辽宁人,南方口音或者与他曾长期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有关),清晰而恰到好处地传到教室最后一排。傅先生是学者中有名的“辞章派”,但课讲得却如同美文,我不知应当归于何派。我曾经作过傅先生课的“课代表”,有一次去傅先生家里,他说:讲课如同织锦,经纬始能成章。我那时没有很在意这句话,因为我绝想不到教书会成为我半生从事的职业。现在想起来,这应是傅先生的教书“家法”的私授。“经纬成章”使我对傅先生的讲课有深入肌理的理解。无论魏晋诗,无论南北朝诗或唐诗,傅先生能将它掰碎了、调制成美味可口的食物让你去接受它、消化它。诗的文本就是“经”,而与诗有关的社会的、文化的、写作的和鉴赏的知识等等,就是“纬”。经、纬交织,也就是傅先生的课堂组织了。傅先生去世的时候,霍松林先生有一幅挽联,上联不记得了,下联是:“说诗最能解人颐”。诚为知言。
傅先生诵读的功夫也是值得称道的。一首诗,一段文,经他一读,大半的意境就出来了。那是对古人诗文深入骨髓理解之后的诵读,绝非现时演艺明星那种故弄姿态的所谓朗诵可比。陕师大已故高海夫先生是傅先生五十年代初的学生,高先生尝说,他们读书的时候,傅先生就是这样诵读诗文一过,然后“啧啧”连声,说“好诗、好诗”,就又去读下一首了。大约因为我们这一代学生的资质鲁钝,傅先生须要稍微的掰碎了讲才行。不过,如高先生说的那种境界我也曾体验过。记得傅先生讲杜甫《登高》,念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时,我的确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深秋,漫天落叶铺天盖地瑟瑟而下的感觉。啊,那境界真是太美妙了。
曾经听到年辈长于我、同是傅先生门生的人对傅先生讲课的的议论,大意说傅先生上课不免于“花拳绣腿”,不过徒然令人感觉眼花缭乱而已。我听了不禁有些愤愤然。我以为,古诗文之美,如花。时隔千余年,如花的古诗文,其颜色,其芬芳,在一般读者眼里,其色香大都消褪殆尽。今人的解析古诗,倘是高手,可以将如花的古诗,隔一层玻璃让你去看它的颜色;而能将如花的诗从玻璃后面取出来,置于你的眼前,让你不但能看到花的颜色,还能嗅出花开时的馥郁芬芳的,是傅先生。
傅先生的课,我就听过这一段。傅先生还有一门“杜诗专题”,要到五年级才开(当年中文系的学制是五年)。可惜,“文革”一起,一切都灰飞烟灭,乱世如浊浪滔滔,哪里还提得到“杜诗”呢?附带说一个细节。傅先生讲课,从不拖堂,他说“今天就讲到这里”,话刚落音,下课铃声就响起,而我从未见过傅先生抬腕看表。套一句流行的话,就是“绝了”。
没有想到1978年我再能入傅先生门下读研究生。自是,我才开始认真地体味傅先生的学术以及他的学术语言。
记得研究生入学第一天,同年们登傅先生门受教。傅先生显得很兴奋,连连说“得天下之英才教育之,一乐也”。其时傅先生的身体已经不大好,十年未见,当年行走轻盈的傅先生变得步履蹒跚、龙钟老态了。然而先生的思维仍非常清晰活跃。大约每两周我们登门受教一次,因为时局宽松,先生的话题很随意,月旦政治,评价人物,常有惊人之论。关于作学问,总括先生的教诲,有这样两个意思:一是要把古典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要有形象思维;二是要集中力量弄通一两个作家,“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傅先生是北大出身,他的研究路子,明显地带着所谓“京派”的特点,从闻一多、朱自清到林庚,无不如此。傅先生颇不满意于乾嘉学派的考据成风,他的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从他四十年代写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就已经确立了;至于“断其一指”,当然是他专于研究杜诗的经验之谈。提到杜甫研究,国内何人不晓先生的《杜甫诗论》呢?
我倒是对傅先生“把古典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这句话极有体会。这句话的含意很多,其中一个意思,我理解就是要把研究文章写成美文,要表达得好,使文学的研究成为研究的文学,不能干巴巴的枯燥,让人读不下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研究同样也是语言的艺术,在四五十年代的研究者中,花大力气于研究语言的锻造,傅先生是最成功的一位。当今学术界,研究的语言普遍乏味,没有灵性,缺乏个性,已成痼疾。如闻一多、朱自清那般的文学研究,已像青烟般消散无踪了。我所以重提傅先生注重研究语言艺术,确有针砭时弊之意。
当年我作傅先生课代表时,先生曾赠我一册他新出的《文学鉴赏论丛》,我珍宝之,可惜“文革”中散失,不知落到哪位同窗的书箧中了。读研期间,先生再赠我新版的《杜诗散绎》、《杜甫诗论》和《杜诗析疑》,加上《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先生的几种主要著作就都读了。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玄秘莫测了,大约还是要从多读、多揣摩中去体会。我曾经像参禅一样仔细揣摩过傅先生的语言,渐有心得,濡染之间,笔下也就多少有了一点先生的笔意,但口不能道得明白。后来我也忝为研究生导师,常常劝我的学生多读傅先生的著作,对他们说,“可以不必先顾及其学术,但务须体会其文字”。
研究生毕业时,傅先生设“家宴”招待我们。同门数人在前往先生家的路上,我妄言说,傅先生似乎写过小说,或如同闻一多、朱自清那样搞过创作。大家都摇头,表示不同意。甫进家门,我贸然以此发问,先生莞尔而笑,师母连连说,写过,写过,人家都说他的小说像废名(冯文炳)呢。多年疑窦,终获一解,表明我对傅先生文字的感受大致不错。得到鼓舞,我又问先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为什么要用文言文写?先生说,当时文字之佳,莫过二朱(朱自清、朱光潜),自信白话文未必胜过他们,所以让二朱一头地,改用文言文。废名的小说,我读的不多,近年看到一篇讨论废名的文章,言及废名文章风格,用“生辣”二字概括之;各位都有吃菜的经验吧?菜非大锅烩煮得稀烂,谓之“生”,入口但觉其刺激味蕾,谓之“辣”。傅先生的小说,我未尝读过,对他小说文字的“生辣”暂无体会;但读他的学术文字,的确有《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宜僚弄丸”那样的感觉,“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砉然响然,莫不中音”。学术文字以说理为主,能到这种境界,真是难得的很了。放眼国内,寥寥数人而已,而后继者尤其乏人。可惜自己资质末流,竟不能学得先生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