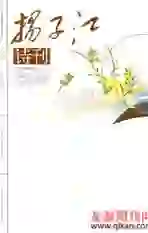杯子是杯子,什么也不像(外一篇)
2009-07-30莫非
莫 非
假如一个诗人,能把“杯子”写出来,最后还“是”那个杯子,就应该满意了。说杯子“像”什么什么,哪怕“像”一只打火机,都是顺手的事情,从口袋里掏出来就可以了。在语言里,一切都是“像”的,没有“不像”的东西。倘若没有隐喻,人人都是哑巴。这里恐怕没什么要说的。是不是一个好的诗人,就是看,那个诗人在自己的语言里有没有写出“是”来。写“是”的诗人,一定是有创造的诗人。有的诗人只是写了“不是”,还有的诗人写了一辈子的“像”。
敢于在词语的本义上下工夫,必然会在诗里练就自己的功夫。并不是说,在词语的本义上,隐喻就不来“干扰”了。她总是藏匿于诗句的缝隙里。这种“隐匿”是语言张力的起点。词语的本来模样,就是查个“五代十国”也是理不清的。过度使用,导致词语的磨损和贬值。当下的词语有着大量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传统的“附着物”,这对诗人是个麻烦。诗,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就是要给短气的和断气的词语注入活力,让“词语”在诗中呼吸,生动,乃至不朽。
“隐喻”不论多么新奇都是权宜的。但是,没有不断的“隐喻”的生成,“本义”也就无法生长。从根本上说,语言是枝叶茂密的大树,枝干是长久的,树叶是轮换的。如果没有诗,语言必死无疑。好在诗人仍在努力,语言继续活着。就拿“杯子是杯子”来讲,听起来很简单,似乎无新意更无深意。其实,那是一种“没有梯子”的写作,“靠”的是真本事。不管“杯子”是空是半是满,杯子是不会变的。因为“不变”,明澈的词语,碰撞的词语,透出来的,就是本来的诗,而“像”诗的诗一碰就碎了。
诗歌就在那里,我们没有注意
养狗的朋友说,狗也会哭。无非是说:狗能够表达它悲伤。对此,我深表怀疑。这跟“花溅泪”一样,是人的意思。如果狗哭了流泪了,与一定不是人能够理解的那种悲伤的表达。“子非鱼”所以不知“鱼之乐”,是可以放之四海的真理。虽然“子非我”,但我们都是“人”,我们的文化先于我们的表达,是可以彼此理解的。狗会哭,是揣测。花溅泪,是移情。鱼之乐,是偷换。结论是,即使狗的悲伤比人类的悲伤有更深刻的表达形式,人就因为是人才妨碍这种理解。一句话,狗的悲伤究竟是怎样人是不知道的。
尽管讨论的是“悲伤的表达”,实际上牵扯的是“表达的悲伤”。表达,有哲学的,有逻辑的,有情感的,最终通过“语言”来实现。人无处不表达,无所不表达。即使无言以对,依旧是表达,甚至是高级的表达。当然,还有一种表达比较麻烦,那就是强迫下的表达。就是你说你本不想说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暴力,比酷刑还残忍。据说,诗歌是语言的冒险。但是,真正冒险的语言,诗歌是挨不上搭不上的。也许,诗歌是语言的绝望。当我们什么都说不出的时候,诗就派上了用场。
应该说,诗歌的表达没有禁忌,所有最恰切的表达就是诗意的表达。诗人透过活的词语挖掘事物。摄影家用光线去抓镜头里任何东西,且不管是实是虚。建筑师用窗子和立柱来盖自己的或人家的房子来表达对时空的理解。有高人说了,如今的房子可以没有立柱。但不要忘记,一面墙只不过是没有间隙的立柱。一切艺术的失败,也就是表达的失败。那些暂时不被理解的艺术,迟早可以被理解。这跟失败无关。其实,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东西,不管走多远,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人要说话,语言要诗歌,诗歌要人照看。如果写作本身不是理由,其他再好的理由也不值一提。诗歌有自己的路径,只是大多时候都是隐藏起来的,所以看上去跟无路可走一样。诗歌的马吃的都是悬崖边的青草,写诗总是绝处逢生。倒是那些半吊子的写作不费什么周折,风一刮,就晃荡,风停了,还是晃荡。多么轻松的事情啊!语言里有流淌的泉水,要是你在夜深人静的当口还不能听见,那就怪不得任何人了。那些可以听可以啜饮的诗人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美妙的歌声,但他们的确值得为我们所期待。
凡是顺理成章的东西都是可疑的。让相信的人享用自己的相信,让怀疑的人继续怀疑。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说的做的怎么都对,一切毫无异议了,我们的世界也就不需要艺术家了,因为这样的世界足够艺术了。人性中非人的一面,总是要照出魑魅魍魉来给我们看,我们越是闭上眼睛,它们越是活蹦乱跳。好在诗人醒着,看见,说出。诗人说出的时候,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出。当他们碰上运气,便可以说得直接、简单、确凿。于是,我们拍着大腿说,哦,诗歌就在那里,我们没有注意。